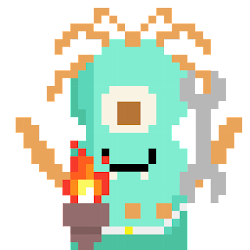公共生活及空間研究簡述
20世紀中後期,歐美城市開始對現代主義所推崇宏大城市規劃理念提出質疑,慢慢開始轉向關注以人為本的城市空間和體驗。
美國著名城市倡導者Jane Jacobs在60年代針對自由主義經濟建設而導致社區環境喪失作出反思,主張城市設計不應該是由從上而下的大型基建主導,而是應該以社區居民的視角去理解城市如何運作。記者/作家出身的Jacob在她的著作“美國城市的生與死“(1961)當中詳細描述紐約下城的社區環境,著眼點不是偉大的建設藍圖,而是城市空間中不同人之間的交流。差不多同期在丹麥哥本哈根的建築師Jan Gehl也循著這個方向研究城市空間,在其早期著作Life Between Buildings(1971)提出對城市設計其應該是基於 生活(life)和 型態(form)-即建築和基建– 之間的互動關係發展。經過多年的研究教學和設計項目的實踐,他的工作室已經發展出一套完善的城市空間研究方法論,聚焦於 公共生活(public life)並用以為設計策略的基礎(2013)。
這些早期的城市研究均以靜態空間為主體去衡量某個特定空間對活動的影響,可是我們能否進一步以動態城市公共生活的角度出發去探討 空間 和 活動 之間的互動性?而公共生活的特質又如何置於文化場所的公共空間之中?
室內,室外 與 半戶外 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研究通常著重於建築以外的開放空間,可是公共生活並不止於建築外部空間,對於公共空間的理解更應擴寬至包括一般公眾可達的室內空間。
建築學者Mark Pimlott提出公共室內空間(public interior)的重要性在於它如何影響公共生活,以及大眾在公共空間所能夠作出自主性的行為(2016,p10)。尤其是藝術文化場所如美術館或劇場,本該是一個鼓勵創作的自由/自主性的地方,但實際上文化建築內部通常是被精心管理/嚴格控制的。即使不一定明文規定,可是文化場所多有一種約定俗成的氛圍,訪客一旦入內便很自然會依循既定的秩序。Pimlott在“The Public Interior as Idea and Project”一書中探討公共室內空間的不同建築典型,從描述實體空間類型如“庭園”或“宮殿”至探討概念空間如“廢墟”或“網路”,總結出 通透性(transparency)或 滲透性(permeability)等共同空間特質。(在後續的研究當中,我們將以這些空間特質來檢視文化建築的公共空間)。
以上的角度把公共空間視作一系列的獨立例子研究空間類型,但公共空間更是一個具連續性的經驗,而當我們把室內外空間看作成一個整體便可以去分析不同空間狀態之間的流動。前文提過的“The Social Logic of Space”的研究便以活動動線為關注點,分析在不同的空間列序之中的流動性,從而傳譯”包容“或”隔斷“等空間/社群關係(Hillier&Hanson,1984)。在這種內外/流動空間理解下,文化建築的整體空間架構便可以用以反映不同的公共生活/社群關係(social relation),而建築元素則成為管理/管制這些交流的工具。文化機構/制度/政策 對於空間如何設計/組織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所以研究空間組織和流動便可以推演出文化制度如何影響公共/公民生活。
文化建築的公共空間與使用者
文化機構的角色本是促進藝術自由表達和公眾文化參與,而公共空間正是協助達成這些目標的重要載體,可是現實情況不一定相符。城市研究員Alasdair Jones在其關於倫敦South Bank文化中心建設過程的研究中指出,文化場所/機構很容易陷入一種流於表面的開放性或包容性,空間策劃雖然始於良好的動機但往往會帶來反效果(2016)。她舉例在South Bank有一處自發而成的街頭滑板場地,但當文化中心試圖為滑板運動改造公共空間以容納更多元活動的同時反而減弱了原使用者對場地的歸屬感,而更多的遊人也導致空間管理變得嚴謹。公共場所的空間設計與功能管理會互相影響,尤其是文化/藝術行為更會突破既定框架發生,由此帶出一個重要議題:如何平衡公共空間的 設計/策展 和 管理/管制,而這些具體措施又如何容納非正式的使用?
在研究文化空間使用體驗的背後,是為了探討文化建築的公共空間如何能成為更具包容性的核心問題,還有文化機構對公共空間創造的影響。這個關於“包容性”的討論可以從探討【集體-公眾】和 【個人-公共空間使用者】的相對定義開始。建築歷史學家Kenny Cupers 認為公共空間的使用者應該被理解為一群獨特的個體所形成的團體,而不是單一個性的“公眾”集體 (2013)。因此在研究公共空間使用時候可以以個人體驗為單元去理解公共空間,在尋求共同性的同時關注各種細微或不顯眼的特性以構建多個獨特個體共同形成的公共生活體驗論述。
以上簡述的研究參考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去研究文化公共空間,從靜態公共空間觀察至提取空間情境與建築元素為基礎,用以分析公共室內外空間的社群關係以及文化機構對公共空間/生活的影響。這樣的研究目的,最終是為探討文化公共空間如何形成和文化機構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
現在許多大型公共文化機構多是20世紀中期福利社會政策的產物,它的宗旨是促進包容性和公眾參與,尤其是在歐美戰後興建的各類“文化中心”正代表著這種願景(Grafe,2014)。於70年代初提出的香港文化中心整體規劃,一方面是本地開始建立自主公共政策的時期,同時對於文化活動的支持與文娛中心的建設多少也受英國的公共服務理念影響。由此出發可以將香港文化公共空間的研究放置於更宏觀的歷史語境之中,通過現今的空間體驗檢視當年的設計意圖和文化政策初衷。
Reference
- Cupers, K. (2013). Use matters :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 Gehl, J. (2013). How to study public life.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 Grafe, C. (2014). People’s palaces : architecture,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post-war Western Europe. Amsterdam: Architectura & Natura.
- Hillier, B., & Hanson, J. (1984). the Social Logic of Sp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cobs, J.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Jones, A. (2016). Orchestrated public space: the curatorial dimension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ndon’s Southbank Centre. In S. Golchehr, et.al. (Ed.), Mediations: Art & Design Agency and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spac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p. 244-257). London, UK: Royal College of Art.
- Pimlott, M. (2016). The public interior as idea and project. Heijningen: Jap Sam Books.
- Sennett, R. (2018). Building and dwelling : ethics for the cit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Stevens, Q. (2007). The Ludic City: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of Public Spaces. Florence: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