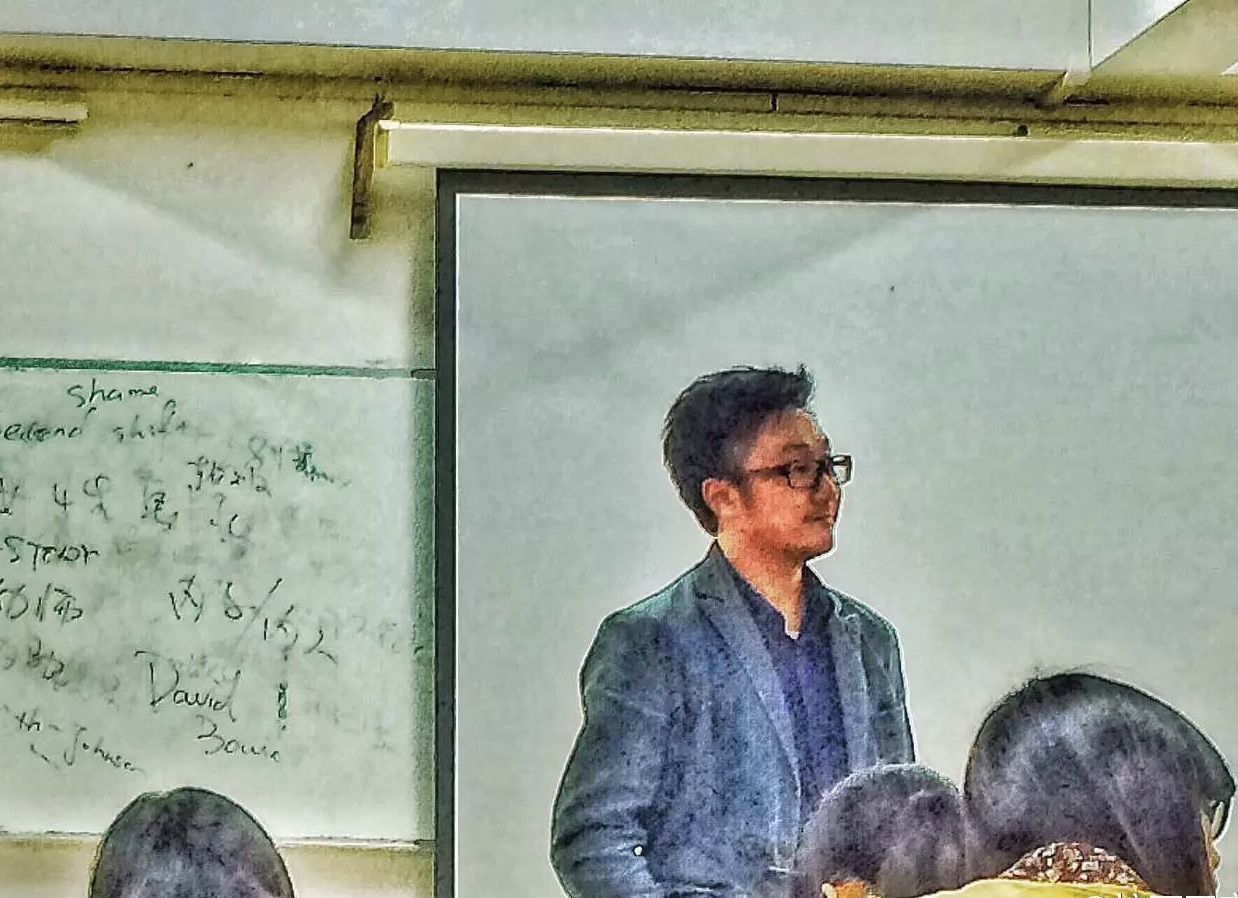為什麼說「憤怒」是種必要的情緒?
本文修改版先發於新京報書評週刊
英國牛津大學設有多個常任齊切利教授講席(Chichele Professorships),從最早1859年設立公共國際法律教授講席(Chichele Professor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到最新1944年設立的社會與政治理論講席(Chichele Professor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最近,牛津大學副教授艾米婭·仕尼瓦森(Amia Srinivansan)被選為齊切利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將在2020年1月正式上任,成為該講席歷史上第一位女性,也是第一位非白人任職者。
齊切利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講席的歷任者盡是學界著名學者,包括思想史家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政治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已故哲學家傑洛德·柯亨(G.A. Cohen)。最近一位講席任者是傑瑞米·沃德倫(Jeremy Waldron),當今法律哲學和政治哲學最重要的學者之一。
35歲的仕尼瓦森也是最年輕就任此職位的學者。她的研究主要關注政治哲學、知識論、女性主義哲學史等等。儘管目前還沒有出版專著,仕尼瓦森的學術文章在學界備受好評。同時,她也積極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寫作面向公眾的文章和接受媒體採訪。
仕尼瓦森的代表工作之一是她對憤怒在政治和道德領域的討論,從2014年的講座「為憤怒一辯」(”In Defense of Anger”)到2018年的文章「憤怒的恰當性」(“The Aptness of Anger”),她仔細討論憤怒的意義,回應長期以來大眾及學界對憤怒的批評。或許,通過瞭解這項工作,我們可以更熟悉仕尼瓦森的學術貢獻。
適得其反的憤怒
儘管憤怒是人類自然的情感之一,可算是日常生活里最常見的情緒反應,我們仍然會對憤怒持有相當負面的評價,特別是對憤怒可能帶來的反效果表示惋惜。在日常交流裡面,我們常常會勸說自己和對方,或者作為第三方勸說當事人,盡量保持冷靜,不要讓憤怒影響可能的理性交流,使得關係破裂。憤怒往往會讓交流達不到期望的效果:情侶會因為憤怒而錯過合理的溝通,無法解決關係中的問題;朋友會因為憤怒而放棄相互解釋的機會,最終不歡而散;親人之間更可能因憤怒而無法彼此體諒包容。
在公共領域,憤怒的表達同樣會因為帶到反效果而遭受來自各方的批評。不管是政治辯論,還是社會運動,憤怒都特別容易影響我們參與理性討論的能力,使得合理的政策商議難以進行,運動也難以展開。這樣的憤怒是適得其反的,即便憤怒可能在最初期能夠動員人們去關注和參與。
而憤怒的適得其反還可能在於憤怒內嵌的報復慾望。著名哲學家瑪莎·努斯邦(Martha Nussbaum)在她2016年的著作《憤怒與寬恕:怨恨、慷慨、正義》(Anger and Forgiveness: Resentment, Generosity, Justice)中詳細分析了憤怒為何會因為這種報復的慾望而變得不恰當。
按照努斯邦的說法,憤怒常常伴隨著報復的慾望,不管憤怒出現在個人關係抑或公共領域之中。憤怒的我們感到受傷而無助,對方憑什麼可以傷害我?我們要麼希望對方承受同樣的痛苦,要麼希望打擊對方,使得受傷的自己重獲同等的地位,不再是受害者。於是,憤怒所帶來的報復慾望不過是不願意接受自己的脆弱所帶來的非理性追求,對於解決問題毫無貢獻,甚至帶來相互打擊的反效果,掩蓋了真正的問題所在。正因如此,適得其反的憤怒應該被放棄和超越。在努斯邦看來,偉大的政治家如曼德拉,運動家如馬丁·路德·金,都是在超越憤怒的原則下追求正義和平等,更證明瞭憤怒的不恰當性。
憤怒的恰當性
除非認為憤怒不過是毫無緣由的情緒衝動,憤怒是否恰當的支持和反對者都大致同意,憤怒具有某種認知性以及評價性內容。憤怒並非無故發生。我們憤怒,是因為不公平或錯誤的對待造成了傷害和痛苦。(我們認為的)公平的結果,並不會讓我們感到憤怒。所以,憤怒具有是否有根有據的要求。
於是,我們總可以提問:當下的這個憤怒是否恰當?不過,在普遍的觀念下,憤怒總會適得其反,帶來並不理想的效果,因此憤怒都是不恰當的。仕尼瓦森的文章便是要反駁這一結論。
我們是否會覺得很熟悉:婦女運動或者女權主義者被告知,如果她們不是常常這麼憤怒,對於各種事情都不停生氣,性別平等和其他女性權益會更容易獲得,男性也更樂意接受。如果女權者不再「女拳」,進步會更加容易。正是因為充斥著憤怒,運動才會由於各種反效果而停滯不前。按照對憤怒的反效果批評,女權者似乎真的不該憤怒,特別是考慮到性別平等的進展。
看到女性普遍受到不公平對待,並決心要改變性別不平等,女權者很難不感到憤怒。勸告女權者應該溫和對話,往往也令我們感到十分不妥:難道他們看不到性別壓迫的嚴重嗎?在仕尼瓦森看來,通過展示憤怒可能引起的反效果來否定憤怒的恰當性,實際上是混淆了不同領域的問題,難怪乎被勸說的女權者會困惑。
在討論憤怒的時候,反效果論一方所提供的理由,其實是明智理由(reasons of prudence)。也就是說,由於憤怒可能帶來反效果,所以,如果想後續發展更好,我們就不該憤怒。就這樣的理由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它說明的是,倘若要實現某些預定的目標,我們應該怎樣做。可是,當詢問憤怒的恰當性時,我們實質上想獲得的並不全是明智理由,而更多是憤怒是否恰當的內在理由(intrinsic reasons):憤怒本身是否恰當,或者說,憤怒本身對不對。仕尼瓦森認為,「只關注於行動者的憤怒可能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批評者不過將我們從內在理由空間帶到工具理由空間,進而掩蓋了行動者憤怒的恰當性。」換句話說,憤怒本身是否恰當這一問題,與憤怒會帶來什麼樣的效果,事實上是兩個在規範意義上不同的問題,我們不能簡單用後一問題來代替前一問題的提出。
想象一下,面對著屢次出軌的伴侶,你感到十分憤怒。同時,你的憤怒會使得關係不得不結束,或許你並不希望如此。又甚至,正如仕尼瓦森的假設,對方還會說,「你越生氣,就越逼著我出軌。」不管這個憤怒會帶來什麼你並不希望的反效果,我們都很難否認,在這個場景裡面,你的憤怒是相當恰當的反應。對方的「勸說」,或者別人勸說為了關係可以修復延續而不要憤怒,不管有何道理,都否定不了這種憤怒的合理。同樣,婦女運動或其他爭取平等權利的運動,行動者或者關注者對不平等的現實表達憤怒,本身也相當恰當,就算這些憤怒可能帶來觀瞻上的反效果。區分上述兩種不同的問題,我們就不該簡單用後者代替前者。
至於努斯邦所說,憤怒內含著報復的慾望,仕尼瓦森認為,我們似乎需要區分報復的慾望(desire for revenge )和承認的慾望(desire for recognition)。當我們受到不公平的傷害時,我們憤怒時很可能希望對方的並不是她要受苦這一簡單報復慾望。很多時候,如果我們的親身經歷能夠佐證的話,我們欲求的,其實是對方能夠承認和認可我們因她而受到的傷害,或許這種承認和認可本身就是一種痛苦的過程,就如羞愧認錯時一種痛苦過程一樣,但這種痛苦不是我們的報復。這種差異可能特別細微,但兩者仍然不同。有些人憤怒會要求報復,另外的人憤怒是為了得到認可和道歉。既然這樣,我們似乎可以認為,憤怒並非必然內嵌著報復的慾望了。
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
既然反效果批評的明智理由與憤怒是否恰當的內在理由不盡相同,那麼事實上就應該存在可能帶來反效果但仍然恰當的憤怒。上文提到,憤怒是對外在世界的反應,特別是對不正義事件的反應。這種情感反應的能力十分重要,我們會因憤怒能力的缺失而感到不妥,就如一個人能夠作出各種正義的行為,能夠指出和分析各種不正義,但卻毫無感到憤怒或表達憤怒的能力,我們會迷惑,可能會疑問,她是否真的瞭解正義與不正義。這也是為什麼女權者會反問,難道看不到性別壓迫的嚴重嗎?因此,仕尼瓦森認為,恰當的憤怒是一種正確認識世界的能力。同時,憤怒也是一種公共表達,用來標記出不正義,呼籲他人關注。
在仕尼瓦森看來,這種可能帶來反效果的恰當憤怒更加展示出,遭逢不正義的受害者不得不面對道德或正義上的衝突。一方面要考慮為改變不正義這一目標所應做的策略和行為,另一方面也需要認識和展示世界的不正義。該不該憤怒,不僅僅是調節情感的個人問題,更是個人的道德困境。而在這種個人困境之外,反效果批評者的勸告或者批判,實質上會帶來另一種困境,對受害者帶來二次傷害。
考慮一下,面對著道德困境而憤怒的受害者,反效果批評者的勸告「不要生氣」,就更像在暗示,其實那些不正義沒那麼嚴重,不過是另一個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而已。仕尼瓦森將此跟勸告女生「不要走夜路,不要穿著暴露,不要喝醉酒」對比。兩者不僅將問題的歸咎在受害者身上,更加把「處理問題的主要責任放在受害者而非侵犯者身上。」明明不正義出現而產生了受害者,受害者還需承擔解決事件的角色,這對於本來就在遭受痛苦的受害者而言就是第二次傷害。
告誡女生「不要走夜路」,看似是有心人的好建議,但「不要走夜路」能夠好建議的前提是,對女性的性侵犯是一種不可改變的事實。在面對不可改變的事實時,再告誡「不要走夜路」才可能是好建議。現在問題恰恰正是,對女性的性侵犯遠遠不是無法改變,它是男性需要承擔道德責任的事件。女性之所以會被侵犯,在於男性去侵犯,而這是男性需要去改變的情況。
憤怒的批評者也類似地將憤怒可能帶來的反效果看作了不可改變的事實。實際上,這些反效果往往只是當下社會結構所產生的結果。這種社會結構使得恰當表達憤怒成為了問題本身,而沒法讓它實現認識世界和公共表達的功能。憤怒的批評者需要認真說明,為何明智理由必須高於恰當性的內在理由,然而這並不容易。仕尼瓦森認為,受害者一方面要考慮自己對受到的不正義的情感反應是否恰當,另一方面又要思考如何改善自身的不公平處境。受害者需要平衡兩者,這個「需要」本身,就是受害者面對的第二層面的不正義,仕尼瓦森稱之為情感不正義。受害者已經受到不正義的傷害,社會還潛移默化地要求受害者承擔消除不正義的責任,對自己的情感表達各種克制和自我審查,這種針對情感的不正義,就是連本來已經無聲的受害者所表達發聲的能力都要壓制。
讓無聲者發聲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仕尼瓦森辯護憤怒恰當性的意義。許多對憤怒的批評都集中在,憤怒對於實現正義沒有意義或者會帶來負面影響。仕尼瓦森要論證的恰恰是,這種情況的出現亦是在於不正義的社會結構。情感不正義之所以是一種不正義,在於表達憤怒的恰當性和改善個人處境本來是完全可以相容的兩個事情,但卻被普遍視作不可調節的矛盾,將受害者拋進道德困境之中。
這種不正義在本來已經被社會邊緣化的無聲者身上尤為明顯。只會感情用事的女人、不夠理性的黑人、天真幼稚的年輕人,他們被刻畫成不能理性對話的人,所以他們的憤怒往往被視作非理性,最終被輕易忽略。他們需要嚴重自我審查自己的情感表達是否有效,以至於恰當的表達都不能出現。
仕尼瓦森的工作便是要揭示出這種不正義。將憤怒和講理對立是錯誤的,它是維護現狀的有用工具而已,維護著不正義存在的現狀。我們批評憤怒的表達的同時,我們也長期忽略了「那些從來不被允許發怒的人,既沒有權力也沒有刀劍的奴隸和女人。」不正義的受害者們發出的怒吼,既然可以評價恰當與否,我們就應該去聆聽,去看清楚並且去感受社會結構中的不公。不輕易忽略憤怒,讓無聲者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