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貿易戰就是階級戰》中國的失衡是否將再次震撼全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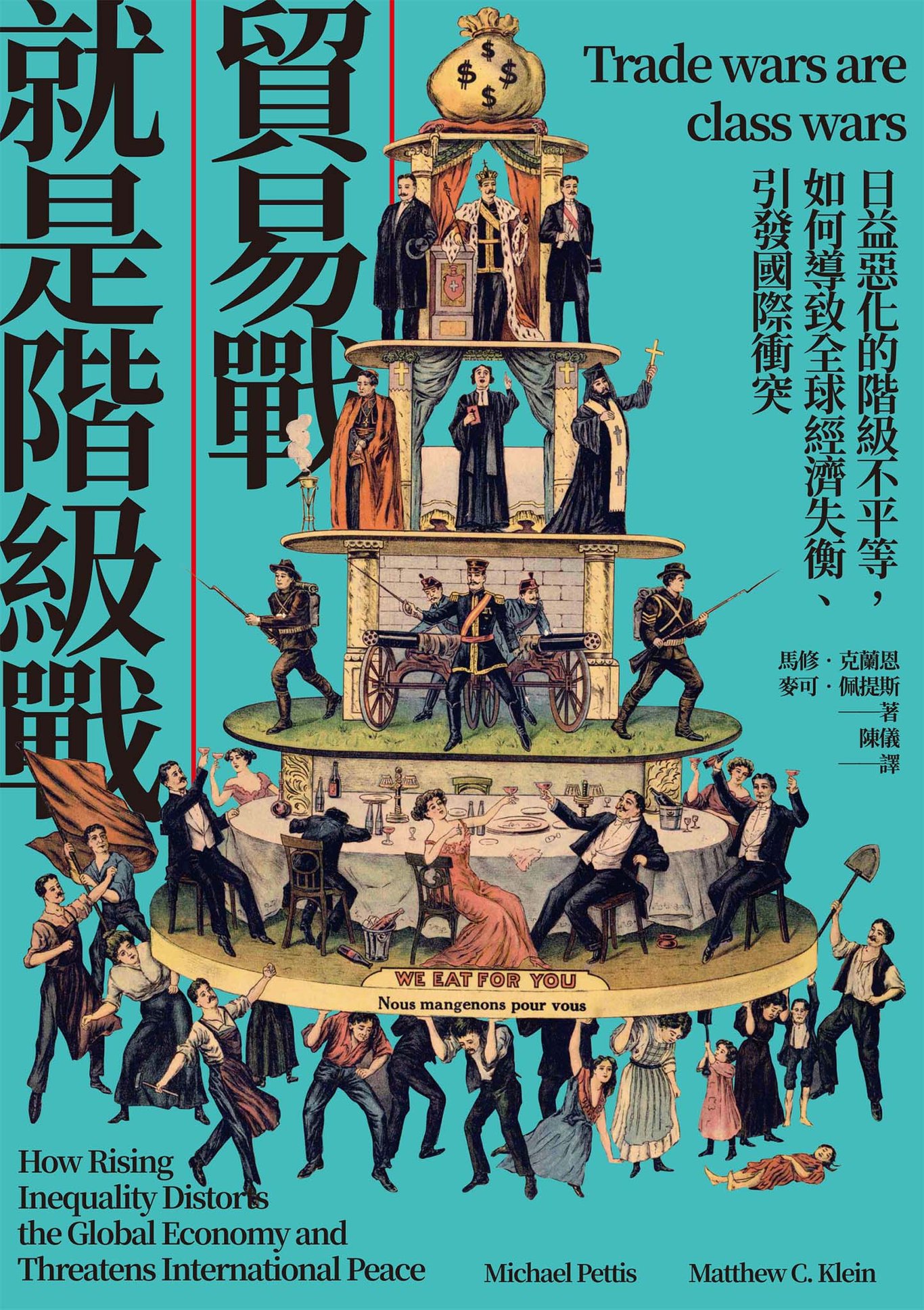
中國的失衡是否將再次震撼全世界
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它的年度經常帳順差在二○○八年達到四千兩百億美元的高峰後便開始萎縮,到二○一九年上半年,換算成年率的中國經常帳順差已降到大約一千九百億美元。無論是以絕對數字或相對中國經濟規模而言,中國的主要失衡之一似乎已經解決。不過,更詳細檢視就會發現,中國的外部再平衡進程非常脆弱,且隨時有逆轉的可能。勞工與退休者的財富持續遭到移轉,並導致中國的消費繼續受壓抑。一旦投資支出減緩但家庭支出卻未出現抵銷性的對應增加,中國的順差將再次擴大,這將對世界上其他經濟體造成損傷。
首先要注意的是,無論是就絕對數字或相對世界上其他經濟體的經濟產出而言,中國的製成品貿易順差已遠比二○○八年時高。換言之,中國的超額生產所造成的過剩供給非但沒有減少,反而進一步惡化,而中國的貿易夥伴吸收這些過剩供給的負擔也變得更加沉重。從這個視角來看,所謂的再平衡根本沒有發生。
令人意外的是,這是發生在中國製造業出口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已漸漸式微的時刻。在二○○七年至二○○八年間,中國的製造業出口大約達到GDP的三○%,但目前這個數字降到只剩一八%。這個現象的局部解釋是,中國產出約當的全球產出的整體占比持續上升,所以中國貿易帳與經常帳收支的變化對中國國內經濟的意義與對其他國家的意義大不相同。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和中國對進口製成品的支出變化有關。一如所有國家,中國進口製成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利用進口的零組件製成品來生產最終成品,而這些成品最後將出口到其他國家,二是進口製成品來滿足國內投資與消費的需要。目前這兩種進口對中國的重要性都日益降低,這導致製成品進口總額約當中國GDP的比重,從二○○四年的二三%,降至目前的一○%以下。這可局部解釋為何中國二○一九年年中的整體貿易順差看起來絲毫未受美國的關稅影響。
部分原因則是中國企業不再需要為了出口最終成品而進口那麼多零組件,因為中國國內的供應商漸漸有能力提供那些零組件。在二○○○年代初期,中國的先進製成品出口值有三分之二來自海外,但如今中國先進製成品的價值多數來自中國本地的勞動力與資本。如今的中國勞工早已不是單純從事零組件組裝(將別處製造的先進零件組裝在一起)作業的低階勞工。在此同時,中國的國內產能也已非常能滿足國內的需要:最終製成品進口值約當中國GDP的比重,已從二○○四年的九%降至目前的五%以下。「二○二五中國製造」的行動計畫明顯旨在加速這個進口替代流程。
進口替代的成功,局部是拜中國政府全面鼓勵中國企業以國內生產取代外國生產的政策所賜,只不過,這使中國消費者的成本增加。中國自二○○一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就小心翼翼地信守它對WTO的承諾,並遵從WTO裁判的決定。但中國經濟體系基本上可能和凡事依規定行事的貿易體系不相容,因為中國向來以黨領政,這個模式使政府掌握了支配企業的巨大力量。多數中國企業一開始就內設共產黨的小組組織,即使是非中國企業在中國設立的子公司也不例外。很多大型企業的高階主管(包括政府未掌握直接所有權的企業)都是共產黨黨員,理由很簡單——黨員的身分讓他們更容易獲得晉升與支持,但他們也因此不得不遵守黨的紀律。
即使是非黨員的高階主管,通常也會努力以北京當局的所有優先考量為重。法律學術界人士柯爾提斯.米爾豪特(Curtis J. Milhaupt)與鄭文通(Wentong Zheng)「發現百大民間企業中有九十五家、十大網路公司有八家公司的創辦人或實質控制者,目前或過去曾是中央或地方黨政組織(如人民大會和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員之一。」監理機關可就任何和那些高階主管有關的主題要求他們接受約談,而這樣的情事也確實屢見不鮮。
中國的金融體系受國營實體支配,這讓黨掌握更大的獎懲力量,積極促進黨的目標的企業將獲得獎勵,而不願意配合黨的企業則會受到懲罰。米爾豪特與鄭文通提到,民間企業「在商業判斷上經常受政府任意干預的影響,幾乎沒有自主權可言」,因為「政府對民間企業行使巨大的法外(extra-legal)控制權」。
正因如此,這個體系幾乎不用關稅也能將國內需求導向國內生產。政府可能經由直接命令的方式,要求企業高階主管採用中國供應商、捨棄外國供應商。這些工具讓中國政府得以進行一種現代版的李斯特國家系統,在這個「顯性關稅已被視為過時」的時代,那是非常合適的國家系統。這些作為的結果是:不同於其他國家,自二○○○年代中期開始,進口對中國已愈來愈不重要。
我們可輕易拿中國的製造業貿易數據和表彰其他國家實際經濟活動的公告數字進行比較。但中國的整體經常帳順差數字並不適用相同的邏輯。根據官方公告數字,中國對其他國家的旅遊服務出口趨向停滯,但中國官方公告的旅遊服務進口數字,卻從二○一二年的一千零二十億美元暴增到二○一八年的二千七百七十億美元。雖然目前在海外消費的中國學生與中國遊客確實比幾年前多很多,但他們增加的消費遠遠低於官方數字所示的變化。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經濟學家在二○一九年提出的一份分析斷定,中國的國際收支數據高估了實際的旅遊服務貿易逆差數字,「二○一八年大約誇大了八百五十億美元。」
這個現象最可能的解釋是,很多被計為旅遊的支出其實是某種形式的資金外逃。就經濟意義來說,中國人到美國購買人壽保險或住宅(或將高價珠寶兌換成美元),並不等同於去度假與購買紀念品。旅遊支出的遽增是發生在習近平的反貪腐運動展開之後,箇中原因不言自明。旅遊支出的遽增也和中國的其他資本外逃指標有著明顯的關聯性,尤其是經常帳與金融帳之間的統計差異,也就是所謂的淨誤差與遺漏(net errors and omissions)。在二○一五年至二○一六年間,這類流出的年度金額達到七千億美元的高峰。
中國政府以引導匯率貶值、拋售外匯準備與調整國內貨幣政策框架等所組成的綜合對策來調和這些流出。然而事實證明,那些對策依舊不足,也因如此,中國政府在二○一六年至二○一七年間漸進式地緊縮資本匯出控制。從那時開始,很多過去特別積極以公司名義在國內貸款再轉而購買海外資產的中國企業高階主管陸續被逮捕,也有很多企業高階主管最終在一些不尋常的情境下死於非命。
這些數據顯示中國的外部再平衡進程並不像表面數字所顯示的那麼順利。儘管如此,中國人對進口原物料商品的支出確實增加了,尤其是黃豆、奶製品與肉類,而且中國人確實花比較多錢在海外旅遊與留學的用途。這對中國有利,也對世界有利。然而,由於中國債務過高與投資過度等所留下的遺毒甚深,所以中國到目前為止所實現的進展還是太脆弱。而且,雖然緊縮信用是中國內部再平衡的必要手段,但這最終也可能造成危害:在各種互補性改革措施還未成功達到提升家庭所得與刺激國內消費的目標以前,投資活動便已先被扼殺。若發生那樣的狀況,將產生國內需求遭到壓抑的淨影響。
那將進而產生兩個選項。首先,國內生產有可能呼應國內需求的降低而減少。在那個情況下,總所得將因實質薪資減少與失業率顯著上升的綜合影響而降低。中國的政治系統可能承受不了那種社會動盪的衝擊,就算承受得了,政府也沒有興趣冒險承擔這個後果。因此,較可能的結果是國內生產降幅將低於國內需求降幅,而那意味中國的貿易順差將因進口相對出口減少而進一步擴大。舉個例子,中國政府可能選擇引導人民幣貶值,或尋找其他方式將這個調整所造成的負擔轉嫁給世界上其他地方。不管具體的機制將是什麼,超額生產所造成的全球過剩供給都將惡化。從這個視角來看,中國的「中國製造二○二五」行動計畫可視為一個旨在限制進口以便為即將降低的國內投資做準備的先發制人對策。
相似的,我們最好將中國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決心理解為中國為管理其內部再平衡進程的利弊得失而想出的方法,而不是旨在爭奪領土或軍事基地的某種謀略。還記得嗎?在二○○八年之前,中國政府將購買力及商品出口給美國人和歐洲人,藉此應付本國產能過剩問題。當時的中國囤積了數兆美元的美國與歐洲金融資產,換言之,它為其他國家日益增加的債務提供財源,並因此避免了國內債務持續上升的命運。然而,等到美國與歐洲的貸款人達到其舉債能力上限,那個做法再也無以為繼。於是,中國政府改弦易轍,轉而鼓勵額外的國內投資,但這個對策也不是沒有代價——中國國內債務大增。誠如我們所見,事後證明這個做法一樣非長久之計,也因如此,中國政府已再次改變路線。過去幾年間,中國政府改弦易轍,將抑制國內信用成長與限制國內投資列為首要之務,只有少數情況例外。
因此,一帶一路的真正前途在於它將創造東南亞、南亞、非洲、中東、東歐與拉丁美洲等地對中國製成品與建設服務出口的新需求。中國的銀行業者將放款給外國政府,而那些外國政府將委託中國企業為它們國家興建港口、鐵道、電網、火力發電廠、電信網路等。到目前為止,一帶一路確實成功創造了海外對中國企業與中國勞工的需求。不過,中國並非沒有為此付出代價:中國經由一帶一路,把中國國內發展模型的很多缺陷出口到世界上其他國家。中國的放款人沒有對那些外國貸款人進行實地審查的積極誘因,因此,接受一帶一路的國家已對中國的銀行業者造成巨額的呆帳。另外,中國企業向來對它們的專案所造成的環保衝擊漠不關心。遲鈍的政治與文化敏感度已導致中國企業和東道國之間發生許多摩擦。即使那些問題都能一一克服,一帶一路國家的整體潛在市場(addressable market)也遠比北美和歐洲小。因此,中國妄想利用一帶一路來取代它失去的傳統出口市場(譯注:北美與歐洲)的如意算盤,實在不切實際到令人難以想像。
這一切的一切都會顯著牽動中國經濟受當前貿易戰影響的程度。只要中國還擁有舉債能力,且中國政府願意使用這個能力,那麼,不管貿易戰的戰況有多麼險惡,中國對外公告的GDP成長率,這個用來衡量經濟活動,但不考慮這些經濟活動是否能增加財富的指標,就不會受貿易戰影響。然而,只要中國人無法自由進入出口市場,中國經濟的永續成長能力將受到影響,因為一旦如此,政府將可能為了因應這個問題而盲目鼓勵增加借貸,以支應愈來愈沒有效益的投資活動或是家庭債務所需的資金。這雖會使中國表面上對出口的依賴度降低,實際上卻會使中國經濟變得更容易受貿易戰傷害。截至目前為止,中國回應美國關稅的方式是提高它的進口替代、引導人民幣貶值以及(溫和)加速國內信用成長,其中包括家庭債務。
中國需要改革一事,已在當地凝聚了相當廣泛的共識,二○一三年十月的中國共產黨三中全會就提供了至少部分的改革藍圖。中國已在很多領域創造了重要的進展,包括利率自由化、環境保護、醫療保險,以及一胎化政策。家庭消費相對總生產甚至也開始上升,只不過,家庭消費約當中國經濟產出的占比,還是遠低於二○○○年代初期的水準。下一個重要的步驟將是如何把巨額的財富與所得,從權貴階級(尤其是中國省級與地方政府以及眾多國營實體)手中。移轉給家庭。這意味中國必須進行土地改革、戶口制度改革、租稅改革、民營化、工會合法化以及其他對策,好讓家庭所得在GDP成長率大幅降低之際繼續快速成長。
此時此刻,有關中國的失衡,唯一的安全預測是:未來十年或二十年,中國的失衡將會被逆轉,那意味未來家庭所得的成長速度將大幅超越GDP成長。不過,這個結果可透過很多管道發生。漸進式的財富移轉將使中國人的生活水準在投資活動成長趨近於零或甚至轉為負成長的情況下繼續維持快速成長。未來中國家庭的所得與消費可能會達到每年五至六%的亮麗成長,而平均GDP成長率則將趨緩為三至四%。
重點是,不管採用什麼方法,中國一定會再平衡它的經濟體系——所謂物極必反,所有的失衡最終都會自我逆轉。但具體的再平衡途徑將取決於政治體系如何與幾個無法並存的約束條件周旋。隨著中國的經濟繼續趨緩,北京中央政府將必須和中國各個不同權貴團體建立一種全新的關係。中國將會打造一些新機構來決定這個世紀後續時間的中國經濟本質。那個新關係與這些新機構將以什麼面貌出現,但憑個人猜想。最好的結果是權貴分子的所得被移轉給一般家庭:這個再平衡作業基本上應該能使中國不再那麼需要強迫世界其他地方來填補它不足的國內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