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在墻上的路:社會主義道路怎麽走?
視頻脚本:
有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沒有:我們經常看見中國民眾控訴習近平開改革倒車,說習近平背叛了其前任政府韜光養晦不折騰路線。但這些人同樣也承認,從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三代領導人執政理念的幕後操盤手都是王滬寧。王滬寧作為首屈一指的黨內理論家,對執政路線的影響無人出其左右,如果執政路線真的發生那麼大轉變,難道是王滬寧自己反對自己?真實情況要比這個復雜很多,因為這關系到改革開放所定位的國家發展道路是怎麼形成的。
中國直到1990年代才正式確定國家發展道路,而這個國家發展道路是一條調和主義道路。形象地說,這個調和主義道路是以王滬寧的新權威主義為砧木,嫁接了民族主義和新國家主義等思想流派,同時實現了向新左派和老左派妥協。可以說這條道路是將一些並不兼容的思想流派雜糅在一起,造成了很多矛盾復雜的社會現象。我們將通過很多期節目和專欄文章來探討當代中國政治思想流派競爭,本期影片我們主要談一談王滬寧的新權威主義是怎麼上升到國家道路層面的。在影片後半部分,我們還會解釋王滬寧和中共的理論困境就像把道路畫在牆上,看上去很美,但是走不上去。對於普通觀眾來說,本期影片也會是一場現實主義的政治訓練:我們不但要知道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現實主義政治,還要知道現實主義政治是怎麼變質的。
首先,本著尊重對手、尊重事實的原則,我們必須承認:中國以新權威主義為基底的國家發展道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確實比較符合現實主義政治原則。葉利欽時代的俄國用休克療法來刮骨療毒,結果造成巨大社會災難。中共的改革開放避開了這些問題。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地方,雖然我們並不和中共站在同一條陣線上,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承認中共黨內有一批清醒的現實主義理論家,他們拋棄了毛澤東時代那種堪稱喪心病狂的烏托邦主義狂熱,這是應該肯定的地方,即使現在黨內理論家所推崇的現實主義對於國家和國民來說,同樣造成了莫大的危害。
現實主義政治固然是危害較小的一種形式,但並不是只有新權威主義這一條路才算是現實主義,更何況中共的新權威主義在其理論根基上存在很大問題,甚至可以說走到了現實主義的反面。假如有一個人走路摔斷了腿,相比於立刻祈求神明保佑和用巫術給自己驅邪,我們認為緊急送醫才是符合現實主義原則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找醫生把腿鋸掉就是合理的。真正的現實主義原則是要在鋸腿和把腿恢復如初之間,找一個損失最小化的折衷區間。假如打石膏可以讓腿痊愈,即使不能與原先功能完全一樣,至少保留了一條健康的腿,而不是在毫無必要的情況下就把腿鋸掉。也就是說,一來就選最壞的選項不等於就是現實主義。
在現實主義各大流派中有一個著名的國家理性學派,其對現實主義政治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提出了必要性原則。國家理性學派與馬基雅維利主義都是現實主義,盡管他們之間存在較大分歧,但是兩個學派不約而同都強調政治實踐中的必要性原則,直到現代保守主義政治興起的時候,其源頭埃德蒙·伯克也同樣反復強調必要性原則。什麼是必要性原則呢?就前面舉例來說,摔斷腿及時就醫肯定是現實主義,為此拿磚頭截停一輛車在緊急情況下是有必要的,但及時就醫不等於一來就要把腿鋸掉,因為假如只是一般性骨折,腿是可以痊愈的,根本沒有必要一來就把腿鋸掉。這個淺顯的道理誰都懂,可是一到政治爭論的時候,就有人故意將必要性原則與現實主義相剝離。
一些自稱現實主義的馬基雅維利分子也是這樣做的。這些人要比拼的不是現實主義政治的清醒、冷靜和克制,而是打著現實主義幌子比野蠻、比殘忍。《呂氏春秋》講過一則政治隱喻就很能說明這種偽現實主義的認知誤區:這個政治隱喻講的是齊國有兩個勇士有一天在街上遇到就相約去喝酒,但是喝酒總不能沒有肉吧?其中一個勇士說:你身上有肉,我身上也有肉,還買肉做什麼?於是這兩個狠人就互相割對方身上的肉來下酒吃,並且把割自己肉不喊疼當成是勇猛的表現,結果呢?這兩個狠人就互相爭強斗狠,直到同歸於盡為止。
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有這種傾向,社會達爾文主義就經常披著現實主義外衣,一邊裝裱政治理性,一邊只滿足於爭強斗狠、尋求同歸於盡。現實主義政治之所以容易出現這種變異,問題通常就出在有人喜歡拿叢林法則打掩護,把凡是不符合進化論原則的反對意見,統統斥責為浪漫主義、激進主義和政治幼稚病。這些人普遍存在同一個問題,那就是忽視了野蠻和殘忍在現實中並不一定有必要。這些情況是要說明的是:現實主義不但可能荒腔走板,還可能變質。現在很多人感慨中國大陸盛行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不是沒有緣由的,1980年代蕭功秦、吳稼祥、張炳九等人鼓吹的新權威主義,對社會達爾文主義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其中蕭功秦堪稱是新權威主義的靈魂人物,是蕭功秦把嚴復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用近代保守主義之名重新包裝上市,結果新權威主義也被稱為中國的新保守主義,其內核就是蕭功秦解讀的嚴復的保守主義思想。
等1995年新權威主義另一位理論家王滬寧從復旦大學空降到中央核心權力圈層,說新權威主義開始左右了中國國家發展道路是沒有什麼問題的。美國政治學家傅士卓甚至認為,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後,江澤民政府就已經走上了新保守主義道路。這種說法既對,也不對。盡管當時江澤民政府還缺少新保守主義鼓吹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狂熱,後來我們會發現,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也一樣不斷上升到國家層面,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內政和外交。
但是我們要問,既然王滬寧並不是新權威主義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新權威主義的其他代表人物比王滬寧思想更深刻、更典型,中共中央為什麼不選拔其他人進京?如果我們回到歷史現場就會發現,新權威主義南派和北派的三個著名代表人物都不符合中共中央選拔標准。
其中南派領袖蕭功秦不僅對馬克思主義缺少建樹,後來甚至還有反馬克思主義傾向,有人還說他鼓吹用民族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另外兩名北派領袖吳稼祥和張炳九在1989年六四運動中遭到整肅,一個坐牢,一個被北大開除。不僅如此,蕭吳張三人所主張的新權威主義有轉型期過渡性質,其最終目的是要導向民主政治的。雖然中共當局很喜歡新權威主義所鼓吹的強人政治和強化專制,但是其間接的民主取向很難取得中共當局信任,而且蕭吳張三人多少都有排斥馬克思主義的傾向,但中共是馬列主義政黨,動搖馬列主義不啻於是動搖國本。
相比之下,王滬寧不僅同樣在80年代表現出新權威主義傾向,同時還系統性運用和發展馬列主義理論,王滬寧1987年出版的《比較政治分析》一書就大量引用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經典理論。也就是說,王滬寧的思想取向是新權威主義和馬列主義結合,但其本質上仍然是馬列主義,這一點與蕭吳張三人完全背道而馳,盡管蕭吳張三人才是新權威主義最重要代表。包括傅士卓等學者在內,不少人誤以為王滬寧在1980年代也有自由派傾向,比如1986年王滬寧在自由派和改革派輿論陣地《世界經濟導報》上發文章,不僅從政治體制角度反思文革,還多次提到民主理念。但是仔細看這篇文章就會發現,王滬寧強調的是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和黨內民主制度,跟自由派的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完全不是一回事。王滬寧鑽研的政治體制改革,目的不是通過漸進改革實現西方式自由民主政治,而是繼續發展和推進中共的社會主義理論,維護中共政權和社會主義體制。1994年王滬寧主編的《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一書可以印證這種說法,該書不僅繼續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還致力於重塑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根基。可以說,王滬寧這種思想取向完美契合了六四運動以後中共當局的理論需求。
此外很值得一提的還有1989年六四運動期間,王滬寧相當狡猾地避開了風頭,嚴家祺說王滬寧當時跑到法國躲了3個月,也有人說王滬寧曾經在反對學生運動的文件上簽字。但是目前沒有任何可靠資料表明王滬寧在六四運動期間的明確態度。對於一個接受過現實主義政治訓練的青年學者來說,王滬寧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持騎牆觀望態度才是合情合理的推斷。在局勢明朗以前,不管是簽字支持鎮壓,還是表態支持學生運動,都不符合王滬寧所信奉的現實主義審慎原則,這個原則說得通俗一點就是精明、謹慎而且狡猾。假如當時王滬寧是明確支持鎮壓的,中共的宣傳系統是會明確指出來的,但是我們並沒有看到這種宣傳。結果王滬寧反而因禍得福,由於成功避開了六四運動風波,王滬寧沒有成為整肅對象。
根據嚴家祺回憶,早在1985年他就引薦王滬寧結識了上海市委宣傳部的魏承思,後來魏承思又把王滬寧介紹給當時主政上海的江澤民跟曾慶紅,這是六四運動以前的情況。同樣是在80年代,嚴家祺還曾推薦王滬寧擔任青聯委員,當時胡錦濤是全國青聯主席,可能也是在這段時間裡,王滬寧也結識了胡錦濤,至少給胡錦濤留下了印象。有這種結交背景,結合王滬寧素來低調謹慎不張揚的行事作風來看,他這種個性也不像是會在六四運動平息之前就明確表態。這種現實主義取向肯定會給王滬寧加分。事後北京當局也並沒有擴大范圍打擊報復那些沒有明確表態的騎牆派官僚,包括後來躋身到政治局常委的高官不少人也在六四運動期間立場模糊不清,這恰恰說明中共當局並不排斥當時沒有站出來明確支持鎮壓的官僚。
當然,王滬寧還有一個重要加分項:他是改革開放以後第一批從事政治學研究的青年專家,是當時中共政府內部極其欠缺的技術型官僚,而且王滬寧不但專注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還有西方訪學背景,被認為通曉國際事務。在六四運動期間上台的江澤民政府長期處在左右夾擊的艱難處境中,挑選王滬寧這種既不屬於新老左派、右派色彩也不明顯的技術官僚,對於江澤民政府來說是最容易實現各方妥協的折衷選項,而且江澤民政府也有自己的政治用意,那就是利用中間派技術官僚來平衡黨內派系斗爭。1994-1997年間,以鄧力群為首的老左派針對中共十四大以後確定的改革路線發起猛攻,接連發出四封萬言書,對才剛剛掌握實權的江澤民政府構成巨大壓力。王滬寧從1994年開始介入中共中央事務,到1995年正式空降到中央政策研究室,這個時間節點正好發生在第一封萬言書引發震動之際。王滬寧進京可以說既是改革壓力催生的產物,也是迫於政治斗爭實際需求。
王滬寧所在的新權威主義也有折衷主義特點,可以說是當時時代背景下的中間派:一方面新權威主義聯合新老左派、民族主義和新國家主義等陣營,阻擊改革派和自由派;另一方面新權威主義也配合改革派攻擊新老左派,並且支持中國改革。王滬寧與其他新權威主義代表一樣:既支持改革,又反對激進,所以主張漸進改革。這些情況是王滬寧從各大派系的復雜斗爭中脫穎而出的最重要原因。
另外,江澤民政府在鎮壓六四運動以後一直在觀望局勢,導致改革停滯了幾年。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指示中共當局不僅要重啟改革,還明確表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因為左右都可能葬送社會主義。在鄧小平給出的改革壓力之下,江澤民政府才慢吞吞地尋求一條折衷路線,於是新權威主義就被包裝成了新保守主義,在左右黨爭之間走一條中間道路。但是我們必須再次說明:王滬寧主導的新權威主義願景與蕭吳張三人最大的不同是,王滬寧對西方民主政治沒有好感,也不把那種民主政治當成奮斗目標。這種特點相當於把蕭吳張三人主張的新權威主義閹割去勢,最終以保存中共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前提,一邊以實現中間道路的姿態向新老左派妥協,一邊以主導改革的姿態安撫自由派,同時也聯合民族主義和新國家主義等派別來鞏固政權。
現在我們想知道,為什麼說王滬寧的新權威主義在其理論根基上出了問題?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在問:為什麼新權威主義形成了一種有毒的現實主義政治?
新權威主義有南派和北派之分,以蕭功秦為首的南派立場更為保守,以吳稼祥和張炳九為首的北派則相對激進。南派主張政府加強宏觀調控,嚴厲打擊官倒、腐敗和社會犯罪,主張利用中央政治權威啟動市場改革、漸進地培育市場秩序,用有形的手培養無形的手,防止經濟失序和政治動蕩;北派則支持中央權威用政治手段直接引進西方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省去其中的漸進環節。蕭功秦批判北派經濟觀念是變相推行激進的經濟自由主義,並斥責這種行為是經濟浪漫主義,還諷刺北派經濟觀念是刺刀下的商品經濟觀。
但是南北派在其他方面差別並不大,比如都推崇強人政治和權威政治,都主張經濟自由化不能與政治民主化同步進行,都想樹立一種過渡性政治權威來引導民主轉型,都希望承認有限的多元化,都設想利用有限的制衡機制和壓力機制來抗衡權威政治的專制因素,都把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模式當成中國的榜樣,這種發展模式推崇權威政治引導市場經濟,最終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漸進地轉型到民主政治。總體來說,王滬寧的漸進改良立場顯然更接近蕭功秦的南派新權威主義,但是王滬寧對市場經濟和民主轉型究竟有多大熱情還未可知。
單從王滬寧80年代寫作來看,他顯然並不認為權威政治是過渡性的,他的民主理念是要完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並不是要像日本、韓國和台灣那樣向民主轉型。新權威主義者之所以主張漸進改良,是因為他們普遍有一種現實主義政治取向。對蕭功秦來說,中國長期的專制傳統和為適應這種傳統而形成的國民性,就是最大的政治現實,如果不能迅速適應自由主義,強推自由主義就可能導致國家陷入新者未得舊者已亡的困境。也就是說,如果突然全面引進自由主義,不但會毀壞原有政治經濟秩序,還無法建立新秩序,其結果就只能造成社會失范,乃至社會動亂。對王滬寧來說,必須承認的政治現實是中國的馬列主義政權和政治文化。王滬寧認為中國歷來推行一種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迥異於西方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盡管近代以來中國有向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轉變的大趨勢,但這個大的轉變趨勢是緩慢進行的,要實現轉型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不管是蕭功秦還是王滬寧,他們理解的現實主義政治奠基在本身就有問題的假設上,就像建築在沙丘上的城堡,風把沙子吹開,城堡就會搖搖欲墜。
蕭功秦的現實主義觀念有鮮明的歷史主義色彩,這是非常矛盾的事情。其一是因為蕭功秦要復活嚴復的保守思想,而嚴復思想的基本原理就是把國家和政治社會看成是一個社會有機體,這是19世紀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典型假設。這種假設當然有問題,因為國家和政治社會並不是具有一貫主體意識的生物體。既然獨裁者可能被推翻,這說明即使政治強人也不能代表國家和政治社會行使其意志。其二是蕭功秦認為近代中國與1980年代中國具有某種歷史同構性。也就是說,蕭功秦認為1980年代的中國就像嚴復所處的晚清,由於他認定這兩個時期的歷史特點有諸多相似性,所以蕭功秦的現實觀念實際上是歷史化的現實,是想象的過去歷史的倒影,並不是1980年代中國的政治現實,而蕭功秦在批判政治浪漫主義的時候,援引最多的也是晚清歷史。
現實主義者經常會犯這種低級的歷史主義錯誤,政治哲學家卡爾·波普爾批判過歷史主義問題,但我們在這裡要說明的是:蕭功秦幻想通過開明的政治強人來推動民主轉型,恰恰是忽視了歷史與現實的錯位。1980年代以來的中共政權既不像晚清政府,也不像朴正熙、全斗煥和蔣經國的個人獨裁,因為中共政權不僅有相當鮮明的政治意識形態,還沒有主動放棄這種意識形態的主觀動機。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的時候先提四項基本原則,這並不是說說而已,而是向改革阻力妥協的結果。四項基本原則關系到中共政權存亡問題,這與朴正熙、全斗煥和蔣經國的個人獨裁性質完全不同,獨裁者放棄個人獨裁之後,大韓民國和中華民國依舊存在,甚至大清帝國也不至於滅亡;但是放棄四項基本原則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了。所以在中共政權基礎上推動的改革,主觀上是不會以滅亡政權為目的的。即使是蘇聯的戈爾巴喬夫改革起初也不是以滅亡蘇聯為目的,只是到後期改革失控踩中托克維爾陷阱,戈爾巴喬夫才只好勉強說他自己也對蘇聯政權不滿,但這只是事後托辭和借口,世界上不會有哪個政權主觀上就想滅亡自己。這樣一來,蕭功秦幻想的政治強人在中共政權這個大前提下是沒有生存土壤的。
這恰恰是蕭功秦等新權威主義者脫離現實的地方:由中共政權推舉出來的政治強人是不會以滅亡中共政權為目的的。在這種情況下,幻想用進化論觀點來推動中共政權緩慢過渡到民主政治就會遇到自相矛盾:假如中共政權確實有統一的意志和決心,那也不會是主動尋求滅亡。你不可能既要保障一黨獨裁,又要同時實現民主政治,這兩者是完全互相不能兼容的。蕭功秦回避這種悖論,轉而批評效仿西方制度來實現現代化會遭遇嚴復悖論。所謂嚴復悖論指的是:單項引進西方制度和全面引進西方制度都不可能,最終推論就是不可能引進西方制度改變中國,所以中國必須依靠一代又一代的開明專制慢慢演化。但蕭功秦說的嚴復悖論根本就是奠基在社會達爾文主義上的假命題,政治社會並不是嚴復想象的社會有機體,因為文化和社會觀念是流通和變動的,制度也一樣具有流通屬性,比如1994年推行的分稅制改革就是從西方引進的,如果單靠封閉的有機體系統自己進化,中國進化了兩千多年怎麼沒有進化出自己的分稅制?話又說回來,中國靠自己的封閉系統進化了兩千多年都沒有進化到民主政治,你憑什麼覺得只要中共推行開明專制就會進化到民主政治?
新權威主義還因為將經濟和政治二元化被批評脫離了中國現實,中國是政治凌駕於經濟之上,經濟服從於政治,不存在類似韓國和台灣威權時代的自由經濟。中共政權既想要市場經濟,又不想市場經濟太自由,還要避免政治改革趨向自由化,在這種情況下,幻想政府不操控經濟是不切實際的,更何況中共把經濟看成政權根基。新權威主義一邊批判政治浪漫主義,一邊自己流露出脫離現實的理想主義色彩,這種現實主義政治理念實際上是假托保守主義之名的虛假現實主義,它在現實中唯一產生的作用就是為中共政權的專制統治背書,而不是推動改革向著民主轉型。另一方面,蕭功秦的漸進改良由於機械照搬嚴復的進化論保守主義,不但對改革阻力估計不足,還誇大了開明專制的必要性,因為開明專制即使是必要的,也不一定是現實可行的,更何況開明專制並不是解決社會弊端的有效辦法。像體制性腐敗、分配不公、司法不公、社會正義缺失、政治失靈都不是開明專制可以解決的問題,而且由於制衡專制統治的機制和壓力自身相當脆弱無力,積重難返的社會弊端還可能反過來惡化專制統治,導致政權向舊權威主義和極權主義倒退。
就此而言,我們必須承認,蕭功秦的現實主義實際上脫軌了,反而走到了現實主義的反面。蕭功秦以現實主義的名義批判抽象的理念和主義,結果自己也掉進了脫離現實的空想陷阱,他不僅無視現實政治的復雜性,還沒有想過漸進主義改革也可能遭遇僵化停滯和倒退風險。蕭功秦當然還沒能預見到,東歐劇變期間迅速實現民主轉型的國家就不是靠推行漸進改良,我們以後再單獨出一期影片來探討中國的漸進改良為什麼會失敗的政治原理。
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王滬寧的情況會不會更好一些呢?從王滬寧早期著述來看,他在許多方面都與新權威主義不謀而合、甚至高度雷同,他的政治文化理念也像極了嚴復的社會有機體概念。但王滬寧並不承認自己是新權威主義,他從始至終都有強烈的馬列主義理論家色彩,他並不把中國的馬列主義政權當成過渡形式,他所理解的現實政治,是順應、而不是尋求架空中國的馬列主義政權。我們必須承認,王滬寧缺少蕭吳張三人的書生意氣,是一個更加冷峻的現實主義者,從王滬寧主導政治路線頂層設計就可以看出來,其靈活的調和主義特點是相當務實的。比如他刪除了新權威主義的民主理想,代之以新老左派要求不改變政權性質的原則性問題;但同時也做出一系列改革姿態來籠絡和分化自由派,給自由派塑造不切實際的政治幻想;還有在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層面的一系列政策舉措,也極大增強了政權凝聚力。
但是王滬寧的問題又出在哪裡?
從王滬寧的政治寫作來看,他的思維模式被打上了很深的馬列主義教條印記,王滬寧所理解的現實是透過馬列主義棱鏡來看的,這個現實與其說是現實本身,不如說是馬列主義願意承認的現實和想要人為塑造的現實。如果說蕭吳張三人是對開明專制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王滬寧則鑽到了自己給自己劃定的理論囚籠裡,這個理論囚籠就是社會主義民主體制改革。王滬寧為什麼會掉進這個理論陷阱呢?其源頭還在於他的政治文化概念。王滬寧想象的中國政治文化結構包括歷時性結構和共時性結構。其中歷時性結構包含古典結構、近代結構和由中共政權建立的最近結構,且不論這樣劃分是否合理,王滬寧的意思是:這些結構復雜地糾纏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母體,任何尋求脫離這個政治文化母體的企圖都可能造成災難。比如王滬寧就認為,文革就是用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結構來擺脫原先的政治文化母體,結果就造成了災難性後果。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相當迷惑人心,依據這種說法,引進民主政治和健全市場經濟就會像文革一樣給中國社會造成災難。這種說法很荒謬。讓司法系統從黨政系統獨立出來,實現政治中立,會擾亂現時的政治文化結構嗎?這會造成什麼災難?至今還沒有哪個國家因為司法獨立而引發災難的。之所以不允許司法獨立,除了擔心政權變色,不可能還有別的解釋。
王滬寧在《比較政治分析》裡批評照搬照抄政治模式的做法,說哪怕是移植蘇聯模式也一樣會失效,最終各國都要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走上適合自己的發展模式。這種說法隱諱地否定了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奉行的蘇聯模式,但其論點落腳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上來。考慮到王滬寧把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視為兩種根本對立的意識形態,他的政治文化論實際上不止是反對照搬照抄自由主義模式,而是根本拒絕自由主義模式。可以說,王滬寧的政治文化論成了晚清中體西用論的翻版,但是打著政治學的旗號。
王滬寧設想的政治文化的共時性結構比歷時性結構更加復雜,簡單地說,這個共時性結構不但要充分尊重中國的政治現實,還要考慮到構成這種政治現實的歷史因素、傳統因素和社會動態。王滬寧認為只有在兼顧共時性和歷時性政治文化的情況下,才可能在中國推動政治體制改革。1987年,王滬寧在一篇文章中分別列舉了民主改革和體制效能改革的五個目標。到目前為止,距離實現這十個目標還遙遙無期,甚至可以說至今進展不足30%,剩下的也不大可能有進展。如果拋棄立場偏見,單純把王滬寧看成是一名政治改革家,我們會發現,王滬寧推行社會主義民主體制改革遭遇到的困境,從根本上講是現實主義政治困境:作為一名改革家,他很清楚在哪些地方推行漸進改良有助於實現目標;但是作為一名現實主義者,改革壓力往往要屈服於現實中的政治壓力,結果改革就只能流於形式化。
就漸進改良的出發點而言,王滬寧與蕭功秦的情況很像,他們考慮現實問題總是摻雜著歷史維度,現實混雜著歷史,就好像背著沉重的歷史包袱放不下來。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政治家當然需要有一定的歷史視野,但他必須同時清醒地意識到現實與歷史之間存在鴻溝,而且並不一定有糾纏不清的隱蔽關系。那些迅速實現民主轉型的國家並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他們一樣有自己的歷史和傳統,歷史和傳統不見得就一定是思想包袱和改革阻力,不見得一引進新制度就造成滅頂之災。
但是王滬寧要面對的現實並不是我們看見的現實,而是一系列悖論的集合體。這個現實指的是中共政權既不願意放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又要追求經濟績效,還要證明自己的制度優越性。於是就只剩下一條路可以走,那就是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繼續改進社會主義制度。但這是一條畫在牆上的路,本質上是一廂情願的現實。中共的知識精英和黨內理論家,至今沒能夠像西方國家那樣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但中共政權一直執著於發展一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這種理論關系到社會主義制度根基、價值體系以及發展方向,關系到堅固政權支持者的信心,一旦失去這種理論支撐,中共政權就有可能演變成韓國和台灣威權時代脆弱的獨裁政體。韓國和台灣威權時代的獨裁政黨就存在意識形態根基薄弱、缺乏凝聚力的問題,其獨裁更多依靠領袖權威、較少依靠政黨權威,由於這種特點,其獨裁政體要傾覆也更容易一些。
中共政權不僅要樹立領袖的個人獨裁,還更強調政黨獨裁來穩固政治根基,這樣不管獨裁者怎麼更迭,獨裁政黨都牢牢抓住政權。這是中共特別依賴意識形態體系的原因。根據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家麗莎·魏丁的說法,意識形態就是一套空洞的儀式和話術,旨在制造服從。現實中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不是一套政治理論或社會理論,而是一套由政策口號、領導人命令、階段性執政理念等術語構成的官方欽定的意識形態。中共政府至今連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都沒搞明白,至今甚至連本國碎片化的市場壁壘都沒有打破,但鼓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卻一套一套的。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沒有什麼理論內涵,說來說去無非就是堅持中共領導和公有制為主導,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根本算不上是理論升級。
三個代表還能勉強重新確定中共轉型期的自我定位,但是遭到老左派猛烈阻擊,和諧社會跟所謂的習近平新時代思想甚至明顯喪失了最基本的方向感,其中不但看不到理論升級的影子,還無法解答將來社會主義制度會向什麼方向發展。由王滬寧主持的宏大概念越來越空洞無物,除了重復政策口號、領導人命令、階段性執政理念以外,中共執政的理論依據依舊是一百多年前的陳詞濫調。像無產階級這類詞語越來越空殼化,這類現象表明:中共的理論貧困不僅造成語言腐敗,還造成思維僵化、停滯不前。
中共的黨內理論家與其說是在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如說在用理論來歌功頌德和承擔國內外罵戰,他們的角色是重復官方欽定的意識形態術語,而不是創造和提出新理論。新馬派代表程恩富提出的社會主義三階段論和當代經濟基本矛盾論,並沒有被官方納入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升級裡,這是因為凡是可以納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范疇,且受到領導人引用跟推廣的說法,既不允許爭論,也不允許批評,這樣一來其性質就不是理論,而是官方意識形態了。沒有理論支撐的意識形態體系不僅越來越空殼化,還有越來越短視的傾向,也就是說只滿足於為現實中領袖權威服務,越來越少對政黨和政權長遠發展道路進行理論探索。事實上這種長遠規劃也是不可能的,不管是民主國家還是專制國家的政黨最終都會專注於眼前事務。但我們現在所了解的自由民主制度也一樣經歷過漫長的理論建設周期,許多哲學家、思想家和理論家都對自由民主制度發展做出過貢獻,這是自由民主制度的自然演化史。正是因為認識到制度困境和道路困境,習近平政府才大力撥款支持全國馬克思主義學院建設。但中共的黨內理論家不但不可能找到跟自由主義平行的替代方案,就算找到了也走不上去,因為那是一條畫在牆上的路:它最多告訴你有路可走,而不是真的要你走到牆上去。就像王滬寧探討的社會主義民主體制,它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就像說方的圓和黑的白,因為一黨獨裁和民主政治是無法兼容的。
對於缺少意識形態理論根基、更關心具體政策取向的其他政黨而言,他們感受不到中共的理論困境和道路困境意味著什麼。對於中共而言,理論困境和道路困境意味著不知道如何調整自己的政黨定位,不知道如何駕馭自己的政治改革,不知道這一套政治體制的前途在哪裡。習近平政府近年頻繁宣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這恰恰說明道路理論和制度問題至今困擾著中共,即使沒有人質問,他們也急於自證。理論貧困就像貧血造成慢性死亡。由於自身發展趨於僵屍化,除了背誦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類教條,難以實現理論升級的中共也將難以適應社會變革和時代潮流變更。王滬寧把習近平思想拔高到無所不包又沒有任何內涵的地步,王滬寧的接班人將來還要面臨更嚴重的理論困境,他不僅需要重新確定中共的政黨定位,王滬寧之前設計三個代表思想就是奔著這個目的去的,王滬寧的接班人還不得不在凌空蹈虛的習近平思想上更進一步凌空蹈虛,而且還會與王滬寧一樣,遭遇道路與現實相沖突的矛盾。我們在下期節目再來分析王滬寧潛在接班人可能出現的理論動向,這關系到下一代中共領導人會如何調整執政路線問題。
(完)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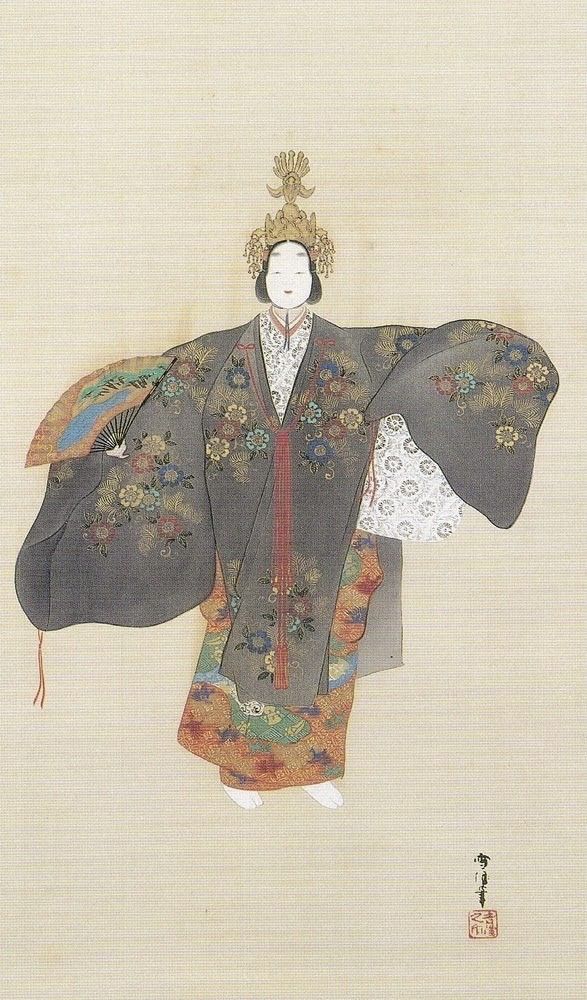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