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記《人類大歷史》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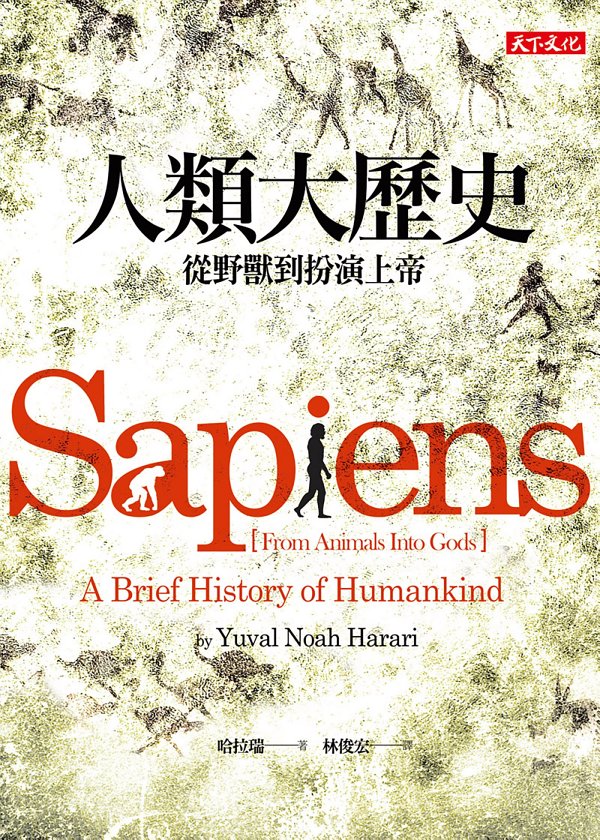
第19章 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在過去的五百年間,我們見證了一連串令人驚嘆的革命。地球在生態和歷史上,都已經整合成單一的領域。經濟呈現指數增長,今日人類所享有的財富,在過去只有可能出現在童話裡。而科學和工業革命也帶給我們超人類的力量,以及幾乎可說無限的能源。不僅社會秩序完全改變,政治、日常生活和人類心理也徹底改觀。
只不過,我們真的更快樂了嗎?
人類在過去五世紀間積蓄的財富,是不是真的讓我們找到了新的滿足感?有了取之不盡的能源之後,我們是不是也得到了用之不竭的快樂?如果我們往更久之前回顧,認知革命以來這動盪不安的七萬年間,世界是不是真的變得更好?到現在,阿姆斯壯的腳印還留在無風的月球上,而三萬年前也有個不知名的人,把手印留在雪維洞穴裡;這兩個不同時代的人,究竟誰比較快樂?如果後來的人並沒有比較快樂,我們又為什麼要發展農業、城市、文字、錢幣、帝國、科學和工業呢?
歷史學家很少問這樣的問題。他們不去討論秦朝人是不是比先前採集為生的人更快樂;伊斯蘭教興起後,埃及人是不是對生活更加滿意;也不討論歐洲帝國在非洲崩潰之後,數百萬非洲人的幸福受到什麼影響。
人民真正幸福快樂嗎?
然而,這些可說是最重要的歷史問題。目前大多數的意識型態和政治綱領,雖然都說要追求人類的幸福,但對於幸福快樂的真正來源為何,卻還是不明就裡。民族主義者會說政治自決能夠帶來快樂。共產主義者會說無產階級專政能夠帶來快樂。資本主義者說自由市場能夠創造經濟成長,能夠教導人自立自強、積極進取,所以能夠為最多人帶來最大的快樂。
如果經過仔細研究,結果卻全盤推翻了這些人的假設,情況會如何?如果經濟成長和自立自強並不會讓人更快樂,又何必將資本主義奉為圭臬?如果研究顯示,大型帝國的屬民通常比獨立國家的公民更幸福,例如假設阿爾及利亞人被法國統治時比較快樂,那我們該怎麼辦?這樣一來,要怎樣評價去殖民化?民族自決的價值又該怎麼說?
這些都還只是假設,但原因就是歷史學家至今還在迴避提出這些問題,更不用說什麼時候才會找出答案了。學者研究歷史,研究了每一個層面,包括政治、社會、經濟、性別、疾病、性、食物、服裝,卻很少有人提到這些現象究竟如何影響人類的幸福。這是我們在史識方面的最大空白之處。
雖然很少有人提出對於快樂的長期歷史研究,但幾乎所有學者和大眾心中都多少有些模糊的定見。常有人認為,時間不斷進展,人類的能力也不斷增加。一般來說,我們會運用能力來減輕痛苦、滿足願望,所以我們想必過得比中世紀的祖宗來得快樂,而他們又一定比石器時代的狩獵採集者來得開心。
然而,這種進步論卻可能是有些問題的。正如我們所見,新的傾向、行為和技能不一定會讓生活過得更好。譬如人類在農業革命學會了農耕畜牧,提升了人類整體形塑環境的力量,但是對於許多個人而言,生活反而變得更為艱苦。農民的工作比起狩獵採集者更為繁重,不僅取得的食物種類變少、營養較不均衡,而且染上疾病與受到剝削的可能性都大增。同樣的,歐洲帝國開枝散葉,同時將各種概念、科技和農作物向四方傳播,還打開了商業的新道路,大大提升了人類整體的力量;但是對於數百萬的非洲人、美洲原住民和澳洲原住民來說,這幾乎完全算不上是好事。
歷史一再證實,人類有了權力或能力就可能濫用,所以要說能力愈高就愈幸福,看來實在有些天真。
有些反對進步論的人,就會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場。他們認為人的能力和幸福之間正好是負相關。他們認為權力使人腐化,人類有了愈來愈多的能力之後,創造出來的是冷漠的機器世界,並不符合人類實際的需求。人類的演化,是讓我們的思想和身體符合狩獵採集生活。因此,無論是轉型成農業、或是後來再轉型到工業,都是讓我們墮入不自然的生活方式,讓我們無法完全實現基因中固有的傾向和本能,也就不可能滿足我們最深切的渴望。就算是都市中產階級,過著舒適的生活,生活中卻再也沒有什麼比得上狩獵採集者獵倒長毛象的那種興奮和純粹的快樂。每次出現新發明,只是讓我們與伊甸園又離得更遠。
然而,如果認為每項發明都必然帶來陰影,似乎也流於武斷,這種態度不也像是「深信進步論是真理」一樣嗎?或許,雖然我們與內心那個狩獵採集者愈來愈遙遠,但並不全然是壞事。舉例來說,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現代醫學讓兒童死亡率從33%降到5%以下。對於那些本來無法存活的孩童,或是他們的家人親友來說,難道這不是讓他們的幸福感大增了嗎?
還有一種更微妙的立場,就是把歷史分成前後兩段來討論:在科學革命之前,能力還不一定能帶來幸福,中世紀的農民確實可能過得比狩獵採集者更為悲慘;然而在過去幾世紀間,人類已經學會更聰明的使用權力和能力。現代醫學的勝利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其他同樣震古鑠今的成就,還包括讓暴力事件大幅降低、大型國際戰爭幾乎已經煙消雲散,而且大規模饑荒也幾乎不再發生。
然而,這種說法其實也流於過度簡化。首先,這裡只根據了非常小的時間抽樣,就做出了樂觀的評估。事實上,大多數人類是到1850年才開始享受到現代醫學的果實,而且兒童死亡率急遽下降,也是二十世紀才出現的現象。至於大規模饑荒,直到二十世紀中葉都還是大問題。像是共產中國在1958年至1961年的大躍進,造成大約一千萬人到五千萬人餓死。大型國際戰爭也要到1945年以後,才變得罕見,而且一大原因還是核戰末日這項新威脅。因此,雖然說過去幾十年似乎是人類前所未有的黃金年代,但想知道這究竟代表歷史潮流已經有了根本轉變,或只是曇花一現的美好,目前還言之過早。
我們在評價歷史進程的時候,經常是以二十一世紀西方中產階級的觀點。但我們不該忘記,對於十九世紀在威爾斯的煤礦礦工、中國鴉片菸的癮君子、或是塔斯馬尼亞島的原住民,觀點必然是相當不同的。楚格尼尼(最後一位去世的塔斯馬尼亞島原住民)的重要性,絕對不下於「辛普森家庭」裡的老爸荷馬(出生於1956年的美國典型藍領階級)。
其次,就算是過去半個世紀這短暫的黃金年代,也可能已經播下未來災難的種子。在過去幾十年間,人類用了無數新方法干擾了地球的生態平衡,而且看來可能後患無窮。有大量證據顯示,我們縱情消費而不知節制,正在摧毀人類賴以繁榮的根基。
最後一點,雖然智人確實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或許值得沾沾自喜,但代價就是賠上幾乎所有其他動物的命運。人類現在取得許多物質和資源,讓我們得以免受疾病和饑荒之苦,但我們是犧牲了實驗室裡的猴子、農場裡的乳牛、輸送帶上的雞隻,才換來這些讓我們洋洋得意的成就。在過去兩世紀間,有數百億隻動物遭到現代工業制度的剝削,冷酷程度是整個地球史上前所未有的。就算動物保護團體指出的現象只有十分之一是事實,現代農牧產業也已是史上最大規模、最殘暴的罪行。要評估全球幸福程度的時候,只看上層階級、只看歐洲人、只看男性,都是巨大的錯誤。或許,只看人類也同樣有失公允。
快樂該如何計算?
到目前為止,我們討論快樂的時候,似乎都認為這是由各種實質因素(例如健康、飲食和財富)建構出來的產品。如果某個人更有錢、更健康,就一定也更快樂。但這一切真的這麼理所當然嗎?
幾千年來,早就有哲學家、神職人員和詩人反覆思索快樂的本質。許多人都認為,社會、倫理和心靈因素對幸福感的影響,絕對不下於其他物質條件。有沒有可能,雖然富裕社會裡的人類荷包滿滿,卻因為人際疏離和生活缺乏意義而深感痛苦?有沒有可能,雖然我們的老祖宗生活條件較差,但因為與家人朋友、宗教和大自然關係緊密,所以反而活得比較滿足?
近幾十年來,心理學家和生物學家開始用科學方法,來研究快樂的根源。究竟讓人感到幸福快樂的是金錢、家庭、基因,還是美德?首先,得先定義要測量的是什麼。一般對於快樂普遍接受的定義是「主觀感到幸福」。依照這個觀點,快樂是一種個人內在的感受,可能是因為當下直接的快感,或是對於長期生活方式的滿足。而如果這是內在的感受,又要怎樣才能由外部測量呢?一種做法是直接詢問受試者,問問他們的感受如何。所以心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就請受試者填寫關於幸福感的問卷,再計算相關統計結果。
一般來說,關於主觀幸福感的問卷會列出各種敘述,再請受試者以0到10加以評分,這些敘述例如「我對自己現在的樣子感到滿意」、「我覺得活到現在非常值得」、「我對未來感到樂觀」、「生活是美好的」。接著研究人員就會計算所有分數,算出受試者整體的主觀幸福感程度。
這樣的問卷能夠用來瞭解快樂有哪些客觀因素。舉例來說,我們可以研究比較1,000位年收入10萬美元的人,以及1,000位年收入5萬美元的人。假設前者的平均主觀幸福感有8.7分,而後者平均只有7.3分,研究就能合理推論:財富與主觀幸福感呈正相關。說得白話一點,也就是金錢會帶來快樂。用同樣的方法,我們也可以研究民主國家的人是不是真的比獨裁統治下的人民更幸福,或是結婚的人是否比單身、離婚或喪偶的人來得快樂。
有了這些資料,就能為歷史學家提供比較基礎,讓歷史學家再運用過去關於財富、政治自由度和離婚率的資料來推論。例如,假設民主國家的人比獨裁國家的人快樂、已婚的人比離婚的人快樂,歷史學家就能主張:過去幾十年間,民主化進程讓人類的幸福感提升,但離婚率成長則有反效果。
當然,這種方式也還有改進的空間,但是在更好的方式出現之前,這些發現也值得參考。
知足就能常樂
目前有一項耐人尋味的結論:金錢確實會帶來快樂,但是有一定限度,超過限度之後的效果就不那麼明顯了。所以,對於經濟階層底層的人來說,確實是錢愈多就愈快樂。
如果你是一個月收入兩萬多台幣的清潔工,忽然中了一張兩百萬的統一發票,主觀幸福感可能就會維持好一段時間的高檔狀態。因為這下子,你可以讓孩子吃飽穿暖,不用擔心欠債愈滾愈多。然而,如果你本來就是年薪六百萬台幣的外商高階主管,就算中的是兩、三千萬元的樂透,主觀幸福感也可能只會提高幾個星期而已。根據實證研究指出,這幾乎肯定不會對你的長期幸福感有太大的影響。你或許會買一部炫一點的轎車,搬到大一些的豪宅,喝些更頂級的紅酒,但很快就會覺得這一切都普普通通,沒什麼新鮮感。
另一項有趣的發現是:疾病會短期降低人的幸福感,但除非病情不斷惡化,或是有持續不止的疼痛,否則疾病並不會造成長期的不快。譬如,有人被診斷患有像糖尿病之類的慢性疾病,確實是會鬱悶一陣子,但只要病情沒有惡化,他們就能調適過來,覺得自己和一般人的快樂程度也沒什麼差別。
讓我們假設一下,有一對中產階級的雙胞胎露西和路克,一起參與了一項主觀幸福感的研究。早上做完研究之後,露西開車回家,卻被一輛大巴士撞上,讓她多處骨折,一隻腿永遠行動不便。但就在救援人員把她拉出車子的時候,路克打電話來,興奮大叫他中了千萬美元的樂透大獎。於是,在兩年後,露西會是瘸子,而路克會比現在有錢很多。但是如果心理學家兩年後再去做追蹤研究,就會發現他們兩個人的幸福感,並沒有多大的落差。
目前看來,對快樂與否的影響,家族和地方社群要比金錢和健康來得重要。那些家庭關係緊密、社群互動良好的人,明顯比較快樂。而家庭機能失調、一直無法融入某個社群的人,則明顯比較不快樂。其中,婚姻又是特別重要的一項因素。多項重複研究發現,婚姻美好與感覺快樂,以及婚姻不協調與感覺痛苦,分別都呈現高度相關。而且,不論經濟狀況或是身體健康如何,情況都是如此。
所以就算是貧窮而有病在身的人,如果身邊有愛他的另一半、愛他的家人、願意支持他的社群,他就可能比一個孤單無伴的億萬富翁,感覺更幸福快樂。(當然,前提是這個人不能真的窮到無法生活,而他的疾病也不會不斷惡化、或讓他持續感受疼痛。)
這樣一來,我們就得考慮一種可能性。雖然過去兩世紀間,人類在物質條件上有了大幅改善,但因為家庭崩潰、社會失調,所以兩者的作用很可能互相抵消。如果真是如此,現在的人並不見得比1800年更快樂。甚至是我們現在如此看重的「自由」,也可能是讓我們不那麼快樂的原因:雖然我們可以自己選擇另一半、選擇朋友、選擇鄰居,但他們也可以選擇離開我們。現代社會每個人都擁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能夠決定自己要走哪條路,但也讓我們愈來愈難真正信守承諾,不離不棄。於是,社群和家庭的凝聚力下降、逐漸解體,這個世界便讓我們感到愈來愈孤獨了。
然而,關於快樂最重要的一項發現是:快樂並不在於任何像是財富、健康、甚至社群之類的客觀條件,而在於客觀條件和主觀期望之間是否相符。如果你想要一臺牛車,而你也得到一臺牛車,你就會感到滿足。如果你想要一輛全新的法拉利,而得到的只是一輛二手的飛雅特,你就會感覺很不開心。正因如此,不管是中樂透或是出車禍,對人們的幸福感並不會有長期影響。一切順遂的時候,我們的期望跟著膨脹,於是就算客觀條件其實改善了,我們還是可能不滿意。而在諸事不順的時候,我們的期望也變得保守,於是就算又碰上其他的麻煩,很可能心情也不會更低落。
你可能會覺得,這一切不就是老生常談嗎?就算沒有這群心理學家、什麼問卷都沒有做,我們也早就知道了。就像千年之前,先知、詩人和哲學家早就說過的,最重要的是知足,知足就能常樂,而不是一直想要得到更多。
不過,看到現代研究用了這麼多數字和圖表,最後得出和先賢相同的結論,其實感覺還是滿不錯的!
看你跟誰比!
正因為人類的期望如此關鍵,想要瞭解快樂這件事的歷史,就不能不檢視各種期望的影響。如果快樂只受客觀條件影響(例如財富、健康和社會關係),要談快樂的歷史也就相對容易。但我們知道快樂有賴於主觀的期望之後,歷史學家的任務也就更為艱巨了。
對現代人來說,雖然有各種鎮靜劑和止痛藥任我們使用,但我們愈來愈期望能得到舒適和快感,也愈來愈不能忍受不便和不適。結果就是我們感受到的痛苦程度,可能還高於先人。
這種想法可能很難理解。這裡的問題在於,我們的心理深深埋藏著一個推理的謬誤。在我們試著猜測或想像其他人(可能是現在的人或過去的人)有多快樂的時候,我們總是想要設身處地,想想自己在那個情況下會如何感受。但這麼一來,我們是把自己的期望放到了別人的物質條件上,結果當然就會失準。
現代社會豐饒富裕,我們很習慣每天都要洗澡更衣。但在中世紀,農民好幾個月都不用洗澡,而且也很少會換衣服。對現代人來說,光是想到要這樣生活,就覺得真是臭到要命、髒到骨裡,完全無法接受。只不過,中世紀的農民似乎一點都不介意。這種衣服長時間沒洗沒換的觸感和氣味,他們早就已經習慣。他們並不是因為太窮而無法負擔換洗衣服,而是壓根就沒有這種期望。於是,至少就衣服這一件事來說,他們其實很滿足了。
靜心想想,這其實也不足為奇。畢竟,像是人類的表親黑猩猩也很少洗澡,更從來沒換過衣服。而我們的寵物貓狗也不是天天洗澡更衣,但我們也不會因此就討厭牠們,仍是照樣拍拍牠們、抱抱牠們,甚至還抱起來親親。就算是在富裕的社會裡,小孩通常也不喜歡洗澡,得花上好幾年的教育和管教,才能夠養成這種理論上應該很舒服的習慣。一切都只是期望的問題而已。
如果說快樂要由期望來決定,那麼我們社會的兩大支柱(大眾媒體和廣告業)很有可能正在不知不覺的讓全球愈來愈不開心。假設現在是五千年前,而你是一個住在小村子裡的十八歲年輕人。這時全村大概只有五十個人左右,老的老、小的小,身上不是傷痕皺紋遍布,就是小孩稚氣未脫,很可能就會讓你覺得,自己長得真是好看,因而滿是自信。但如果你是活在今日的青少年,覺得自己長相不怎麼樣的可能性,就要高多了。就算同一個學校的人,外表都輸你一截,你也不會因此就感覺開心。因為你在心裡比較的對象是那些明星、運動員和超級名模,你整天都會在電視、臉書和巨型廣告看板上看到他們。
有沒有可能,第三世界國家之所以會對生活不滿,不只是因為貧窮、疾病、政治腐敗和壓迫,也是因為他們看到了第一世界國家的生活標準?平均來說,埃及人在前總統穆巴拉克的統治下,死於飢餓、瘟疫或暴力的可能性,遠低於在古代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或埃及豔后克麗奧佩特拉統治的時期。對大多數埃及人而言,這根本是有史以來物質條件最好的時刻。在2011年,理論上他們應該要在大街上跳舞慶祝,感謝阿拉賜給他們這一切的財富才對。然而,他們反而是滿懷憤怒,起身推翻了穆巴拉克。原因就在於,他們比較的對象不是古代的法老王,而是同時代的美國總統歐巴馬。
這麼一來,就算是長生不老,也可能會導致不滿。假設科學找出了能夠醫治所有疾疾的萬靈丹,加上有效抗老療程和再生治療,能讓人永保青春。那麼,最可能發生的事,就是整個世界感到空前的憤怒和焦慮。
那些無力負擔這些醫學奇蹟的人(也就是絕大多數人),一定會憤怒到無以復加。縱觀歷史,窮人和受壓迫者之所以還能自我安慰,就是因為死亡是唯一完全公平的事。不論再富有、權勢再大,也難逃一死。光是想到自己得死、但有錢人居然能長生不老,就會讓窮人怒火中燒,不可扼抑。
而且,就算是那極少數負擔得起的有錢人,也不是從此無憂無慮。他們有太多需要擔心的事了。雖然新療法可以延長壽命、常保青春,但還是沒辦法讓屍體起死回生。也就是說,他們絕對更需要避免發生意外──出門不能被酒醉駕駛撞到、不能被恐怖份子炸成碎片!人在家中坐,也要擔心飛機從天上掉下來!像這些理論上可以達到長生的人,很有可能一丁點風險也不願意承擔,時時刻刻活得戒慎恐懼;而且一旦真的失去愛人、子女或密友,他們感受到的痛苦更會高到難以想像。
快樂有天生的「空調系統」
研究快樂的時候,社會科學家做的是發問卷調查主觀幸福感,再將結果與財富和政治自由等社經因素結合。至於生物學家的做法雖然也用一樣的問卷,但結合的是生化和遺傳因素。他們得出的研究結果令人大感震驚。
生物學家認為,我們的心理和情感世界,其實是由經過數百萬年演化的生化機制所形塑。所有的心理狀態(包括主觀幸福感)並不是由外在因素(例如工資、社會關係或政治權利)來決定,而是由神經、神經元、突觸和各種生化物質(例如血清素、多巴胺和催產素)構成的複雜系統而定。
所以,不管是中了樂透、買了房子、升官發財,或是找到了真正的愛情,都不是真正讓我們快樂的原因。我們能夠快樂的唯一原因,就是身體內發出快感的感官感受。所以,那些剛中了樂透、剛找到真愛的人,之所以會快樂得跳了起來,並不是因為真的對金錢或情人有所反應,而是因為血液中開始流過各種激素,腦中也開始閃現著小小的電流。
但很遺憾,雖然我們總是想在人間創造出快樂的天堂,可是人體的內部生化系統似乎就是對快樂多所限制,只會維持在恆定的水準。快樂這件事並不是天擇的揀選標的,因為,如果你是快樂的獨身隱士,你無法把快樂基因傳遞給後代;相對的,兩位整天焦慮的爸媽,卻能把不快樂的基因傳遞下去。快樂或痛苦在演化過程裡的角色,就只是配角、不是主角,只在於鼓勵或妨礙生存與繁衍。所以不難想像,人類演化的結果,就是不會太快樂、也不會太痛苦。我們會短暫感受到快感,但不會永遠持續。遲早快感會消退,讓我們再次能夠感受到痛苦。
舉例來說,演化就把快感當成獎賞,鼓勵男性和女性發生性行為,將自己的基因傳下去。如果性交沒有高潮,大概很多男性就不會那麼熱中。但同時,演化也確保高潮要來得快、去得也快。如果性高潮永續不退,可以想像男性會非常開心,但那會連覓食的動力都沒了,最後死於飢餓,而且也不會有興趣再去找下一位能夠繁衍後代的女性。
有學者認為,人類的生化機制就像是恆溫空調系統,不管是嚴寒或酷暑,都要想辦法保持恆定。雖然遇到某些事件會讓溫度暫時有波動,但最後總是會調控回到原來設定的溫度。
有些空調系統會設定在攝氏25度,有的會設定在攝氏20度。至於人類的快樂空調系統,也是人人的設定皆有不同。如果說快樂的程度是由1分到10分,有些人的生化機制天生開朗,就會允許自己的情緒在6分到10分之間來回,大約穩定在8分附近。像這樣的人,就算住在一座冷漠的大城市,碰上金融市場崩潰而喪失了所有積蓄,還被診斷患有糖尿病,還是能相當樂觀的活下去。
也有些人就是倒楣有著天生陰鬱的生化機制,情緒在3分到7分之間來回,大約穩定在5分附近。像這樣的人,就算得到了密切社群的支持,中了幾千萬的樂透,健康得可以當奧運選手,還是會相當憂鬱悲觀。事實上,如果是這位天生憂鬱的朋友,就算她早上中了五千萬美元的樂透,中午又同時找到了治癒愛滋病和癌症的妙方,下午幫忙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達成永久和平協議,晚上又終於與失散多年的孩子團聚,她感受到的快樂程度仍然頂多就是7分而已。不論如何,她的大腦就是沒辦法讓她樂不可支。
想想你的家人朋友。是不是有些人,不論發生多糟的事,還是能保持愉快?是不是也有些人,不管得到了多大的恩賜,還是一直鬱鬱寡歡?我們常認為,只要換個工作、找到老公、買了新車、寫完小說,或是付完房貸,做完諸如此類的事,就能讓自己快樂得不得了。然而,等我們真正達到這些期望的時候,卻沒有感覺真的比較快樂。畢竟,買車和寫小說並不會改變我們的生化機制。雖然可以有短暫的刺激,但很快就會回到原點。
歷史何價?
不過,先前的心理學及社會學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結論,例如平均而言,已婚的人比單身更快樂。生物學對此要怎麼解釋?
首先,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研究只證明了相關性(correlation),但是真正的因果方向,有可能和研究人員的推論正好相反。確實,已婚的人比單身和離婚的人更快樂,但這不一定代表是婚姻帶來了快樂,也有可能是快樂帶來了婚姻。或者更準確來說,是血清素、多巴胺和催產素帶來並維繫了婚姻。那些生化機制天生開朗的人,一般來說都會是快樂和滿足的人。而這樣的人會是比較理想的另一半,所以他們結婚的機率也比較高。而且,和快樂滿足的另一半相處,絕對比和鬱悶不滿的另一半相處,來得容易,所以他們也比較不容易離婚。確實,已婚的人平均來說比單身更快樂,但如果是生化機制天生憂鬱的人,就算真的找到好對象,也不一定就會比較快樂。
話說回來,大多數生物學家也不是完全只看生化學這一套。雖然他們主張快樂「主要」是取決於生化機制,但也同意心理學和社會學因素同樣有影響力。畢竟,我們這套快樂空調系統雖然有上下限,但在這個範圍裡還是可以活動活動的。雖然要超出邊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結婚和離婚卻能影響心情在這個範圍內的偏移。那些平均只有5分的人,永遠不會忽然在大街上開心的跳起舞來;但如果找到樂觀的好對象,就能讓她三不五時感受到7分的愉悅,而更能避開3分的沮喪。
如果我們接受了生物學對於快樂的理論,歷史這個學門的重要性就大減了;畢竟,大多數的歷史事件並不會對我們的生化機制有什麼影響。雖然歷史可以改變那些影響血清素分泌的外界刺激,然而無法改變最後的濃度,所以也就是無法讓人變得更快樂。
讓我們用古代中國農夫和現代香港企業家為例。假設我們這位古代農夫住在沒有暖氣的小土屋裡,旁邊就是豬圈;企業家住在擁有各種最新科技的豪宅,窗口就能俯瞰南海的浩瀚海景。直覺上,我們會覺得企業家想必比農夫更快樂。然而,快樂是在腦子裡決定的,而大腦根本不管小土屋或大豪宅、豬圈或南海,只管血清素的濃度。所以,農夫蓋完了他的土屋之後,大腦神經元分泌血清素,讓濃度到達X。而在現代,企業家還完最後一筆豪宅房貸之後,大腦神經元也分泌出大量血清素,並且讓濃度差不多也到達X。對於大腦來說,它完全不知道豪宅要比土屋舒適太多,它只知道現在的血清素濃度是X。所以,這位企業家快樂的程度,並不會比那位足以當他高高高高高祖父的農夫來得高。
這點不僅對個人生活如此,就算是眾人之事也不例外。我們以秦朝統一天下為例。秦朝統一天下之後,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文化、社會和經濟體制。但這一切都並未改變中國人的生化機制。因此,雖然天下大一統讓政治、社會、意識型態和經濟,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動盪,但對於中國人的快樂並沒有多大影響。那些生化機制天生開朗的人,不管是活在戰國時代,或是秦漢時代,都會一樣快樂。但那些生化機制天生憂鬱的人,過去總是在抱怨戰國諸侯,現在也只是轉而抱怨秦朝天子,並不會有什麼改變。
但這麼說來,究竟把中國統一有什麼好處?如果沒辦法讓人更快樂,又何必要有這麼多的混亂、恐懼、流血和戰爭?像是生物學家就絕對不會攻向巴士底獄。就算有人認為這些政治革命或社會改革會讓他們開心,到頭來總是一次又一次被生化機制玩弄於股掌。
說到這裡,我們終於發現,歷史上似乎僅有一項發展真正有重大意義。那就是:現在我們終於意識到,快樂的關鍵就在於生化系統,因此我們就不用再浪費時間處理政治和社會改革、叛亂和意識型態,而是開始全力研究唯一能真正讓我們快樂的方法:操縱人類的生化機制。如果我們投入幾十億美元來瞭解我們的腦部化學,並推出適當的療法,我們就能在無須發動任何革命的情況下,讓人民過得遠比從前的人更快樂。舉例來說,百憂解(Prozac)之所以讓人不再沮喪,靠的不是對任何體制的改革,而只是提高血清素的濃度而已。
講到這套生物學理論,最能抓到精髓的,就是著名的「新世紀」(New Age)運動的口號:「快樂來自內心」。金錢、社會地位、整形手術、豪宅、握有大權的職位,這些都不會給你帶來長久的快樂。想要有長期的快樂,只能靠血清素、多巴胺和催產素。112
1932年,正值經濟大蕭條的時代,赫胥黎出版了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書中將「快樂」當成最重要的價值,而且政治的基礎不是警方、不是選舉,而是精神病的藥物。每天,所有人都要服用一種合成藥物「蘇麻」(soma),這能讓他們感到快樂,而且不影響生產力和工作。在美麗的新世界裡,「世界國」統治全球,所有子民不論生活環境條件如何,都對這感到無比滿足。也因此,政府完全不用擔心會爆發戰爭、革命、罷工或示威遊行等等威脅。這下子,赫胥黎想像中的未來,可能還比歐威爾的《1984》更為棘手。赫胥黎的世界似乎對大多數讀者來說都非常可怕,但又很難解釋原因。所有的人永遠都是很快樂的;這到底能有什麼問題?
生命的意義
赫胥黎筆下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新世界,背後有一項假設:「快樂等於快感」。在他看來,快樂就是身體感覺到快感。因為我們的生化機制限制了這些快感的程度和時間長短,唯一能夠讓人長時間、高強度感受到快樂的方法,就是操縱這個生化機制。
然而,這種對於快樂的定義,還是受到一些學者質疑。在一項著名的研究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康納曼(Daniel Kahneman)請受試者描述自己一般上班日的全天行程,再分段一一評估他們究竟有多喜歡或討厭這些時刻。他發現,大多數人對生活的看法其實會有所矛盾。讓我們以養小孩為例。康納曼發現,如果真要計算哪些時刻令人開心、哪些時候叫人無聊,就單純的數字來說,養小孩可說是非常不愉快的事。很多時候,養小孩就是要換尿布、洗奶瓶、處理他們的哭鬧和脾氣,這些都算是沒人想做的苦差事。然而,大多數家長都說孩子是他們快樂的主要來源。難道這些人都是腦子有問題嗎?
當然,這是一種可能。但還有另一種可能:調查結果讓我們知道,快樂不只是「愉快的時刻多於痛苦的時刻」這麼簡單而已。相反的,快樂要看的是某人生命的整體;生命整體有意義、有價值,就能得到快樂。快樂還有重要的認知和道德成分。價值觀不同,想法也就可能完全不同,例如有人覺得養小孩的人就像是悲慘的奴隸,得伺候一個獨裁的小霸王,但也有人覺得自己真是滿懷著愛,正在培育一個新的生命。113
正如尼采所言,只要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幾乎什麼都能忍受。生活有意義,就算在困境中也能甘之如飴;生活無意義,就算在順境中也度日如年。
不管任何文化、任何時代的人,身體感受快感和痛苦的機制都一樣,然而他們對生活經驗所賦予的意義,卻可能大不相同。如果真是如此,快樂的歷史很可能遠比生物學家想像的,要來得動盪不安。這個結論並不一定是站在現代這邊。如果我們將生活切成以一分鐘為單位,來評估當時是否幸福快樂,中世紀的人肯定看來相當悲慘。然而,如果他們相信死後可以得到永恆的祝福,很有可能就會認為生活真是充滿了價值和意義;相對的,現代世俗子民如果不信這一套,就會覺得人到最後就只有死亡,遲早會被遺忘、沒了任何意義。如果用主觀幸福感問卷問道:「你對生活整體是否滿意?」中世紀的人很可能得分會相當高。
所以,我們的中世紀祖先會感到快樂,就只是因為他們有著對來世的集體錯覺,因而感覺生命充滿意義嗎?沒錯!只要沒人戳得破這種幻想,又為什麼要不開心呢?從我們所知的純粹科學的角度來看,人類的生命本來就完全沒有意義。人類只是在沒有特定目標的演化過程下,盲目產生的結果。人類的行動沒有什麼神聖的宇宙宏圖為根據,而且如果整個地球明天早上就爆炸消失,整個宇宙很可能還是一樣,不受影響的繼續運行下去。
目前為止,我們還是不能排除掉人類主觀的因素。但這也就是說,我們對生活所賦予的任何意義,其實都只是錯覺。不管是中世紀那種超脫凡世的生活意義,或是現代人文主義、民族主義和資本主義,本質上都完全相同,沒有高下之別。譬如可能有科學家覺得自己增加了人類的知識,所以他的生命有意義;有士兵覺得他保衛自己的國家,所以他的生命有意義。不論是創業者想要開新公司,或是中世紀的人想要讀經、參與聖戰、興建新廟,他們從中感受到的意義,都只是錯覺與幻想。
這麼說來,所謂的快樂,很可能只是讓「個人對意義的錯覺」和「現行的集體錯覺」達成同步而已。只要我自己的想法能和身邊的人的想法達成一致,我就能說服自己,覺得自己的生命有意義,而且也能從這個信念中得到快樂。
這個結論聽起來似乎很叫人難過。難道快樂真的就只是一種自我欺騙嗎?
認識你自己
如果快樂是在於感受快感;想要更快樂,就得操縱我們的生化系統。如果快樂是在於覺得生命有意義;想要更快樂,就得騙自己騙得更徹底。還有沒有第三種可能呢?
以上兩種論點都有一個共同假設:快樂是一種主觀感受(不管是感官的快感或是生命有意義),而想要判斷快不快樂,靠的就是直接問他們的感受。很多人可能覺得這很合邏輯,但這正是現代自由主義當道的結果。自由主義將「個人主觀感受」奉若圭臬,認為這些感受正是權威最根本的源頭。無論是好壞、美醜、應不應為,都是由每個人的感受來確定。
自由主義政治的基本想法,是認為選民個人最知道好壞,我們沒有必要由政府老大哥來告訴人民何者為善、何者為惡。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想法,是客戶永遠都是對的。自由主義藝術的基本想法,是各花入各眼,看的人覺得美就是美。崇尚自由主義的學校和大學,叫學生要為自己多想想。廣告叫我們「做就對了!」就連動作片、舞臺劇、八點檔連續劇、小說和流行歌曲,都不斷在向大眾洗腦:「忠於自我」、「傾聽你自己」、「順從你的渴望」。對於這種觀點,盧梭的說法稱得上是經典:「我覺得好的,就是好的。我覺得壞的,就是壞的。」
如果我們從小到大就不斷被灌輸這些口號,很可能就會相信快樂是一種主觀的感受,而是否快樂,當然是每個人自己最清楚。然而,這不過就是自由主義獨有的一個觀點而已。歷史上大多數的宗教和意識型態認為,關於善、關於美、關於何事應為,都有客觀的標準。在這些宗教和意識型態看來,一般人自己的感覺和偏好可能並不可信。從老子到蘇格拉底,哲學家不斷告誡人們:「認識你自己!」但言下之意也就是:一般人並不知道自己真實的自我,也因此很可能忽略了真正的快樂。佛洛伊德很可能也是這麼想的。[1]
基督教神學家應該也會同意這種說法。不管是聖保羅或是聖奧古斯丁,都心知肚明:如果讓人自己選擇的話,大多數人寧願把時間用來做愛,而不是向上帝祈禱。這種選擇絕對是順從你的渴望,但這意思是想要快樂就該去做愛嗎?聖保羅和聖奧古斯丁可絕對不會這麼說。對他們而言,這只證明了人類本來就有罪,容易受到撒旦的誘惑。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大多數人類都多多少少沉溺在類似海洛因成癮的情境。假設有個心理學家,想調查吸毒者的快樂指數。經過調查之後,他發現這些吸毒者全部有志一同,所有人都說吸毒的時候最快樂了。請問這位心理學家是不是該發表一篇論文,告訴大家想快樂就該去吸毒?
除了基督教以外,還有一些生物學者也認為,主觀感受不該是最大重點。至少在講到主觀感受的價值時,甚至達爾文和英國演化生物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都有部分觀點,與聖保羅和聖奧古斯丁相同。根據道金斯在名著《自私的基因》提出的論點,正如同其他動物,人類在天擇的影響下,就算對個人不利,他們也會選擇要讓基因繼續流傳下去。大多數男性一生勞苦、終日煩憂,因為競爭激烈而不斷爭鬥,硬是沒辦法享受一下平靜的幸福;但這是由於DNA操縱著他們,要他們為基因自私的目的做牛做馬。DNA就像撒旦,用一些稍縱即逝的快樂做為引誘,令人為之臣服。
佛法無我
大多數宗教和哲學看待快樂的方式,都與自由主義非常不同。最看重快樂這個問題的,就是佛教。兩千五百多年來,佛教有系統的研究了快樂的本質和成因;正因如此,最近有愈來愈多科學團體開始研究佛教哲學和冥想。佛教認為,快樂既不是主觀感受到愉悅,也不是主觀覺得生命有意義,反而是在於放下貪求主觀感受這件事。
根據佛教的觀點,大多數人太看重自己的感受,以為快感就是快樂,不愉悅的感受就是受苦。於是,人類就渴望能有快感,並希望避免不愉悅的感受。然而,這是大大的誤解。事實是,人類的主觀感受沒有任何實質或意義。主觀感受就只是一種電光石火的波動,每個瞬間都在改變,就像海浪一樣。不論你感受到的是快感或不快、覺得生命是否具有意義,這都只是剎那生滅的波動而已。
如果我們太看重這些內部的波動,就會變得太過執迷,心靈也就焦躁不安,感到不滿。每次碰上不快,就感覺受苦;就算已經得到快感,因為我們還希望快感能夠增強,或是害怕快感將會減弱,所以心裡還是不能感到滿足。貪求這些主觀感受,十分耗費心神,而且終是徒勞,只是讓我們受制於貪求本身。因此,苦的根源既不在於感到悲傷或疼痛,也不在於感覺一切沒有意義。苦真正的根源就在貪求主觀感受這件事,不管貪求的是什麼,都會讓人陷入持續的緊張、困惑和不滿之中。
人想要離苦得樂,就須瞭解自己所有的主觀感受都只是剎那生滅的波動,而且別再貪求某種感受。如此一來,雖然感受疼痛,但不再感到悲慘,雖然愉悅,但不再干擾心靈的平靜。於是,心靈變得一片澄明、自在。這樣產生的心靈平靜力量強大,是那些窮極一生瘋狂追求愉悅心情的人,完全難以想像的。這就像是有人已經在海灘上站了數十年,總是想抓住「好的海浪」,讓這些海浪永遠留下來,同時又想躲開某些「壞的海浪」,希望這些海浪永遠別靠近。就這樣一天又一天,這個人站在海灘上徒勞無功,把自己累得幾近發瘋。最後終於氣力用盡,癱坐在海灘上,讓海浪就這樣自由來去。忽然發現,這樣多麼平靜啊!
這種想法對於現代自由主義的文化來說,完全格格不入,所以等到西方的新世紀運動碰上佛教教義,就想用自由主義的方式加以解釋,結果意思卻是完全相反。新世紀教派常常主張:「快樂不在於外在條件,而只在於我們內心的感受。我們應該別再追求像是財富、地位之類的外在成就,而是要多接觸自己內心的情感。」或者說得簡單一點,就是「快樂來自內心」。這與生物學家的說法不謀而合,但與佛教的說法幾乎是背道而馳。
佛教與現代生物學和新世紀運動的相同點,在於都認定快樂與外在條件無關。但佛教更重要、也更深刻的見解在於:真正的快樂也與我們的主觀感受無關。我們如果愈強調主觀感受,反而就愈感到苦。佛教給我們的建議是,除了別再追求外在成就之外,同時也別再追求那些自我感覺良好的心裡感受了。
人類是否瞭解自己?
總結來說,我們現在會使用主觀幸福感問卷,希望找出來我們主觀認定什麼時候有幸福感,而且認為找到特定的情緒狀態就是找到了快樂。但相反的,許多傳統哲學和宗教(如佛教)則認為,快樂的關鍵在於追求真我、真正瞭解自己。大多數人都以為自己的感覺、想法、好惡就組成了自己,但這是一大錯誤。他們感覺憤怒的時候,心裡想「我很生氣,這是我的憤怒。」於是這一輩子做的,都是想要避開某些感受,貪求另外某些感受。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發現,苦真正的來源不在於感受本身,而是對感受的不斷貪求。
如果真是如此,我們過去對於快樂這件事的歷史認知,就有可能都是錯的。或許,期望是否得到滿足、感受是否快活,都不是重點,真正重要的問題在於人類是否瞭解自己。我們有什麼證據,證明今天的人比起遠古的採集者或中世紀的農民,更加瞭解自己呢?
學者一直到幾年前,才開始研究快樂這件事的歷史,而且現在還停留在初始階段,正在做出初步的假設、尋找適當的研究方法。這場討論才剛剛起步,要得出確切的結論,為時過早。最重要的,是要瞭解各種不同的研究方法,並且提出正確的問題。
大多數的歷史書籍強調的都是偉大的思想家、英勇的戰士、慈愛的聖人,以及創造力豐沛的藝術家。這些書籍對於社會結構的建立和瓦解、帝國的興衰、科技的發明和傳播,可說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對於這一切究竟怎麼為個人帶來快樂或造成痛苦,卻是隻字未提。這是我們在史識方面的最大空白之處。而且,現在該是開始填補空白的時候了。
心理學要研究主觀幸福感,靠的是受試者要能夠正確判斷自己的快樂程度;但矛盾的是,之所以會出現心理學,正是因為人類並不真正瞭解自己,有時候需要藉由專業人士的幫助,以避免做出自我毀滅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