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寫信給你
你十五歲時,坐在維也納的咖啡館談論著巴黎最新的文學著作,你和一樣出生於資本家庭的朋友是輕易地取得別人望塵莫及的一切。年輕時就懂的欣賞文學藝術、喝著咖啡,你們精通多國語言,早已周遊列國。
你曾說:「出於絕望,我正在寫我一生的歷史。」
戰爭來時,摧毀的是一個民族、一個政權、一種理念或宗教,戰火是無情的,也很諷刺的能說是公平的,就像卡繆在《瘟疫》中說瘟疫的出現將一視同仁的蔓延,此時不再有階級之分,不因為誰富裕或掌握較高的權力而得以倖免。
但說到此時,我想起你們民族的逾越節典故,那是你們得恩典卻是別人受害的日子。正月十四,將羔羊血塗在門框、門楣上,使滅命的看到血則會跳過該戶,不擊殺該家的長子,這是分辨以色列人與他族人之間的記號。
羔羊的血拯救了你們,實際上卻是他家的長子以血還債——一個他們也不知道的債。
不過說了「你們」卻是一種偏激的言論。
你們大多也不要戰爭,甚至不愛自己的血統,你也說過,有兩三個祖國的人,比沒有祖國的人更悲慘,你因為對世界絕望而於二戰期間結束自己的生命。再撐下去會怎樣?這個民族早已沾滿了鮮血,再撐下去只會更絕望。
我其實討厭人們提到像你這樣中產出身而經歷過戰爭的藝術家時,總帶有的那種惋惜。不,可惜的不是你曾經享受過「幸福」的日子又親歷無情的戰火,那些一輩子與幸福無緣、權力的世界與他們毫無瓜葛、搞不清楚自己國家所處的地位或是政府信奉的政治信仰⋯⋯等等的無名之輩才是最無辜可憐的。而且若他們犧牲,鮮少會被人提起。
祖先不讀的那卷書上說:「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總想到上週五看到一位婦女在東正教會祈禱的照片,她如何相信這可能是預表,被同樣信仰的人攻打,又想起就是這個教會在一百年前迫害了你們/我們⋯⋯但任何教會若在此時表達這是「宿命論」,也只是徒增痛苦並且是二度傷害。
這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第五天,平民的傷亡人數已超過兩百人,其中包含兒童。星期一早上基輔和哈爾科夫都再次聽到爆炸聲。 與此同時,該國北部城市切爾尼戈夫(Chernihiv)也拉響了空襲警報。
只能將想法轉換為寫給「你」的信,因為普丁打著去軍事化和納粹化的旗號,就有人扯到集中營,(然後我們就應該閉嘴?)但這根本不是同一個意思,烏克蘭有自己的主權,也會有自己的民族意識,那和過去與俄羅斯人分享歷史的事實是不相干的。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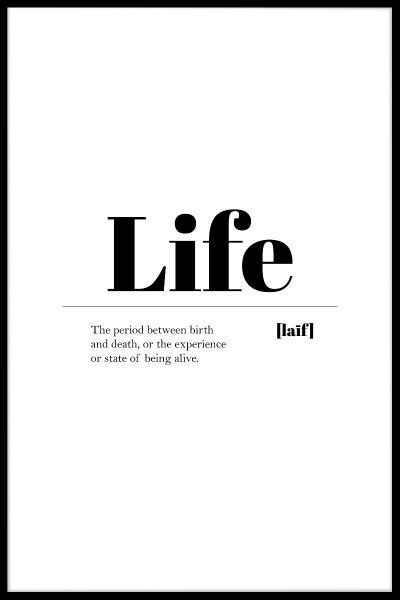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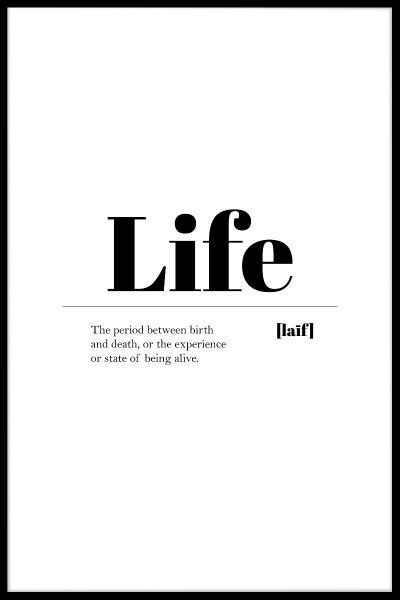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