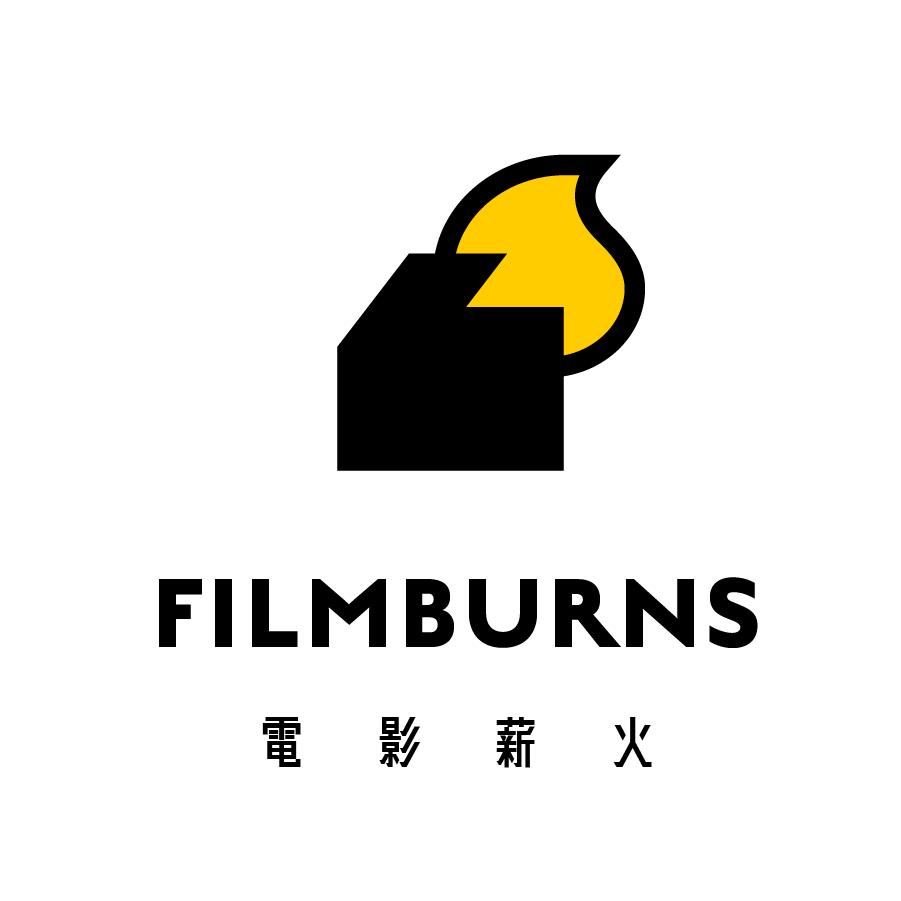《沙丘瀚戰:第二章》:奇觀和叫喊
文|中田

電影是一門需要龐大資金的生意,製作成本愈大,持份者愈多,它就愈不可能成為完全純粹的個人創作,除非是自資製作,或者是 Martin Scorsese、Quentin Tarantino 這類聲名顯赫的大導演。像籍貫加拿大的 Denis Villeneuve 才剛闖進荷里活不久(《銀翼殺手2049》 (Blade Runner 2049) 是他首部大製作,惜票房失敗),要將無數前人改編失敗的科幻巨著《沙丘》(Dune)拍成電影,面對耗資過億的製作,可以猜想背後每步必然是營營役役,構想一份可以實行拍攝的鏡頭清單(前車可鑒,曾經嘗試改編的智利鬼才 Alejandro Jodorowsky 就因滿腦無法實踐的實驗性狂想,令計劃終被腰斬)。這種經過高度計算的創作,使《沙丘瀚戰:第二章》每個落點也很準確,片段式的文戲武戲扼要地呈現「太空史詩」(space opera)壯闊的世界觀,滿足書迷、魔幻片影迷的各種期望——單看主角騎乘沙蟲的一幕,場面夠壯觀了吧。然而,在看完氣勢磅礴的「王子復仇記」以後,要問的是:除了達至官能上的滿足,《沙丘瀚戰:第二章》還餘怎樣的價值?大製作的電影本質終究是甚麼?

美國作家 Frank Herbert 在六十年代創作小說《沙丘》,源自他曾研究美國農業部抗衡沙漠流動的計畫,此後 Herbert 對沙漠生態產生強烈興趣。因此《沙丘》不獨是作家想像的虛構未來,當中包含著歷史考據。譬如英國軍官 T. E. Lawrence 在一戰期間協助阿拉伯人起義反抗奧圖曼帝國的史實,Herbert 便取其骨幹代入出身貴族的 Paul 加入沙漠部族 Fremen,以救世主的姿態領軍推翻帝國。而 T. E. Lawrence 一度在阿拉伯發跡的故事,被英國導演 David Lean 拍成留名影史的史詩作品《沙漠梟雄》(Lawrence of Arabia)。回過頭來,《沙丘瀚戰:第二章》拍的就是原著小說(有沙蟲有幻術)的魔幻世界以及《沙漠梟雄》的旅程。

Villeneuve 早前在訪問中說自己討厭對白,認為對白只適用於電視劇和劇場。事實上,David Lean 也曾講過類似的話:「我認為人們記住的往往是影像,而不是對白。」(I think people remember pictures not dialogue.)不過有別於 Lean 強調構圖和取景的場面調度,Villeneuve 多是透過聲音忽爾沉靜,製造影像的懸疑感,強調脅迫主角存在的外力的強大——《心敵》(Enemy)投射心理的巨型蜘蛛便是他的小試牛刀。《沙丘瀚戰:第二章》的動作段落全是建基於角色之間的強弱懸殊與身型的對比,營造高壓氣氛和決鬥 / 征服時的狠勁,其中生性暴戾的反派 Feyd-Rautha 在只有黑白色彩的星球打了一場不公平的對決,攝影師 Greig Fraser 特意選擇在現場運用紅外線的攝影技術,令黑和白份外硬朗銳利,這種現場作法避免了後製時奉命要修改的風險,更進一步證明 Villeneuve 經營與別不同的視覺畫面的決心。

儘管導演 Villeneuve 與攝影師 Fraser 努力擴闊電影的視覺元素,還未能將《沙丘瀚戰:第二章》提升至史詩電影的高度,原因是電影對「救世主」Paul 一路上的成長描繪與發展薄弱。Paul 成功俘虜人心,自我愈益膨脹,大幅度的性格轉變竟是以他承受了母親的幻術施計作為解釋,而劇本只賦予 Paul 的母親一個存在目的,就是借兒子奪得權力。Paul 以外的角色全都是襯托、成就救世預言的圖騰。唯一有意抗衡預言的是女主角 Chani,但卻只是為配合性別平等而作出的設計(原著 Chani 是一個無條件支持 Paul 行動的情人),沒有對劇情產生任何影響,彼此關係變化欠缺細節。電影間中賦予女性角色有凌駕男人的權力——Léa Seydoux 飾演的 Lady Margot 以崇高姿態在觀眾席凝望 Feyd-Rautha 於戰場上的殺戮(整段戲幾乎是以 female gaze 的角度出發)——提醒觀眾黃雀在後,唯獨這些只是沒有結果的鋪陳,埋沒了理應集中敘述的皇室復仇故事。
最近在看石黑一雄的小說《被埋葬的記憶》,三百多頁,是一個有龍有魔法有騎士的世界。故事跟《沙丘》一樣有歷險的元素,因長期生活在迷霧裡而失去記憶的兩老夫婦,長途跋涉前往兒子所在,途中捲入了騎士屠龍的任務。安坐 Villeneuve 塑造的沙丘殿堂裡,穿梭光影間,我想起了這本書。到底自己為何那刻想跟那對老夫婦走一趟,而不是專心追隨 Paul 的征途?那不過是個只有三百幾頁的故事世界。書本聚焦的因記憶所致的愁緒,反省騎士精神,創作關乎心靈、精神層面。相比起來,《沙丘瀚戰:第二章》畫面好看,卻始終無法觸及觀眾內心,因為它的世界裡沒有人,只剩動作奇觀和叫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