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2 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歐逸文
野兽按:2015年这本《野心时代》刚出版不久,就购读了。也曾经在北京见到过几次欧逸文,他当年租住我居住的小区,见过他到小区邮箱取订阅的《纽约书评》。五年过去了,觉得有必要再重读一遍。当年影响深刻的是第一章,关于林毅夫如何游过海峡投奔中国大陆的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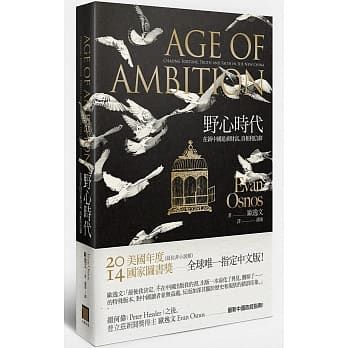
2014年美國國家圖書獎 非虛構類大獎
美國人最新中國指南,連歐巴馬都要買來看。
作者請讀者買台灣版,他申明放棄簡體中文版,因為不願被中國閹割審查。
如果中國是另外一個宇宙,那麼它又為何如此?《紐約客》記者筆下的中國,為什麼和台灣人所見的中國不一樣?
《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經濟學人》、《商業周刊》……西方各大主流媒體及政治觀察家一致贊賞
新浪、搜狐、南都周刊、外灘畫報、新周刊、人物周刊……中國主流媒體也紛紛評論連線採訪
亞洲週刊、蘋果日報、中國時報、明報、風傳媒……港台媒體也討論歐逸文旋風
1996年,本書作者第一次到北京,這座城市讓他大跌眼鏡,他看到的中國首都,地理和風貌上更肖似蒙古風吹草原而非霓虹燈閃爍的香港。等他2013年離開中國後,新書《野心時代》則變成美國政治人物和普通人理解中國社會和政治的最新指南。
作者認定,在廿一世紀頭幾年,中國由兩個宇宙組成:既是全球最新超強,也是世上最大的集權國家。「有好些日子,我早上跟新大亨在一起,晚上則與軟禁在家的異議人士為伍。你很容易把他們看待成代表新中國、舊中國;涇渭分明的政經領域,只是到最後我歸結認為,他們是同體合一的。」
本書敘述兩股力量的碰撞:個人的野心志向與集權主義。因為政治及貧窮,四十年前的中國人事實上沒有取得財富、真相或信仰的管道,他們沒有機會經商;沒有力量挑戰政治宣傳及言論刪檢;沒有法子在共產黨外找到道德靈感。但在一個世代內,這三種東西他們都有管道取得,而且要得更多。只是共產黨依舊孜孜不倦於控制,他們想規定的東西,不止於誰領導國家,甚至列車服務員微笑時能露幾顆牙齒都想管,但這與外界生活的變化已相牴觸。「我在中國住愈久,愈感覺到黨釋放出世界史上最偉大的人類潛能擴張,而且可能孕育出對其存亡最強大的威脅。」
這本書奠基在作者長達八年的訪談,行文則側重在不同領域打拚的男男女女,他們奮力想從某一領域推開一條路到另外的領域,不僅限於經濟,也涉足政治、思想及性靈。這些人很多是你我耳熟能詳的中國公眾人物,如異議藝術家艾未未、偶像作家兼賽車手韓寒、戴著鐐銬跳舞的媒體人胡舒立、逃跑到美國北京大使館的盲人律師陳光誠、從台灣泅水潛逃中國的林毅夫,還有很多是我們不甚熟悉,但在中國則知名度甚高的人物,如瘋狂英語的創辦人李陽、中國最大相親網站的創辦人龔海燕、用近乎虔誠的方式復興愛國主義的「憤青」唐杰、以及網路身份是詩人、真實身份是從農村移居北京的清潔工。歐逸文栩栩如生地描繪這些人,並將他們置放於轟動全球媒體版面的各種公共事件的背景下、放置於中國的政治和歷史的邏輯框架中,檢視他們何以代表了這個野心時代,及他們賦予給中國的意義。這些人物從表面看幾乎並無相似之處,但他們共同呈現出野心勃勃的新中國關鍵詞: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政治獨裁的高壓無處不在;人們追逐成功,與此同時也備感空虛,轉投信仰以尋求寧靜;自我意識的覺醒澆灌了個人主義,但也同樣滋生割裂感與不安。
唱衰中國和押寶中國,是目前外部世界看待中國的兩種主要視角,而作者不會如此簡化。他指出,由遠處看,大家經常描述中國已經無可逆轉地邁向康莊大道,但是在中國內部,人們則更小心謹慎。中國的一切,都是靠鐵、淚水及火而取得的,而中國人比誰都更曉得一切無常——誠如費滋傑羅形容:「真實的不真實,宛如一個許諾,即這個世界的基石乃是安置在精靈的翅膀上。」在北京的最後幾個月,那種脆弱感更深地纏繞著作者。
中國太複雜多樣,一直很難被定義,也永遠沒有終極答案。如今的中國,空氣中瀰漫著一種蠢蠢欲動的情緒,它驅動中國成為最新興的超級大國,也使得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威權政府感到擔憂。官方用「中國夢」來回應這種情緒,將其描述為一種復興強國的慾望;本書作者敏銳精準地捕捉到這種情緒,但他稱之為中國的「野心時代」。
如果每個時代都有它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傳記,中國的這幾十年則是由歐逸文來蓋棺定論,冠之以「野心時代」。
作者簡介
歐逸文(Evan Osnos)
出生於倫敦,1998年畢業於哈佛大後加入《芝加哥論壇報》,並在2002派駐開羅,負責伊拉克戰爭、埃及、敘利亞等中東事務的報導。2005年遷居北京,擔任《芝加哥論壇報》駐京記者。2008年他繼Peter Hessler(何偉)之後擔任《紐約客》雜誌駐北京特派員,一直到2013年。他現為《紐約客》雜誌駐華盛頓分社記者,負責政治和外交事務的報導。
2008年,作為《芝加哥論壇報》的報導團隊之一,他就曾榮獲普立茲調查報導獎。此外,他也獲得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Overseas Press Club)獎和 Osborn Elliott獎。
歐逸文成為繼何偉之後,描述和詮釋中國最好的作家和媒體記者。其在《紐約客》網站上連載的專欄「中國來信」(Letter from China),更被視為解讀中國的經典之作。相較於敘述更個人化、精於探討內心的何偉,歐逸文更具宏觀掌控力,他擅長將中國人和中國的公眾事務放置在廣闊背景和歷史脈絡中,勾勒出複雜的中國全景圖。
《野心年代》是歐逸文的第一本書,出版當年(2014年)即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之最佳非虛構獎項。
譯者簡介
潘勛
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研究生。目前為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的撰述委員。譯有《富強之路:從慈禧開始的長征》《性的歷史》、《Dr. Tatiana給全球生物的性忠告》、《鋼琴教師》、《達文西密碼大揭密》、《微趨勢》等書,合譯有《活出歷史:希拉蕊回憶錄》、《一中帝國大夢》、《我的人生:柯林頓回憶錄》、《世界是平的》、《歐巴馬勇往直前》等書。
序
PART Ⅰ 財富──
01.鬆綁
02.召喚
03.文明的洗禮
04.心靈的胃口
05.不再是奴隸
06.割喉
07.任重而道遠
PART Ⅱ 真相──
08.戴銬而舞
09.自由引導著人們
10.奇蹟與魔法引擎
11.獨唱團
12.抵抗的藝術
13.七項判決
14.雞舍裡的病菌
15.沙塵暴
16.電閃雷鳴
17.發光的東西
18.硬道理
PART Ⅲ 信仰──
19.精神空虛
20.視而不見
21.靈魂之舟
22.文化戰爭
23.真正的信徒
24.突圍
結語
PART Ⅱ真相──
CH.9自由引導著人們_(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
節錄:
自由引導著人們
那年春天,中國官方正以迎接宗教慶典般的熱情,倒數計時北京夏季奧運的到來。黨在天安門廣場邊組了一個巨大時鐘,細數時間分秒逼近,直到奧運展開;整個首都,以呼籲團結至上的口號來裝點門面:「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一天早晨,我踏出前門,發現兩名市府工人正在我寢室的紅磚外牆厚塗水泥。老北京市大塊地區正在拆除或重新整修,為奧運營造乾淨、現代的背景。工人把一板光滑的水泥放下來,正在用尺及鉛垂線來雕鑿直線及交角。我看了半响,才了解他們正在老舊真磚的上頭,重新畫上新磚的模樣。正對我前門的巷弄牆上,還有一點已褪色的文化大革命時代塗鴉,用肥短字體寫著「毛主席萬歲!」,用水泥抹子刷兩下,「偉大舵手」就消失在水泥之後了。
追求完美的衝動擴展到競逐獎牌。體育部官員矢言要摘下比以往更多的金牌,依據《2001-2010奧運爭光計畫綱要》,計畫涵蓋一百一十九個項目,要在競爭激烈的奧運,奮力贏得更多金牌。根據列表,中國總獎牌數估計應為一百一十九面,絕不容許變數發生:奧運籌辦人員想找個小女生在開幕典禮獨唱,但找不到聲音與容貌的最佳結合,所以他們創造一個合成體,訓練一個小女生在舞台上表演,同步與幕後的另一個小女生對嘴唱歌。
中國一家豬肉供應商則表示,正在特別飼養「嬌貴」的豬隻,確保摻有生長激素的肉,不會影響中國運動員無法通過藥檢──但是,這反而使得一般老百姓開始懷疑自己吃的肉,以致於北京奧委會必須頒布《奧運豬相關澄清報告》,譴責有關豬肉的報導「誇大不實」。
京奧籌組人員越是眾志成城,就越容易碰到控制範圍以外的事。奧運火炬傳遞,中國稱其為「和諧之旅」,將掃遍六大洲,登上聖母峰,由二萬一千八百八十八名運動員參與,規模空前。中國媒體把火炬稱為聖火,而且說一等它在希臘奧林匹亞點燃後,將長達五個月不滅,直至抵達北京。在夜裡或上飛機,不能擎火炬時,火焰將保存在一組燈籠裡,維持光明。
三月十日,和諧之旅展開不久,西藏拉薩市有幾百位喇嘛發動遊行,要求當局釋放因慶祝美國政府頒國會金質勳章給達賴喇嘛而被關的西藏人,結果數十名藏僧被捕。
到了三月十四日,抗議的示威惡化,變成一九八○年代以來最嚴重的暴動。政府表示,有十一名漢人、一名藏人躲在暴動者縱火的建築物裡,因此被燒死,另有一名警察、六名百姓因毆打等原因致死。達賴呼籲冷靜,但中國政府把這次暴動形容為「達賴團夥預謀、主使及煽動」。安全部隊坐著裝甲車輛進駐拉薩,控制該市,軍警開始圍捕嫌犯,導致數百人被捕。西藏流亡團體指稱,拉薩掃蕩行動中有八十人喪生,然而,中國官方卻對此斷然否認。
當火炬通過倫敦、巴黎及舊金山時,抗議鎮壓西藏的聲音沸沸湯湯,以致於主辦單位不得不熄滅聖火,或者改道避開憤怒的群眾。中國民眾──尤其是海外留學生,對這些批評,以罕見的怒火回應;火炬抵達南韓時,親中與反中示威者在街上打架;中國境內,數千人到法國連鎖超市家樂福示威,只因為他們認定法國支持西藏活躍人士;甚至中國入口網站龍頭之一的搜狐,其首席執行官、擁有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的張朝陽,還呼籲杯葛法國產品,「讓完全充滿偏見的法國媒體與民眾覺得失落、痛苦。」
國營媒體則使用不合時宜的語言。當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atricia D'Alesandro Pelosi)譴責中國對西藏的管理方式,新華社說她「令人憎惡」。《瞭望》周刊警告說,「國內外敵對勢力已經把北京奧運,當成滲透及破壞的焦點。」西藏自治區書記把達賴稱為「披著僧袍的狼。有人臉的怪獸,禽獸其心」。在匿名的網路討論版上,不堪入目的污言穢語更是難以計數。
一家國營報紙的論壇上,有人發言說:「嘴巴噴屎的人,我就用大便塞到他喉朧去!」另一人寫道:「有誰來給我一把槍!對敵人不必憐憫。」這些發言讓許多中國人感到難為情,同時不能忽視的是,外國記者開始收到言語恐嚇。有人匿名發函到我在北京的傳真機,警告說:「如實報導中國的事實……不然你或你的家人會生不如死。」
抗議不斷滋長,我開始快速搜尋中國網路最具創意的愛國言論。四月十五日早晨,有支標題為「二○○八,中國站起來!」的視頻短片出現在中國入口網站新浪網,它的起源沒人知道;沒有上傳者,沒有旁白,而且除了英文縮寫CTGZ以外,沒註明作者。
視頻是支自製的紀錄片,一開頭是用鮮明色彩繪製的毛主席,他的頭部發射出陽光。萬籟俱寂中傳來合奏,眾鼓咆哮如雷,黑屏不斷閃爍,用中、英文寫了毛最著名的箴言:「帝國主義從不從放棄其摧毀我們的打算。」接下來跳到最近的圖片與新聞前影,快轉穿越種種陰謀、背叛──今天與中國對峙的「法西斯、騙局及災難」:中國股市下跌(此乃外國投機客的傑作,他們「瘋狂操作」中國股價,誘使菜鳥投資人血本無歸);全球「貨幣戰爭」初露曙光,西方打算「叫中國人為美國的金融災難買單」。
接下來再跳畫面到另個戰線:暴徒在拉薩洗劫店面、鬥毆。「所謂的和平示威!」閃爍在這些場景。紀錄片以蒙太奇手法處理外國媒體批評中國的新聞剪貼──它們都「不顧事實」、「用扭曲的聲音說話」。螢幕塞滿CNN、BBC等外國新聞機構的商標,最後全讓位給納粹宣傳部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的肖像。
影音交響及修辭敘述攀往最後文句:「顯然,這些光景背後有個陰謀,想包圍中國。新的『冷戰』!」再來跳到巴黎場面,示威者想從官方聖火跑者手中奪走火炬,迫使警衛不得不保衛他們。視頻末尾是五星旗照片,陽光下閃閃生輝,還有個嚴肅的許諾:「我們永遠會屹立、團結,和諧如一家人。」
CTGZ的視頻長度雖然只有六分鐘,但卻捕捉到當時四處瀰漫的民族主義情緒,上網第一周便吸引百餘萬點擊、數萬好評,成為該影音網站最受歡迎的第四名(第一名則是新聞主播打哈欠而出糗的畫面)。平均而言,視頻每秒鐘就有兩人點擊,它變成一群自命保衛中國榮譽急先鋒的代表宣言,而那群人則被稱為「憤青」。
天安門示威發生十九年後,中國青年菁英再度奮起,但不為追求自由民主,而是為保護中國名譽,令我驚訝。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創辦人兼網路早期意識學家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曾預言,網路延伸到全球,將改變人們認定自己國家的觀念。他預測,「國家之消失有如樟腦丸,由固體直接變成氣體」,此外「民族主義的發展空間,比天花來得小」。在中國,事態發展大不相同。我對CTGZ很是好奇。這個使用者名稱連結到一個電子郵件網址,擁有人是一位上海二十八歲大學畢業生,他名叫唐杰。
中國頂尖學府之一的復旦大學,其校園中心為兩座高三十層樓的鋼質玻璃大樓(很容易被誤為企業總部),再往外輻射。我與唐約在大門。他穿一件粉藍細條紋襯衫、卡其褲及黑色正裝鞋。他眼睛呈明亮的淡褐色,臉圓而擁有稚嫩的五官,頰邊有一抹山羊鬚及上髭。我踏出計程車,他立刻蹦出來歡迎我,還搶著想幫我付車資。
我們走過校園,唐說自己很高興能趁論文寫作的空檔休息一下;論文主題是論西方哲學。他專攻現象學──尤其是觀念的「相互主觀性」,此說是德國哲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提出,他的影響力下及薩特等人。除了中文以外,唐的英文、德文閱讀流利,但不常講,所以有時候,他會不好意思地在三種語言裡換來換去。他另外還鑽研拉丁文及古希臘文。他是如此謙虛,輕聲細語,以致於有時候聲音聽來低到像在喃喃自語。他頗為嚴肅,不常笑,彷彿是為了節省力氣。
娛樂休閒方面,他聽中國古典音樂,話雖如此,他也愛香港影星周星馳的無厘頭喜劇電影。唐對自己的不嬉皮引以為榮,跟「瘋狂英語」的張濟民不一樣,唐不用英文名字。CTGZ這個使用者名稱,是採自中國古詩的兩個晦澀詞彙「長亭」與「公子」,意思是「長亭裡的貴子弟」。跟其他中國精英學生不同的是:唐從未加入共產黨,唯恐黨員身分,會讓他的學者客觀性受到責難。
唐邀請幾位朋友作陪,我們一起到「胖兄弟四川餐廳」吃午飯,過後我們到唐的房間。他自己住在只能步行上樓的六樓,室內面積不到七十五平方英尺,很容易被誤會成是是一個愛挑剔老學究住著的圖書館藏書間。房間四壁都是書,而且從他書桌書架開始疊起,越疊越高。他豐富的藏書包羅了各領域的人類思想:柏拉圖斜靠著老子、維根斯坦(Wittgenstein)、培根、弗朗日、海德格以及《古蘭經》。唐打算把自己的床弄寬個幾寸,他便橫過床框鋪上三合板,邊緣部分用書堆支撐。事實上房間裡書本泛濫成災,而且還用紙箱裝著,堆疊如牆,擱到他前門以外。
唐一屁股坐到他的椅上。我問他是否想過自己的視頻會如此受歡迎。他笑了,說:「顯然我表達出人們共同的情感、共有的觀點。」
坐在他旁邊的是劉晨光,一位寬臉、充滿笑意的政治學博士生,他最近才把哈佛保守派教授曼斯菲爾德(Harvey Mansfield)論「男性氣慨」(Manliness)的演講譯成中文。趴在床上、穿一件灰運動衫的是熊文馳,他取得政治學博士後擔任教職。坐在唐的左側的是曾可為,身材瘦削而模樣時尚,他攻讀完西方哲學碩士後轉向金融,目前是銀行家。他們都二十多歲,也是家族裡第一個上大學的人,都曾受西方思想吸引而研讀過。
劉晨光說:「中國整個現代史落後於西方,因此我們從西方學習,總是在找出西方何以變強大的原因。我們受教育的人都有這個夢:學自西方而變強。」
跟我認識的中國遊客及艾未未「童話」的參與者一樣,我身邊這幾位年輕人看待西方的誘惑時,混雜著尊敬與焦慮。當時蠻令人錯亂的,他們在抗議「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不實,但同時又有個英語研讀計畫,在中國猛打廣告,口號是「一個月後,你就能聽懂CNN」。
唐跟他的朋友們是如此親切有禮,以致於到最後變成我在傾聽他們講話,也開始好奇,中國那一年春天的怒火,是否該視為一時偏差。然而,他們請求我別犯那種錯誤。
曾可為說:「我們研讀西方歷史很久,知之甚詳。我們想,自己愛中國,支持政府,謀求國家福祉,倒不是自動自發的反應,而是考慮周詳之後,才發展成型的。」
事實上他們對中國走向的看法,只要免除尖刻,倒是與中國主流吻合一致。中國人支持國家運作的比例幾達十分之九──在那年春天「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調查的二十四個國家裡,比任何國家都高(在美國,相形之下,出聲支持的只有十分之二)。實在很難斷定中國的愛國主義正向的改變有多普遍,但學者們指出,一份中國反對日本取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會員權的請願書,到最後竟取得四千多萬人的簽名,這約略等於全西班牙人口。
我請唐示範他怎麼做那支視頻,他掉頭看著自己桌上型電腦的螢幕,問道:「你曉得『Movie Maker』嗎?」指的是一種視頻剪輯軟體。我回答說,一竅不通,問他怎麼從書上學懂。他憐憫地瞧著我,說逐頁看「說明欄」就學會了。他說:「我們得感謝比爾.蓋茲。」
唐推出自己的視頻處女作一個月前,中國超越美國,變成世界第一大網路使用國。上網民眾達二億三千八百萬人;雖只是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六,但換算下來,將近二十五萬中國公民每天第一件事便是上網,而且正在改變了思想傳播的方式。最熱絡的線上社群註冊會員成長到幾百萬,名列中國共產黨以外最大的組織。
在一個因方言、地理及階級而分割的國家,網路能讓人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發現彼此。一群中國志工聚起來,開始每周逐字翻譯《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而且免費提供給讀者。譯者解釋他們的目標時寫道:「網路時代,最強大的力量不是貪婪、愛或者暴力,而是獻身於一種興趣。」他們年紀輕,對科技烏托邦的信仰不計毀譽。
他們寫道:「網路讓你連結到志同道合的人,釋放不可思議的能量。」為了避開刪檢官員,他們先行公開自我審查,告訴新會員:「文章若是涉及敏感話題,你不確定是否獲准的話,請別冒險。」那種自我審查就是一種自我管理。有些網站會招募志工,移除可能令網站陷入麻煩的題材。他們以「版主」的身分而知名,但是,若用戶認為版主太嚴或太寬,還可以換掉他們,此一過程通稱為「舉報」。
中國最早期的網路使用者是一批熱心的愛國志士。一九九九年春天,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戰機使用美國情報,誤將三枚炸彈投入中國駐貝爾格勒(Belgrade)使館,中國網路界發揮出他們的力量。愛國駭客把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首頁用「形同野蠻人!」這樣的口號蓋起來,而且用洪水般憤怒的電子郵件淹沒癱瘓了白宮網站。有位評論家說道:「網路是西方發明的沒錯,但……我們可以用它對全世界說,中國不能被侮辱!」對很多人來說,民族主義提供一位愛國青年形容的「初嘗言論自由的神聖權利。」
跟其他許多同齡者一樣,唐杰把大部分時間花在網上。二○○八年三月拉薩發生暴動時,除了中國官方媒體以外,他密切觀察歐、美新聞網站報導。在政府防火長城下挖地道,他可毫不猶豫。他使用代理伺服器──一個海外的數位小站,可以讓網民連上被封鎖的網站。他只在網上看電視,因為網路電視有更多選擇。
他還從中國的海外留學生那裡接收了外國新聞剪報;過去十年,中國留學生人數成長近三分之二,來到約六萬七千人。外國不少人認為,與唐杰同世代的中國人,由於刪檢的扭曲,似乎不那麼有智慧。這一點令唐感到困惑。他說:「因為我們生活在這種體制之下,總是捫心自問,是不是被洗腦了;我們熱中由不同管道取得其他資訊。只是,當你生活在所謂自由體制中,你根本不會有思索自己是否被洗腦的問題。」
那年整個春天,有關西藏的新聞及輿論不停在復旦的電子布告欄(簡稱BBS)打轉。以科技來看,BBS是老古董了──很簡單的論壇,有多條談話貼文──只是當時推特還有它的中國同類還沒生根,對許多中國人來說,BBS首度讓他們體驗進入數位空間,滿是陌生人,而且敢放聲直言。在復旦BBS上,唐杰讀到很多外國新聞剪報,那些剪報在中國網友讀來,是充滿誤導又不公平的東西。
例如在CNN網站上突顯一張照片,內容是軍方卡車鎮壓住手無寸鐵的示威者。但另外搜尋到的照片沒經突顯的版本則顯示:一群包圍卡車的示威者,其中有人高舉武器,向卡車丟擲物體。在唐杰的眼中,那張突顯的照片看來的確是蓄意扭曲了。
他毫不留情地說:「這真是笑話。」那張真實照片及其他照片被電子郵件在全中國傳開,大家寫上批評,其他人則加上更多取自倫敦《泰晤士報》、福斯新聞、德國電視及法國廣播的案例。這麼多新聞機構報導不實,在有成見的人眼中,就有幾分陰謀的意味了。很多人,包括唐杰,本來都很相信西方媒體的,卻因此震驚了,但更重要的是:它觸怒了他們。唐杰認為,他生活在自己國家現代史上,最繁榮開放的時刻,而這個世界似乎依然以狐疑的態度來看待中國。
CNN評論員卡弗蒂(Jack Cafferty)似乎想嘩眾取寵,竟稱中國「還是蛇鼠一窩,過去五十年來沒變。」這句話登上全中國媒體的首頁,惹得後來CNN也為此道歉。唐杰跟許多同儕一樣,無法理解外國人何以會對西藏如此激動──依他看來,那兒是凋蔽的內陸地區,中國竟窮數十年光陰想教以文明。因西藏之故而杯葛北京奧運,這種邏輯對他來說,好比抗議美國虐待切羅基族(Cherokee),而不參加二○○二年的鹽湖城冬季奧運一樣。
他搜遍YouTube,想找到反駁的影片澄清中國人的觀點,但在英文發音的短片中,除了支持西藏者,別無其他。唐杰本來就很忙──他跟出版商簽約,把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形上學序論》(Discourse on Metaphysics)等著作譯成中文──但他想替中國人發聲的念頭揮之不散。
他說:「我當時想,好,我會做點東西出來的。」
然而,在唐杰可以動工前,他被迫回家幾天。當時是收穫季了,他母親要他回去田裡幫忙,還有刨竹筍。
访谈
欧逸文:野心塑造中国
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 困困
2014年5月19日
如今的中国,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蠢蠢欲动的情绪,它驱动中国成为最新兴的超级大国,它也使这里世界上最大的威权统治政府感到担忧。官方用“中国梦”来回应这种情绪,将其描述为一种复兴强国的欲望;一位美国前驻华记者也捕捉到这种情绪,他称之为“野心时代”。
《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刚刚出版新书《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书中呈现了样本丰富的中国人真实经历,包括被成功欲望猛烈冲击的企业家,用近乎虔诚的方式复兴爱国主义的“愤青”或英语学习者,为追求真相而承受压力或陷入囹圄的媒体人、艺术家和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物从表面看几乎并无相似之处,但他们又共同呈现出野心勃勃的新中国关键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政治独裁的高压也无处不在;人们追逐成功,与此同时也感到空虚,转投信仰以寻求宁静;自我意识的觉醒浇灌了个人主义,但也同样滋生割裂感与不安。
欧逸文1990年代中期曾在北京学习中文,2005年作为《芝加哥论坛报》的驻京记者迁居北京, 2008年至2013年他开始为《纽约客》杂志担任驻华记者,他与前任——何伟(Peter Hessler),《纽约客》2000年至2007年驻北京的记者,共同完成了该杂志中国报道的样本:用铺展、深入的特写报道,记录转型中的中国最激动人心又击中本质的人或事件。他们在中国读者中颇有声望,甚至获得了“非虚构写作双胞胎”的昵称。但欧逸文与何伟是一棵树上结出的两个迥异的果实:如果说何伟的叙述更个人化,精于探究内心,欧逸文则更具记者的全局掌控力,他擅长将讲述对象放置在广阔背景中,勾勒出复杂的中国全景图。
欧逸文在中国生活的八年,也恰好是中国充满矛盾的时期。如何平衡这种矛盾,既是他身在中国时切身的感受,也是他离开后写作这本书时要处理的议题。在为《纽约时报》观点与评论版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欧逸文写道:“对当代中国的描写中,最艰难的部分就是掌握它的比例:有关中国的故事中,有多少是真正鼓舞人心的,有多少残酷无情的?针对中国的价值观,科技初创企业和自主创业的故事能体现多少,防火墙和滥用权力又能代表多少?”
他希望不怀偏见。《野心时代》做出了有益的努力,书中选择的人物样态丰富,兼具“鼓舞人心”和“残酷无情”,讲述也足够从容,在人物的个人故事与宏大背景之间灵巧转换。在书中,也许无法读到判断或预言,但它忠实讲述了刚刚过去的一小段历史,以及正在发生的故事,或许暗藏着中国未来可能的转变。
欧逸文对中国怀有情感,对这本“中国报告”,他有两个目标:希望中国人读到这本书;希望中国人读到完整的这本书。遗憾的是,因为他无法接受中国大陆的出版审查制度,《野心时代》将不会出版简体中文版。
目前欧逸文是《纽约客》杂志驻华盛顿分社的记者。2014年3月,因为参加一个文学节,他回到中国。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北京对他进行了专访。以下是访谈实录,经过编辑和删减。
问:你是如何找到“野心”这个关键词作为新书题眼的?
答:2005年我搬到中国后就对“热” 这个词产生了兴趣。不论我在中国探究任何文化现象,或者某个人物的流行,我总是听朋友用“热”这个词来形容它们。这是一个栩栩如生,又极具力量的词汇,因为它形容了某种现象有如病毒一般在人们之间传播,很快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蔚为大观。
实际上,早在1979年“热”就在中国出现了。我想是邓小平——当时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他用这个词来形容当时在中国兴起的小农场和小工厂热潮。在当时,这种热潮正如鸡舍里的传染病似的,从一只鸡传染到整个鸡舍,然后又不知不觉蔓延到整个地区。
2005年我到中国后,先后出现过“博客热”,当时最著名的是写性经历的木子美;英语热,比如李阳的疯狂英语等等。2008后,还出现了“奥运会热”。但是“奥运会热”与其他“热”的不同之处在于:奥运会是由政府发起的,奥运会热的流行是由政府推动的,它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现在我们回头看,没有人会说,木子美,你会成为一股热潮;李阳,你会成为一股热潮,是人们选择了他们。但是奥运会热却是由政府主导的,这是一种官方热。
另一个引起我兴趣的是“个人主义”这个词。一开始我对人们说起个人主义,大家都觉得这不是个好词。即使今日,个人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听上去依然太自私了。但是我书中写到的每个人,都被认为是有“个性”的,是指这些人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且卓尔不群。他们在某一领域独当一面,不可或缺,富有创意,很有潜力或者大权在握。我发现人们开始追逐个性,追逐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但是个人主义这个词并不那么容易被接受,我感觉个人主义在中国存在并且非常重要,但是要使用这个词汇却并不那么使人感到舒服。
之后我开始对“野心”这个词感兴趣。野心的用法在中国也经历了一些转变,20年前,假使我们说某人有野心,那是对这个人的冒犯;但是如今的中国,野心成了必须,如果你没有野心,那你就落后了。而在“热”和“个人主义”背后,正是“野心”在驱动。这就是我开始研究野心的过程。
我挺迷恋一个词用法的流变,在中国尤其如此,有时候因为我对一个词感兴趣而开始采访研究,有时候又是因为某一个词流行起来驱使我去发现它流行的原因。
问:谈到中国的个人主义与野心时代,感觉与美国的1920年代有很多相似之处?
答:是的,有许多相似之处,当然也有所不同。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到此刻的中国与美国的1800年代末期或20世纪初期有着诸多相似。美国的20世纪初期,后来我们叫它“爵士时代”,或者“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代”,那时处处隐藏着可能性,那种一个来自北达科他州小镇的的青年可以在大城市成为大亨的可能性,只因为他富有决心,也许还有一点不守规矩。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正是那时候美国建起了摩天大楼,正是那时候美国修建了全国铁路,也正是那时候美国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因为财富太多而人又那么少。那时候只要你打破规矩,敢于牺牲,你就能达成目的。这种可能性正是此刻中国与当时美国的相似之处。
但激动人心的背后隐藏着社会系统逐渐失去控制,因为一小部分人精于利用制度的漏洞从中谋利。因此,也正是那时候美国开始治理食品的不安全,查处危害工人健康的工厂,调查财团或富人操纵政治以谋私利。这一切都使我感到,这多么像中国。从积极的角度看,美国走过那个痛苦的,剥削的,权势人物豪夺强取的时代,继续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因为人们意识到过速的野心与发展带来的弊端使我们必须停一停。因此美国当时采用了一些方法,比如利用工会,媒体,中产阶级来修正这些弊端,尤其是中产阶级,也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他们认为有必要对同胞负责。由此治理了腐败,在权力与机会之间找到平衡。
因此,当时美国所经历的一切告诉我,此刻中国与当时美国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无法像美国当时那样有效回应并解决公共压力。中国经常让我担忧的一点是,制度在金钱、政治和权力之间失衡了。如果制度合理,就会迅速回应社会压力并作出调整,而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导致反应滞后,滋生不满和愤懑,最终会演变为混乱无序。
问:你这是在预言中国会往何处去吗?或者你的书中有这方面的预言?
答:我不知道,我也不愿意做任何预言。也许几年前,我还感到中国可能会经历某种程度上的政治转型,因为当面临存亡考验的时候,这个政治体系会因为一种生存本能而选择转型。这有点像人体机能运作原理,当人体暴露于酷冷环境时,最先是手指停止供血,之后是手,胳膊,以此来保全核心器官。政治也同理。1978年时,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舍弃了一部分,以保全更大的整体,当时他们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因而也重新定义了究竟什么是共产党。如果十年后的中国共产党与如今的中国共产党不同,我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因为最强大的本能是生存。
但是基本上我是不愿意做任何预言的,因为预言很廉价,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因此在我的书中你是读不到任何预言的。我花了很大篇幅来谈论现在和刚刚发生的过去,因为这是我知道的。我更愿意读者得出自己的判断,而非由我来告诉他们即将发生什么。而如今中国所经历的一切又是特别特别值得书写,它需要被精确地、关注细节地来描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中又暗藏着某种预言,这些预言就暗藏在那些我所写的一个一个人的生活中。
问:另外,“野心”这个中国关键词跟“中国梦”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你怎么理解中国梦的?
答:很有意思,“中国梦”这个提法出现于我在中国的最后几个月。当他(习近平)谈论中国梦时,我感觉到里面的逻辑, 因为我在中国的这几年感受到中国人的野心,希望与渴望,我觉得中国政府也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的这种情绪,他们也在想办法去走在它的前面。因此我觉得中国梦正是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一种追赶。
但是中国梦有一个问题,它隐含的逻辑是中国人民被准许做梦了。我并不确定人民真的同意他们所谈论的中国梦。习近平说中国梦是“伟大复兴”,可当我问中国人你的中国梦是什么,他们的答案绝非如此:我的中国邻居的中国梦是打赢一场官司;前两天我碰到的一个人,他说他的中国梦是去新加坡探望在那里读书的女儿。这些答案让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的语言与中国人民的生活是如此脱节。党使用的这些字眼,“科学发展观”,“伟大复兴”,是无意义的,空洞的。也许他们应该学习一下可口可乐或者iPhone式的销售语言。
而普通中国人的中国梦也使我想到另一个启发我写作这本书的作家:鲁迅。他有一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当我采访书中人物时,他们很多人在1960或1970年代过着没有希望、没有信仰的痛苦生活,然后忽然间他们有了某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以彻底改变人生。这正如同鲁迅的这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说的其实是一种渴望的能力。在1970年代,因为前面我所说的生存本能,中国共产党给了人民一种具有渴望能力的权利;与此同时,这种渴望的能力又如此强大,它使人民觉醒,使人民重新发现自己,变成一种最终不再受控的力量。
问:你的书写到了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的人,能不能说说为什么选择这些写作对象?
答:好的。我越多地研究中国人的野心,越发现赋予野心力量的三种追求。首先很自然的会追求财富,我的书中写了龚海燕(相亲网站“世纪佳缘”创始人)的故事。之后就是追求真相的野心,也就是说发现你身边的现实与事实,不论是过去的还是当下的,这也意味着一个人不再满足于被动的灌输和接受,他们学会挑战,他们不再相信。
胡舒立(财新《新世纪周刊》总编辑)是一个真相追求者。她在体制内,看上去她所做的事情是受限的,但是她深知,如果她彻底独立,是无法完成她对真相的追求的,只有学着打擦边球,学着非常小心地在游戏规则内,来发现利益集团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但是她是有渴望的,她饱含希望,当她早年间去美国学习新闻时,一个教授告诉她,别回中国,在中国你永远都无法从事真正的新闻事业。这让她很苦恼,因为她为中国人的身份骄傲,她也希望做得比《纽约时报》还要好。最终她回到中国,她用自己的方式——艰难的方式——来完成她的野心和她的渴望。
在写追求真相的人物时,韩寒(作家)也是一个例子。他选择不相信,不相信中央电视台,不相信媒体,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说真话的人,他似乎是被打造成说真话的人,人们开始相信他。人们想,我也不相信中央电视台,这个家伙挑战央视,那么也许我可以相信他。人们也一直在寻找一个这样的人,这个人挺普通的,有点像我,可能是更好版本的我,于是人们就说,好的,我相信他。但是当韩寒陷入到造假风波后,人们忽然发现一个说真话的人也许并没有说真话,人们就失望了,甚至愤怒。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经阐释过“一种犬儒主义”:当一个社会持久地倾向用谎言替代真相,那么最终人们会拒绝相信任何事。中国正是如此。 我也关注过韩寒和方舟子(科学工作者)之争,韩寒是否造假?也许我的判断是错的,我不知道,不过我感觉韩寒没有造假。韩寒是我去年夏天离开中国前最后一个见到的书中人物。有关他的造假风波隐藏着一个逻辑:他是一个真相代言人,但是当人们不再相信任何真相的时候,他也被拉下神坛,与此同时,新的真相追求者诞生了,那就是方舟子。
如今在中国,人人都开始追逐真相了,简直成了一股时尚。也就是25年前,人们还难辨真假,你很难分辨,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太强大了。现在互联网和现代技术为人们提供了调查真相的可能性和能力:胡舒立,她在追求真相,她已经非常非常接近真相;艾未未,他为什么对四川汶川地震感兴趣,为什么要调查地震中倒塌的豆腐渣工程和遇难学生名单,因为这些事关真相。这些人不仅追逐真相,这种追求也像一种信仰。
问:驱使一个人追逐什么,往往深层次的原因都跟信仰有关,不一定是宗教信仰,可能是一种坚信。
答:是,对信仰的追求可能是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人们开始追问一些大问题:我相信什么,我的人生的道德准则是什么?可能人们拥有了财富,但是金钱是空虚的,人们希望获得更多,有一些人求助于宗教信仰,有一些人开始追求一些别的信仰。
比如说,像书中的一个人物唐杰(Anti-CNN网站、四月网创始人,发起“新爱国主义运动”),到最后,唐杰所追逐的事情已经成为信仰。一开始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他相信中国,但是最后,在我书的末尾——这里我做一点剧透,他说他相信自己,这就是他的信仰,他真心地认为自己拥有解释中国的权利。
书中还有一个人物林谷,他曾是新华社和BBC的记者,可以说他的职业生涯就是追求真相,但是他无法感到满足,当他面临一些大问题时,比如人生的意义,他选择求助宗教信仰。我在中国的时候,居住在国子监孔庙附近,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前来寻找大问题的答案。有一些人求助于儒教;有些人求助于佛教;有些人求助于基督教;有些人求助于巴哈伊;有些人求助于疯狂英语……。此刻的中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觉醒的时刻,同时,这种信仰又是如此个人化。
问:除了野心,你的书中还抓住了其他的中国关键词,比如“割裂感”与“不安全感”。
答:对,我用一章的篇幅来写小悦悦的故事。小悦悦事件发生于2011年,她正展示了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割裂与不安。这个新闻出现的时候,我对这个事件非常感兴趣,一个被两辆车碾压的躺在佛山五金城旁街道上的小姑娘,18个人从她身边路过而无人援助。
这些路过的人是一些聪明人,他们在追逐财富,他们努力工作,他们能够一手建筑一个自我的小世界。与此同时,他们也都是个体,“个体户”,这个20多年前出现的词教会他们一个教训,他们的个人小世界只有他们自己可以依靠,制度无法帮助他们,制度不可靠。这些路过的人也几乎都听过“彭宇案”(2006年,南京彭宇扶救倒地老人被讹诈的案件),他们学到另一个教训:遇到这样的事件最好不要卷进去,赶紧离开,因为冷酷能帮助他们,而警察帮不了他们。
因此我去了佛山,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跟人们聊。路过小悦悦的18个人,他们之所以不施以援手,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不是因为他们是对孩童冷酷的人,很多人也是父母,他们这样做是本质上是因为中国的制度设计使他们感到制度不可靠,不可信。他们不施救,甚至是一种“理性”的决定,他们中有人说我不能帮助小悦悦,因为如果我牵涉进去,我的小世界就会崩塌,我努力获得的一切就会消失。对我来说,我感到不论是这个五金城里的人,还是中国别的地方的人,都有如生活在一个一个孤岛上,每一个岛都枝繁叶茂充满可能性,可是从岛外望过去,任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会让这个岛断水,会让岛毁灭。
中国人总是在讨论“不安全感”,是因为人们感到失败就在距离成功不远处,你的生活可能是一种假象。你有住所,你的生活比你的父辈、祖父辈都好,但是即使很小的事情发生,你就可能毁于一旦。你不能去找法院,法院帮不了你,法律帮不了你,政治帮不了你,人大代表帮不了你。谁能帮你?只有你自己。这也许也是个人主义消极的一面。
问:书中人物,哪一个花了你最长的时间来采访和写作?
答:我想应该是林毅夫(经济学家)。他的人生精彩纷呈,他是我这本书的开篇人物。1979年以前,他生活在台湾金门岛,但他怀有一种强烈的野心:他说,我要去中国大陆,我可以影响中国。之后他放弃了一切,他的妻小他的家庭他的军职,然后一路从金门岛游到了大陆。这是我见过最惊人的有关野心的故事,同时他也极好地诠释了什么是个人主义。我对他的故事非常感兴趣,尤其是他在1979年作出决定的那一刻——他并不了解大陆,但是却有一种提前的预知,未来将会翻天覆地不同,这使他坚信自己必须到海峡那边去。
我2010年认识林毅夫,之后陆陆续续采访了他五,六次,直到2013年7月。过程中我还前往台湾金门岛,查阅和收集了一些当时的资料,台湾军方一直在调查他。我非常感激他愿意谈论自己的经历,因为这些往事对他是苦涩的。一开始他不愿意谈,他说这都是些旧事了。我猜是我的诚挚打动了他,他也意识到我是把他的经历放到中国的大背景下来理解。然后他就非常慷慨、真诚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问:你的书中人物,有很多你也为《纽约客》杂志也写过文章,书跟《纽约客》文章有什么不同?
答:我很难给出一个百分比数字。书中的确有几个人物是我在《纽约客》工作时候写过的。有一些人物是我为《纽约客》采写之后,又持续跟踪他们,比如唐杰,我在2008年为《纽约客》写过他,但在书中,我又扩展写到了他的2008,2010和2012年的不同经历。还有一些人物,是因为我有这本书的计划,因此选择他们为《纽约客》采写,比如龚海燕,当我听说她的故事的时候,我意识到她之所以创办“世纪佳缘”这个公司,是一种自我选择,选择追逐财富,我希望她也成为书中的一个人物。《纽约客》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他们欢迎一个驻刊作家先在杂志上发表一部分书的内容。这是一种特别棒的做法,因为它让你重新思考你的人物和写作,让你成为更好的作家。
问:如果一家中国出版社计划在中国大陆出版这本书,但是因为审查制度,需要删掉一些章节,你会接受吗?
答: 哦,不。我不会接受任何删节。我无法为他人做主,但我可以为自己做主。对我来说,这本书中所写的人与事,都是我认为值得谈论和书写的,我希望人们在整本书的框架下来理解这些人与事。如果我删去了这本书的某一部分,它一定会改变人们对这个话题的理解。我绝对不认为接受这本书被删节是什么好主意。我会尽一切努力让中文世界的读到这本书,也许会出版繁体字版。对我来说,我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我希望中国人读到这本书;另一个是,我希望中国人读到完整的这本书。
问:简单谈谈你离开中国后,身在中国之外看中国,跟以往有什么不同?
答:因为我迷恋中国,所以我无法那么轻易放弃关注中国。当我们搬回美国后,我现在的工作也并非停止写中国,只不过也开始写美国了,看上去,中国越来越少地占用我的时间,而美国越来越多,可实际上,我是不可能忽然像这样(打了一个响指),就一下子停止了对中国的兴趣。我不会停止有关中国的写作,不同的是,在未来的四五年时间内,我会更多地写世界各地包括美国的故事,以往我对中国的观察视野是狭窄的,现在更加广阔了。因此我会常常回中国。
困困是纽约时报中文网文化版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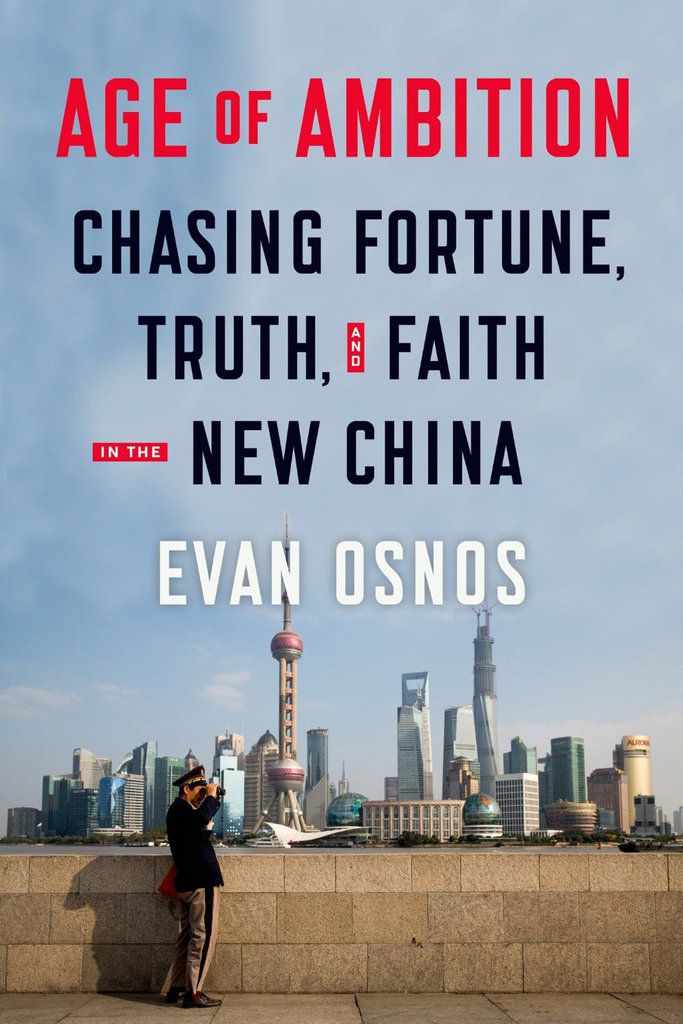
随笔
一个中国年轻人读到的“野心时代”
周诗梦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6月11日
《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是《纽约客》前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最新出版的一本书。书中,欧逸文讲述了他从1996年到2013年期间三次前往中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以及在这期间采访和整理的中国各阶层不同人物的百态人生。欧逸文同时扮演起历史的亲历者和旁观者的双重角色,把他的个人经历和受访者的人生故事融合在一起,在不同人物和时间的交错叙述中逐渐勾勒出当代中国万物生长背后那个隐约可见的复杂轮廓。
我坐在都柏林的家中阅读这本书的英文版本,身处跨越几世纪的欧洲老宅里,内心却随着笔者的叙述跌宕起伏,仿佛回到了高楼耸立的北京城,来到了人潮涌动的鼓楼大街,回到那种充斥着兴奋、饥渴、疲惫或者迷茫的情绪中。“野心”是这本书的关键词,对于大多数西方读者和书评人而言,“野心”两个字很好的诠释了中国在过去30年中演绎的惊世骇俗的经济奇迹和触目惊心的政治真相。但是,对于更多像我这样出生于八十年代末,在过去十年里亲身感受了中国社会发展浪潮的年轻一代来说,“真实”或许是对这本书更好的注解。
在书的第一章《财富》(Fortune)中,欧逸文这样描述婚恋网创始人龚海燕年轻时的外貌:“她薄唇削肩,即便处于放松状态,脸上也挂着警惕的表情。”这个简单而富有细节感的描述,让我想起了周遭很多长辈亲戚脸上时常挂着的表情。然而,正是这位出生于农村,外表在传统的中国观念中并不讨喜的女子,在日后的岁月里为了改变命运放弃工厂的稳定工作,在21岁时重新投入学业,并且最终依靠自己在婚恋经历中的挫折以及从中发掘出的当代中国男女关系的需求,创办了中国最成功的婚恋网之一“世纪佳缘”。2011年5月,“世纪佳缘”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龚海燕成为坐拥7700万美元资产的财富新贵。这样命运沉浮的人物故事在《野心时代》中还有很多,通过展现不同中国人命运戏剧性的大起大落,作者试图勾勒中国社会在过去30年里经济发展的复杂脉络。
“在所有追逐个人成就的道路中,没有哪一条路比英语学习更吸引人。”欧逸文用这样的开篇语描述中国过去20年里逐渐兴起并且沸腾的“英语热”。作为从小生长在英语学习浪潮下的年轻一代,《野心时代》里没有什么话题比“英语热”更能引发我的共鸣。欧逸文从李阳在2008年的一堂英语培训课开始了他对当代“英语热”的探究。在那堂课上,“李阳站在学生面前,像一个宗教领袖高举右手,带领大家高声呐喊英语。‘I’他呐喊着,‘I’学生们回应着”。
这不禁让我回忆起2002年我第一次感受李阳“疯狂英语”千人嘶吼的空前场面。12年前,那年我14岁,在成都念初中二年级,当我和几千人一起挤在四川省体育馆内,热切期待一位英语老师的莅临时,那感觉无异于期待一位歌坛巨星的到来。“疯狂英语”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它标志着英语学习从刻板的书面教学摇身一变成为了一门“说”的艺术;印有李阳标签的“英语呐喊”教学法,更是把某种个人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人们似乎从李阳的呐喊中找到了自己抒发内心的出口,年轻人从此不再顺从于八股式的完形填空和英语阅读选择题,他们需要个性十足的呐喊。那个12年前的夜晚,我和数千人一同跟着李阳高举右手尽情地呐喊着“I Love English”(我爱英语)、“I am foolish”(我是傻瓜)等各式口号。李阳富于激情的演讲也让全场观众像是被引爆high点的摇滚歌迷一样激情澎湃。当李阳用他浑厚磁性的普通话讲述自己在兰州大学读书时站在空旷的楼顶呐喊英语,克服性格中胆小和怯懦的奋斗史时,英语在他口中就是改变性格和命运的武器。有趣的是,随着对英语培训领域的持续关注,我逐渐发现,“英语改变命运”似乎成为了整个英语培训行业的精神口号。2003年,初三毕业那年,在成都新东方《新概念英语3》的培训班里,我和200多名年龄各异的学生一起坐在一间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听一位年轻的女老师讲述她教英语赚得“数钱数到手发软”的故事;2006年,大一那年,在中国传媒大学的400人报告厅里,我与学校各系的师哥师姐翘首企盼着英语培训帝国“新东方”的缔造者俞敏洪的到来,听他讲述自己娶老婆、交兄弟和创业的故事;2010年,大四那年,在新东方总部的一个分享会上,我与新东方的英语老师们一起聆听高层校长讲述自己靠学英语成就事业和改变命运的故事。
无论英语学习是否真的具有改变命运的功效,它确实成为了许多中国年轻人奋斗的目标和信仰。在我2010年本科毕业的时候,大学英语四级依然是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的必考科目。很多学生从大学,甚至高中开始就积极准备出国留学。2013年,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完成的报告,2012-2013学年超过80万海外留学生前往美国留学,其中最多的学生来自中国,达到了超过23万人,比上一个学年增长了21%。我与很多背景各异的英语学习者交流过他们参加英语培训班的缘由,无论他们学习英语的需求是出国留学还是考过大学四、六级,除了知识本身,他们参加各类英语培训大都还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就是找到一群同舟共济的人,为自己孤独的学海生涯寻求一处心灵的寄托,也为了在培训班老师们绘声绘色的段子里找到一点轻松时刻。亦如欧逸文书中描述的那样,在各类“疯狂英语”的出版刊物封面上,李阳标志性的“无框眼镜”和他“正统而威严的笑容”曾代表着无数人的精神信仰。但即便是信仰,也有崩塌的时候。2011年,李阳的妻子李金(Kim)在新浪微博中控诉李阳对其实施家暴并要求离婚,把李阳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也使他面临史无前例的公众形象危机。今年5月,在接受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专访时,欧逸文曾经用李阳家暴事件来说明中国的不可预知性。他说:“这个曾经寄托着无数人精神信仰的偶像,突然间变得一文不值,这样戏剧性的转变是没有人能够预测的。”
《野心时代》的第二章《真相》(Truth),欧逸文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在表达、监管、突破与受挫中艰难前进的中国新旧媒体发展图。中国的媒体业长期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媒体人需要在不断地探索和试错中寻找报道“真相”的尺度和边界,这无疑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中国媒体业内人称之为“戴着脚镣跳舞”。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给了更多中国人自由表达的机会,但也同时加快了政府进行信息监管的步伐。社交媒体新浪微博时常出现“此条信息因违反相关规定已被删除”的提醒,中国的网络审查系统防火长城也成了一个公开的不能说的秘密。2006年,我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我记得刚上大学不久,就在某一堂专业课上听到老师这样评价:“中国的媒体机构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你们作为其中的一员,就是在为党和政府发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领域的前辈对中国的媒体业作出的直观定义。当时,我并不理解这句话在具体的工作语境下意味着什么,但我能明显感受到“限制”的信号,它也在我内心深处慢慢滋生出一种精神压力和抵触情绪,毕业时我没有求职于任何传统媒体机构。《野心时代》中,欧逸文讲述了一个努力追逐的媒体人的故事——胡舒立。胡舒立1998年创造《财经》杂志,后2009年离开《财经》,创办财新《新世纪》周刊。在欧逸文的描述中,《财经》是一本极具风格的杂志:“《财经》杂志是中国仅有的几本可以发出不同声音的媒体刊物之一”,而胡舒立这个名字,则是“中国自由表达边界的测量尺”。2003年,当SARS病毒已经开始在广东省肆虐,但当地媒体集体保持缄默时,《财经》是首先打破沉默的媒体之一,发表了一系列关于SARS病毒传播与感染的权威详实的报道;2008年,当相关部门禁止一切关于汶川地震伤亡及房屋垮塌的报道时,《财经》另辟蹊径,发表了一篇12页的调查性报告,用数据和事实讲述房屋垮塌背后政府对公款的挥霍以及对建筑标准的忽视。欧逸文在采访中问胡舒立,报道敏感话题时,她的杂志是如何面对来自权威机构的压力,胡舒立回答:“我们从来不用轻率或者过于感性的语言来报道新闻,比如‘你是骗子’,我们尝试分析这个系统,然后解答为什么一个好的想法或者一个好的愿望无法变成现实。”
当“戴着脚镣跳舞”变成不堪的重负,也有媒体人选择放弃,转而投身于宗教信仰,寻求向内的力量。比如书中欧逸文的记者朋友林谷,他在38岁时放弃记者职业,归隐山林,潜修佛法。佛教给了他媒体业无法给予他的答案,“‘我已经寻找真相很久了’,他说”。这是《野心时代》关于中国的另一个有趣观察。经济发展给了中国人更多选择的机会,互联网给了中国人更多自由表达的空间。经济和精神的复苏让中国成为这个时代拥有最多可能性的国度。
在欧逸文看来,某种程度上,人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信仰。对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唐杰来说,“信仰”是相信自己,不依赖于任何媒体寻找真相,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西方媒体。唐杰是短片视频《2008!中国站起来!》的制作者。通过短短6分钟的图文描述,唐抨击了西方列强在经济上对中国制造业的压榨,对金融业的破坏,揭露了西方媒体关于中国人权、民族问题的诸多失实报道,鼓励国人站起来表达自己。对于“疯狂英语”的学习者Michael来说,“信仰”就是英语,他相信英语能够为他开启一番事业,同时改变他的命运。然而,对于那个在“世纪佳缘”的相亲活动上被女方拒绝的男性征友者来说,“信仰”也许就是一套房子和一辆车子。
读《野心时代》,我读到了“真实”,这种真实是我身处中国时感受到的真实。人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追逐财富、真相与信仰,同时也承受着由此带来的压力与困苦。年轻人在努力为生存寻求机会的同时,也试图为精神找到表达的出口或心灵的寄托。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因为每一个个体的参与,而显得复杂而不可预测。欧逸文撷取了一些片段,观察每一个受访者,试图记录下正在中国发生的故事。他也许无法呈现整体,但那些个体的故事身上,多多少少都可以看到我自己曾经走过的路途。
周诗梦是自由撰稿人,曾供职于互联网媒体公司,现居爱尔兰都柏林。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