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美中貿易戰,戰什麼?》WTO為何無法馴服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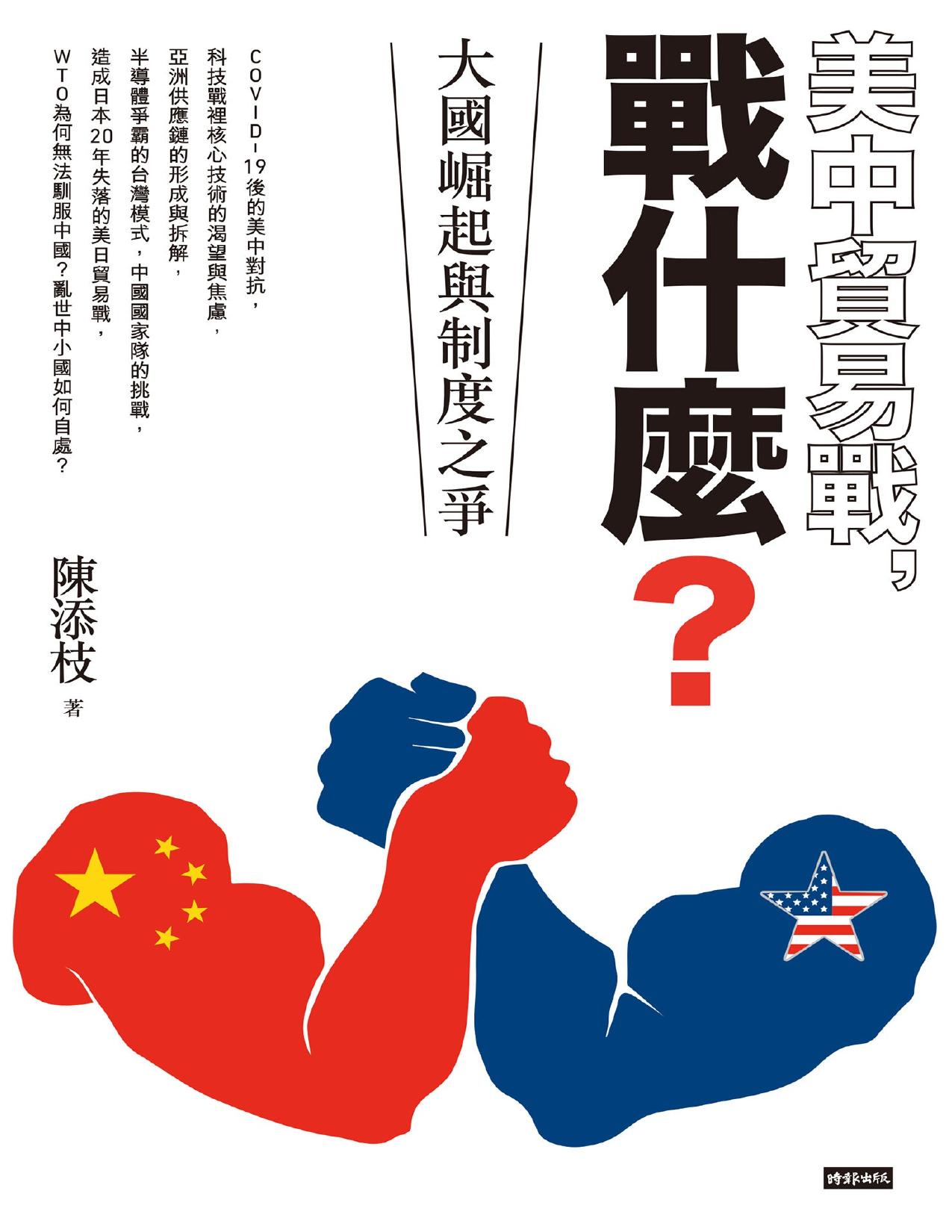
WTO為何無法馴服中國
中國在二○○一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當時西方國家都期待中國在WTO的體制下,將徹徹底底的轉型成一個市場經濟的國家。在中國的入會協議書中(Protocolof Accessionto WTO),中國承諾在十五年內被以「非市場經濟」國家對待,顯然西方國家期待中國只要誠實履行其入會承諾,十五年內就會脫胎換骨轉化為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可是,當這條款在二○一六年到期時,美國和歐盟都拒絕承認中國已經變成一個市場經濟,而堅持繼續以「非市場經濟」國家的身分處理與中國間的貿易關係。中國認為美歐沒有誠信,美歐則認為經過WTO十五年的洗禮,中國的經濟體制並未比入會時更接近市場,甚至越走越遠。
中國在一九八六年申請加入WTO的前身GATT,歷經十五年的辛苦談判,才在二○○一年順利加入WTO。西方國家在入會談判時,極盡需索,讓中國做出各種承諾和讓步。不論工業、服務業或農業,中國承諾的自由化程度,都超過一般開發中國家的水準。中國入會以後,表面上也誠實履行降稅和允許外商進入中國市場的承諾。十五年過去了,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量都大幅度成長,使中國一舉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貿易國家。二○○一年入會時中國對外貿易總額是五,○九七億美元,二○一六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是三.六八六兆美元,成長七.二倍;其中出口由二,六六一億美元成長為二.○九八兆美元,進口由二,四三六億美元成長為一.五八八兆美元,因此貿易順差由二五五億美元擴大為五,一○○億美元。
雖然中國與世界的貿易量雙向均大幅成長,但西方國家發現他們在中國市場的占有率不但沒上升,許多領域反而節節下降。例如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汽車消費市場,每年汽車銷售量超過二千萬輛,但進口車的市占率不升反降。中國依承諾開放國內的金融市場,外商銀行蜂擁進入中國市場,但外商銀行在中國貸款市場的占有率還低於中國入會前的水準。全世界的知名消費品牌在中國入會後,爭先恐後搶進這個世界的新舞臺,但十五年之後,成功者少,失敗者眾。顯然中國入會所做的承諾,並沒有帶來西方企業期待的利益。如果不是中國耍了什麼陰謀手段,欺騙了世人,就是WTO的規範已經失去功用,無法馴服化外之民。無論是何者,都表示對付中國必須用新的手段,而美國選的就是雙邊的手段。
中國的入會承諾
中國在加入WTO時做出廣泛的市場開放承諾。中國在入會的二○○一年時,工業產品的平均關稅率是一二.五九%,中國承諾在八年內將將平均稅率降到八.九二%;入會時農產品的平均關稅率是一九.二八%,中國承諾在十年內將將平均稅率降到一五.○二%。不只降稅幅度大,中國同時答應所有承諾的關稅都是約束關稅(boundtariff),也就是一旦降到承諾的水準,將來只能調降,不能調升;如果調升,利益受損的會員國可以求償。中國所有產業部門均被要求開放,幾無倖免。例如入會前汽車的進口關稅是七○%到一○○%不等,中國承諾於六年內降到二五%,而且取消進口配額的管制。如果對照同時入會的臺灣,僅承諾將汽車關稅由三○%降到一七.五%,分十年調降(二○一一年執行完畢),且調降期間還保有配額的限制,中國對汽車市場開放的承諾,大膽而俐落。美中貿易戰發生後,中國政府在二○一八年七月自發性的把汽車進口關稅從二五%再降為一五%,低於臺灣的關稅,更凸顯其對國內汽車產業的競爭力充滿信心。
中國在入會時也同時簽署資訊產業協定(Information Technolog yAgreement ; ITA),在五年內把約九成的資訊產品關稅降為零,包括電腦、通訊設備、半導體產品等。這項承諾後來證明是中國加入WTO最有成效的承諾,中國在很短的期間內就成為全球最大的資訊產品生產國、資訊產品的最大出口國,同時半導體產品也成為中國最大的單一進口項目。雖然中國政府積極設法進行半導體產業的進口替代,但顯然也認同ITA開放帶來的利益,於二○一五年和美國聯手促成第二期ITA協定的簽署,把零關稅的產品範圍進一步的擴大,其中中國的零關稅項目由第一期的四一八項增為四二五項。這項協定也是兩岸電子資訊產業鏈得以無縫接續的重要根基。
和ITA相對照,中國在入會時拒絕以簽署《政府採購協定》為其入會條件,但承諾入會即啟動簽署的程序。入會後,中國拖到二○○七年才提出參加《政府採購協定》的承諾文件,但因誠意不足,不為各國所接受,此後歷經六次文件修正,迄今仍未完成簽署。中國在文件中顯示願意向國際開放的政府採購範圍,不論是開放的機關或開放的金額門檻,都與西方國家的期待相去甚遠。例如機構部分,二○○七年提交的初始文件只包括五十個中央機關,二級機關(省和直轄市)以下和國營企業一概不在開放範圍內。其後的修正版本雖略有放寬,但距離西方國家的要求仍然遙遠。在沒有國際條約的約束下,中國的《政府採購法》第十條明定「政府採購應當採購本國貨物、工程和服務。」而所謂本國,還不一定包括在中國投資的外國企業或合資企業。中國入會後,政府採購金額以超音速成長,二○○一年時政府採購金額是六四三億人民幣,二○一九年膨脹到三.三○七一兆人民幣,一般認為這數字還是低估的。外商看著政府採購大餅的年年成長,只能垂涎三尺,卻無計可施。
中國在入會前,除關稅外,有各種進口配額的管制,配額大部分保留給國營企業使用,而且數量多少也不很明白。入會時,中國承諾廢除所有工業產品的配額,只以關稅配額的型式保留部分農產品的進口數量限制。這項承諾,使中國廢除了至少二四○項工業產品的配額,除上述的汽車外,還有冰箱、映像管、錄影機、輪胎、照相機、手錶、摩托車、石油等等。取消了配額,使大部分的進口執照變成沒有必要,中國承諾對進口執照的申請和核准保持透明性。配額的取消對國營企業產生巨大的衝擊,必須以別的方法加以救濟。
中國在入會前,對貿易權也有嚴格的限制。在中國投資的外國企業,就本身所生產的商品有出口的權利,就生產所需的原材料有進口的權利,但超越生產之外的商品就沒有進出口的權利。進出口的權利叫外貿權,外國企業在中國享有外貿權,但限於和本身生產相關的運作,不可以進口商品轉賣,也不可以代替別人出口商品。而外商在中國完全沒有內貿權,不能有國內販售行為,即便是自己在中國本地生產的商品,也必須交給國內廠商銷售,不能自行販賣。中國在入會時,承諾賦予外商外貿權和內貿權,包括合資和獨資的外商,不過開放時程有先後之別。即使中國政府向來視為敏感的商品,如化學肥料和石油,也承諾在一定時間後開放內貿權。只有歷史悠久的國家專賣品食鹽和香菸,不賦予外商內貿權。內貿權的開放,讓外國品牌在中國市場的競爭獲得立足點的平等,也讓外國的零售商如沃爾瑪、家樂福等獲得合法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
入會前,中國的服務業十分封閉,只有少數行業、少數城市,試驗性的開放給外國廠商經營,例如少數外國銀行被允許在一級城市經營外幣業務。各國在入會談判時,都看準中國服務業市場的巨大潛力,要求開放的壓力很大,中國因此承諾開放的幅度也相當大。若以不同行業、不同貿易型態別的開放與否衡量,中國承諾開放的比率是五七.四%,甚至高於已開發國家在烏拉圭回合後承諾開放的平均水準二。例如在金融服務方面,中國承諾在五年內,允許外商銀行在中國開展所有銀行業務:入會時立即開放部分城市供外商銀行承做外幣業務,但限於服務外國人和外資企業;兩年內將開放外銀承做人民幣業務,以本國企業為對象;五年內外銀將可承做所有銀行業務,並取消區域營業限制,實現國民待遇。
世界工廠的魅力
中國自二○○一年加入WTO後迄今,進出口雙向均成長七倍以上,一舉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家,關稅也降到相當低的水準,為什麼西方國家仍然指責中國市場封閉難進?我們如果仔細看中國對外貿易的內容,可以發現中國的貿易主要是為生產服務,不是為消費服務的。中國的進口品主要是生產原料、中間財和設備,供外銷生產和內銷生產所用。關稅的下降,其實對外銷生產的影響不大,因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建立了加工貿易的體系,加工出口所需的原料、中間財、設備都可以免稅進口,只要確定加工後的產品出口而不內銷就好。因此入會降關稅的主要受惠者是加工內銷的生產事業,他們可以較低的成本取得所需的外國原料或中間財。因為貿易權開放了,因此內銷的生產事業必須和進口的產品競爭,國內生產不見得有競爭力。但中國的諸多體制設計,使國內生產大部分時候都較直接進口更有利,各種對生產活動的優遇措施,使中國很快成為世界的工廠。重生產,輕消費,本來就是「重商主義」的傳統,中國自計畫經濟時代以來,就是不折不扣的重商主義者,改革開放也沒有改變這個信仰。
例如在汽車業方面,中國在入會時大幅度降低關稅,取消配額管制,許多人擔心中國的汽車產業將全面消失,事後證明這種擔憂是杞人憂天,中國的汽車產業不僅未消失,而且現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車生產國和消費國。中國汽車年消費量超過二千萬輛(二○一九年乘用車和商用車合計銷售二,五七七萬輛),九成以上是本地生產的,進口車占比不及五%。全球的知名汽車品牌,不論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系列,在中國都設有合資工廠,以「地產地銷」的方式服務中國的消費者,進口只作為產品線缺口的補充之用。國際大車廠採取在中國地產地銷而不進口的原因很簡單,前者較為有利。進口必須負擔二五%的關稅,本已構成進口車競爭的劣勢,如果加計國內稅的影響,則差距更大。中國的國內稅包括加值稅(一七%)、消費稅(五-五○%)、汽車購置稅(一○%)等,雖然國內稅對進口車和國產車一體適用(國民待遇),但所有國內稅的課徵,都把進口關稅計入為稅基計算的一部分,因此稅率雖同,但稅負墊高了。以一輛二○○○cc的進口汽車為例,適用二五%關稅、一○%的消費稅、一○%的汽車購置稅,總稅負比同級的國產車高出約三三%。
國際車廠幾乎都是以五○-五○合資的方式和地方政府合作生產汽車,例如市占率最高的德國福斯和上海汽車合作,美系的通用汽車也是和上海汽車合作,日系的豐田和瀋陽的第一汽車合作,也和廣州的廣汽集團合作,美系的福特和長安汽車合作,韓國的現代和北京汽車合作等等。中國政府不允許外國車廠擁有超過五○%以上的股權(直到最近美國特斯拉的投資案才破例),是為確保中方的經營控制權。對於外人投資的股權限制,是目前WTO所不規範的範圍,當初中國入會時,也沒有做出相關承諾。近年美國和歐盟鑒於中國利用外人投資的限制,限縮外商市場參入的機會,或脅迫換取外國企業的技術,要求與中方進行投資協議的談判,但迄今尚無具體結果。
其實,從汽車業的角度觀之,和中國地方政府合作,恐怕是突破市場參入障礙最好的方法。外商現在雖有了內貿權,但若沒有地方政府的合作,銷售也仍極為艱難。中國的土地都控制在地方政府的手上,沒有地方政府的協助,汽車廠、經銷商、維修廠所需的龐大土地取得將十分困難。地方政府有許多行政資源可以影響汽車的銷售,包括公務車採購、地方擁有或管理的計程車車隊、汽車牌照的管制,甚至交通規則,都可以構成銷售的助力或阻力。在中國的城市旅遊,可以明顯看到汽車品牌的地域性特徵,在上海滿街風行的福斯汽車,到了北京就變成少數族群。地方政府對汽車業有特別的偏好,汽車是「火車頭」工業,產業關聯效果大,一個大車廠對GDP的貢獻很大。中國的主要城市幾乎都熱衷汽車產業,沒有機會吸引外商投資的城市,也可能發展自主品牌,例如安徽的奇瑞、浙江的吉利、廣東的比亞迪等。
有地方政府的熱心支持,加上中國市場正處於汽車消費起飛的風口,許多國際車廠在中國市場獲利相當豐厚。例如中國已經成為美國通用汽車獲利的主要來源,二○一九年通用在中國的汽車銷售達三○九萬輛,超過美國本土銷售量的二八九萬輛;同年通用的全球銷售量約七七○萬輛,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不言可喻三。在二○二○年爆發新冠病毒之後,川普政府提供通用汽車紓困補助,但面對通用公司在中國的巨大生產量和就業量,川普十分不滿而口出惡言,指責通用公司是「輸出就業」。
中國地方政府對於生產性投資的支持,不遺餘力,是中國成為製造業天堂的重要支柱。晚近中國大力發展電動車,企圖在新世代的汽車產業中彎道超車,一舉凌駕西方老牌的汽車製造大國。為達此目的,祭出各種電動車的優惠措施,包括免徵汽車購置稅、提供購車補助等。地方政府響應政策,紛紛加碼,例如電動車可以優先取得牌照,免受牌照數量的管制。在政策加持下,中國很快成為全球電動車最大的市場。美國電動車龍頭特斯拉於二○一八年獲准在上海市設立海外第一個生產工廠,中國政府破天荒的同意特斯拉可以獨資,不須有當地的合夥人,並且提供了浦東新區一塊八六公頃的漂亮方正土地。特斯拉的超級工廠(giga-factory)從二○一九年一月破土興建,在同年一二月就生產出第一部Model三的電動車。如果沒有地方政府的積極協助,這絕對是不可能的任務。正式生產後不久,就碰到新冠病毒的流行,上海也遭封城,但解封以後,地方政府使出渾身解數,協助員工返回工廠復工,使生產線很快恢復正常運轉。據報載Model三基本款在中國售價二九一,八○○人民幣,扣除政府補貼二○,二五○人民幣,消費者實付二七一,五五○人民幣,和美國市場的價格相當。
在中國生產銷售比進口銷售有利是中國貿易量不斷擴大,但各國仍感覺中國市場封閉的主要原因。為了支援汽車的在地生產,中國必須進口國外的汽車零組件,為了減少對進口的依賴,政府有許多政策鼓勵汽車零組件產業的發展,因此也帶動國內外企業對汽車零件產業的投資,使中國也變成了汽車零組件的生產大國。中國的汽車生產量雖然驚人,但品牌眾多,車型繁雜,單一車型的數量不一定很大。許多在中國投資有成的汽車零件廠,為實現經濟規模的效益,零件除供中國本地汽車生產需要外,也出口供應境外其他工廠相同車型生產的需要。國際車廠的生產鏈跨境調度,形成汽車零組件雙向貿易同步成長的現象。
結構性阻礙
美國在一九八○年代和日本打貿易戰時,對日本最大的抱怨是日本的內銷市場雖然開放,但難以進入。日本的關稅很低,也沒有其他進口管制,在日本國內行銷,不論是自建通路,或委託本地廠商代銷,也看不出什麼特別的行政歧視或法規限制,但產品就是賣不進日本市場。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後來把這些看不見的行銷障礙,統稱為「結構性阻礙」。日本的結構性阻礙主要來自日本特有的企業關係和商業習慣,它形成一個封閉的交易網路,外部的成員很難打進去。美國後來啟動對日本的雙邊談判,企圖消除這種結構性的阻礙,但談判還沒有具體結果,日本企業已經因為這種結構的特性,逐漸失去國際競爭力,美國對於所謂「結構性」問題的關心也很快就雲消霧散。
今天中國的內銷市場,也是表面開放,其實銅牆鐵壁,打不進去,中國也明顯存在「結構性阻礙」,但和日本不同,阻礙不是來自企業,而是來自政府。
中國在入會前,內銷市場原則上不開放,只有在特殊情形下,安排少數的例外。例如國際零售業的巨頭家樂福和沃爾瑪分別在一九九五和一九九六年以合資的方式進入中國,但限制在少數城市經營。中國在入會時,承諾開放內貿權,讓外商進入國內零售市場,不受股權和地區的限制。因此自二○○二年以後,國際零售業的大廠爭先恐後進入中國,瘋狂展店,一年展多少家店變成許多企業進軍中國的工作指標,好似展一家店就等於打下一片江山。除家樂福和沃爾瑪之外,還有來自臺灣的大潤發,來自英國的特易購(Tesco)、瑪莎(Marks & Spencer),來自德國的麥德龍(Metro),幾乎無人缺席。這些國際的大軍團,兵強馬壯,糧草充足,曾一度打得中國傳統的零售店落花流水。然而二十年後的今天,這些外來軍團紛紛拋戈棄甲,不再戀戰,把辛苦建立的通路和商店賣給中國本地的同業,撤出中國,只剩沃爾瑪仍苦撐頑抗。二十年來的攻城掠地,有如黃粱一夢,大起後大落,中國的市場還是還給了中國人。到底是怎麼回事?
在計畫經濟的時代,地方政府控制了地方零售的通路。改革開放後,零售業是個體戶和小型企業的樂園,因為市場進入的門檻不高,資本要求不大,但它們建立的通路零散而缺乏整合,即使是政府擁有的大型零售商也只是地方割據的霸主,沒有能力從事全國性的行銷。國際大型零售業的進場,帶來中國的通路革命。它們以大規模經營的模式、現代化的採購、物流、行銷技術,提供消費者更新鮮、更低廉、來自更遠地方的產品。國際大型零售業擁有的這些優勢是地方政府的天然夥伴,它們和地方政府合作,進行土地的開發利用,帶來客流、帶來商機,使土地的價值提升,而土地正是地方政府最寶貴的資產。國際大型零售業不只開發自用的賣店,它們開發大型的商場,帶來群聚式的投資效應,例如賣場的周邊經常被各式餐飲店和娛樂設施所包圍。若無地方政府的協助,大型賣店無法取得土地;若無大型賣店投資開發,土地的價值難以提升,因此雙方是天生一對的好夥伴。
國際大型零售業通過成吉思汗式的展店,深入重要的城市,形成一個全國串接的銷售網路,打破中國內銷市場的地方割據局面。它們統一採購、統一銷售,形成一個大型的內部市場,打破了地方保護主義的藩籬。例如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食品零售通路的大潤發,在出售前擁有三九五家賣場,橫跨全國各省,縱深及於四線都市,它有全國發貨的倉儲設施和物流網,這些都是經歷長期與各地方政府合作打造起來的基礎架構,是大潤發登峰造極的神祕武器,連中國本土擁有央企背景的零售商如華潤超市,也不一定有這種能耐。例如物流的核心工程是運輸,地方政府對可以用什麼車輛、運送什麼貨物、走什麼路段、在什麼時間點可以進城卸貨,各地都可能規定不同,而且無明文可考,如果和地方政府沒有良好的溝通協調,就會四處碰壁。
通路打造成功,固然提高了商品流轉的效率,降低了末端銷售的成本,但卻不容易創造價值。價值的創造要靠引進高毛利的商品,這方面受到各種明規則、潛規則的約束。例如賣場若要銷售菸酒,必須另外申請執照,要設立洗衣部,也要另行申請執照。一般來自工廠的快速流通消費品(fastmoving consumer goods),競爭激烈,難以差異化,毛利相當有限。毛利較高的生鮮肉品或海鮮,其供應源受農業部門和其他政府機構的控制,有很高的不確定性。衛生機關的檢疫標準和流程不透明,外商大賣場在政治敏感時刻忽然被檢出不合衛生標準,或者標示不實,因而被勒令停業的事情,時有所聞。通路雖好,如果供給端掌握在別人手裡,龐大的通路,反而成了負擔。
更麻煩的是,全國性通路的效率優勢,在網路銷售崛起後,逐漸流失。實體通路必須不斷設立新據點,才能提高滲透率。新據點的設立,隨著城市規模變小,效益逐漸下降,很快達到投資的極限,網路銷售正好彌補了這個缺點。中國線上銷售的崛起,如大風捲落葉,不斷侵蝕實體通路的市場,使其獲利下滑,而且看不見盡頭。這種局面,終於使國際的零售通路大廠,或者知難而退,或者見好就收。例如大潤發曾成立「天牛網」,嘗試經營線上銷售,以抗衡阿里巴巴的「天貓」,但發展不如預期,後來在二○一八年決定賣給了阿里巴巴。家樂福則在次年賣給了目前中國最大的零售商蘇寧易購。阿里巴巴和蘇寧易購都不是國營企業,它們代表中國零售業轉型的成功案例,一個是線上銷售龍頭,一個是線下銷售龍頭。
國際的零售業者告別中國市場的不只是通路商,還有一大堆的品牌廠,包括Revlon、L’oreal等。中國消費者對西方品牌的熱愛,絕對不輸其他國家,這由中國消費者在巴黎搶購名牌服飾皮包的情形可見一斑。國際品牌,尤其是服飾和化妝品品牌,在中國難以經營的主要問題是仿冒品橫行,而政府執行智財權的保護不力,使侵權歪風難以遏止。連LVMH的杭州旗艦店也曾發生賣仿冒品的事件,使消費者對國內販售的著名品牌失去信心,寧可出國到香港、日本或歐洲等地購買真品。理論上中國遵守WTO有關智慧財產的相關規定,但執行上,距離保護原創的精神仍然相當遙遠。例如,最近北京高級人民法院判決日本的無印良品公司應賠償中國廠商棉田公司六二.六萬人民幣,並停用「無印良品」的商標於浴巾、毛巾、床單等產品上,因為這商標已經被棉田公司所註冊。法官無論如何引證法條,都難以抹去品牌的真主必須賠償山寨品的印象,明顯踐踏WTO關於國際著名商標保護的條款。
中國市場還有一項結構性問題,不可預測,但卻十分凶險,且難以控制,那就是政治風險。例如中國反對法國政府接待達賴喇嘛,消費者就杯葛法商家樂福、LVMH;反對日本東京都把釣魚臺納入行政管轄區,消費者就杯葛日本品牌的汽車;反對韓國接納裝置美軍的反飛彈系統,消費者就杯葛現代汽車和樂天在中國的超市,逼使後者自中國撤資。國際品牌因為企業發言不合國策,而遭中國消費者杯葛的案例不可勝數。消費者的愛國運動,如燎原野火,不可預期的燃起,有時候燒過頭,政府還會出來滅火。在中國經商,必須政治正確,因此要保持和政府密切而友善的關係。但即便如此,有時候因本國政府的政策,使遠在外地謀生的企業遭池魚之殃,則是難以控制的風險。
明規則、潛規則
據說中國在加入WTO前,和美國的雙邊談判進行到最後關頭時,還有幾項美方堅持但中方無法讓步的議題,使談判陷入破裂邊緣,最後由總理朱鎔基親自出馬和美方代表團進行「上駟對下駟」的談判,做出重大讓步,而讓雙方達成最終協議,其中一項就是金融市場的開放六。
中國承諾在入會後大幅度開放金融市場,尤其是銀行業務,在入會五年後(二○○六年開始)對外商銀行幾乎全面開放,不限制法人形態,可以獨資、合資,或以分行型態在中國營業,而且取消地區限制,開放人民幣業物,與本國銀行享受同樣監理標準。這項承諾,基本上是五年後給外國銀行國民待遇,當時驚天動地,超越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入會水準,也超越中國談判官員的想像。然而十年以後,外商銀行在中國的市場地位不進反退,朱鎔基的勇敢承諾證明是做不到的承諾。
只能說,開放銀行業務二十年後,銀行國家隊完勝。
表面上,中國並沒有黃牛,外商銀行已經進入中國,而且可以經營人民幣業務,在中國設立的法人銀行,基本上也享受國民待遇。設立分行者,因總行在境外,沒有國民待遇問題,只能吸收大額的定期存款,現行規定為五○萬人民幣以上。雖然外銀經常抱怨銀監會(二○一八年後改為銀保監會)對它們的監管比較嚴格,反映在外銀的呆帳比率較本國銀行低、資本適足率較本國銀行為高等指標上,但這些監理的歧視對外銀的發展影響有限。外銀發展不如預期的最大原因不是監理問題,而是市場進入的受限。外銀所受限制包括進場的資格和等待期,例如要申請成立法人銀行(子行),外國銀行母體的資產要超過一○○億美元,而且須先在中國設立辦事處兩年,績效良好,才有申請資格。如果申請設立分行,則外國銀行母體的資產必須超過二○○億美元。但這些門檻也非最大障礙,最大的障礙是境內服務據點的拓展困難。
外銀除了初始進入中國的審核和等待,此後在中國新設分行或支行,都必須要通過銀監會的「審慎性」審核,取得執照。任何分行的設立,必須由母行先提供營運資金,如果只有外匯業務,營運資金最低二億人民幣,如果開辦人民幣業務,另加一億人民幣。銀監會對分行或其支行的執照卡得很緊,有臺商銀行說,潛規則是一年最多只能拿到一張新執照,以中國四大國有銀行全國至少擁有一萬家分行和支行的現狀,外銀要追上它們的規模,至少要等一萬年。
拓點困難,使外資銀行難以取得本地的存款,也就難以拓展貸款業務。在存款不多的情形下,只能靠自有資金或母行的貸款來提供放款,而外銀與母行間資金的往來除受銀監會的監理限制外,亦受人民銀行的外匯管制,沒有外匯額度,有錢也匯不進來。
美中貿易戰發生後,中國政府在二○一九年自主性的做了一些金融市場開放的鬆綁,包括對外資參入保險市場和證券市場的放寬,但對銀行業務著墨甚少。除了把外銀分行吸收定期存款的下限由一○○萬人民幣放寬為五○萬人民幣,並准許外銀同時申設子行和分行外,對外銀最苦惱的境內業務拓展問題並未處理。銀行做為中國資金分配的核心機構,是政府控制企業資源的核心工具,不能輕易放手讓外國人主導。
國營企業
在中國即將成為WTO會員的二○○一年一月,時任國務院資訊中心常務副主任的劉鶴,出席在日本東京由亞細亞研究所舉辦的一場研討會,談到中國加入WTO的挑戰。他認為最大的挑戰是國營企業,國營企業必須進行劇烈的改革,才能因應市場開放的挑戰,他認為國企最大的衝擊將發生在資本密集的部門,如汽車業和石化業。他認為中國必須準備忍受較高的失業率,因此要加速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他提出國營企業改革的方法是股份化,讓它們在資本市場接受檢驗。他也預測,中國入會以後,過去中國產業常見的供給短缺現象將消失,反而會有供給過剩的現象,必須慎防通縮的出現。
劉鶴精準的預測入會後供給過剩的問題,至今天仍然困擾著中共的決策者。但他所預測的國企面臨的衝擊,不論在汽車業或石化業都沒有發生,甚至他認為可以完全交給民間企業經營的水泥業,國企經過一番爭扎混戰後,也屹立如山。更重要的是,他所期待的國企改革,在入會後只走了四五年的一段小路,就躑躅不前,然後掉頭逆向而行。劉鶴從二○○三年起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主任,後來擔任主任,現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對美國貿易談判的首席代表,目睹也參與中國入會後國企政策的轉變,不知到底做什麼樣的解釋?有什麼樣的心情?是此一時、彼一時,情境的發展和他的預期有所出入?還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其實劉鶴當初預測國企占有重要地位的產業部門,將出現供給過剩的現象,應該已經預知國企不會因為開放進口競爭,而退出市場,國企的產品和進口品並陳,才造成供過於求。國企在中國加入WTO後,因應進口競爭的方法是增加投資,引進更新的設備,生產更多的產品。不問是汽車業或者石化業,國企都選擇和國際大廠合資設新廠,增加國內的產能。汽車業的案例已如上述,石化業因應WTO開放的政策也相似。
投資增加、產能增加,也發生在其他資本密集產業,如鋼鐵、水泥、機械業等,造就中國成為世界的最大製造國。國企在這過程中,不但沒有退場,而且越做越大,靠的是中國資本市場的支持。
股市的蓬勃發展,使國企獲得一泓生命的源泉,但中國的資本市場仍是間接融資大於直接融資的局面,銀行貸款才是企業資金最重要的來源,股市僅居其次。各國金融市場發展的經驗是,當銀行提供企業資金的重要性大於股市時,比較容易形成企業集團,中國也不例外。因為政府掌握最大的幾家銀行,因此銀行貸款的流向偏愛國營企業也就不足為奇。自改革開放以來,銀行就是國營企業的救命繩索,國企為了生存,不斷向銀行借款,使銀行的不良放款不斷升高,在國企改革最積極的一九九○年代末期,四大國有銀行的呆帳比率曾達到五○%的水準。政府在一九九九年以後成立了幾家國家資產管理公司(AMC),移除了國有銀行的一些呆帳,政府再重新注資,使國有銀行去腐肉、生新肌,再度活過來,當時估計AMC吸收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債權,高達一.四兆人民幣。
在國有銀行的庇護下,國營企業持續擴大生產,不受市場紀律的束縛,生產過剩的產品只能出口,也造成對外貿易的嚴重失衡。二○○八年美國引爆全球性的金融風暴,使中國的出口嚴重受挫,為了挽救經濟成長,中國政府提出四萬億人民幣的刺激內需方案,鼓勵鐵路、公路等基礎建設,也要求國有銀行擴大對企業投資的支持,而大部分的新增放款都落到了國企的手上,國企又成為救經濟的主力部隊,大肆擴大投資。當金融風暴逐漸收斂,國際市場漸漸回復平靜時,中國發現國內產能過剩的問題已經到無法輕忽的程度。於是政府啟動國企的合併重整,在過程中也強制性的關了一些工廠,甚至用直接爆破的激烈手法。但政府選擇留下的國企,變得比以前規模更大,對市場的控制力比以前更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