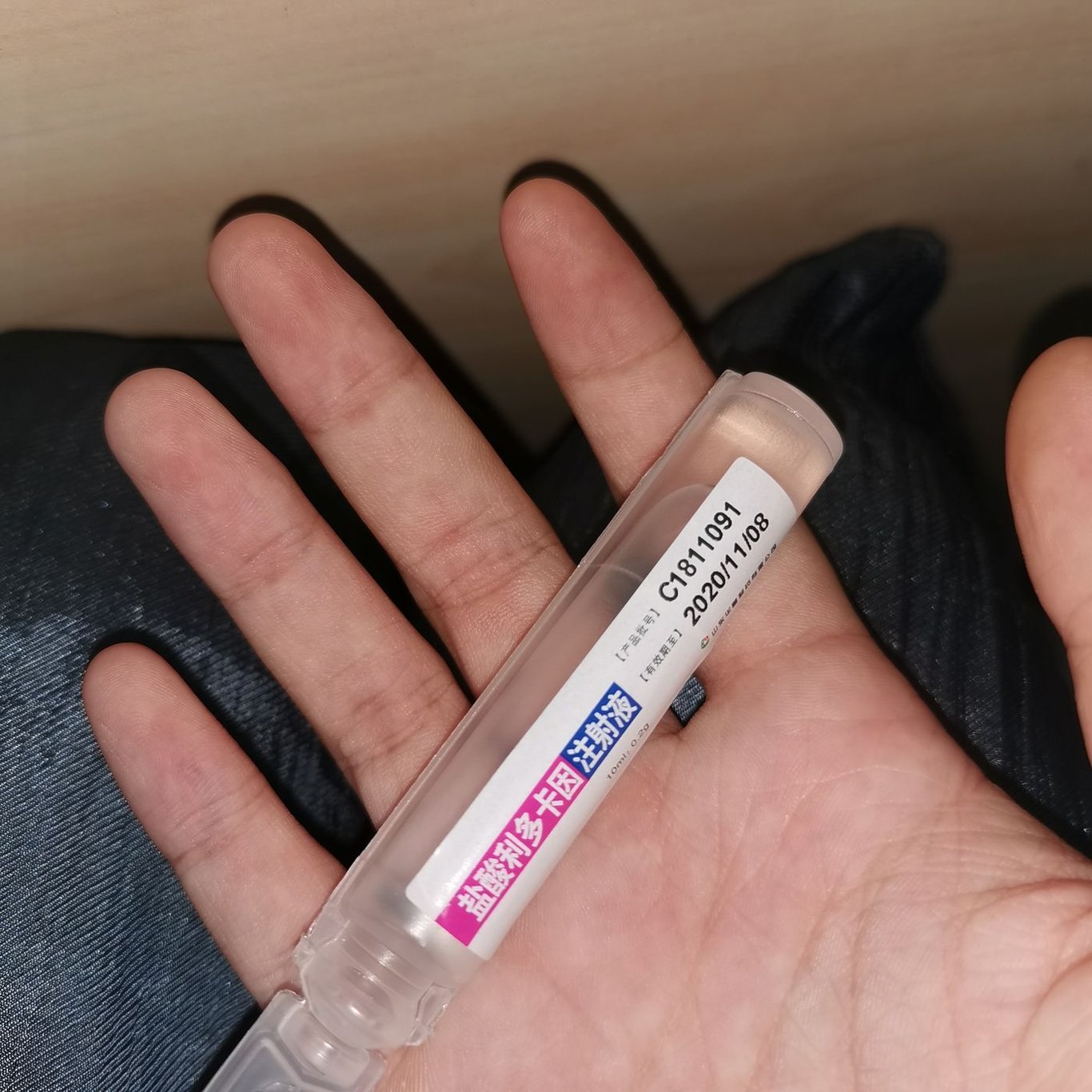儅恐懼成爲真實
01“你是子午俠士嗎?”
先從去年我的朋友遭遇過的一件事説起。
微博上一直有一個非常活躍的賬號,叫做“子午俠士”。據我個人的觀察,這個賬號會發佈的大多數是對國内女性主義議題的抨擊、恐同言論、對LGBTQ群體的污名。該賬號的關注體量很龐大,且賬號下評論和支持的人,大多都持有相同的立場。他們最習慣的操作是將對性/別事件進行討論的組織和言論進行曝光,並引導同好進行網絡暴力。
去年大概也是四五月閒,我的朋友曾發起過在他們校内、城市區域閒的獨立影展扶持計劃。因面嚮的扶持對象是LGBTQ主題的學生影像,所以在發佈后很快被這個賬號及其關注著盯上,帶上他們學校的Tag進行攻擊。
這是非常奸詐、行之有效和骯髒的做法。舉報,調動一個集體的權威以對少數群體施壓,并且扣上政治的帽子。儘管對當事人來説根本沒有這樣的企圖。
在微博上因它大體量的粉絲圍攻、而形成了一定的輿情之後,朋友遭遇了來自校内導員的盤問和警告。
導員詢問他爲什麽網絡上會出現對學校的討論,且問他到底做了什麽。始作俑者將事件操控得像是一個學校欠缺了對其學生的管教,而放任他們“進行與境外勢力有關的活動”——好大的帽子。
通常來説,這樣的行爲都會經歷三個階段(我總結的)
- 有關部門發現輿情
- 有關部門將輿情監控傳遞給學校
- 學校找到發佈相關信息的學生個人並勒令“辦事人員”將輿情消滅
但是他的導員在詢問和警告他的過程中,表現得太像一個機械的辦事人員,連基本瞭解情況的能力都喪失了。ta大概接到的指令只是“處理掉在微博上帶有學校大名的負面輿論散播者”,但卻不知道個中詳情,並不知道,我的朋友、被他盤問的那個學生本人其實遭遇了來自這個賬號的網絡暴力和基於性取向的攻擊,ta只關心的是這個賬號帶出的流量讓學校的名聲蒙羞。
以至於在盤問的時候,這位導員發出了令人發笑的疑問:
“你就是子午俠士嗎?”。
可笑之極。我們每個人、每一個邊緣的小組,作爲性少數個人的我們本身,都曾經遭受來自它和它的粉絲的攻擊。被誤認爲是這些人背後的運營者,莫説是一件荒唐的事情了,簡直是一種侮辱。我的夥伴,我的朋友都對這樣的群體嗤之以鼻,恐同者背後的邏輯和動機,大概是我這輩子永遠無法理解和共情的。而它們以舉報而沾沾自喜的行爲,不過是玩弄審查、玩弄監管的利益既得者。黨同伐異是他們的手段,扣帽子是它們慣用的伎倆,只要披上紅色的外衣,一切就都可以順從它們的心意。
02 從“瞭解情況”到“建議刪除”
這樣的辦事邏輯,在我(們)身上并不是第一次發生。我覺得至今我對很多事件已經趨於麻木了。即便如今我已經甚少接觸社群的活動,但是這樣的攻擊帶來的陰影卻是無法抹去。
今日午時接到來自導員的兩通電話,直指此前發佈過的文章。
第一通詢問我是否有在“外網”發佈一篇關於新冠肺炎、上海疫情政治的文章,我承認,並開始了之後的溝通。
一開始詢問我的文章内容是什麽,并且試探我個人的態度是否是配合這樣的盤問和所謂“瞭解情況”的體察的。我解釋說Matters并不算作是外網,而是一個華文寫作平臺;并且說文章無涉任何政治立場,而僅僅是講述從二零二零年到二零二二年我生活在上海自身經歷的與疫情相關的情緒和生活的;更重要的是,我並不想表達我對當前防疫政策的任何帶有明顯立場性的評價,而只是想要記錄我自己的生活和情緒。因爲每天觀察許多新聞,我認爲作爲人最基本的態度是對不公平現象感到憤怒,而記錄下這些憤怒是一種開解自身情緒的方式。
我想象中這樣的溝通可以讓她能夠理解到我的寫作初衷。儘管她在打電話給我之前,甚至都沒有讀過我的文章到底寫了什麽。我將文章鏈接貼在我個人的社交媒體,且沒有屏蔽任何人。從想要分享,到發佈開始,我的態度都是如此。
而第二通電話則完全不同。話術完全改變為希望我將文章刪除,起碼是“不要在被搜索到,再被看到”的情況。我詢問是否是因發表在朋友圈,或之前嘗試發佈在微信公衆平臺而被違禁,所以遭遇到了某些人的舉報。但是被否認。對方直指是我發表在Matters上的文章。
大抵我之前的寫作從未獲得如此體量的關注,以至於,我沾沾自喜的、被大家認可的成就,已成爲“有關部門”眼中的把柄。
這樣“規勸”的立場在於一種他們表現出的“對學生的保護”。不可否認,可能這個邏輯某些方面是正確的。審查的部門無法直接找到我,而是通過聯絡學校的輿情處理人員,再將壓力慢慢下發到每一個可以直接聯絡到我的人身上。我不需要直接面對某些能夠左右我的生活的人。所以這個傳話筒,可能是導員,或者我的導師。話術最后都变成一种“对年轻人的规劝”,帶著他們認爲經驗之談的、應對這個機器的姿態:
“先讓這波疫情平息,先將文章刪除,不然以後你的所有信息都會被監控,這樣的滋味不好受吧?”
相伴而來的,還有對“我能夠順利在校内讀書”這件事的承諾,宣稱并不會對我個人的評價形成一個污點。
我承認,我是被説服了。甚至説,我已經對這一套話術和運行的機制有些過於瞭解,以至於在這樣的熟練中越發的無奈,因爲我知我自身無法完完全全地抵抗它。
曾經被詢問的朋友,也是選擇與我相同的辦法處理和“了結”這件事。我們無法找到別的方法能夠避免來他們的盤問和騷擾,以至於在身爲學生身份的當下,這是一種無奈的妥協。但我們也討厭這樣的妥協,最後只有對自己的責備和無奈。
如果說這篇文章是上一篇文章的後記,那麽產出這個的後記代價實在是太大。這個過程對我自己是一種消耗,甚至是情緒上完全負面的影響。我無法從追問中獲得“到底怎樣的内容是不被允許發佈”的信息,甚至,我認爲Ta們大部分握有權力,執行行動的人,都未見得真正地去閲讀過我的那些文字,就像我的朋友被誤認爲是那個始作俑者一樣。
人們不見得能夠共情和瞭解作爲性少數者的我們是怎樣生活的。又或者立場是最容易被關注,也最容易被誤解、最容易被降下罪名的。
03 留存
從未有這樣一個時刻感謝新的“技術”和“網絡”對我一息尚存之地的保護。發佈在matters上的文章“無法遭受永久刪除”,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了。雖然這不太能得到來自網友的繼續支持和在評論區的鼓勵與討論,但我已經足夠開心。
目前來説,分佈式節點仍舊可以閲讀之前我發佈的文章:
- https://matters-meson.net/api/cdn/10vbg9/ipfs/QmaHjfvBfiEVq31DbtzxnZ9hoivLNUDnfSwfrXNPMYEFq7
- https://ipfs.io/ipfs/QmaHjfvBfiEVq31DbtzxnZ9hoivLNUDnfSwfrXNPMYEFq7
- https://gateway.ipfs.io/ipfs/QmaHjfvBfiEVq31DbtzxnZ9hoivLNUDnfSwfrXNPMYEFq7
但出於我對這一技術的有限知識,我不確定它是否真的可以“永久留存”。我已經被這樣的審查毀滅過很多次我自己的作品,以至於我至今無法回想我二零二一年得知小組賬號不復存在那個時刻的痛苦。
曾經我認爲是我對簡體中文平臺太過於信任,以至於在反復地試探過後終究還是接受了那些不好的結果。但是現在,在一些無法拒絕的邏輯背後,還有更多對自己的責備:我是否是太過於天真或相信言論自由的空間,以至於自身一定要遭遇一些不被允許的禁令、刪除的游説,才能夠讓我真正地意識到“這個世界的規律就是這樣運作”的?
又或者説,將這樣的權力運行方式内化,其實也是一種不得以的退步。我們不斷接納和認同這些信息,并認爲理應如此的過程,想想都是深深的恐懼。
我曾經數次在與一些朋友的辯論中被批評為是一個“不夠激進/基進”的人,在於我過去的經驗認識,會希望真正地與一些人共存,與一些事件共存。或者說想要贏取一些人的同情和關注。
二零二一年末時,我對自己說計劃寫下一個主題的文章,在之前的文章裏也提到:
二零二二伊始,閱讀與寫作計劃 | 備份 二零二一,我親歷的性/別事件: 這其實更像是一(自認為的)行動者在社群裡的觀察和體會。我很少在博客裡提到,性別研究學生的身份其實與我LGBTQ小組行動者的身份是分不開的。而2021年,我與我的朋友們身上都同時發生了許多不公平的事件:小到日常活動叫停,大到我們的公眾號被封禁(是的,就是七月份那一波“未命名公眾號”事件),我們個人被警察找上門都與此相關。過去三四年裡,我不同程度地參與了大陸不同地區的lgbtq活動,雖然地區和場所有所局限(我個人的學生身份),但是體會卻都是類似的。 很需要用寫作以記錄,不然,總有一天會忘記,或被忘記。所以這注定是一篇並不“積極”的文章了。
如果說這些内容是我對自己行動和經驗的記錄,不若說是一種對策略的記錄。
但諷刺的是,我相信,我,我的夥伴,我們之中任何一個人,都不想要習得和積纍這樣的策略。因爲這個經歷,實在是太不好受了。但是沒有辦法,許多事情真實地發生,那些話真實地在你耳邊響起。你恐懼的事情成爲真實,而不是你虛構的假想敵。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