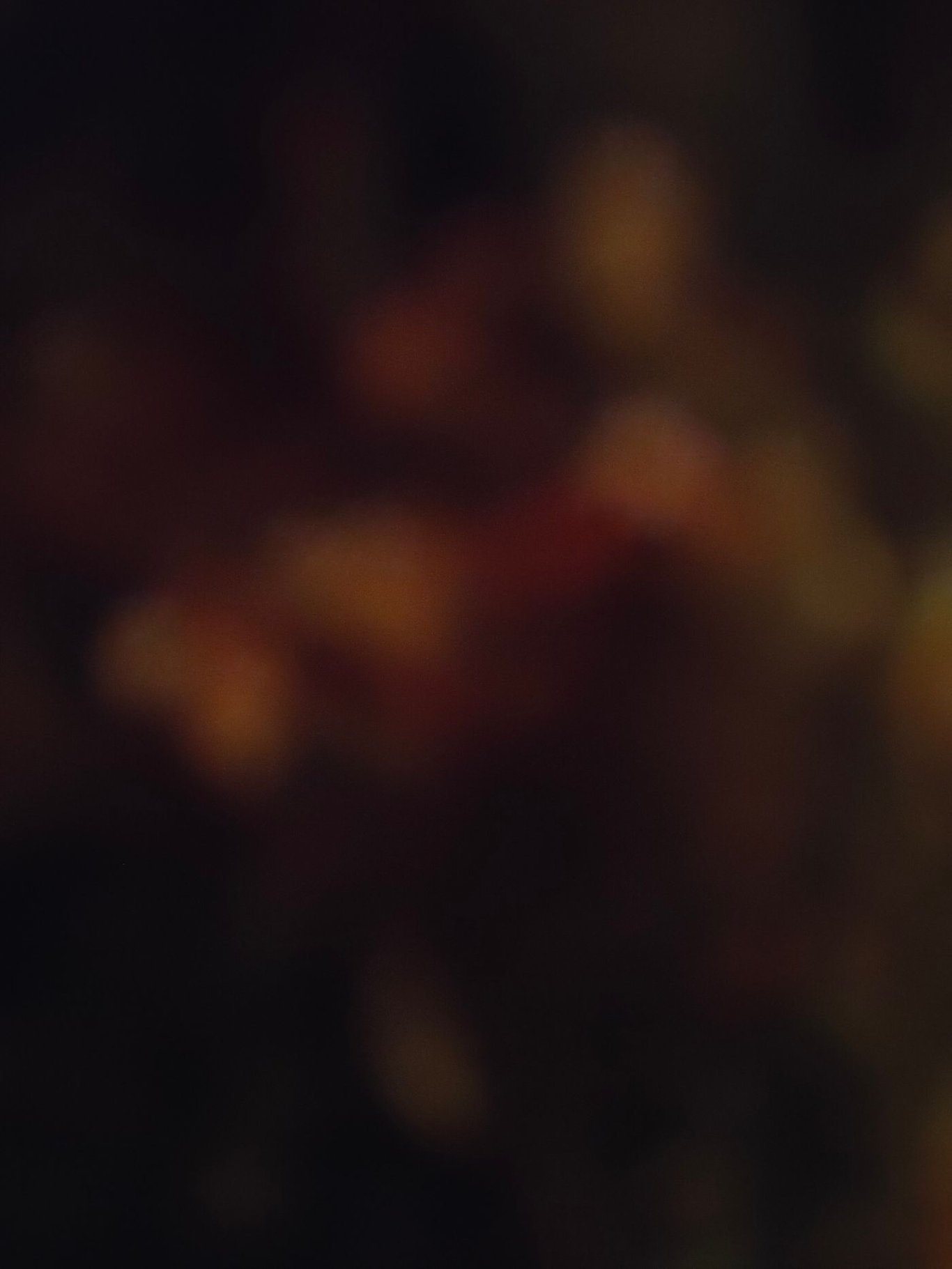翻译:当代艺术中的思辨主义与去中心策略
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将美学作为构建“真正的政治自由[1]”和公民自治的基础学科。美作为一种“生活形式”将有可能解决始终纠缠于人类的理性状态与原始状态,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这也是席勒的当代性所在。面对这种对立,席勒表明了缓和两种状态之间关系的必要性,以使得第三种状态得以展现:
这种既不以肉体或精神的方式决定灵魂,又在这两方面都有效的中间特性,称得上是自由的特性。如果我们说,肉体状态具有感性的特性,道德与逻辑的状态具有理性的特性,那么我们可以将这种真实的且具有积极特性的第三种状态命名为美学状态。[2]
因此,根据席勒的观点,美学是一种从三个尺度上判断客体的方法:感性(通过肉体),道德(通过意志),理性(通过理解力)。两个多世纪后,哲学家们在“思辨实在论”或“唯物现实主义”(尽管他们可能会对这些标签提出异议)的派别下联合起来,试图摆脱康德的影响,建立一套真正的知识体系,以把握客体自身的独立性,换言之,事物即事物本身。对于不同的方法论(例如思辨)进行过审视之后,知识将基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改变其状态,并且后者无需前者的限定便可以被认知,这便是相关性。由Quentin Meillassoux[3]与Ray Brassier[4]提出的进入“大外部”,可以被视为思想扩展的另一种路径,这一理论自2007年被创立以来,迅速地传播到了形而上学领域之外,对美学及当代艺术领域也产生了影响。
然而,面对基于主体与客体完全分离的知识系统,我们如何才能使感性与美学的层面都更加合法化?当只有抽象概念与科学的叙述才能阐明真相时,艺术的位置在哪里?《唯物现实主义艺术》[5]和《思辨美学》[6]的出版揭示出了现实主义的局限性与可能性,并表达了对于知觉的怀疑[7]。
在现如今信息与传播技术越来越依赖于美带给人图像的愉悦感之时,一种贯穿于传播与新媒体研究中的[8],以忽略内容的方式对于艳俗图像的批判,只能称之为是一种“按摩”,而不是解放。早在1795年,席勒就曾经断言:“在一件真正美的艺术作品中,形式大于一切,而内容并不重要。因为形式可以对所有人产生效力,相反地,内容只能作用于一小部分人群。”他也许没有料想到政治和金融对于美的操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今天是否应该忽略感性、知觉与物质,并且仅将理性作为一种知识,置于美学结构的均衡之中?独立于观众的作品会是什么样子?它会以什么形式呈现?我将首先从经验的角度,以两位当代艺术家尝试过的创作策略为例进行研究并寻找其来源。随后,我将研究美学以何种方式对上述问题产生了影响,及其所处的背景。
伊恩·程,一件独立的作品?
在一个平面上(直接投影到墙壁上),我们可以观察到运动的图像。它的呈现形式与电子游戏相似:一个由山谷、沙地和绿色植物构成的单调的三维景观(很明显的像素颗粒使我们不会误以为它是真实的),还有些人类、非人类、植物相混杂的物体和符号遍布在这个场景之中。人类的眼睛有时会变成鲜红色;那些石头和植物仿佛都能自己移动甚至悬浮起来,并且它们的颜色会随着时间流逝而产生很大的变化。这些物体上都有一层多孔的软体组织:它们可以互相结合,就像一个人的腹部装饰着一堆高耸的草丛。它们有时用可被人类理解的语言(英语)交流,有时用一种虚拟的语言进行交流。不仅如此,它们似乎可以组织起来,制定共同的行动。但是,整个画面运行的节奏一直是断断续续的,不论向上或向下,放大或缩小,穿过其他物体或落到地面,都使其成为一个非线性的事件。有时,图像仿佛卡在了某个视角,会停顿很长一段时间。

我试图寻找眼前这个画面中的逻辑,并预测其下一个动作或定义出故事发展的轨迹。对我而言,这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画面中所有的物体都是虚构的。我必须抛弃我的惯性思维以及既有的知识,全神贯注于这个没有规律可循的感性空间。实际上,这些元素虽然不遵循我所理解的现实世界运行的规律与准则,但它们却呈现出了某种有组织的集体行为。标题为《Droning like a Ur》(2014)的动态影像作品,其形式并不是一部预先录制好的视频或电影,而是根据算法对于图像的“实时模拟”,艺术家伊恩·程[9]将其称之为“Simulation live”。该算法是一个由计算机生成的程序,其具有非常复杂的对于环境状况进行分析与回应的功能。依靠强大的算力,其反应速度已经超过了人类的思维。伊恩·程也会给这些由算法生成的元素下达指令,这些指令通常很奇怪,例如“给物体遇到的所有东西起名”。通过强大的自主学习能力,物体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进行演化与发展。就像在传统的电子游戏中一样,它们不需要玩家从外部对其进行操控。

人工的与天然的
如果说伊恩·程的“实时模拟”是一种在严格的算法机制下的产物,那么我们倾向于将其的人工属性视为一种有机成分。例如一些大胆的尝试可以使“实时模拟”出的物体的进化近乎于表观遗传生物学现象:进化的胚胎阶段不由程序决定,而是与具介质即表观遗传相关。一些漏洞对环境的影响使胚胎呈现复杂化的特征。在伊恩·程的模拟中,异常复杂且快速的算法机制使人们以为这是一场活生生的进化。然而有趣的是,伊恩·程将这两种特性放在一起,它们并没有相互融合。超越人为的(Hyper-artificielle)“实时模拟”可以产生一种类似生命的图像。于是,无论我们如何尝试对模拟的本质内核进行研究,以更好地了解我们人类自身的特性,都将是徒劳的。甚至拥有人工智能科学硕士学位并且是作品创作者的伊恩·程也无法做到。相反,这便是人工与自然生命之间的差异。是什么一直维持着这些模拟不会被人工和机械所触及。有哪些人类或生物的特性是“实时模拟”永远也无法仿制与重现的?此时,伊恩·程的作品成为了一种符号,满怀焦虑地对这种差异以及人与机器之间越来越糢糊的边界进行着发问。
自主性与依赖性
关于“实时模拟”,伊恩·程表示:“我们能感知到这种模拟,但它并不在乎我们。[10]”实事上,这件作品以自主的方式运行,它超越了电影或表演这些给观众留出位置的艺术形式,即便它们也可以运动。也就是说,其完全不被外界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政治环境所影响。如果作品按照如此强大且复杂的算法所设定的轨迹运行下去,那么观看它的人,甚至创造它的人都无法对其之后的行动进行预测。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它的运行和发展不能被我们所理解。创作者或观众与作品之间建立了一种对彼此出现的状况无视的关系。当某个观众走进展览时,只能了解到作品当前的状态,而非全部内容。他无法对其预测或判断,只能被动地跟随作品的节奏。审美上的评判与作品本身之间的不再有联系。晦涩之处在于,它成为了自身历史的书写者,一个完全独立运行的主体,不再需要通过观众或创作者表达其含义。这种独立的形式加上其有机的内容,使“实时模拟”的每个部分都成为了主体而不仅是一个客体的图像。只凭模拟就可以构建出一个世界,一个时时刻刻都在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正如我们将作品中的人工图像与有机图像同时放置在一起样。同时保留主体与客体的特性与质疑它们之间的边界都非常重要。这也开始了一场对于伊恩·程的作品及其所处时代的有趣的思考。正如哲学家Graham Harman提出的“面向客体的哲学[11]”。
从审美体验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假定,使接收者更加兴致盎然的状态带有康德哲学中崇高特征:在这种具有自主性的,叙事晦涩的作品面前,我们遇见了一种比我们的理解力更高的力量。当客体在生与死的微妙边界间振荡之时,崇高也可以朝着数学的(精确的)或动态的方向发展[12]。被拓展后的康德美学还指出了人类理解力的局限性,且其具有双重的价值:提醒接收者自身的有限性,以及向接收者展示超越自身能力的可能性。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事情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一天,在伊恩·程编写“实时模拟”的运行程序时,发生了错误,并且机器突然自动关机。艺术家神经紧绷,脸上浮现出些许忧虑。他再次接通电源,重新让所有的物体从同一个初始状态开始运行。然而,由于其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导致其无法复制出与上次相同的运行路径。当这个Bug出现时,伊恩·程的表情很异常,因为这中间出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这个作品一直在模拟生命的运行,但在它停止时,它也模拟了死亡。这件作品如此难以理解且无休无止,但它却以一种既脆弱又独立的形式呈现在了我们眼前。作品不再被理解为客体被观看,而是成为了主体。。对于伊恩·程来说,“实时模拟”是活的,所以它也会消亡。创作者注视着它的发展,如同看着一个孩子长大。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模拟的生命,我们有对其产生情感的趋势,并且继续质疑人与人造物之间的边界。
因此,当作品脱离人类自主运行时,它将具有崇高的特性:晦涩不明,观众完全无法理解,并且处于无限优越的地位。在这些条件下,客体的知识永远无法被获取。相反,只有当它呈现出一种与人类依赖的关系时,它才会作为主体,向接收者开放其含义。观众的精神出现了一种知觉的循环,其试图体验作品晦涩独立与开放明确的两个方面。如此,作品就像席勒和康德所描述的那样,激发出了某种审美活动。但是,一方面,这种现象只在极端对立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作品被认为是超出人类理解的,不稳定的,以近乎生命的方式自主运行),另一方面,这种循环只发生在观众的精神层面。观众处于艺术作品的客体位置,并且在失衡的中心,最终,观众会对作品产生某种依赖。这可能是问题所在。现在,让我们从作品中主体不受约束的变动与偏移开始,对一组使用另一组策略,并且赋予客体对象思辨能力的作品展开研究。

皮埃尔·于热,去中心
在德国卡塞尔的卡尔萨维公园(Karlsaue Park)中,一个人正坐在水塘边的一堆混凝土板上读着一本博尔赫斯的书。一条白色的瘦狗在周围游荡,它的一条腿被染成了亮粉色。一个由混疑土浇筑的,半躺着的裸体女人雕塑隐藏在高高的草丛里,头上顶着一个蜂巢。这件由皮埃尔·于热[13]创作的名为《Untilled》(2011-2012)的作品展于第十三届卡塞尔文献展。当我们站在这件作品前,我们并不能用肉眼看到其中发生的所有事情。《Untilled》由各种不断发展的生命或非生命实体组成:如致幻植物、蜜蜂、秧苗、种子等等。于热意图构建一个“物质、生物与矿物在没有我们的状态下不断生长且强烈地变化。没有任何组织、叙述和表达”的空间。


几个月后,在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皮埃尔·于热回顾展[14]上,呈现了这样一件作品:一个女孩在一块黑色的冰面上滑行[15]。各种不同时期的史前海洋生物分布在三个鱼缸里。一个戴着鸟头造型帽子的男人坐在长凳上,和另一个人一起看着鱼缸。鱼缸中,一只寄居蟹栖息在以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的雕塑《沉睡的缪斯(La Muse endormie)》为形象做成的树脂面具中。女孩在雨中玩着伞[16],蜘蛛和蚂蚁沿着一些细线移动[17],一个男人正在听着Erik Satie的钢琴曲,一旁亮着一支罩着面具的白色LED灯管和一个随着音乐节奏变换光线颜色的立方体[18]。《Untilled》中头顶蜂巢的雕塑以及粉色爪子的狗也在这个展览中出现了[19]。


存在与现象
虽然这两个项目的语境非常不同,但是它们都表现出了某些极其特殊的美学结构,吸引着我们对其进行研究。
这两个作品都从侧面体现出了对于作品是否完全出自艺术家之手的疑惑。正如我所说的,重要的是它在展现其发生的动作,而这并不需要被观众看到。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运动,而不是一种现象。因此,我们不能先验地将其作为固定图像进行理解,我们应该将其理解成一种灌输给我们的,游走在可见与不可见空间边缘的运动。在塑造作品的过程中,于热不希望将其限制在固定的状态下,而是倾向于将其解放,置于不可控的运动中。像伊恩·程一样,于热也为作品运行的状态设定了一些条件。使其在展览空间中仍然沿着这些设定无休无止地发展。它被设定成一种类似于生命的,自由的运动,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及不可预测的运行轨迹。其没有固定的路径,并且使观众处于一种迷惑的状态。如果不了解作品创作的背景,可能就很难体会到艺术家想要传达的含义。在不描述作品的情况下展示作品,就会冒着不确定观众是否可以从其中获取意义和知识的风险。但这也使得观众花时间沉浸于作品,去认真观察,产生疑惑[20]。


也许这正是于热作品的力量所在,其不仅仅是运行在展览现场的活动。在这两个项目中,于热展现了一些可被叙述的点,它们与确定或不确定的周遭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品中的许多元素都被修饰过,使其指向某种虚构的身份:女性雕塑的头上顶着蜂巢,狗有粉色的爪子,寄居蟹将布朗库西雕塑的微型复制品当作住所。意外情况的增加使它们脱离了表现的规则,诗意且敏感,观众注视着它们并引起了某种反思。这些诗意的瞬间中不但容纳了思想,也体现了某种超越现实的自由。如果说这些项目的运行方式类似于生物的机制,那么它也会被激发出一种强烈的与现实不符的形象。它们带我们进入了一个超越我们认知的,没有约束的虚构空间。生命终于摆脱了现象的束缚,奔向真实的存在。


另一方面,作品中也体现了一些从真实事件中提取的叙述:例如在蓬皮杜艺术中心展出的电影《The Host and The Cloud》(2009-2010)中[21],出现了两个法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1977年中非共和国“皇帝”博卡萨的加冕,以及1988年对于“直接行动”成员的审判。其他作品中也讲述了各种关于反抗与镇压的历史事件。尤其是在为“业余时间协会(Association des temps libérés)[22]”创作的海报《le Procès du temps libre (Part 1-The Clues)》(1999)中,或在作品《Lucie》中,他用法语给《白雪公主》配音,使其失去原本的声音甚至身份[23]。这些叙事与低语在悄然间与政治发生着关系。


同构
为了在微妙的生命运动之间维持平衡,一方面要从事实中提取出诗意的虚构现象,另一方面,皮埃尔·于热在与观众有关的作品结构上运用了非常特殊的策略。
首先,在这两个项目中,观众不需要从作品的正前方观看。相反,观众位于作品的内部:在其中游走穿行。观众的身体将被置于一个由形式与材料相互纠缠的空间之中,这个空间不受艺术家和其他任何人的控制。由于作品没有固定的运行轨迹,使得其边界得以延展且可以将观众容纳进作品的内部。它们是多孔隙的,就像伊恩·程在“实时模拟”中编写并开发出的物体一样。因此,展览不再是一系列作品以某种形式的堆砌,而是构成了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我们无法对其每个部分进行单独分类。这就是艺术家一直追寻的:“没有分类,没有中心”。但是,与伊恩·程相比,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于热的作品并不是在一个封闭且与观众分离的画面中活动,它不仅活跃于观众的精神世界中,而是作为真正的实体存在,并且在现实空间中与所有的事物相互联动。
因此,当观众浏览作品的同时,作品也对观众产生着影响:观众是作品的一部分,作品也成为了观众的一部分。这样的孔隙性使得我们很难介定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例如,在雨中行走的人并不是皮埃尔·于热雇来的表演者,而是参与进了作品的观众,是共同构成这个作品的参与者。观众不仅被纳入了作品之中,他还在展览空间内进行着种种行为动作:他在这个空间中的行为方式将对作品中的其他元素(人类或非人类)产生新的意义。
然而,不同于需要依靠观众才能成立的那种参与性的作品(可参照Niolas Boumaud在其书《Esthétique relationnelle[24]》中提出的理论),作品将观众容纳进自身,而不是单纯地依赖观众。观众有可能走在雨中,同时手里在玩着一把伞。对于作品来说,观众并不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元素,但是一种可以使整个空间处于平衡且富有弹性的元素,其可能使作品产生新的含义,从而塑造出新的美学形态。观众并不是作品的中心,却一直处在作品之中。
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回顾展与作品《Untilled》都创建了一个使每个元素都可以平等分布的场域,使其可以在同一空间中相联系,进而构成一种知识,一种行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着作品。因此,这种作品能以席勒所描述那种的美的形式存在,但这种美并不只是呈现在观众面前,而是把观众也带入到美之中。它们旨在作为某些潜在的知识,或唤起更多的想象。观众不再处于作品的主导地位,而是与皮埃尔·于热创造出的元素一起平等地参与进其中,他们不再是作品的中心,但依然对作品负责。
我们注意到,无论在皮埃尔·于热还是伊恩·程的作品中,都有种与思辨实在论相似倾向的意志。每种为了作品而被创作出来的客体都表明了其自主性与独立性。它们生成一种假象,并向外延伸,以一种或类似于机械或近乎生命活动的方式与人类身份的边界相连接。如果没有实现思辨实在论所提出的那种绝对的分离与独立,那么它就会产生彻底的改变。
作品不再仅仅为了观众而存在,也不会将观众置于其中心地位。在伊恩·程的作品中,观众成为了一个被消除了理解能力的观察者,使得他可以完全掌握空间中所呈现出的逻辑。如果说作品的独立性和理性力量是无所不能的,那么它将把不了解其复杂机制的观众排除在作品的意义系统之外。如此,作品的意义被锚定在了无所不能的理性力量之上,进而缩减了观众的位置。皮埃尔·于热作品中的意义是开放的,他构建了一个并不排斥观众的空间。没有边界,所有的元素都可以参与进作品之中。诗意的或现实的叙事将观众引向某些明确的方向,这导致其意义并不是完全可塑或晦涩不明的。但因为它们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才有了产生意义的可能性。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去中心化的含义及其背景,让我们快速了解一下最近在人文
学科中通过去中心化修改其工作方法的现象。
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去中心化
在历史和人类学中,去中心化的概念可以改变我们将世界作为一个一整体考虑的现状,从而作为某种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的支柱。在《L'Histoire à parts égales》中,历史学家Romain Bertrand通过叙述在与荷兰人、马来人与爪哇人之间的相遇中欧洲人长期处于更优越地位的例子,提出了一种研究世界史的方法论。为此,他并没有像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从荷兰人的角度叙述历史,而是选择了从爪哇人和马来的角度。他这样描述他的方法:
然而,要参透爪哇宫廷和马来人的诗歌与文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写作的技巧、叙事的方式、语法与句式、对于情感和因果关系的修辞:这一切对于消除我作为一个外国人的震惊并沉浸于这些文本中似乎都很重要……保持对于历史的尊重是个不小的挑战,一个看似简单的箴言道出了历史“对称”的赌注:没有任何一种分析是显而易见且普遍适用的[25]。Bertrand想要改变并分散以历史学家为中心的叙述视角。他主张深入到那些“隐秘的历史材料”以外的部分,使观点多样化,并学习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寻求一种超越于历史之外的碰撞。
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
以Bruno Latour, 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和Philippe Descola为代表的研究者开启了一种人类学向“本体论”转向的趋势。人类学家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在其文章《Les pronoms cosmologiques et perspectivisme amérindien[26]》中描述了美洲印第安人文化里一个特殊的属性,即他们的“身份视角”构成了一种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自然与文化的二分法被颠覆了,人类被视为一种统一的原则,所有的肉身都将被具体化。并根据观看者的视角,人类以不同的形式出现[27]。从这一观点出发,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该论断同时也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证明了对于世界的思考以及对于现实的记述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西方的思想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因其并非处于一个以他者的原则为基础的统治关系之中,而是在一种平等的状况下。在名为“是谁害怕本体之狼?[28]”的讲座中,Castro将他这一阶段的思想定义为向本体论的转折时期。因为它触及了存在的属性: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研究证明,存在多种的思维方式,西方人所谓的多民族文化只是其中的一个概念,而不是让我们思考世界的唯一概念。这种本体论的转向也被定义为政治性的,因为如果本体论产生变化,人们也必须学习如何处理与被重新定义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因此,根据Castro的说法,这是一种他者的实践,这关系到人类与其所在的世界之间位置的差异。
在《世界性的条件:身份陷阱对于人类学的考验》(2013)中,人类学家Michel Agier提出了一些可以带动欧洲政治环境向好发展的人类学方法。Agier将他思考的重心聚焦于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并且为移民的权利而战。他将当代情景下的人类学称为“去中心化”的。这种立场与人类学家Maurice Godelier的观点一致,其既是学术性的,也是伦理性和政治性的。它在人类学家与其研究对象之间诱发出了一种交互的形式,并且双方都是积极的:“理解他人的信仰,但不一定要赞同他们,不禁止自己批评他们,并且意识到,通过他人使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Agier扩展了Godelier的思想,认为“这不再只是一个通过人类学看世界的方式去中心化的问题;而是一个通过世界的眼光使人类学去中心化的问题(在人类学家对于知识的见解上)……正是因为知识和观点的多元化,从这些知识和观点观察和表现世界,构建出了关于世界的整个人类学知识[29]。”这段话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介入了关于“他者”美学的构建,就像在Quai Branly这样的空间中“图像和对象因为移动而改变其意义,进行着彼此的适应与整合。”这必然使对象的“主体”消失[30]。对于“在民族学当下”的写作是实现“民族学家与其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的条件之一,这是一种能够适应我们所处的整个世界的他者政治。
这三个例子让我们从组织和目的的方面,对于寻求生产关于外国知识的主体去中心化取得了进展。与思辨实在论倾向于构想一个不与之建立关系的世界(独立于我们的客体)不同,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将自己锚定在一个他们自认为独立的领域,但他们只能通过置身于其中才能理解。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能站在所研究对象的中心立场。人类学家们很清楚,他的生活方式也应该被当作诸多的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中的一种。必须平等对待主体,从多元的维度考虑,并与其建立一种交互的关系,这将会促进知识客体的转化。摆脱时间的束缚之后,客体陷入困境的溃败是一个必要的时刻,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也是如此。后者的时间性将是漫长的,但这并不妨碍知识的形成。相反,它将知识当作可能不同于那些对其类别和基础所构想的知识。因此,对于人类学家来说,进入客体的内部是知识产生的必要条件。
所以,去中心化应当被理解为一种与空间的多极交互。其源于最初独立于西方思维机制的客体对于霸权将知识歪曲这一问题的表达意识。由此可知,去中心化将成为一个校准仪,其不仅会摧毁主体原本的知识体系,还将与被研究的客体一起构建出新的知识体系。其诞生于研究者与被研究的客体多元交互的关系之中。对于Castro和Agier而言,这些将伦理道德与知识相结合的态度也是一种政治。
让我们回到对于皮埃尔·于热、美学以及感性的关注。席勒认为,美学的自由基于两个方面:艺术家自由地创作艺术作品;同时,作品对于观众没有任何强制力。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摆脱固有的身份限制。正是因为这建立在既符合感性又符合理性的自由之上,所以他们可以接近政治自由且远离社会的限制与约束。
思辨实在论的哲学家与艺术家一样,正如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所写的,他们都是时代的公民。许多人都注意到了主体对客体的霸权以及金融力量对于美的物化,这些其实都被同一个意图所驱使:找到更好的方式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这造成了严重的失衡。然而,通过对比人类学家和艺术家的策略,我们可以推断出的是,为了构建更加均衡平等的知识而抛弃感性并非明智之举。无论是对于人类学还是艺术,对于客体产出对象的思考都是知识建构的重要部分。更确切地说,需要考虑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重新平衡。将权力去中心化,转移主体,这将为新知识产生的条件。从多元合作的角度进行思考(而不是主体和客体二元论的)。意识到自己在空间中的行动,思考这种存在,体会到自己是具中的一部分,体会到那些关注与态度,这也是皮埃尔·于热在其项目中所研究的核心。
因此,无视感性与情绪,就将会以一种命令式的立场消除艺术中潜在的微妙性以及多元性。另一方面,将理性与感性的激烈程度降低至一定程度,是可以检验人类生存条件的一种有趣的策略,正如我们在伊恩·程的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样。如果艺术应该面对的是更多元的群体,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特定的小团体,那么就不应该排斥任何一部分人。席勒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将力量全部集中于理性,固然可以带来巨大的进步,但这是基于个人禁欲主义的实践。席勒曾断言,建立一个平衡的社会,缓解紧张的局势,仅凭理性是无法做到的:“将所有人都置于平等的环境之下,幸福的人类与完美的人性才能诞生[31]。”如果我们遵循他的思想,那么摆脱相对主义将是一条通往思想解放之路,但这只适用于思想,而不适用于人类的多元化。
皮埃尔·于热在蓬皮杜的展览打破了观众人数的纪录,媒体们也注意到他作品的质量以及吸引观众的能力是多么惊人。其作品的形式是易被接受的。因此可以将感性的部分以及不为大众所知的事实传递给更多的观众。他的作品实现了一种巧妙的平衡:以一种易被接受的形式,将作品的力量传达给观众,且其中的内容与形式同样重要。
如果对于席勒来说,美学是实现政治自由的前提,那么这样的假设在今天是否依然成立?对于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去中心化带来了一种新的政治。至于美学,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对于皮埃尔·于热的两个艺术项目的研究使我们发现,某些艺术创作的策略甚至属于伦理学的范筹。通过去中心化,客体的差异得以浮出水面:锚定在一个多元的体系循环当中,每个事物都有着构建客体的潜在能力,沉浸其中,生长,死亡。一切都有平等的机会被影响亦或是被忽略,虽然这看上去不那么现代。
[1] Friedrich Schiller, 《Lettres sur l'éducation esthétique de l'homme》(1795), trad. fr. Robert Leroux, Paris, Aubier, 1943, p. 76.
[2] 同上,p. 168
[3] Quentin Meillassoux, Après la finitude. Essai sur la nécessité de la contingence, Paris, Seuil, 2006.
[4] Ray Brassier, Nihil Unbound: Enlightenment and Extinc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5] Christoph Cox, Jenny Jaskey, Suhail Malik (dir.), 《Realism Materialism Art》, Center for Curatorial Studies, Bard College, Sternberg Press, 2015.
[6] Robin Mackay, Luke Pendrell, James Trafford (dir.), 《Speculative Aesthetics》,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7] 更具体地说,第一种性质(客体固有不变的,可量化的性质)与第二种性质(潜藏在主体之中,可变的性质)在感性层面上有所区别。第二种性质将会成为艺术作品的一部分。
[8] 参照Marshall McLuhan的著作《Message et massage》, un inventaire des effets (1967), trad. fr. Jérôme Agel, Thérèse Lauriol, Paris, Jean-Jacques Pauvert, 1968.
[9] 伊恩·程(Ian Cheng),美国艺术家,1984年出生,工作生活于纽约。《Live simulation》是他自2013年以来创作的一系列作品。
[10] Ian Cheng : « A live simulation that we can feel, but does not give a fig for us ».
[11] “面向客体的哲学(Object Oriented Philosophy)”最初称为“面对客体的本体论”,是思辨实在论的一个分支,其主张将客体独立于人类存在,并对其价值进行重估,试图拒绝以人类为中心的所有知识。参考Graham Harman的著作《L'Objet quadruple. Une métaphysique des choses après Heidegger》。
[12] Emmanuel Kant,《Critique de la faculté de juger》, présenté et traduit par Alain Renaut, Paris, Aubier, 1995.
[13] 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艺术家,1962年生于巴黎,工作生活于纽约。
[14] Pierre Huyghe,《Rétrospective》, Centre Pompidou, Paris, 2013-2014. Commissaire : Emma Lavigne.
[15] Pierre Huyghe, L'Expédition scintillante, 2002, Acte 3 : 《Untitled (Black Ice Stage)》.
[16] Pierre Huyghe, L'Expédition scintillante, 2002, Acte 2 : 《Untitled (Light Box)》.
[17] Pierre Huyghe, 《Umwelt》, 2011.
[18] Pierre Huyghe, L'Expédition scintillante, 2002, Acte 2 : 《Untitled (Light Box)》.
[19] 如果说,在《Untilled》中的所有元素都是相互依存并且统一在某个主题之下的,那么在这个项目中,皮埃尔·于热通过为它们分配不同的主题来对其进行区分:《Human》, 2011-2013, 《Untilled (Liegender Frauenakt)》, 2011.
[20] 当你询问参观者时,会惊讶于他们在展览中所花费的时间:他们通常会用好几个小时去看,去听,坐下,让自己感受。许多人还说,他们已经反复看了好几次,享受着每次都不会看到相同场景的乐趣,并且总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
[21] Film et événements, musée des Arts et Traditions populaires, Paris.
[22] 该协会由Angela Bullock, Dominique Gonzalez-Foerster, Carsten Höller, Jorge Pardo, Philippe Parreno, Rikrit Tiravanija, Xavier Veilhan创建于1995年。
[23] 《Blanche Neige Lucie》, film, 1997.
[24] Nicolas Bourriaud, 《Esthétique relationnelle》, Dijon, Les presses du réel, 1998.
[25] Romain Bertrand, 《L'Histoire à parts égales》, Paris, Seuil, 2011, p. 20-21.
[26] 收录于《Gilles Deleuze : une vie philosophique》。
[27] 如果我们将皮埃尔·于热和伊恩·程的作品与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所描述的美洲原住民形而上学做比较,可以发现这两者之间错在这某种微妙的关联。
[28] 《Who Is Afraid of the Ontological Wolf ?》, 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2014年5月30日。
[29] Michel Agier, 《La Condition cosmopolite, l'anthropologie à l'épreuve du piège identitair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3, chap. « Repenser le décentrement » introduction, p. XX.
[30] “在这个过程中,客体(在认识论对物体的理解中)流转、重生,而主体却消失了,这种消失并没有使雕塑的展示失去多样性,这种表达无非是对主体被剥夺后的一种补偿。”
[31] Friedrich Schiller, 《Lettres sur l'éducation esthétique de l'homme》, op. cit., lettre VI.
原文作者:Flora Katz
原文标题:《Pierre Huyghe, Ian Cheng : Spéculations à l'épreuve dans l'art contemporain et stratégies de décentrement》
翻译/编辑:王靖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