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从彩礼问题再看中国的“半截现代化”
最近几年的两性关系领域有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就是男女之间的大额财物往来(尤其容易表现为彩礼的形式)。一个社会事件里只要出现相关字眼,那么大众的注意力就会都到它上面,各方围绕着它展开激烈的攻防大混战,不管是已婚的还是待婚的还是恐婚的全部都会参与进来。为什么会这样?
鉴于现在的人都不想看长篇大论,我也不绕圈子,直接说结论:这种现象的背景是,这几年以来愈演愈烈的经济衰退叠加中国一贯以来的分配不公,导致除了上层精英以外的人分到的蛋糕基本都在变小,于是相对剥夺感普遍滋生,每个人都有理由认为自己是当前社会的受害者,都处于严重的愤怒、不满和焦虑中;与此同时,当局不出意外地选择继续粉饰太平、维稳堵嘴,以至于“极致低消费”竟然成了个敏感词。在这也不能说,那也说不得的情况下,男女之间的经济纠纷作为一个更偏向于私事的话题,就成了一个相对“安全可控”的热点(因为是“人民内部矛盾”,难以直接用于攻击当局),平台可以放心推送相关话题坐吃流量,网民也可以借此释放被压抑的情绪。

如果这个结论让你满意,那可以直接关闭本文了。然而,细想一下就会发现,上面这段话其实是在用一个更大的议题(经济下行分配不公让每个人都心怀不满戾气爆棚)覆盖原本的议题,试图以此蒙混过关,并没有解释为何“男女之间的大额财物往来”偏偏能成为一个高度争议的焦点。特别是“两性关系中男方承担大部分开销”“结婚时男方给女方彩礼”这些曾经被认为天经地义(或者说是社会共识)的东西,现在已经成为导致社会割裂的严重分歧。所以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本人之前的文章中曾经提出过两个概念,一个是“半截现代化”,一个是“发达中国和不发达中国的平行存在”,分析彩礼问题恰好也可以使用这个框架。
在传统社会,婚姻的主要功能在于维系族群的繁衍及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结婚本质上是男方家庭从女方家庭购买一个女性劳动力和生育力,女性一旦结婚就成了男方家的人(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于是彩礼就相当于男方家庭给女方家庭的补偿[1],不管是解释成对女方父母辛辛苦苦把女儿拉扯大的补偿,还是预支给女方父母的养老费用,总之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进入现代社会,理论上这种人身依附的传统婚姻模式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消失,但实际上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并非均匀铺开,上层建筑更是滞后于经济基础的现代化。在不发达中国(或者说现代化落后地区),由于长期以来的性别比严重失衡[2],再加上女性进城务工,在极端男多女少的情况下,彩礼成了反映婚配市场“供不应求”状态的指标和搞“竞价婚配”的工具。“天价彩礼”新闻几乎都发生在农村(还成了江西的地域黑刻板印象),收来的天价彩礼也往往不会到女儿手里,而是变成女方家庭给自家儿子婚事准备的彩礼(这种模式被戏称为“扶弟魔”),这就形成了一个畸形的“彩礼经济”。
彩礼经济不仅让彩礼成为男方家庭的沉重负担,甚至男性要举债结婚,还让女性继续处于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合法人口买卖”的困境之中,同时女方家庭也并非赢家,立场一转换就成了下一个男方家庭。一旦婚姻发生矛盾(天价彩礼往往会变成婚姻的潜在矛盾爆发点),传统习惯法无法解决,最终诉诸现代法律,那么彩礼在司法上如何处置就成了另一个中国特色难题,为此最高法还在去年专门出台了针对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可见问题之大。更严重的是,彩礼纠纷在极端情况下是会出人命的。可以说,彩礼经济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在不发达中国,彩礼成了一个近乎无解的结,造成了多输困境,那么发达中国作为现代化先进地区,总不存在这样的事了吧?是也不是。一方面,人人平等、独立自主的观念深入人心,传统的人身依附婚姻模式被彻底批判;另一方面,彩礼及其变体、类似物依然存在,但这里的彩礼问题和不发达中国的彩礼问题是两回事。
之所以说是两回事,是因为发达中国的彩礼虽然名义上还叫“彩礼”,但其实质与传统的彩礼并不相同。上文已经说了,传统的彩礼是男方家庭给女方家庭的补偿,传统的婚姻也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男女双方虽是婚姻当事人,但其自主权受到各自家庭的严重制约,也就是所谓“包办婚姻”。然而,现代讲究人人平等、独立自主,现代婚姻是男女双方之间的事,各自家庭最多只能干预指导,而不能包办代替。再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在城市执行得比较彻底,“扶弟魔”模式也无法成立。这种情况下,彩礼(包括其变体、类似物,下文亦统称为“彩礼”)的实质变成了男方证明自己经济实力(或者说与女方门当户对)的证据,彩礼也不再是给女方家庭,而是用于男女结婚后成立的新家庭。十年前有一个流行词“丈母娘经济”,指的是在丈母娘的要求下,男方必须买房买车才能结婚的情况,这甚至成了拉动楼市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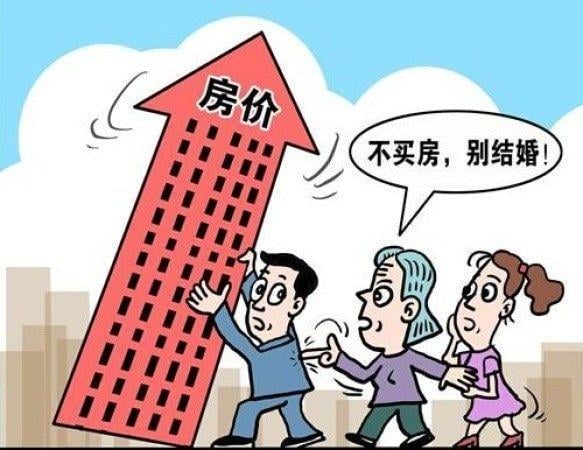
很不幸的是,这一套目前也玩不转了 。原因很简单,此一时彼一时也。前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人人都觉得自己能跻身中产行列,能轻松拿下房和车,大不了就贷几年款。现在经济有多差,生存压力有多大,失业率有多高,应该不需要我在这特意说明。就算真有人头铁敢继续当“房奴”,还有“烂尾楼”这个大坑在等着。多种因素叠加之下,哪怕是原本结婚意愿很高的人,在理性权衡后都得搁置结婚事宜。
以上就是对不发达中国和发达中国两者各自的彩礼问题的分析。必须强调的是,这是一种简化的看待问题的模型框架,现实中的具体情况还是要具体分析,且现实往往不会如此泾渭分明。
分析到这就算结束了吗?问题意识敏锐的人会发现,上面尽管用了大量篇幅辨析两种情形的差异,但是两者有一个共通的因素,就是家长对子女婚姻的主导或影响,而家长作为上一代人,不管是吃了时代的亏还是享受了时代的红利,总之不可避免地拥有大量守旧和过时的思想,与年轻子女之间存在深深的代沟。那么,如果年轻人能够摆脱家长辈的影响, 作为独立的个体建立亲密关系,是不是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
理想很美满,现实很复杂。事实上,年轻人里不乏彩礼支持者,特别是有一些标榜独立、进步、女权的城市中产女性也支持彩礼。至于支持彩礼的理由,有说彩礼体现男性对女性的诚意和尊重,有说彩礼能给女性安全感,也有说彩礼是给女性的生育补偿。正是在此处,彩礼成为了舆论场上能够引发广泛性别对立的核弹级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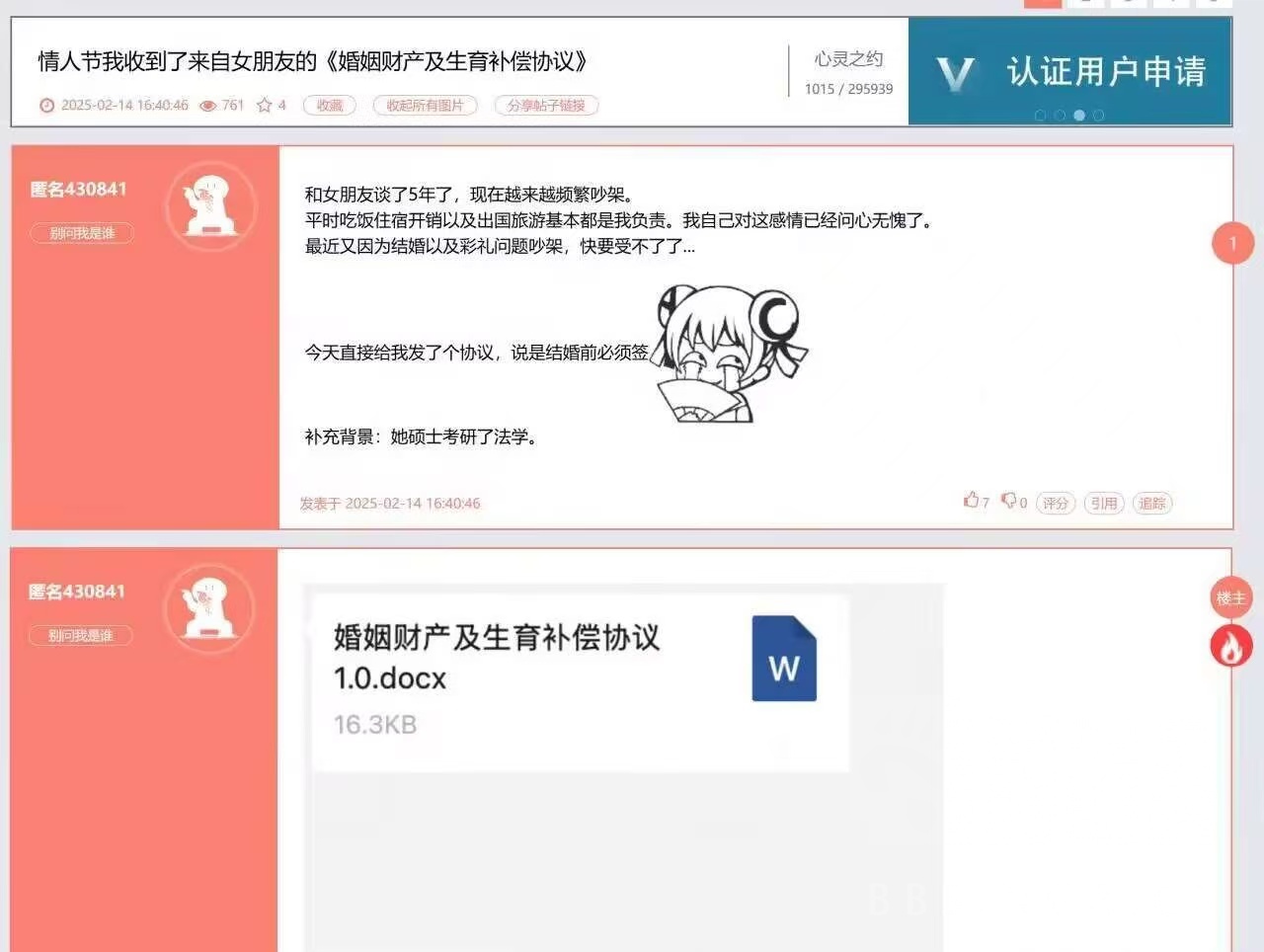
在我看来,这里非常体现当前中国“半截现代化”的困境。这些支持彩礼的城市中产女性,一方面充分享受着现代化的种种成果,要求平等、尊重的现代两性关系;另一方面,在涉及到具体的物质利益时,又选择性地拿传统来为自己辩护。这些人支持彩礼的理由,说白了是用传统社会框架下才能自洽的女性“(作为一种资源的)稀缺性”和“(作为一种工具的)生育价值”来索取经济补偿,同时又拒绝进入传统女性的性别规范并承担相应责任。然而,到了其他话题上(如多年前曾经的热点话题“处女情结”,以及近几年的“服美役”),这些人又会改口,转而挥舞起“拒绝物化女性”的大棒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种心态并不罕见,也不是新鲜事物,其实就是钱理群早就提出来的“精致利己主义”,不仅利己,还善于用各种话语包装利己行为,试图在传统和现代杂糅状态的缝隙中套利。另外多提一句,精致利己不局限于特定群体,一些男性同样精通此道,此处按下不表。
分析至此终于算是结束了,但解决问题的方法作者实在想不出来,只能眼看着少数本就具有优势的人能够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底层人只能在互害的漩涡里挣扎,结构性问题越来越看不到改变,最后只得仪式性地感叹一句“实现现代化任重而道远”。
注:
[1] 女方家庭也会出嫁妆,但嫁妆是女方家庭支持女儿的婚后生活,乃至于提高女儿在男方家庭的地位和话语权的投入,与彩礼功能并不等同,本文不做展开讨论。
[2] 这要“归功”于另一个传统习俗——杀女婴,真是极大的讽刺。至于杀女婴为何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本文不做展开讨论。
作者:ConsLibSoc
本文得到了 Gemini Deep Research 的协助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选集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