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事采集 | 之6:青苔
剛認識噶哈巫四庄不久,就聽聞過「青苔」的大名,被稱為是傳統美食中難得一見的逸品。學長姐說來埔里好幾年,連看都沒看過,我有幸在來埔里第二年,就在牛眠社區的一場晚會上嚐到了。

口感滑溜黏稠,兼一點點蒜碎的脆感,雖被叮囑感受它獨特香味,但可能因為我鼻炎體質,沒能品嚐出來,比較感受到的是蒜頭和淡淡醬油的鮮鹹調味。
聚落阿姨們慈愛微笑著看我的試吃初體驗,問我覺得怎麼樣。
「蠻好吃的,有點像是清淡版的海苔醬?」我說
「欸,說對了,這就像是淡水裡的海苔,只有在很乾淨的水源才有,現在很少了,你能吃到運氣很好!」阿姨們熱情回應道。
有幸嚐過一回,知道了它的樣貌和口感。但對它學名是什麼,生長環境如何,我仍一無所知。
每每想瞭解青苔的來處,有說是族人買來的,但不確定是誰。有說是在乾淨的泉水養的,但不確定是哪裡。總是無法得到進一步明確的訊息。
依著「淡水+水草+生食」這些關鍵字,我試著擴大範圍尋找,會不會有其他族群也有食用呢?
在林務局出版的「邦查米阿勞-東台灣阿美民族植物」中,讀到這段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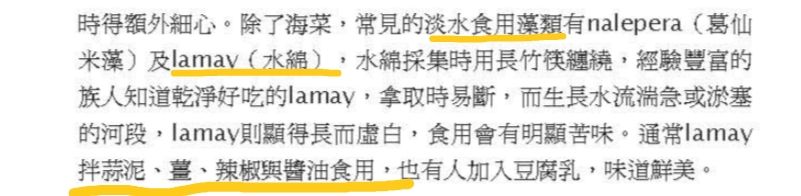
而在原民台對都歷部落族人採訪的影像中,進一步確認了長相和吃法,鎖定了很可能就是叫做水棉的這種藻類。
然而我後來才知道,在吃青苔這件事情,查出它的學名是什麼,也許是最不重要的問題之一。
甫聽聞青苔這個食材時,心中隨即浮上一個疑問:「那跟路邊的青苔一樣嗎?」
終於在和部落叔伯熟悉了一點後,得以小心開口提問。
要回答這個問題,顯然用看的用摸的,都比用說的快,部落叔叔領我騎上機車,出了部落徑直往水邊去。
在田邊圳溝臨停,叔叔踩著雨鞋直接往水裡一撈,舉起一坨綠色纖維,告訴我「這也是青苔啊,可是這不能吃。」細看其手中纖維粗糙如尼龍繩,混著淤泥和雜草。

「因為不乾淨嗎?」我問。
「也是一個原因啦,還有就是太粗啦,這麼粗,很刮(嘴)的,要怎麼吃?」
而後我們繼續往幽靜少人的溪畔去。4月的溪水不深,尚有涼意,挽起褲腳走下去,感受它徐徐流過。叔叔翻動著石頭一邊比劃,一邊解釋:可以吃的青苔應該是細細綿綿的,如果長的地方太陽太大,水流太急,纖維就會變粗變老不好吃。如果是死水都沒流動,那也不行。
定睛一看,的確溪中到處都長著青苔,但是隨著石塊分佈,影響了流速,以及上方有無遮蔭,都造成了青苔不同的生長狀態。
對比著記憶中吃過的青苔狀態,以及叔叔傳授的技巧,我在溪水中笨拙地模仿著,用樹枝到處戳起不同塊石頭上的青苔觀察,興奮舉起給叔叔驗收,這個對嗎?我可以拿回去吃吃看嗎?

「對是對了,但這條水裡的..還是不要吃吧..」
叔叔瞇著眼接過我手中的青苔,又抬眼望向溪水上游。儘管視野被山勢遮擋,但在叔叔的腦海裡,自有一張水文圖,越過山勢繼續延展,他知悉著這些溪流行經何處,途中有哪些聚落,人煙多寡。最後下了「最好還是別吃」這個結論。
總而言之,關於「可以吃的青苔」,關鍵並不是找對物種(因為到處都會長),而是觀察它所生長的水源乾淨度、日照強度、水流湍急程度等等。
是相當需要「意會」去判斷的...
因為青苔是生食,而隨著晚近埔里人口激增,環境汙染,原本周遭溪水唾手可得的青苔,族人多半顧及衛生問題而不再敢隨意取用。那麼,我上次吃到的青苔是從何而來的呢?

在田野待得夠長了,終於打聽到,鎮西的愛蘭台地因為有天然湧泉做為潔淨水源,有人在該處進行少量的養殖販售。還曾拿來鎮東的蜈蚣崙部落兜售。並仰賴族人的協助指認,部落的慶伯略帶誇耀的語氣說道「他來的時候齁,還是我報給他,哪戶是自己(族)人,應該會吃」。
對應鄰近客家聚落的一次山林活動,長者也是提到「這個青苔我們是不吃的,但隔壁四庄的他們會吃。」
似乎在埔里的野菜中,青苔是少數具有族群邊界意義的一項食材。(相較於箭筍、刺蔥而言)

青苔找到了,怎麼吃呢?叔伯們說得籠統,「就蒜頭醬油膏拌一拌就好啦!」
當我們試做給長者們品嚐時,大姐們露出了「不忍潑孩子冷水」的微妙笑容。後來不抵我好奇追問,才緩緩透露:
「其實不用醬油膏啦,青苔本來就有滑了啊,用醬油就好了,比較爽口。」
「還有,要放一點醋,也是爽口,再來就是跟蒜頭功能一樣,殺菌嘛,畢竟是吃生的。」
「你們是馬上拌,接著馬上吃嗎?其實可以提早一餐拌好放著,讓它入味。」
原來看似簡單的涼拌青苔裡還有這麼多know how,這是我沒想到的。卻也和目前為止的學習經驗一致,男性長輩擁有許多辨識採集的知識,而女性長輩在料理和味覺審美上教會我更多。

要吃青苔,就要挑春天和初冬。跟著長輩學習,漸漸的,氣溫體感都會召喚出味覺記憶。比如最近這時節,陽光不烈,水流不急,青苔便能長得又細又棉,正是品嚐的好時候,涼拌起來,很是下飯。如何,來一口嗎?

此為本系列第6篇,前面5篇詳見關聯。也歡迎追蹤臉書粉專:山事采集,會不定期更新田野小插曲~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