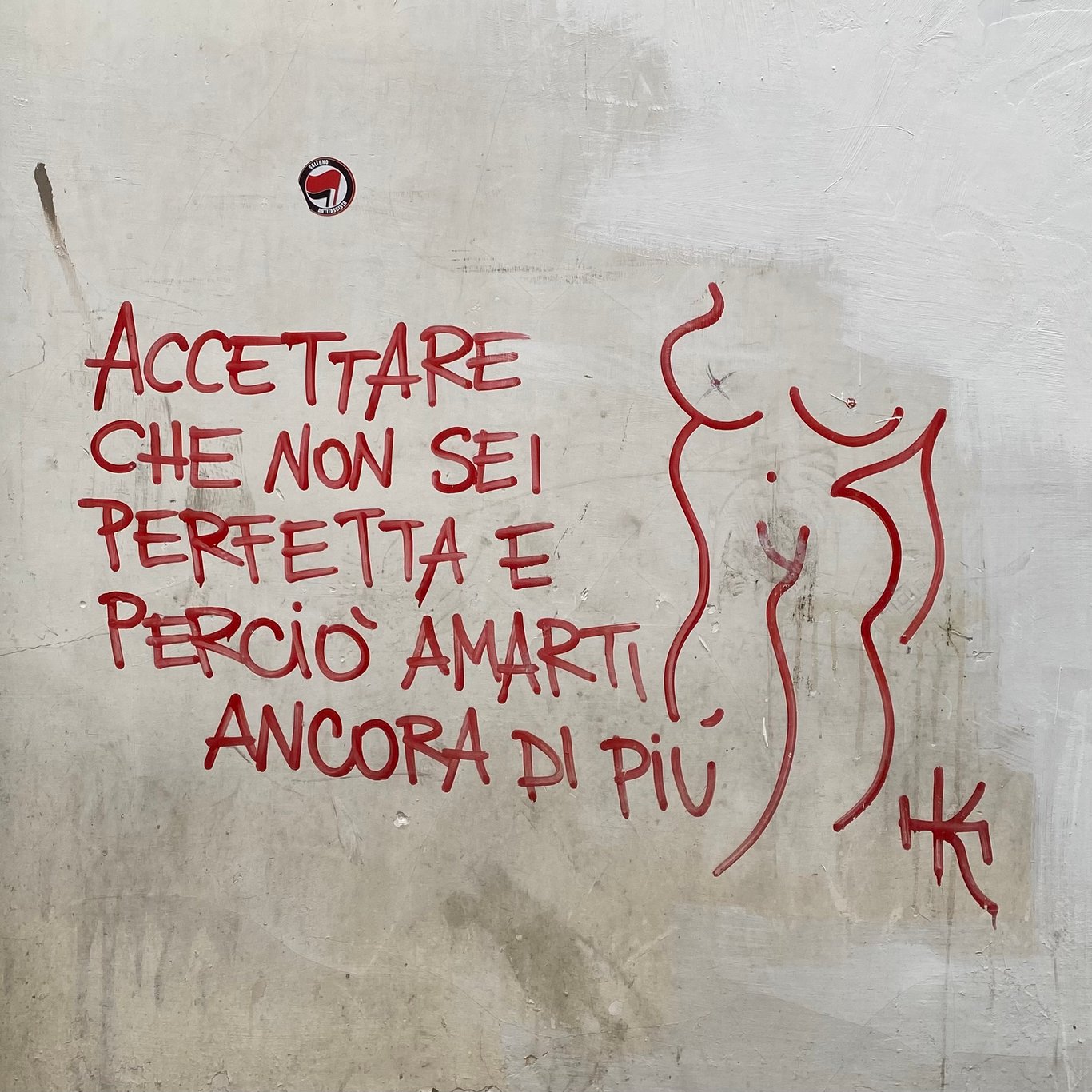七日书D1|贫穷的基因
很早我就意识到了,贫穷不只是暂时的经济状况,而是一种会经由血脉和家庭遗传下去的东西。贫穷是一种基因。
要说我真的经历过贫穷,这大概是不准确的。但我一直感到贫穷。从小听母辈和祖辈受苦的故事长大,譬如童年的妈妈如何喂猪、做饭、照顾弟弟,一直到十岁终于有机会上学了,她于是开始每天背着弟弟走过好几里的山路。譬如上小学的爸爸因为交不起一元钱的学费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站起来,和其他也交不起学费的同学一起当堂比赛,证明更有资格得到那一元钱的助学金。我最常听到的一句俗语是外婆说的,“糠den掉到米den里了”,说的同时通常伴随着我不情不愿地吃白米饭,于是我在愤愤中也默默想象着糠的味道。
那些故事被反复诉说,直到我也都能自然流利地复述出来,就好像自己都亲身经历过一样。我坚定地认为我们是贫穷的。
贫穷无疑使人节俭。
在我和父母共同生活的家,每一盏灯都一定是不辱使命的。我爸对于电的使用效率抱有极高的敏锐度,哪怕有人只是离开房间去上了个厕所,回来的时候灯大概就已经被关上了。我们也相当节水,卫生间经年不变地放置着一些盆盆桶桶——不若如此,每次洗澡前面放出的凉水难道都要直接流进下水道吗?接出来的水则用来冲马桶、拖地等等。小时候第一次在课本里学到环保的概念时我大为骄傲,同时也非常不解:难道真的有人会在洗手打肥皂的时候就让水龙头一直开着?这怎么还会是需要提醒的事情呢?
很多年我都骄傲于自己家环保理念的先进,直到发现爷爷家的水龙头永远在漏着几滴以“偷水”,而并没有任何人对此事发表过意见。虽然那些水被接起来也都是用在有用的地方,其实并不与“环保”的理念相悖,但我还是一下子察觉到了这其中不那么体面的部分,以及它映射出我们到底为什么而节约的真相。
就像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一样,我们罹患囤积癖。这个病有着致命的遗传性。不大的厨房里,专门有一个橱柜堆放着所有买菜带回家的塑料袋。我熟练掌握给塑料袋打结的技术,并持续应用直到今天,在伦敦出租屋的厨房里也开辟出了一个作用相同的抽屉。听黄阿丽的单口喜剧,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段子是她吐槽自己妈妈的囤积癖,“……so you’d better hold on to the retainer from the third grade because it might come in handy as a shovel when you’re busy stuffing gold up your butt and running away from the communists!” (你不能丢任何东西,因为你不知道独裁者什么时候掌权,所以你最好留着你三年级的牙套,等到有一天共产党在你后面追的时候把它可以被当作一个很好用的小铲子,把金子塞进你屁股里。)我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在心里忍不住赞同她妈妈,是啊!花了那么多钱的牙套怎么好随便扔掉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用呀!
贫穷也使我对食物的有一种极强的敬畏之心——因为当然,饥饿就是贫穷的姊妹篇。
食物的作用是让人吃饱,不是享受,这是明白无误的道理。在我妈曾经生活的中部农村,最不缺的粮食是红薯,她们叫山芋。在那些个每天凌晨四点、我某个勤奋的舅舅就抢在全村人前面去挑粪的年月,垒到屋顶的山芋化作一大锅又一大锅的山芋稀饭,效益最大化地保证她们还有力气劳作、干活,度过一个又一个冬天。相比有些人可能会在三十年河西之后就性情转变,我妈对山芋满怀感恩之心,至今依然在冬半年的每天都继续煮山芋稀饭。
我爸对待食物的态度则更如履薄冰。作为一个城市人,幸运的是他从小就实现了我外公奋斗终身、为儿女铺设的终极理想:吃商品粮。而这份命运的礼物也在价码上极为坦诚:吃不饱。一家六口分着差不多够一半人吃饱的粮票,如何精俭地计划、安排食物成了生存的最大学问。我的奶奶精于此道,在最迫不得已的时候分出最薄的肉片,搭配市场上捡来的烂叶子,勉力支持着一顿顿饭。在这样的情况下,剩菜是绝无可能出现的,每盘菜的份量根本都少得可怜,而我爸也性情不改,对这种生活方式深以为然。
于是童年饭桌上经常出现的一个矛盾就是,妈妈和外婆都喜欢炒尽可能多的菜,煮一大锅一大锅的稀饭,而我爸动辄生气,坚称所有的菜都应该刚刚好,一顿吃完。
反正这话说起来很容易,他从不做饭。
好笑的是我们家吵的始终是食物的份量而不是品质或味道,对后者我们都没有什么追求。第一次完整地吃大闸蟹是在一个阿姨家,她教我怎么用筷子捅出蟹腿的肉——这其实算是最基础的吃蟹方法。但那之后我爸妈念念不忘,经常提起她们家作为一种骄奢生活的象征,“啊,她们爱吃螃蟹,她们都很会吃螃蟹。”
我对时间的管理能力很差劲,有时候我觉得这也和我遗传的贫穷有关。“一寸光阴一寸金”,这我只当学校里的客套话听听。对我来说,一寸金才是一寸金,而时间,时间是我最贱的东西。如果有什么可以通过耗费时间而少花点钱——比如在夜里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来的公交,还要中转下一班,可能最终花上两三个小时回家——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个方法,反正时间留给我也总归是一种浪费。我习惯于鼠目寸光地活着,看不见太长远的东西。在穷人的世界里,可以掌握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常常有一种幻想。如果造出了时光机,我一定要想办法弄来一些钱,最好是百元大钞,然后坐时光机回到妈妈童年的家。我对这个方案计划得很细节,比如我不会多停留,避免碰见任何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我会一门心思地找到一个明显而安全的地方,留下一沓钱,然后离开。
我太常幻想这件事甚至产生了一种满足感——想象外公外婆从田里回来惊吓而惊喜的样子,然后她们可以大大地减少一些劳累,因为有了可以供所有孩子读书的钱。
当然我也愿意去一下爷爷奶奶的家。但由于我爸对我的讲述不多,我的想象也就有限。不过他那么羞愤了半辈子的一元钱学费的创伤,总归也是可以被抚平了。
我一直背负着这样的幻想,就如同一直背负着愧疚。就如同我虽然从未真正挨饿受冻,却一直感受着贫穷和饥饿的滋味。
有时候我也很疑惑,明明我不是真的贫穷,但为什么我总感觉这么胆怯、这么低微?难道是我享受把自己变成一个受害者的过程吗?可是,我又是真的感到贫穷,所有写穷人的文章我都是那么能够共情,恨不能自己去代替书里的人物受苦,为此不知道在乡土文学里流了多少眼泪、不慎受了多少男作家的毒害。
我喜欢听别人说自己的家族故事,聊天中我发觉自己惊人的敏锐力:如果说我爸的特长是第一个发现正在浪费的电灯,那么我则总能第一时间判断出说话人的父母、祖父母曾经过着怎么样的生活。虽说那是一个全中国共患寡的年代,但不均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我听到对方的妈妈在城市里,只有一两个姊妹;当我听到对方的奶奶识字,甚至曾经做大学老师;当我听到对方的外公是支内的工人,虽然这辈子再也没有回过上海生活;当我听到对方的家庭里并没有世代流传的饥饿……我突然感到贫穷的记忆在我体内强烈地作用了起来,我从另一重角度看见了我母辈的故事,直剌剌地明白在我妈妈和爸爸的讲述里,她们是如何作为身边所有人中最穷的那个人。
我当然是一个穷人,因为我是穷人的女儿,是穷人女儿的女儿。贫穷或许可以改变,可是贫穷的基因呢?
我想贫穷是一种比记忆更顽固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即便记忆不在了,因记忆而塑造的那些习惯仍可以一辈辈传承下去。它真的好像一串DNA的序列,埋藏在没有人能看得见的地方,只有我自己知道,某个在别人看来十分不值当、兀自步行几公里的凌晨,或是无端端产生同情心想流泪的一瞬,都是它正在我体内发生作用,那是几代人的人生越过几千公里绞缠在一起,掀起一场巨浪。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