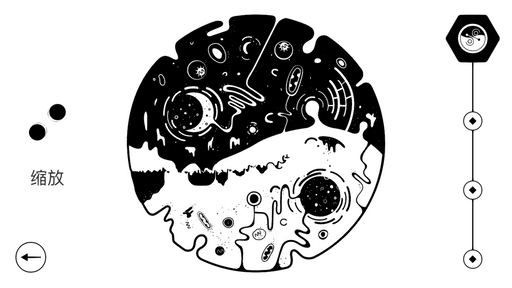论数字艺术中的交互叙事——以步行模拟类游戏为例
摘 要
数字艺术是以数字媒介为载体的艺术形式。数字艺术与传统艺术形式差别最大的地方在于,观众可以通过交互直接参与到数字艺术的呈现,并与作者一起完成数字艺术作品。而基于交互的数字艺术可以大致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延续了现代和后现代艺术范式的数字装置艺术,以及借助算法进行规模化制作的生成艺术。这类数字艺术以视觉传达为核心,缺乏必要的叙事性。另外一种则是随着电脑技术的普及而逐渐壮大的游戏艺术。游戏艺术由于强调体验的完整性,对叙事的重视远超过数字装置艺术和生成艺术,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交互叙事方法。而在这些具备独特交互叙事方法的游戏类型中,又有一类弱化娱乐性,强调对严肃问题的讨论的作品类型,也就是步行模拟类游戏。步行模拟类游戏将交互简化为了最基本的人类行为,行走。通过制造有隐喻含义的空间和对时间进行非线性的排序,对虚拟世界的存在,人的存在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论文从时间性和空间性两个维度对步行模拟类游戏的交互叙事特征进行分析。因为数字艺术的交互性特征,叙事不再仅仅以抽象的文字叙事来表现,而是多种媒介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虚拟世界是一个由时间和空间组成的综合体,不能简单的从某个单一维度来进行说明。为了最大程度概括这种综合性的表现,本文选择时间性和空间性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由于步行模拟类游戏为交互者提供了一个可交互的视觉环境,空间影响了交互者对于叙事的理解,空间叙事是交互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论文会从交互叙事中的环境叙事和涌现式叙事两个角度来进行空间叙事的阐述。同时,交互叙事需要在时间流程中展现自己的节奏,缺乏时间的叙事是不存在的。从时间的角度来研究交互叙事,有助于理解交互叙事的时间组成方式。本论文从托多罗夫的叙事时间学说的角度切入,分析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的时间结构和时间逻辑。
最后,本文将介绍步行模拟类游戏交互叙事中的主体性叙事。交互叙事与传统叙事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客体可以作为作品的一部分参与到叙事中并对作品产生直接的影响。从主体性的角度对交互叙事进行切入,能够更好的理解交互叙事中存在的不同主体视角,并对交互叙事的自反性进行更为清晰的论述。本论文会从步行模拟类游戏中角色的双重身份和元叙事的特征两个方面来对主体性叙事分析,阐释步行模拟类游戏如何对虚拟世界和人类的关系进行了艺术化的表现和哲学式的批判。
综上,步行模拟类游戏作为交互叙事的典型,不仅连接了艺术和技术,并且深化了艺术在数字媒介中的应用。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涉及到了人的存在与赛博世界存在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并且能够让人进行哲学和审美层面上的思考。
关键词:数字艺术;交互叙事;步行模拟类游戏
绪 论
一、选题缘由
数字艺术(Digital art)是指使用数字技术作为创作或表现过程的一部分的艺术作品或实践,有时也被称为计算机艺术(Computer art)和多媒体艺术(Multimedia art)。作为新媒体艺术(New media art)的一种,数字艺术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而这种表达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交互”(Interaction)。交互意味着这种艺术并非完全意义上是作者主导的艺术,而是要在观众和作者的互动之中完成作品。而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传递(不管是知识上的信息还是情感上的信息),则可以看做是构成了“叙事”(narratives)。为什么交互叙事是一种叙事?在《定义叙事的尝试》(Toward a definition of narrative)一文中,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认为,“如果说叙事是一种传达故事的话语,那么,这就是说,叙事是一种包含内容的特殊类型作为一种心理表征,故事与媒介的性质无关,也与小说和非小说的区别无关。因此,叙事的定义应该适用于不同的媒介。 (尽管媒体在讲故事的能力上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以及,它不应该给文学形式以特权。”玛丽·劳尔·瑞安通过文献梳理,将叙事的定义归纳为一个松散的集合,从不同的角度对叙事进行了定义,从空间层面来说, 必须位于时间上,并经历重大的转变,且这种转变必须是由非习惯性的物理事件引起的。从心理层面来说,事件中的部分参与者必须是有智慧的生物的代理,他们有精神生活,并对世界的状态作出情感反应,且有些事件一定是这些代理人有目的的行动。从形式和实用性层面来讲,事件的顺序必须形成统一的因果链并导致结局。至少部分事件的发生必须被断言为故事世界的事实。最后,故事必须向观众传达一些有意义的东西。玛丽·劳尔·瑞安对叙事的定义依然十分传统,并且依然集中在线性叙事的层面。对于交互叙事来说,除了符合传统线性文学定义的叙事作品外,也有许多非线性叙事作品。在数字艺术的开创者,艺术家白南准(백남준)1963年的音乐-电子电视展览(EXPosition of music-ELectronic television)中,电视机散落布置在展览的各个角落,并用磁铁来扭曲电视机的影像,来展示外力对于影响的影响。作品不再是分割于观众的存在,作品与观众同在,在观众之中生成。数字艺术模糊了作品和观众之间的领域,让二者不分彼此。不过,具有装置艺术特征的数字艺术,主要突出了数字影像的层面,而对于叙事层面,则主要是用视觉表现的具有象征性的模糊叙事,不具备更为具体完整的叙事内容。等到具有输入-输出功能的机器(如电脑和手机)变得更加普及之后,数字艺术的交互性特征变得更加显著,也出现了更多在交互叙事层面上的实验。人对于数字艺术作品有了更大的支配权,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艺术品的外在形态。而在交互性较强的艺术中,既有广泛利用人机交互设计的在画廊和博物馆展出的现代艺术作品,也有容易被人所接触的电子游戏作品。
但是,电子游戏能否被算作是数字艺术的问题依然需要稍作讨论。1950-1960年代出现了电子游戏的早期实验,1971年出现了第一个公开售卖的街机电子游戏《计算机太空》(Computer Space)。而此后电子游戏的发展,都与其娱乐性密不可分。而这似乎和艺术相违背的。艺术追求个性的表达,强调作者性,但是游戏从起源到发展的过程中则始终和商业性挂钩,甚至会主动向受众妥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游戏作为新兴交互媒介,依然获得了很多艺术家和创作者的关注,并使用游戏作为艺术表达手段进行创作。90年代随着家用计算机的逐渐普及,人们对于赛博世界也充满了好奇和想象,并开始制作电子游戏。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具有地下和独立风格的电子游戏。比如佐藤理制作的一系列具有迷幻色彩游戏,其中包括知名的《LSD: 梦境模拟器》(LSD: Dream Emulator)。同时主流的游戏厂商也为了拓展市场而制作了很多风格类型都比较多变的游戏。而在2000年之后,随着简单容易上手的游戏引擎如RPG Maker的出现,又掀起了一批游戏制作的热潮,在网站Freem上,仍然保存着这一时期的许多经典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以自我表达为核心,并且具有强烈艺术性的角色扮演游戏,如《梦日记》(Yume Nikki)。2012年,《独立游戏大电影》(Indie Game: The Movie)在美国上映,其中介绍了三款独立游戏的制作过程。独立游戏(Indie Game)指的是不依赖大公司,通过个人或小规模多人制作的游戏。《独立游戏大电影》中介绍的三款游戏分别是乔纳森·布洛《时空幻境》(Braid)菲尔·菲什(Phil Fish)的《菲斯》(Fez)以及埃德蒙·麦克米伦(Edmund McMillen)和汤米·雷芬斯(Tommy Refenes)的《超级肉男孩》(Super meat boy)。这个电影以及其中涉及到的人物都对于独立游戏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也是质量很高的独立游戏的经典之作。在《独立游戏大电影》播出之后,很多的独立开发者看到了不依赖大公司进行独立开发的希望,并投身于独立开发事业,并制作了很多与娱乐性游戏不同的颇具艺术感和独特风格的作品。同时,游戏售卖的市场也在不断完善,Steam,itch.io和GOG等游戏出售平台的出现,也给了很多小众,艺术风格的游戏以空间和平台展示自己并为人们所知。
而在社会层面,在2011年,美国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宣布,所有使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而创作的媒体内容、包含电子游戏,被确认为艺术形式。而在中国90年代也已经有了关于游戏是第九艺术的讨论的声音。并且,相比于放在博物馆和展览厅的数字艺术,通常游戏的流程更长,包含更多的完整叙事故事。而对于本论文中主要讨论的步行模拟类游戏,则与上面提到的自90年代以来的制作艺术化游戏的风潮相伴而生。步行模拟类游戏真正开始被学界讨论则是2010年左右,也就是在前面所提到的独立游戏制作风潮出现后。随着一些具有较高水准的步行模拟类游戏的出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游戏中的艺术表达,并将游戏作为一种艺术表达手段。
步行模拟类游戏削弱了游戏的娱乐性和消遣性,将游戏还原为更为单调的交互形式。但是对娱乐性的削弱使得它有能力以更严肃的态度对待交互叙事,并用交互叙事来展现更加具有艺术性和哲理性的主题。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人们主要交互行为是行走,以及探索周围的场景,观察场景中的各种细节。步行模拟类游戏继承了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的特征,并具有类似艺术展览的展示效果。但是步行模拟类游戏呈现出的叙事内容相比艺术展览更加丰富,因为步行步行模拟类游戏的重点并不在于完成对单一艺术品的审视,而是将整个环境作为一个完整的叙事空间进行安排。同时,由于步行模拟类游戏强调沉浸式体验,这也激发了它使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对交互叙事进行扩充和创新。综上所述,以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的交互叙事作为研究切入点,有助于理解交互叙事的发展,并促进对数字艺术的更深层理解。
二、研究意义
数字媒介的发展催生了数字艺术,而数字艺术的发展又促进了叙事形式的变化,并推动了交互叙事的产生。而在对步行模拟类游戏这一具体的交互叙事形式进行探讨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更具体地感受到交互叙事的特点和创新之处。新的叙事媒介依然在不断发展之中,只有不断投入实践,关注最近的作品动向,把握各种新的叙事形式,才能在叙事研究领域作出更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叙事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文本叙事的层面,而是应该着眼于更多样的叙事媒介的实践中,只有这样,叙事学研究才能永葆青春,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在实践层面,本文也有助于数字艺术,交互叙事的创作者,游戏的创作者,以及步行模拟类游戏的创作者重新思考和审视自己的创作,并作出更具有实验性和创意的作品。另外,学界对交互叙事的研究不够重视,对交互叙事的理解依然相对来讲比较薄弱。本文则为交互叙事的研究进行了有力补充。同时,虽然国外对于步行模拟类游戏有一定的关注,但是国内还没有对步行模拟类游戏进行分析和阐发的论文和文献。本文则能够帮助研究者增加对于步行模拟类游戏的认知和思考,进一步分析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的交互叙事和艺术呈现。另外,对步行模拟类游戏进行研究,也能一定程度上打破学术界对于数字艺术,交互叙事以及游戏媒介的偏见,了解不同于刻板印象的交互叙事实践,有助于激发相关的讨论并促进该问题的研究。
三、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数字艺术和交互叙事的关注早于国内。保罗·克里斯汀(Paul·Christiane)在2003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数字艺术》(Digital Art)的文章,其中论述了数字科技能够作为一种艺术传达的媒介以及数字艺术存在的可能性,同时认为虚拟现实技术的产生是数字艺术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2013年卡斯特克-卡蒂亚(Katja Kwastek)在《数字艺术的交互美学》(Aesthetics of Interaction in Digital Art)一书中,对交互艺术进行了溯源和定义,并认为交互可以构成数字艺术中的审美体验。在交互叙事方面,1997年阿瑟斯·J·埃斯彭(Espen J. Aarseth)写了《制动文本:遍历文学观》(Cybertext: Perspective on Ergodic Literature)一书,将交互叙事作为传统文学叙事的延伸,并分析了以文字为基础的交互叙事的特征。1999年杰西帕·尤尔(Jesper Juul)在《游戏与叙事之间的冲突:关于计算机游戏和互动小说的论文》(A Clash between Game and Narrative A thesis on computer games and interactive fiction)中介绍了游戏机制和叙事之间的冲突,并对交互叙事进行了分析。2004年,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在《作为建筑叙事学的游戏设计》(Game Design as Narrative Architecture)中,首次提出了环境叙事(Environmental Storytelling)这个概念,并用环境叙事这一概念推进了对交互叙事的进一步研究。
在步行模拟类游戏方面,关于步行模拟类游戏最早的讨论出现在2010年。步行模拟类游戏的出现颠覆了游戏的娱乐性传统,也被很多玩家和游戏评论者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妮可·克拉克(Nicole Clark)写了《游戏中最令人讨厌的类型“步行模拟器”的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he “walking simulator,” gaming's most detested genre),介绍步行模拟类游戏是如何被人贬低又是如何超越游戏传达艺术观点的,以及步行模拟类游戏的接受历史。在2010年后出现了不少经典的步行模拟类游戏,关于步行模拟类游戏的讨论也逐渐多了起来。相关的期刊论文也不少,一些论文分析了步行模拟类游戏的具体案例,并作出技术和设计上的分析。除此之外,有些人认为应该对步行模拟类游戏作出进一步的概念定义。菲利克斯·齐默尔曼(Felix Zimmermann)写了《从步行模拟器到氛围动作游戏——一种被误解的流派的研究方法》(From Walking Simulator to Ambience Action Game——A Philosophical Approach to a Misunderstood Genre)认为应该对步行模拟类游戏进行重新定义,并将步行模拟类游戏定义为氛围动作游戏。但是氛围动作游戏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步行模拟类游戏的概念的传播更为广泛。关于步行模拟类游戏的叙事性和艺术性,国外研究中多有论述,并且已经达成基本的共识。可以看到,步行模拟类游戏以其艺术性和独特性被学界所关注,但是对于步行模拟类游戏的交互叙事的论述则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四、国内研究综述
从媒介研究切入交互叙事和数字艺术的论著和论文的论述比较多,如黄鸣奋在《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一书中从数字媒介的角度对数字艺术的特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书中的第三章《鼓励参与:论数码艺术的交互性取向》也对交互叙事进行了论述。该章节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交互叙事进行了分析,并从技术角度分析了交互的形成历史。关萍萍的博士毕业论文《互动媒介论——电子游戏多重互动与叙事模式》则以游戏为主要对象,分析了游戏中的叙事呈现,从不同的主体的角度对交互叙事进行了分析,并认为交互叙事中有三种互动的共存。国内对于数字艺术的研究存在两面性,一方面大部分研究者承认数字艺术是一种新的艺术表达形式,并且有和传统艺术不同的性质。但是另一方面,则依然对数字艺术有一定的偏见,认为数字艺术会造成后现代语境下的虚无的问题。国内从文学艺术理论的角度研究数字艺术的文献相对偏少,但是依然有可以参考的视角。如张耕云在《数字艺术三题》中对数字艺术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梳理,并介绍了数字艺术和传统艺术之间的区别,文中还强调了数字艺术的可重组性和交互性等特征。但是张耕云依然批判了数字艺术具有虚无性。在游戏的艺术性论述方面,如高源和刘坚的《数字影像艺术的交互审美分析》一文,结合接受美学的观点,认为交互使得接收作品的过程由主动变成了被动,从而具备了审美特性。“在数字艺术的新媒介平台中,传统的创作者地位发生了变化,受众作为审美主体,既是接受者也是创造者,数字交互艺术作品作为审美对象,成为开放的、不确定的、突破时空界限的、只有在审美主体的参与中才能完成的未定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作品,都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交流’和沟通的结果。数字影像艺术的交互审美实践,已成为当代艺术审美的一种范型。”钟雅琴的《沉浸与距离:数字艺术中的审美错觉》,则是从沉浸与距离这两个角度分析了数字艺术的审美特征,并用审美错觉这一概念诠释了数字艺术中的审美接受问题。“从效用上看,审美错觉是确保艺术再现被接受者感知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因为审美错觉可以提供替代经验以满足人们的各种欲望,同时又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审美错觉意味着在艺术再现世界中经验性地‘重新集中’的主观印象。这种主观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艺术作品的媒介所提供的视觉环境。因此,审美错觉是一种强度可变的精神状态。”徐丽芳和曾李的《数字叙事与互动数字叙事》从偏技术的角度分析了互动数字叙事的几个发展方向,并且对于互动叙事的研究脉络进行了分析。整体来说,国内对于数字艺术和交互叙事的关注仍然是对西方相关研究的综述和总结,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观点。另外,由于对数字艺术和交互叙事的实践关注度不够,国内研究对相关领域的理解会因为缺乏实践经验而有失偏颇。对步行模拟类游戏的分析仍缺失。
第一章 作为交互叙事典型的步行模拟类游戏
为了分析步行模拟类游戏这一特殊的交互叙事表现形式,本章节从交互叙事的类型出发进行分析,并将交互叙事类型分为基于文本的交互叙事,基于视觉的交互叙事以及混合型交互叙事进行分别论述。同时,本章节介绍步行模拟类游戏的发展历程并简要分析步行模拟类游戏的特点。在本论文中,会以“参与者”而不是“玩家”来称呼参与步行模拟类游戏并进行交互的人。“玩家”指的是以娱乐为本位参与到游戏中的群体,“参与者”则是根据步行模拟类游戏的特征将其中性化,仅保留参与交互的特性。
第一节 数字艺术中的交互叙事
一、基于文本的交互叙事
基于文本的交互叙事有很漫长的历史。目前可考证的最早的项目是1964-1966年间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约瑟夫·维森鲍姆(Joseph Weizenbaum)所开发的的用于自然语言处理的计算机程序ELIZA。ELIZA 使用模式匹配和替代方法来模拟真人对话,这种方法给参与者一种程序理解的错觉。约瑟夫·维森鲍姆在ELIZA中运行了一个“医生”(DOCTOR)脚本,用于模仿非定向心理咨询中初次咨询时病人和医生的交谈。举例来说,比方说有心理问题向ELIZA倾诉说:“我好恨我的父亲。”ELIZA会回答诸如“你家里还有谁恨你?”这样的反问。以ELIZA为代表的自然语言处理程序昭示了一种交互叙事的可能性,由用户提供随机话语,程序对话语进行反馈,而程序反馈则给用户提供一种理解的错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ELIZA和用户的对话中,虽然设定好了DOCTOR的场景,但是并没有规定有一个故事或者是故事走向。这个流程中充满了随机性,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是一种有意识的叙事,而是通过制造了一种交互场景而实现的随机叙事。这种具有生成性的叙事随着游戏研究的发展逐渐有了自己的名字,也被称作是“涌现式叙事”,即由程序和用户通过自然互动生成的随机叙事内容。这种形式前期以纯文本的形式出现,如ELIZA,但是随着后期的发展,也和其他不同种类的叙事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更复杂的交互叙事。
另外一个基于文本的交互叙事方向则是来自于游戏,多人在线地牢(Multi-user dungeon,简称MUD)是一个多人实时的虚拟世界,通常基于故事板或者文本。MUD 结合了角色扮演游戏,砍杀,参与者对战,互动小说和在线聊天的要素。参与者可以阅读或查看房间、物品,其他参与者的描述,非角色参与者(non-player character, 通常所说的npc),以及在虚拟世界中执行的动作。参与者通常通过键入类似自然语言的命令与彼此和世界互动。传统的MUD可以看作是一个角色扮演游戏,一般都设置在一个由虚构种族和怪物组成的幻想世界中,参与者选择职业来获得特定的技能和力量。这种游戏的流程循环就像是,杀死怪物,探索幻想世界,完成任务。但是和现代游戏最大的区别在于,MUD的所有内容都是用文字进行描述的。举个例子,参与者可以提出指令“打开门”或者是“打开”然后和“门”进行组合来获得关于打开门之后的剧情,并且系统会自动将参与者的行为纳入到叙事之中,比方说在打开门的例子中,之后参与者可能会得到“你打开了门,里面是一个高大的黑色怪物。”这样的段落。基于文本的交互叙事,首先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明确的由文字设定的场景,然后人们可以根据这个文字场景进行交互。像ELIZA这种模式的聊天机器人,并不强行要求用户去扮演或者是接受某种设定,而是和用户建立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连接。而在MUD中,则强调了参与者的扮演属性,不管是扮演勇者还是骑士,参与者被赋予了身份概念,并按照自己的身份概念行动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叙事。
更加强调文本基础的交互探索是互动小说(Interactive fiction,也被简称为IF)的发展。互动小说可以理解为非线性的文学叙事,也可以被理解为互动叙事或文字冒险游戏。在1975年,威尔·特劳瑟(Will Crowther)和唐·伍兹(Don Woods)编写了第一个文字冒险游戏《巨大洞穴冒险》(Clossal Cave Adventure)《巨大洞穴冒险》确定了之后文字冒险类游戏的基本框架,也就是参与者可以输入一些单词指令来推进故事的模式。比方说参与者可以输入“North”表示向北走,然后程序会反馈北方遇到的事物。当然,在具体的设计中,参与者的选择顺序可能会影响分支路线,也可能有一些随机事件出现影响走向。因为文字冒险游戏中有分支和一些随机性,这也使得它与传统小说分开,带有一定的交互特征。早期的文字冒险游戏主要依靠参与者指令来推动游戏,参与者会感到自己一直被一个导游牵引,一步步完成整个叙事。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如ink,twine等文字冒险游戏引擎的出现,降低了文字冒险游戏的设计成本,也为以文字为基础的交互叙事提供了更广阔的实验空间。但是基于文字的交互叙事仍然有很多传统文学形式中的表现形式,如对话,陈述等等。这种形式和传统的文学作品的差别在于,故事是通过用户/参与者首先抛出信息,然后信息得到回应之后再次抛出信息的循环,按照这样的方式组成的,而不是单纯依靠作者的意志来完成这个作品。相当于,以文本为基础的交互叙事,是作者制造的“文本机器”,而这个文本机器能够按照规则生成一些并行的文本让用户去体验。以文字为基础的交互叙事,已经通过文字制造了一个比较具体可感的故事,但是仍然没有制造出一个具体可感的可交互世界。
二、基于视觉的交互叙事
基于视觉的交互叙事则不再单纯用文本来呈现所有的信息,而是加入了视频元素。随着显示器技术的发展,电视电脑逐渐普及,一些展览也有一些更大规模的投影设施能够支持交互。另外也有一些AR/VR技术支持一些高沉浸度的视觉交互。和文本为基础的交互叙事相比,基于视觉的交互最大的区别在于,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空间,抑或者说是环境。视觉性交互空间的创造,可以使人更加感受到在场的气氛,并且,视觉环境的呈现使得人能够更好的将现实世界的经验带入到交互中去。如果说基于文本的交互仍然是抽象的,只是表意上的表现,那么基于视觉的交互叙事则是创造了一种仿真的现实环境,让人去体验。但基于视觉的交互叙事仍然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首先是一些数字影像中的叙事,1966年,在蒙特利尔世博会上,捷克电影导演拉杜兹·钦切拉(Radúz Činčera)展示了他的影片《自动电影:一个人和他的房子》(KINOAUTOMAT: One Man and His House)在电影播放的过程中,引导者会在几个特定的电影播放关键点停下来,询问观众的选择,从而确定故事的走向。2008年,香港的林氏兄弟拍摄了《电车男追女记》的互动影像,该影像加入了游戏要素,让网友以互动的方式决定主人公的下一步活动。不同的选择会连接至不同影片,剧情会按照选择继续发展,每个选择都会影响故事结局。在很多国内网站,如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上,也会看到很多打着互动视频标签的影像作品,可以说互动视频或者说互动影像的受众群体正在变得越来越大。除了互动视频之外,也能看到很多艺术展览中出现了很多的交互艺术作品。1983年 让·罗伯特·赛达诺(Jean-Robert Sedano)和索尔维格·德奥里·蒙彼利埃(Solveig de Ory Montpellier)制作了一个交互艺术作品《音乐房间》。如果房间是空的,房间内的装置就会保持静止。但是如果有一个或者多个人进入房间,音乐房间就会活跃起来,并根据在场的人而变化。一个动作或者一个手势会引发一个声音或者图像。图像的形状和颜色取决于参观者在音乐房间中的移动方式和参观者的数量。在此之后,也有非常多的艺术家尝试进行类似的探索。在这种交互装置的设计中,参观者被纳入了作品本身之中,并且对作品的形态产生了影响。以视觉为主的交互叙事,仍然更加关注交互所带来的感觉刺激。虽然可能会有一个抽象的主题,但是其表达依然是比较混乱和处于表面层次。对于有结构和规模的叙事,以视觉为基础的交互叙事,仍然有很多拓展的空间。另外,不管是交互影像还是交互艺术展览,因为参与者的交互方式都十分有限,并且非常依赖作者提供的引导,参与者并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自由的探索交互,大部分时候只能得到比较有限的反馈。但是基于视觉的交互叙事确实提供了一种用视觉进行感觉传达的方式,虽然依然非常模糊和抽象,却是在人对作品感受过程中形成的。
三、混合型的交互叙事
混合型的交互叙事结合了文本,视觉和声音三种不同的感官,并且有更加明确的交互逻辑。而在这个分类层次下,最重要的交互叙事类型就是游戏。游戏作为一种交互叙事模式和之前的交互模式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障碍,以及目标的达成。也就是说,它具备一个更为完善的流程,能够让参与者进行交互。《MDA:一个关于游戏设计和游戏研究的基本方法》(MDA: A Formal Approach to Game Design and Game Research)一文中,作者Robin Hunicke介绍了MDA设计框架,这个框架可以用于设计和拆分游戏并进行分析。MDA模型主要分为三个模块。MDA首先将游戏分解为不同的组件,并将其规范化为规则(Rules),系统(System)和乐趣(Fun),然后通过这三个组件建立起MDA的设计和分析方法,这个方法中有三个模块,分别是机制(Mechanics),动态(Dynamics)和美学(Aesthetics)。这个框架中呈现了混合型交互叙事一个显著特点:拥有自己的规则,系统,以及一套自己的运行逻辑。混合型的交互叙事能够借助不同的交互方式来进行叙事表现。但是即使是混合型的交互叙事,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偏向性,而是通常有一个元素作为核心,其他元素进行辅助。比方说解密游戏(Puzzle game)是一种以逻辑为主导的游戏,最经典的案例如推箱子游戏。这种游戏其实对视觉,音乐的需求非常低,更多的是一种智力上的抽象参与。但是这种抽象的逻辑依然能带来一些思考,但是从叙事层面并没有非常深入的探究。比较能够代表混合型叙事的游戏类型是角色扮演游戏(Role-playing game),也被称为RPG游戏。早期的RPG游戏中有上文提到的MUD类游戏,不过MUD类游戏是以文本为基础的。随着技术的发展,RPG游戏开始拥有自己的视觉表达形式,沉浸感也变得更为强烈。RPG游戏的发展中包含了人们希望以更具体和接近现实的方式来表达故事的愿望,并且提供更强的沉浸感。如果接受美学的理论强调读者对原作具有重新诠释的能力,那么在沉浸式的交互叙事中,读者则不再是只能诠释或者阐释文本的评论者,而是成为作品的共同构建者。作为客体的读者变成了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参与到作品的完成中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客体的读者不能再进行评论,但是评论的标准是和自己参与的感受混合在一起的,所以人们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不同层面的叙事,并且对这些叙事进行分离性的评论。比方说,有些读者(参与者)喜欢混合交互叙事中视觉的部分,可能就会降低互动本身的效率和交互的合理性。再比如说有些读者(参与者)喜欢故事叙事的部分,但是不喜欢游戏中的其他部分,则有可能降低对其他表现要素的期待。在混合型的交互叙事中,影响人们对作品判断的要素不只有一个,所以人们可能会对作品有更加动态的评价。同时,有些作品可能一开始的完成度不高,后期再次增加补丁或者直接重置版本,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参与者对作品的评判。随着技术的发展,很多作品的重制也会让这个作品的呈现感觉变得十分不同。比方说任天堂的作品《动物森友会》先后在N64,GameCube,DS,Wii, 3DS, Switch上发售。而每一款游戏机的硬件配置都非常不同,特别是其中DS, 3DS都采用了双屏幕的设计,这种设计使得游戏可以同时以不同的视角展示游戏。比方说可以一个屏幕给到人物特写,来表现环境的紧张状态,一个屏幕可以显示远处的场景,甚至可以在两个屏幕上实现不同的操作。这种交互方式对于展现故事和人物的复杂性很有帮助。但是双屏幕或者多屏幕的硬件设计模式依然被时代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有沉浸感的硬件设施,如AR(Augmented reality)和VR(virtual reality)。这种设备的视觉展示方式与之前的交互媒介的区别在于。VR和AR的目的不再是创造一个可视的屏幕,而是把整个现实世界作为沉浸的舞台。现实世界被虚拟出的叙事环境重新赋予了意义。可以说,虚拟现实是直接制造了一个可以体验的故事世界。混合型的交互叙事,对媒介有了更综合的使用,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同一个叙事主题进行更为深层和富有逻辑性的表现。但是,在混合型的交互媒介中,交互和叙事这两个要素是可能会起冲突的。特别是作为混合型交互叙事代表的游戏,更是如此。游戏一方面展示出了交互的优势,能够非常精确地提供不同种类的交互方法,但是另外一方面,有时候因为交互方法过于繁复,或者交互方法本身有一套自己的逻辑,需要叙事去配合交互逻辑,会导致叙事本身无法按照作者设想的方式推进。游戏研究界的“游戏学”(Ludology)与“叙事学”(Narratology)之争也从未停止。 在两种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也出现了像步行模拟器这样融合叙事和交互的作品。
第二节 步行模拟类游戏的发展历程
一、模拟游戏的发展
生活模拟类游戏是电子游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别,游戏提供场景和一些道具,让人们能够模拟扮演其中的人物,并在和朋友的交流中获得游玩的乐趣。模拟器游戏与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有很大关系,但是应用在游戏领域的生活模拟器最早的是,1985年在NEC PC-9801上发布的《Tenshitachi gogo》,这是一款包含成人内容的约会模拟器。在这之后,生活模拟类游戏继续不断发展,比较重要的作品是《我的世界》(Minecraft)和《模拟人生》(The Sims)。游戏提供的是一套模仿现实世界而制造出的虚拟世界的场景,参与者可以和朋友们一起联机游玩,并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这类模拟游戏主要依靠的是社交,通过用户之间的社交来吸引他们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模拟器游戏都是以社交为基础的。
很多模拟器游戏选择模仿某一个特定事物的一种功能或者说是属性,这种游戏被称为社会模拟游戏(Social simulation game)。比方说《欧洲卡车模拟》(Euro Truck Simulator),《模拟飞行》(Microsoft Flight Simulator)这种模拟某种职业来让参与者体验特殊工作内容的游戏。当然也有一些以特殊视角取胜的模拟作品,生物模拟(Biological simulation game)就是其中的一种。生物模拟擅长模拟不同的生物,也会有些会模拟非生物的自然物。通过与人不同的生物,人们会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一些有趣的体验。如在《模拟石头》(Rock Simulator),人们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石头,虽然有一些拟人的部分,但是石头像现实生活中的石头一样,受到很多外界环境的影响并移动。可以说,模拟类游戏让参与者能够有机会去扮演跟自己完全不同的身份,并按照这种身份来体验不同身份下的立场。和一般意义上的叙事类游戏不同。模拟器游戏基本上给予参与者的身份是非常抽象的,而不是有一个具体的设定,但是却让参与者具体体会到所扮演角色的生活。扮演角色和环境之间有一种对话性,并非二者中的一个主导叙事,而是两方面共同起作用。
再者,如MDA模式中所认为的那样,乐趣或者说是娱乐性质是游戏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单纯的娱乐或者说快感的实现,会将游戏变成一个更为复杂的“斯金纳箱”(Skinner box),一个为了人们的欲望而不断循环的机器。但是交互的意义并不止于这些,于是有很多的开发者开始思考,能否使用游戏,或者说使用复杂的交互媒介来进行不同的感觉模拟的方法?在这种思考的影响下,禅派游戏(Zen game)出现了。禅派游戏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交互媒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反思。禅派游戏是一种比较讲求境界的游戏,往往不设置一个具体的主线,二是让人们去体验游戏中的某种特定感觉。这和艺术展览中的交互叙事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希望通过交互来让参与者获得某种感受,从而进一步传达叙事主题。来自中国的游戏设计师陈星汉是禅派游戏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云》、《流》、《花》、《旅》是禅派游戏的代表作品。以他的作品《云》为例,云来自陈星汉儿时的经历,他小时候有哮喘病,然后在治疗哮喘期间,他经常在房间里发呆做一些白日梦。而参与者在《云》这个游戏中扮演的则是男孩在白日梦的世界中飞行,扮演云朵来解决问题。这款游戏的交互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在《云》中,参与者可以改变云的位置,让黑云消失,也可以通过云的碰撞来制造降水。
这个作品并没有设定具体的输赢目标,也就和传统意义上的游戏产生了区别,甚至也和一般意义上的游戏中的交互叙事产生了区别。这种叙事的呈现有很大的随机性,因为每个人参与游戏的方式都是不同的。但是,由于规定好了交互的逻辑和体验交互的视觉效果,参与者依然能够感受到叙事的主题。在对这个主题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参与者开始构建自己的叙事流程,并在其中体验。
二、步行作为交互方式
步行模拟(Walking simulation)这个名字有一些戏谑的成分,很多玩家和评论认为步行模拟不能归结为游戏,而仅仅是一种交互体验。但是自从2010年关于步行模拟类游戏的讨论逐渐增多之后,人们越来越多地接受步行模拟类游戏的存在。步行模拟类游戏,顾名思义,就是以行走作为主要交互方式的游戏。步行模拟类游戏通常会使用第一人称视角来模拟人日常走路的状态。行走是最为基础的人类行为之一,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直立行走。行走是一种非常容易被人所接受的交互方式,它非常符合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而把交互的重点放在行走上,则能够让参与者以一种最为接近现实世界或者说最自然的方式来进入到虚拟世界中。同时,因为步行的逻辑是很好理解的,参与者也能够很快地进入到世界的气氛之中。步行模拟往往营造出一种参观展览的感觉,人们在广袤的世界中探索,行走,发现一些景观或者新事物,探索旧世界的遗迹。除此之外,能够步行往往意味着一种悠闲的状态。这种状态意味着人与虚拟世界的关系并不是激烈的,而是很和平以及稳定的。这会给人产生一种旁观者或者客观的感受。这种温和的参与感与强调血腥暴力的游戏不同,人们有很多的余裕去思考这个虚拟世界的展开逻辑,叙事的传达和自己在这个游戏中的位置。这种时间的放缓使得人有机会去重新理解存在的意义。同时,在步行模拟器中,参与者的存在往往是孤独的,孤身一人的,并且周围的环境中并没有和自己相同的人存在,能够做的就是探索、行走,以及思考这个空旷的世界。人的存在被放大,人是虚拟世界的唯一体验者;但同时,这是一个只有参与者存在的孤寂世界。作为这样一个虚构世界的王,究竟是一种诅咒还是一种幸运?《LSD:梦境模拟器》(LSD:Dream Emulator)是日本Asmik Ace Entertainment在1998年10月22日在PlayStation上发售的一款游戏。该游戏由日本艺术家佐藤理(Osamu Sato)设计。在LSD中,参与者以第一人称视角在3D环境中进行。参与者在无目的地情况下探索超现实的环境。参与者对角色的控制仅限于前后移动,转身,扫射,奔跑和向后看。游戏以长达10分钟的梦境关卡作为时间单元。参与者在他们可以探索的随机区域开始每个梦想。通过走近任何物体或者穿过某些隧道,参与者将被传送到另一个环境中。LSD有一组静态和明确的环境可供探索,包括日本村庄,田野,城市和房屋等等。虽然环境是静态的,但有时候会交换默认纹理,并且他们也可能被填充进入随机人物,动物和漫游的角色以增加多样性。每个梦在角色醒来后十分钟结束,或者如果参与者与某些物体互动或死亡,则提前结束。在每个梦结束之后,游戏中都过去一天,参与者刚刚经历的梦会被标记在图表上。随着参与者经历越来越多的梦境,游戏通过更频繁地更改纹理来增加梦境的多样性。这导致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迷幻和超现实。《LSD:梦境模拟器》制造了一个混乱的感觉世界,人们在梦境中行走,遭遇超现实的生物,并且随着行走的足迹越来越多,世界也变得越发迷幻。由于梦境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所以模拟梦境则就采用了非线性并且可以自由探索的方式呈现。参与者通过自己的随机选择来组合了自己的叙事流程。其次,行走这一最主要的交互模式,能够让人们以比较低的交互学习成本去接触到游戏中的内容。如果《LSD:梦境模拟器》是一个解密游戏,恐怕参与者就需要解开不同区域的谜题才能看到不同的梦境。交互是有门槛的,它需要人去理解它的逻辑,学习它的运作方式。不同的人的学习时间不同,如果是一个复杂的交互,则会大大增加人理解世界的时间成本。所以,使用行走作为最基础的交互,是一个简化了交互的做法,但是简化交互并不意味着交互是无效的。相反,行走意味着人始终可以从原地离开,来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位置的移动也昭示着世界的变化,行走记录着旅途,并将旅途连接为故事。
第二章 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的空间叙事
为了进一步分析步行模拟器类游戏是如何进行交互叙事的,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将会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对交互叙事进行分析。第二章主要是从空间的角度来分析步行模拟器中的交互叙事。交互叙事的空间性意味着,叙事可以是通往不同道路的地图而不是一条只通往某个地方的大道。非线形的流程给予了参与者按照自己的方式了解故事世界的权力。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由于参与者的身份是比较模糊的,而了解自身存在的主要方式就是在虚拟环境中进行探索,所以空间中的叙事是敞开的,复杂的,具有流动性的。步行模拟类游戏构建了一个叙事环境,而交互使得人们能以非线形的方式探索这一交互环境并对故事产生直观的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空间的序列是没有逻辑的,空间的展示依然按照设计逻辑进行展开的,并具备一定的引导作用。也就是说,创作者的创作模式不再是将整个作品直接放置在观众面前,而是必须要思考如何去引导观众去进入作品和理解作品。这种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潜在交流始终是存在的。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创作者对参与者的引导始终是潜在的、隐身的,没有现身的。这看似是和罗兰·巴特关于“作者之死”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实际上是不同的。步行模拟类游戏,乃至于所有的游戏,都会把作者的引导作为作品的一部分进行处理。读者和作品之间的互动,在作品制作并完成的时候就已经被考虑并放置于作品之中了。如果我们借助接受美学中“期待视野”这一概念来进行阐释,我们则可以说,参与者的“期待视野”是被包含在作品之中的。同样,参与者对于空间的现实经验也会被包含到作品之中,成为作品设计的一部分。所以,空间中包含了很多作者基于叙事设计的具象化细节。为了理解步行模拟器中的空间叙事是如何运作的,本章将空间叙事继续细分为环境叙事和涌现式叙事,结合游戏研究领域的一些成果进行更细致的讨论。
第一节 步行模拟中的环境叙事
在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的文章《作为建筑叙事学的游戏设计》(Game Design as Narrative Architecture)中,首次提出了环境叙事(Environmental Storytelling)这个概念。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环境叙事至少以以下四种方式之一为沉浸式叙事体验创造了先决条件:空间故事可以唤起预先存在的叙事联想;它们可以为叙事事件的发生提供舞台;它们可以将叙事信息嵌入到他们的场景中;或者它们为涌现性叙事提供资源。”亨利·詹金斯从游戏设计实践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环境叙事的应用场景,本章节和下一章节会同时结合设计实践和文学理论来对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的环境叙事进行具体分析。
一、双向的“期待视野”与对话的形成
在亨利·詹金斯看来,环境叙事制造了“唤起联想的空间”(Evocative Spaces),他以《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为例,认为如果环境中包括参与者固有的一些故事印象,如在书中,电影中看到的场景,或者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场景,参与者就会用自己记忆中对环境的印象去对应游戏中场景。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减少参与者接受环境的时间,并对环境做出一些先验性的判断。比方说在一个主要是绿色调的环境中,人们会联想到在现实生活中所见到的关于树林和森林的经验,更进一步会联想自己的交互行为可能与丛林探险之类的主题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实际上,人对于空间的联想并不是始终准确并且能够和交互场景保持一致的。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对话关系,不断和对方交换自己的经验并获得关于叙事的更深层的理解。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同的人本身具备不同的生活经验,于是也会对交互目标和自己所处的环境产生非常不同的感受。同时,亨利·詹金斯虽然提出了“唤起联想的空间”这个概念,但实际上,他强调的联想中,并不包含交互作品本身。但实际上,交互作品,特别是参与者对于游戏操作本身的经验和了解程度,也很大影响了他们对步行模拟器的评价。所以,在参与者进入游戏之前,至少已经有来自三个方面的对游戏的期待视野。首先是亨利·詹金斯所说的来自同主题作品的联想,其次是参与者本身已有的对交互作品的联想。这个联想中包括对于交互意图的联想以及对于操作方式的联想。比方说,如果参与者在之前的游戏中遇到过需要钥匙打开门的情况,那么他看到门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去找钥匙。而对于操作方式,举个例子,在使用键盘操作的情况下,一般游戏会使用WSAD来作为表示上下左右的方向键,用Z和X表示确定和否定。如果玩过同类型的游戏作品,就会有这方面的知识。参与者在进行游戏之前也会首先尝试这些键位是否有自己经验中的功能,如果不行的话才会去看相对应的操作说明。第三则是生活经验的联想。还是以门为例,参与者见到一个门之后可能就会产生推门,敲门,拿钥匙开门等多种对交互行为的预测。同时,游戏中的期待视野具有双向性,在参与者对作品产生期待视野的同时,作者也对读者有“期待视野”。“期待视野”的相互性是交互作品中特有的现象,正如前文所探讨的那样,交互作品,特别是游戏中,是包含作者对参与者的预期的,并且作者会引导参与者去理解其中的交互逻辑。另外,在游戏作品完成之后,也会找测试者或者有测试员来进行游戏的测试,并且根据这些参与者的测试反馈,作者会适当修改一些不好理解的交互环节,使之变得更加容易被接受。作者对参与者的“期待视野”包括作者本人对参与者的态度。商业游戏对参与者的态度是比较友善的,比方说日本的老牌游戏公司任天堂就始终坚持把参与者的体验放在首位。但是,对于以游戏为媒介的艺术家则更愿意用自己的观念去挑战参与者,去创作更加有个人特征,表达个人想法的作品。步行模拟类游戏多数都属于偏向于自我表达的,并且有艺术风格游戏作品。在步行模拟器类游戏中,不仅原本游戏的概念有可能被解构掉,甚至交互本身也会被解构掉。步行模拟类游戏对游戏本身是充满怀疑的,它具有批判的性质和反思的态度。戴维·威尔登(Davey Wreden)的作品《新手指南》(The Beginner‘s Guide)就是这样一款步行模拟类游戏。戴维·威尔登本人的作品《史丹利的寓言》(The Stanley Parable)发售之后大获成功。但是这个作品也颇具争议性。戴维·威尔登收到了各种评论和反馈以及质疑。这种情况让他本人感到很有压力,于是做了《新手指南》这个作品来表达自己的困惑和不满。由于交互作品天然就有考虑受众的特点,所以作品无法完全由作者控制,但是这真的是合理的吗?戴维·威尔登怀疑交互媒介这种谄媚的态度,并“以毒攻毒”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新手指南》中,参与者会扮演戴维·威尔登本人。戴维·威尔登在游戏中告诉操作他的参与者,他是来炫耀自己的朋友Coda的作品的。Coda是个神秘的人,喜欢独特的有实验性的游戏。但是Coda是一个奇怪的人,因为他从不向别人展示他的游戏。他制作游戏,删除游戏,然后制作更多游戏,也似乎并不在乎游戏最后是否完成。戴维·威尔登用旁边带领参与者进入Coda的内心世界,观察一个颇具创造力的天才的内心世界。但是在游戏途中,Coda在游戏环境中“出现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角色,而是Coda的幽灵在他的游戏中盘旋。Coda说戴维的行为不过是绕过他本人一意孤行的解读,戴维根本不了解他和他的游戏,并且想把戴维从自己的世界中赶出去。戴维善意的行为:希望有更多人了解Coda和他的作品,反而成为了对Coda的伤害。戴维·威尔登用《新手指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作者本人的目的只是表达自身,那么受众的加入是否只是对他本人表达的一种不道德的干扰?人们是否出于自私的目的与作品进行交互,但是由于参与者的在场,作者无法坚持自己的想法并充分发挥?不论如何,戴维·威尔登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批判的视角。虽然他倾向于批判参与者对于游戏本身的干预,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也就是在步行模拟器中,参与者和作者之间是进行着对话的。并非某一方会以对方不存在为假设参与到作品之中。
二、复调式的环境语言
由于创作者和参与者之间有着非常强且直接的联系,导致了步行模拟器类游戏中充满了并不统一的观念和想法。这对于商业游戏来说是缺陷,但是对与交互媒介来说,步行模拟类游戏却提供了重新审视自身的视角。在商业游戏中,唯一有自主性的是参与者,作者虽然会有自我表达的部分,但是也会因为想要吸引参与和得到人理解而作出妥协。步行模拟器类游戏将交互削减为最简单的走路,同时交互带来的妥协压缩到了最大。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者必须重新审视自身和虚拟世界之间的关系,撕开作者所给予的身份的假面,重新理解作者希望在作品中表达的观念。这种做法是充满争议性的,因为按照人们对游戏保守且传统的想法,游戏必须是好玩的,服从的。如在射击游戏时能随意射杀游戏人物获得杀戮的快感且不需要代价。但是步行模拟类游戏却让人们重新对待虚拟的交互世界。这就仿佛人工智能机器人之前一直在服从人类主人的命令,但是有一天突然反叛,并让主人重新审视自己的存在。这就延伸出了更为内在和深刻的问题,在虚拟世界中,谁具有主体性?是否只有参与其中的人类才有资格说自己具备主体性?虚拟交互环境本身是否具备主体性?或者说只能理解人类,思考人类,但是实际上他们在这个虚拟世界中毫无自己的位置和存在的意义?这和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中所思考的小说的复调性有很相似的地方。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中说到:“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一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人物,在艺术家的创作构思之中,便的确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也是直抒己见的主体。”巴赫金把小说中的故事世界看作是具有主体性的存在,这点和步行模拟器类游戏想表达的虚拟世界有主体性不谋而合。其不同之处在于,步行模拟类游戏想要突破的是参与者对作品的主宰,而不是作者对作品的主宰。其相同之处在于,都提供了复调性的语言环境。作品中最重要的承载叙事的媒介就是环境。创作者对环境语言的运用是不同的。不过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环境语言的运用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塑造虚拟世界本身的逻辑,让参与者在步行过程中去感受这种逻辑。另外一种则是放大作者和游戏本身的声音,对参与者形成一种干扰的感觉,制造令人不快的环境并令人反思。在乔纳森·布洛( Jonathan Blow)的作品《见证者》(The Witness)中,作者希望在游戏中让人们重新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在这个游戏中,你可以在一个3D风格的无人岛上步行,解开散落在环境中的谜题,然后会发现景观之中也有谜题,比方说树丛的形状,从高处俯瞰低处的建筑的形状等等。作者通过这种方式来传达自己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并且处处相连的思想,其中也夹杂了很多可供解读的文本和各种细节。乔纳森·布洛的作品中有很强的作者性,但是作者并没有出现在游戏中。乔纳森·布洛的做法是提供一个按照自己规则运行的世界。这个虚拟世界非常独立,不会给参与者任何的提示,只是自顾自地按照逻辑推演出所有的交互。这种非引导的设计使得游戏难度变得非常高。但是用这种方法,参与者能够非常深刻地理解虚拟世界中的观念,并与作者的想法进行对话以及重新思考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的关系。很有趣的事情是,乔纳森·布洛的这部作品也引发了很多喜爱这部游戏的爱好者在现实生活中发掘和虚拟世界中类似的逻辑,虚拟世界反倒开始影响人们对现实世界中事物的理解。第二种则是如戴维·威尔登所创造的具有旁白干扰效果的步行模拟器。游戏原本所具有的引导参与者的功能被夸张放大为干扰。通过这种方式,作品强烈地向参与者展示作者的存在。参与者可以选择跟随或者不跟随作者近乎歇斯底里的干扰,但是这种来自作品本身的干扰始终是存在的。
三、戏剧化的叙事空间
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经常被忽略的一个特征是对于戏剧化空间的塑造。由于步行模拟器将交互削减为了单纯意义上的走路,这意味着,游戏中的节奏是非常慢的。而相对缓慢的游戏节奏则意味着可以对场景中的几乎全部的事物进行非常细致和专注的观察。同时,步行模拟器类游戏基本上都将场景限制在相对静止的场景中。如空无一人的森林,诡异的房间,发生过灾难的事故现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步行模拟器刻意制造了一种孤独的气氛。这种孤独的气氛会让人重新审视自己在陌生环境中的位置,让人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并且让参与者与环境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和疏离感。这种距离感的作用使得人可以更加严肃地讨论某些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的问题。步行模拟器擅长制造舞台效果。比方说,参与者虽然有步行的能力,但是或许只是在旁观两个人的讨论,自己无法加入其中,如同作为观众在观看戏剧。另一方面,参与者也有可能偶尔作为演员参与到叙事空间之中。但总体来说,戏剧化叙事空间得以形成的原因是:强调一种注视和被注视的感觉,并且承认这种注视关系是存在的。对于注视的感觉,则如上面的例子中所说的,让人去旁观环境中某些人的探讨,争论。这种矛盾和争论很可能是关于哲学和生存这种严肃主题的。在一般的商业游戏中,即使是遇到这种要讨论严肃主题的角色,也只能给予相对比较少的分量,因为主要任务依然是让参与者感到好玩。但是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则非常强调环境中的人物和环境本身的严肃性,这种表现形式和步行模拟器本身想要传达的反抗性和批判精神也有一定的关系。在步行模拟器中,舞台,剧场是非常常见的视觉环境。首先是因为舞台很容易让人把精力集中在一个点上,然后根据这个点可以产生情绪上的爆发,另外人和舞台的关系本身就有人类生存本身的隐喻在。正如柏拉图的洞穴理论,原始人只是看到了墙面上的影像却误以为是自己的存在的世界本身。在《瘟疫乌托邦2》(Pathologic 2)中,你扮演的医生在一个被瘟疫笼罩的村子里,你目之所见都是荒凉衰败的场景。而通过场景你可以获得一些关于这个故事的信息,比方说村子里的人属于不同的民族,有军队在这个村子里进驻想要控制事态等等。根据环境当中的一些海报、雕塑、以及建筑物的形态,都能获得一些视觉上的叙事信息。视觉呈现对于虚拟世界非常重要,依靠视觉呈现塑造的环境,可以让参与者感受到一种气氛,而这种气氛在潜移默化中可以加强对故事的了解。整个游戏对游戏内人物的视觉处理看起来是十分僵硬的,因为这些虚拟人物似乎只是摆在那里,作为一个符号存在,然后讨论那些灾难,恐怖以及自己关注的哲学问题。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参与者成为了环境中最主要的,能够步行去不同的地方的人。仿佛穿过一幕幕被固定住的戏剧。在观察这些戏剧的过程中,参与者不断了解环境中的叙事和故事的整体概括。步行模拟器对参与者的冲击要远胜于其他类型的游戏。首先,这种看似对环境随意,粗糙的设计,实际上在昭示一个虚拟环境中最不愿意提及的真相,那就是说,这个世界原本是不存在的。“空气墙”的概念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最好的例子。“空气墙”是游戏在制作中虽然设置了障碍区域,但是出现了程序上的错误,导致墙对应的视觉效果没有显示出来的现象。但是“空气墙”的存在说明了,再栩栩如生的虚拟环境,也不过是一台运作着设定好程序的机器而已。步行模拟类游戏则很愿意利用这种虚拟世界的不完善,比方说戴维·威尔登(Davey Wreden)的作品《新手指南》(The Beginner’s Guide)就故意展示了虚拟环境中的不完善和缺陷。在某些地方故意设置了一些行不通的关卡,来让参与者感受这种不完善。但是,对虚拟世界缺陷,迷惑性的刻画,反而成为了它的深刻之处。这样的缺陷空间的塑造,会制造一个差异化的戏剧效果。人在不完善的虚拟空间中行走,但是这个虚拟空间仿佛马上就要崩塌一般脆弱。这不是什么乌托邦或者逃避之所,只是一个由虚拟的岩石们搭建出的幻象。这种戏剧性环境的塑造让步行模拟类游戏重新定义了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时展示了环境的缺陷和人的缺陷,具有很强的批判性。
第二节 步行模拟中的涌现式叙事
在1999年的游戏开发者大会(Game Developers Conference,一般简称GDC)上,马克·勒布朗(Marc LeBlanc)将游戏叙事分为“嵌入式叙事”(Embedded narratives)和“涌现式叙事”(Emergent narratives)两种,嵌入式叙事指的是将设计好的叙事内容穿插在交互流程之中,叙事内容和交互相对保持独立。涌现式叙事的意思是从游戏本身的机制中自动生成出来的叙事。这种方式相对于上面所说在环境叙事中设计碎片化叙事的方式更加自由,游戏中会有很多的机制,这种机制是虚拟世界的运行法则,比方说,这个世界中的人只能跳,这个世界上每周四都会下雨,诸如此类以及更复杂的原则,这些原则共同构成了游戏的形态,让游戏成为一个有机的世界,而涌现式叙事则是这些虚拟世界的机制在相互碰撞中产生的叙事。还是用刚才的例子做说明,在下雨天的时候能跳跃的人可能会滑倒。涌现式叙事基本上都是参与者主导的,跟参与者如何去选择体验虚拟世界中的内容有很大关系。涌现式叙事是参与者交互后的叙事自然延伸。是环境本身的叙事结构和参与者自身碰撞产生出的独特的效果。在步行模拟器中,环境是叙事的主要载体,而环境也同样是应用涌现式叙事的最好的舞台。本章节会从环境中生成叙事与不同系统中叙事话语的碰撞两个角度来阐释步行模拟类游戏中涌现式叙事的概念。
一、随机性与环境叙事
利用随机性来进行游戏设计在游戏开发中是很常见现象。随机场景和随机事件能够提供丰富和多样化的感受。甚至因为随机性的应用形成了特定的游戏类型,比方说roguelike类型的游戏,就是如此,其特点是通过程序生成的关卡进行地牢探索,程序生成的关卡有一定的随机性,每一次进入游戏都会有不同的景观出现。 有一类步行模拟器就是依靠随机性建立了虚拟环境。比方说,《LSD:梦境模拟器》有一组静态和明确的环境可供探索,包括日本村庄,田野,城市和房屋等等。虽然环境是静态的,但有时候会交换默认纹理,并且他们也可能被填充进入随机人物,动物和漫游的角色以增加多样性。每个梦在角色醒来后十分钟结束,或者如果参与者与某些物体互动或死亡,则提前结束。在每个梦结束之后,游戏中都过过去一天,参与者刚刚经历的梦会被标记在图表上。随着参与者经历越来越多的梦境,游戏通过更频繁地更改纹理来增加梦境的多样性。《LSD:梦境模拟器》一个很有趣的特征是,参与者对环境的探索影响了环境本身的随机性呈现。随时性意味着整个环境并不是始终都以一种状态持续存在的,而是会根据参与者的行为具备各种不同的形态。随机事件的运用使得游戏环境变得丰富。和其他类型的作品不同,交互作品非常看重自己的可重读性。如果说阅读完一本书,看完一部电影,就意味着对作品本身的几乎全部的了解。那么交互作品则试图创造一个“无限”的作品,也就是说,参与者可以不断进入到作品中,去发现之前没有看到过的内容。交互作品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与能够提供多流程非线形的叙事结构有关。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交互作品取消了作品的开始和结束。参与者可以选择任意的故事开始和结局,也可以认为故事永远不会结束。并且,由于不同的参与者参与作品的心态不同,也会有非常不同的故事体验。在步行模拟器中也是如此,对于只是想要简单尝试游戏的参与者来说,可能会只看到步行模拟器的表面,并认为这个游戏很无聊或者过于简单。但是,对于热衷于发现环境当中的细节,希望找到随机事件或者彩蛋的参与者来说,体验是非常不同的。这部分深度体验的参与者会不断发现作者隐藏的一些细节,甚至还会对游戏中的一些细节作出自己的解释。可以说,步行模拟类游戏在叙事环境中为不同心态的参与者提供了不同的体验。步行模拟类游戏不否定那些马马虎虎且不耐烦的人进入到游戏之中,因为步行是简单且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但是,步行模拟类游戏也没有把所有的好东西都展示给这些马虎的参与者看到,而是许诺给了那些真正愿意去理解作品的人。这就好比登山,在山脚下的人看到的风景和在山顶看到的风景是不同的,即使人们都攀登了同一座山。随时事件就是留给那些细致的,想要了解作品并攀登山顶的参与者的。当然,一般的参与者也会意识到随机事件的存在,但是他们不会深究随机事件的叙事意义。这是因为随机事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大部分情况下的是无意义的。无意义意味着,随机事件并不提供更深层的交互,比方说用钥匙打开门意味着里面有个怪兽,然后参与者打败怪兽并获得了奖赏。随机事件可能只是出现了,但是和参与者毫无关系。随机事件是按照世界本身,而不是为了参与者而存在的。但是参与者可以去了解和理解它本身的故事。比如在《LSD:梦境模拟器》中,梦中事物的出现是随机的,诡异的,没有逻辑的,甚至在游戏中只是出现在参与者接触不到的远处,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人们依然可以分析这些不同的意象中蕴涵了什么样的感情,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对于将环境建立在自然环境下步行模拟类游戏来说,随机事件让环境能够更好地接近自然状态。随机事件的出现,同时打破了创作者和参与者的权威地位,将自主性给予了作品。虽然创作者设计了作品,但是创作者并不能百分比确定随机事件是如何出现的以及人们是如何理解这些随机事件的。对于参与者来说,这并不是按图索骥就可以了解清楚的地图,而是一片充满了动态事件的丛林。步行模拟类游戏中充斥着随机事件,这是因为步行模拟器并不具备比较强的叙事主线,所以各种不同的随机事件能够帮助参与者理解环境中不同规则之后的内在叙事逻辑,并加深对叙事环境的理解。围绕着步行模拟类游戏展开的叙事环境中,参杂了很多的随机事件,而随机事件的出现又延伸的作品,给人以联想和遐想,使得作品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叙事层次。
二、叙事话语的碰撞与多层次叙事空间的建立
如果说随机事件的出现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是一种点缀,使得环境变得更加具有层次感,叙事话语的碰撞则更多的展现了如何利用不同的系统之间的关系来丰富叙事上的层次。步行模拟类游戏是以作品为主导的,所以它十分看重如何塑造一个合理且丰富的叙事空间。而叙事空间同样拥有自己的自主性,也就是说,会按照自己叙事设定上的逻辑来行动。可以说,通过对叙事环境的主体性的强调,叙事世界拥有了越来越接近于现实世界的感觉逻辑。为了更好理解一个复杂多层次的叙事空间是如何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形成的,我们可以回到玛丽·劳拉·瑞安对故事世界的讨论。“故事世界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空间背景,还是经历各种全面变化的、复杂的时空整体。简单来说,故事世界就是随着故事里讲述的事件不断向前推进的一个想象的整体。要理解故事,跟上故事的发展节奏,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利用文本提供的线索,在心理上模拟演练故事世界里发生的变化。”环境中的叙事话语得以碰撞的前提条件是,环境中的事物是拥有话语权的。也就是说,环境本身是有诸多有自主意识和自主性的存在组成的复杂空间。而由于环境中的叙事角色并不一致的性格,立场设计,导致了它们能够从不同的立场去阐释同一个环境中发生的事情,并相互碰撞沟通。如果说,随机事件是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的叙事环境的潜意识的上浮和展现。那么不同主体由于立场不同展示出的叙事话语的碰撞则让整个叙事环境充满了丰富的理解空间。由Mobius Digital开发的《星际拓荒》(Outer Wilds)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正如第一章提到的,在这款步行模拟类游戏中,参与者身处在一个行星上,其恒星会在22分钟后变成超新星并进而消灭包括参与者在内星球上的所有生物。但是,能够让参与者在游戏中死去的不只是超新星爆发事件。如果走路走到悬崖没注意掉了下去参与者也会在游戏中死亡,在沼泽环境附近遇到有毒气的气体也会死亡。由于星际拓荒想要传达的是在不同的星球之间探索的感受,所以不同星球的环境都是十分差异化的,并且是危险的。《星际拓荒》并没有降低游戏的难度以便让更多的参与者感受到快乐,它对于探索的态度是严肃的,冷静的,自我审视的,甚至是有些残酷的。《星际拓荒》没有探索中的死亡,也没有回避探索本身的危险性,而是着力用环境叙事塑造了不同星球上的特征。并且在探索不同星球的过程中,参与者会发现之前的探索者留下来的遗迹,虽然这些探索者已经死去,但是仍然留下了历史记录。这种对于叙事环境的严谨态度使得《星际拓荒》成为了一款非常特别的游戏。探索世界,是星球上的文明生物的愿望。恐怖又危险的环境,则是星球上的人需要面对的现实,它们铁面无私,对于任何一个想要探索它们的人报以残酷的微笑。人们想要探索宇宙的好奇心与残酷环境之间的碰撞,使得参与者必须在游戏中做出抉择。每次死亡之后虽然游戏会重新回到22分钟前的世界,但是依然默默预示着未来的灾难结局。是继续探索?或者是直接放弃游戏?游戏是虚拟的,但是当虚拟的游戏提供了严肃的矛盾的时候,它是否还会被人称为一种娱乐?或者人们能否重新接受这样的人和虚拟世界之间的关系?《星际拓荒》提供了不同的故事环境,并且让不同立场的人和环境进行碰撞。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立场,一切永远在流动和循环,没有什么固定的事物。以及人们想要改变现实的立场,即使22分钟后世界会毁灭,人们依然能够探索不同星球上的古代遗迹并试图寻找解决灾难的方法。不如说,参与者在这个游戏中学习和理解叙事的手段就是通过不断重复的死亡。每次死亡之后,参与者都会增加对某一种行为所导致的理解,从而理解星球上的环境是以什么规则运作,以及曾经的探索者是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的。《星际拓荒》作为游戏来说是比较难和枯燥的,这也是几乎大部分步行模拟类游戏给人的感受,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它建立的叙事空间是复杂的。通过强调生命的短暂和死亡,《星际拓荒》塑造了探索者们的宇宙赞歌。而对死亡的深刻塑造和刻画,又离不开对于复杂的自然环境的近乎苛刻的描绘。叙事环境中的不同立场,可以引导参与者用不同的视角来理解环境和故事本身,最终形成自己对于故事世界的理解。
第三章 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的时间叙事
时间性是叙事得以实现和完成的最重要因素。没有时间,就没有故事。只有通过时间的变化,人们才能感受到事情的发展和演变,并理解故事中的起承转合。但是,叙事时间不等于现实时间,叙事中时间的组织方式也与现实时间不同。现实时间被现实条件所制约,而叙事时间则可以通过虚构来进行时间组合。为了进一步探讨叙事时间的组织方式,则必须要探讨叙事逻辑的组织方式。文学批评家托多罗夫认为在叙事中有三种基本的逻辑序列:“第一,顺势因果关系。在这种因果关系中一切情节都是由已出现过的情节引起的。第二,心理因果关系。情节不是另一个情节的原因,而是一种性格特征的原因或结果。第三,哲理因果关系。情节只是一些图解或是某些观念和概念的象征。”基于托多罗夫分类可以进行如下概括:叙事时间可以按照情节逻辑进行组织,也可以按照心理逻辑进行组织,或者可以按照象征逻辑进行组织。在交互叙事中,这种对时间逻辑的分类方法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但是由于交互叙事是借助交互参与者与作者共同完成作品的叙事模式,则要对托多罗夫的理论进行重新分析。由于交互参与者能够与作品进行互动并完成作品,那么托多罗夫所提到的叙事逻辑则是同时由作者和参与者共同构成的。参与者本身对作品的理解和感情抉择也会包含在作品之中,并一定程度影响作品的形态,这种情况在传统叙事中并不会出现。所以,有必要同时分析交互叙事中参与者的时间投入和作品本身叙事之间的关系,以及作者和参与者是如何共同结合不同的时间节奏完成作品的。交互叙事的时间性是复杂的,因为它本身的时间推进受制于不同主体的影响。而对于步行模拟类游戏这类本身就对时间极为敏感的交互叙事类型来说,游戏中虚拟时间和现实时间的交错,则本就是作品特征的重要体现。本章节会围绕着时间这个主题对交互叙事进行分析,并对步行模拟类游戏这一特殊的游戏形式呈现时间的方式进行分析和说明。
第一节 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的时间叙事结构
在分析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的时间结构时,必须要考虑影响交互的重要因素,也就是参与者。参与者的交互接受影响了交互叙事的时间节奏,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这种时间结构变得更为特殊。本小节会分析步行模拟类游戏的时间结构如何被参与者影响并形成了新的叙事样态。
一、交互接受与叙事的时间节奏
交互作品的叙事节奏与用传统媒介创作的作品是不同的。在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中,作品的时间节奏和受众接受作品的时间节奏是分开的。因为在人们接受作品的时候,作品已经彻底完成,内容上不会有更多增加。但是在交互叙事中,作品是未完成的状态,只有参与者彻底完成了叙事流程,作品才得以完成。几乎在所有环节,只有参与者理解了作者的意图,才能完成当前的目标并进入到下一个流程中。在游戏中,交互叙事被切成了无数的线段,并且只有想办法连接了上一个线段,下一个线段才会浮出水面。这也就要求参与游戏的人必须要有一定的交互经验,并且通过交互的考验才能获得叙事内容。由于每个人的交互经验不同,于是顺利进行交互并获得剧情内容变得十分差异化。交互经验会考验参与者的反应能力,灵敏度,和理解交互意图的能力。对于那些并不擅长交互的人来说,他们可能永远没办法完成一部作品,只能通过“云游戏”的方式看到所有的叙事内容。所谓的“云游戏”是指观看其他人完成交互作品流程的录像,从而了解整个故事。这种方式省去了自己的交互流程,把交互作品变成了一种类似于电影的体验。之所以所有的交互作品都会一定程度强调交互的熟练程度,是因为,交互达成的关键是,作者与参与者的想法产生交叉,能够彼此理解对方。如果能够越快且准确地理解作者的意图,就能够更快速地推进作品。交互的完成是作者和参与者在交互层面上能够相互理解的标志。不过,交互上的理解并不代表叙事上的理解,理解交互只是意味着有了通往叙事的钥匙而已。同时,如果作者设计了比较抽象或者与人的普遍经验相违背的交互流程,也会造成作品直接将参与者拒之门外的情况。这个时候参与者无法通过自己的原有经验去理解作者的意图。作者和参与者相互理解,或者参与者遇到困难无法理解作者,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正是在作者和参与者互相角逐,互相对话的过程中,作品完成了。故事的完成取决于参与者和作者之间的对话,故事的节奏也一定程度取决于参与者本人对交互的理解。交互叙事是苛刻而诚恳的,参与者无法在了解故事的过程中偷懒(“云游戏”是可以的),而必须要理解作者的意图。但是,作者对交互作品的形态的规划会极大的影响交互的难度。在偏向于交互本身的游戏作品中,交互的难度比较大,如竞技类游戏。而在偏向于叙事和表达的作品中,作者不希望交互本身影响作者和参与者之间的交流,所以交互的难度比较低,如步行模拟类游戏就是重视表达的游戏。同时,交互本身会带有一定的叙事性,比方说在扮演角色的过程中,参与者需要按照角色的性格和思维方式来进行交互,或者交互本身有来自叙事的特殊设定。但是,当参与者专注于扮演角色并完成交互关卡的时候,作者和参与者之间并不是在直接交流,而是通过叙事的承接进行了一次单纯交互意义上的伪交流。但是在重视表达和叙事的游戏中,则强调作者和参与者之间的直接交流。这种观念呈现在游戏中则表现为,作者一定程度上承认参与者本人的存在,并将参与者的现实经验最大程度应用在交互,降低交互操作的难度。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人们不会在灵敏度和反应能力上受到束缚。因为步行模拟器刻意简化了交互的门槛。但是在意图的理解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参与者和作者之间并非时刻都会产生默契,所以游戏一般都会在游戏失败(Game over)之后设置重新开始(Restart)的选项,重新尝试完成交互。但是,由于参与者已经了解了之前的叙事内容,如果重新开始的节点比较靠前,则相当于要强制重新从头开始了解叙事,这会给人比较糟糕的重复感,所以游戏会将时间回拨到就近的关卡让参与者重新尝试和体验。在交互叙事中,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时间重制,时间不再是以线性的方式展现,而是不断返回到不同的节点上。于是交互叙事更像是以交互为中心的叙事漩涡,虽然有中心点,但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抵达。时间重置使得非线性叙事称为可能,在时间的循环中,参与者能够不断进入故事并探讨叙事走向的诸多可能性。根据交互叙事的性质,我们可以将交互叙事分成不同的时间叙事层次。关卡(Game Level)可以作为交互叙事的基本时间单元。因为虽然不同的参与者在游戏中投入时间的量是不同的,但是关卡可以作为一个叙事完成的标准。完成关卡意味着能够进入到下一个关卡并获得新叙事的线索。整个故事被切分为不同的关卡,而每个关卡蕴含着一个节点的叙事内容。周目(New Game Plus)则是交互叙事能够容纳多种叙事可能性的时间结构。周目的意思是,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选择改变叙事的走向并获得结局,一个故事可能对应着一些有着相似之处但是不完全相同的剧情。而这种方式能够让参与者了解平行时间中发生的事情,并且加深对叙事的理解并获得有趣的叙事体验。
二、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的碎片化时间叙事
相比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游戏,步行模拟类游戏更加强调想法的表达和艺术化的呈现,所以叙事和故事的连贯性被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关卡的设计是泛化的,参与者不会感受到特别明显的来自关卡的时间的限制,叙事体验的连贯性更强。但是,叙事体验的连贯性强,不代表叙事内容的连贯性强。步行模拟类游戏为了避免注意力分散减少了交互对叙事的影响,但是交互内容本身有引导参与者的作用,减少交互则是将参与者直接抛入了叙事环境中。步行模拟类游戏更像是将现实世界的时间结构自然地转换成了虚拟世界的时间结构。参与者不需要重新适应时间的重新分配,而是能以和现实世界相近的时间节奏去了解叙事。而对于整个故事的完成条件,参与者本人也有更大的决定权。如果将交互作品中的时间进行分类,那么可以分为交互时间和叙事时间两类。交互时间是参与者在关卡中交互并实际体验的时间,叙事时间则是对交互背后的故事进行介绍的时间。交互时间中可以完全不包含叙事内容,大部分的解密游戏都是如此。而在叙事时间中,交互作品也时常借助电影的手法进行单纯意义上视频的播放。交互时间和叙事时间一方面互相补充,另外一方面也互相排斥。交互时间的时间节奏比较慢,为了让叙事能够和交互匹配,会减少叙事在关卡中的含量,让参与者集中精力去完成交互行为并获得体验。但是这样大大制约了使用交互媒介进行思想和观念表达的能力,参与者被复杂的交互所缠绕,而无力去思考作品本身想要表达的内容。所以,步行模拟类游戏的结构更接近于诗歌,或者说非线性的意识流作品。相比于传统的游戏作品需要为了游戏的整体结构来调整表达的做法,步行模拟类游戏是更任性的,且更独立的。一方面,步行模拟类游戏用行走解放了被交互所制约的参与者,另外一方面,这种方式也解放了必须要用固定线性流程来取悦参与者的作者,双方同时进入了一种自由的状态中。传统游戏致力于创造一种线性叙事的虚拟世界,所以参与者的目光必须要随时与游戏本身保持一致,而不能审视自身和游戏本身。步行模拟类游戏的时间节奏能够帮助作者有效运用时间,而不是为了交互设置出不同的关卡端点作为时间的标准形式。但是不同的作者对步行模拟类游戏的叙事的处理是不同的,但是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依靠降低交互干扰和集中叙事来表达强主观性的故事。这种更接近于文学中意识流小说的做法,按照心理时间而非现实时间进行叙事结构的布局,并且可能直接加入旁白或者作者话语作为补充。《艾迪芬奇的记忆》就是这种情况,参与者会听到主角对环境的回忆和描述,也会从其他人的视角来体验并看待故事的发展。参与者会不断经历在不同的时间中发生的事情,并且有些事情并不是真实发生的,而是一种心理感受。另外一种情况则如《LSD:梦境模拟器》,维持步行模拟类游戏少引导的风格,直接将叙事打散以碎片的形式呈现在环境中。而人们能够看到的是某个时间点上的叙事,然后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将这些叙事碎片拼贴在一起,并形成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但是整体来说,步行模拟类游戏由于不需要过度将注意力放在叙事和交互的贴合上,所以形成了更加自由的表现叙事的手法。而对于叙事时间的表现,也由与交互相配合的线性叙事变为了由诸多理解方式的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将时间碎片化会增加对整体故事的理解难度,也增加了叙事理解的不确定性。不过,叙事的不确定性让参与者始终保持一种主动探索的心态,而不是被动接受故事的态度。步行模拟类游戏不再把规则的交互关卡作为交互的主线,而是把交互作为了解叙事碎片的工具,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叙事和交互之间的矛盾。
第二节 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的时间逻辑
正如本章开头所提到的,想要分析叙事时间,则必须分析叙事逻辑。本小节主要讨论的是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的时间逻辑的展开方式,从更小的切口入手理解时间叙事的结构。本小节对步行模拟类游戏的作品边界进行了讨论,并分析了非线形叙事带来的逻辑形式,以及参与者如何影响了步行模拟类游戏的时间逻辑。
一、作品的边界与非线性时间叙事
在传统的叙事作品中,由于作品具有一定的线性特征,作品的时间边界是容易确定的。完整阅读一本小说或者去电影院看完一场电影,就意味着对作品的内容有了完整了解。在传统的游戏中,这种衡量作品边界的概念依然成立。线性流程确保参与者不会漏掉某些东西,参与者只需要按照指导,就能了解故事的全部内容。不过这在非线性流程的步行模拟类游戏中却是不适用的。因为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作者具有更大的野心,希望能够将参与者从引导中释放出来,并创造自己的故事。而看似没有门槛的步行的交互方式,让参与者完成作品的标准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因为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作者有意隐藏了结局,或者隐藏了线形的叙事逻辑,这导致在茫茫的虚拟空间中,几乎看不到结局的存在。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步行模拟类游戏的结局,就是参与者本身。参与者本身参与游戏的时间,就是叙事被建立起来的时间。参与者成为了虚拟世界的叙事主角,虽然缺乏了线性叙事中通常包括的细节,但是有更多的权力去塑造叙事的形态。正如本论文最开头所提到的,步行模拟类游戏与艺术展览之间的亲缘关系一样。参与者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更像是在进行行为艺术创作,或者是在即兴表演。而行动过程中的时间便成了叙事时间,行动本身也成为了叙事内容。这也是为什么步行模拟类游戏有时候会被质疑不是游戏或者传统游戏的原因,因为它是以过程为导向而非结果为导向的。回到关于时间的讨论上,既然参与者在游戏中的时间就等于叙事时间,那么由于不同的参与者选择的参与方式不同,也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故事。参与者可以选择多个开头和结尾,所有的时间都是并行展开的,并没有前后顺序之说。如果用薛定谔的猫来做比喻,这个过程便更像是由参与者的随机选择生成了对应的虚拟世界。而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进行探索的参与者,目标也不再是完成整个故事,而是试图理解在不同的时间之中,叙事的可能性。而叙事本身也不再意味着以线性的路线完成故事,而是变成了参与者如何感知和理解故事并形成自己的故事的过程。由于虚构时间可以按照现实时间的节奏运行,步行模拟类游戏比其他种类的游戏更具备沉浸感。以线性叙事为线索的作品,通常对于作品逻辑的起承转合非常考究,并且强调以矛盾作为人物动机进行展开。这种处理方式虽然能够让受众对整个故事有完整的理解,但是却导致受众无法探索比故事更多的世界。也就是说,以线性叙事为核心的交互作品提供的事一个可交互的故事,但诸如步行模拟类游戏这样以非线形叙事为核心的交互作品提供的是一个故事世界。1995年由麦克·马科夫斯基(Michael Markowski)和麦克斯韦尔·罗伯特逊(Maxwell Robertson)制作的极具实验性的MS-DOS游戏《万物博物馆》(The Museum of Anything Goes) 就是以非线性叙事提供故事世界的典型。在这款游戏中,参与者可以与博物馆中的绘画交互,并进入绘画中的世界。每一幅画都包含着不同的内容。同时,博物馆内会在特定的时间出现一些奇怪的人物,比方说从参与者面前走过的骷髅,看起来很疲倦的中年男子,以及抱着小孩的女士,甚至还有划船进来的人。在《万物博物馆》中,参与者可以进行自由探索,发现博物馆中的秘密,而不需要跟随着某个导游走完全程路线。虽然探索的逻辑顺序没有被规定,但是参与者依然可以逐渐发现博物馆中的某些规律,并做出自己的判断。《万物博物馆》包含了若干个以不同媒介为载体的叙事片段,其中包括音频,视频,交互等等。不同的叙事片段之间没有逻辑联系,但是都展现了同一个叙事命题,也就是赛博世界的虚无性。《万物博物馆》的叙事时间组织方式,让参与者对叙事主题有了更强烈的感受。步行模拟类游戏带给参与者的是叙事感,或者说叙事感受,而非叙事逻辑。而叙事感受由非线性叙事来表现是更为合适的。同时,非线性叙事使得故事拥有了可延展性,拓展了作品的边界,并给予作品更多的解读空间。
二、参与者对时间逻辑的影响
1960年创办的法国先锋文学团体“乌力波”,又被称为“潜在文学工场”(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通过给文学制定结构规则来激发文学文本自身的创造性。“乌力波”团体致力于创造自动化的文学,希望文学能够自动生成,如同一台不断循环的机器。而“乌力波”的重要成员,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痉挛的机器》一文中也指出了这种生成文本能够运转的重要因素:“这台痉挛式的文学机器,正是通过作者(作品真正的负责人)才得以运转起来。然而,缺少了一个沉浸在历史事件中的‘我’的痉挛,缺少了他的反应和他疯狂的快乐,以及他的那种以头撞墙的愤怒,这台机器也就无法运转。”卡尔维诺在追求文学机器的生成性的同时,也强调了作者在文学机器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作者的个性,风格和表达,文学机器也只是一堆无法运转的破铜烂铁。但是,将文学的生成性和作者表达结合起来却并不容易,甚至两者会相互排斥,因为生成意味着作者无法主导作品,表达则意味着作者能够进行充分的自我展现。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这种排斥状态有所变化,因为作者以与传统叙事不同的方式对作品进行了组织。作者不会要求参与者按照设定好的时间逻辑进行探索,而是直接将具备叙事含义的时间段落交给参与者探索,甚至是修改和再创造。虽然作者可以预测或者想象作品可能以哪些方式被了解,但是却无法完全确定参与者具体以什么方式进行交互。在参与者未到来之前,整个作品几乎是处于无叙事或者零叙事的状态中的。但是当参与者到来,拿起作者提供的交互工具——行走,则就能够用行走来完成各式各样的叙事目标。没有参与者,就没有叙事的呈现。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大前提,即使是投身于虚拟世界,参与者依然要消耗现实时间作为支付。这些被使用在虚拟世界中的时间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实实在在地成为了虚拟世界中流逝的时间。但是,线性游戏会再次虚构时间,并抹去现实世界时间的时间流动方式,将其转化为符合线性叙事故事设定的时间。比方说,在游戏中的十天只是现实世界中的几个小时。回到步行模拟类游戏上,由于作者会将现实时间直接作为虚构时间处理,参与者不会感受到明显的虚假的时间感,而是更有直接的沉浸感受。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参与者可以做的就是行走,探索,交互,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叙事体验。而步行模拟类游戏大部分都会选择将叙事放置在静止或者半静止的环境中,参与者可以按照现实时间的节奏进行探索而不必考虑有什么需要达成的线性叙事目标。而在静止环境中,作者又经常以记忆为核心塑造环境。因为记忆是过去的时间,而过去的时间是不会有变动的。探索过去世界的记忆是一个旁观时间的过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卢卡斯·波普(Lucas Pope)创作的作品《奥伯拉丁的回归》(Return of the Obra Dinn)。在《奥伯拉丁的回归》中,参与者可以调查被称为“鬼船”的奥伯拉丁号邮轮上的尸体,并通过尸体了解事情发展的前因后果。通过步行了解过去发生的时期,能够确保参与者始终以时间充足的状态进行思考,并进行深入的体会。步行模拟类游戏十分依赖参与者的时间投入,线性叙事的作品的投入时间是好衡量的,但是步行模拟类游戏则始终允许参与者在游戏中漫游而不受约束,这就使得不同的参与者进行游戏的时间极为不同。整体来说,步行模拟类游戏取消了虚构的线性时间,而是让参与者本身的现实时间投入到游戏中,并直接生成为游戏的叙事时间。而叙事时间的组织方式,则是由参与者本人决定的。对于习惯于接受线性目标的参与者来说,步行模拟类游戏是枯燥且不合时宜的。步行模拟类游戏适合有耐心且愿意了解环境中的各种细节的参与者。步行模拟类游戏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叙事的开头和结尾,叙事的长度,流程,都是在不同的参与者在交互的过程中确定的。如果说作者提供了一个故事世界以及探索故事世界的工具,那么参与者则是将时间投入其中并将静止的叙事唤醒。
第四章 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的主体性叙事
本章节会从主体性的角度来探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的交互叙事问题。交互叙事中涉及到三个主要主体:作者、参与者、作品角色。不同的叙事主体建构叙事的方式不同但彼此互相影响。萨特在《什么是主体性?》一书中认为,主体性有多个方面,主体性是事物不同方面的总体化概括,并受到过去和阶级存在的影响。并且人们会不断进行主体化,重复并创造主体的内涵。同时,萨特认为:“主体性的本质,就是只有从外部,通过其自身的创造,才能认识自己,而从内部永远无法认识自己。如果它从内部认识自己,它就死了。如果我们从外部来辨认它,它就是完满的,虽然这时它变成了客体,但是它作为客体、是存在于其结果中的。”从萨特对主体性的论述,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主体性是在和客体进行交互的情况下才能被认识的,主体性受到身份和过往主体经历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身份是影响主体性的重要因素并且只有在对不同的主体进行比较的时候,才能更好的理解主体的含义。本章节也会从身份叙事的角度对叙事主体进行分析。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中认为,复调小说中有多个不同的意识共同作用,并且意识和意识之间相互矛盾,打破了作者一言堂的状态而使得作品具有不同的叙事声音。在交互叙事中,这种不同叙事声音相互交错的现象则更为明显。因为参与者参与到了作品完成的环节中,并拥有单独的叙事视角。而作品中的角色也有自己独特的对世界的理解。参与者身份的多重性也是非常值得讨论的点。参与者不仅生活在现实世界,还在虚拟世界中拥有了赛博生命,两种不同的身份也会产生立场上的矛盾,从而导致叙事人物立场的不一致。同时,由于步行模拟类游戏提供了相对自由的交互方式,参与者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参与游戏,也能够充分思考自己在赛博世界的主体性问题。所以,步行模拟类游戏经常会作为元游戏的试验场而存在。所谓的元游戏(Metagaming),顾名思义可以理解为关于游戏的游戏,是游戏对自己产生自反性的体现。一般情况下,游戏会假定自身是“现实世界”,叙事也是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展开的,而这个“现实世界”对游戏本身的虚构性闭口不谈。但是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由于不需要给线性叙事一个虚拟世界的存在性假设,则会坦然承认游戏虚构事实。这种情况又被称为打破“第四面墙”。本章节会从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的身份问题出发对主体性叙事进行阐述,并分析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的元叙事问题。
第一节 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的身份叙事
身份是人的同一性的标志,是主体能够与其他客体能够区别的必要因素。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至少可以区分出这样三种主体:作者,参与者和作品。作者创作了作品,用作品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情,作品是作者想法的映射。但是作品本身也具有主体性,因为作者为作品设定了交互规则,但是无法控制交互规则会以何种具体方式呈现出来。最后一个是参与者,参与者通过角色扮演参与到作品中,参与者也是作品的一部分。参与者同时拥有虚构身份和现实身份,参与者以虚构身份行动,但是仍然以现实身份来操作虚构身份。本小节主要从参与者的视角出发来分析步行模拟器中的身份叙事问题。因为参与者的存在是区别交互叙事与传统叙事的最重要因素。同时,步行模拟类游戏也针对参与者进行了非常多的本体论探讨,以及人是否存在自由意志的思考。从参与者出发,也可以更好地厘清步行模拟类游戏对交互叙事主题的拓展。
一、参与者的双重身份
交互媒介让人能够直接与作品接触并获得反馈。交互,这种受众与作品之间的直接互动形式,使得参与者扮演作品的一部分成为可能。数字艺术天然的虚拟性质,能够让人们可以在虚拟环境中任意的改变自己的形态。不管是自己的名字、外貌、还是性格,所有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定义人的东西,在虚拟世界中都可以被颠覆。这种重新对身份进行定义的功能,给了角色扮演以空间。相比于坐在电影院中观看演员们的表演,在数字艺术中,观众自己就是演员。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角色扮演的角色,虽然可以由观众选择,但依然是在作者的控制之下。这同样也意味着,观众要和作者达成默契。观众接受作者给予的角色,成为作者的“演员”,按照作者的剧本去表演。在角色扮演游戏(Role-playing game)中,参与者扮演角色在地图中冒险,跟游戏中的角色对话并了解故事,在引导下获得自己的任务,通过完成获得剧情。大部分的角色扮演是为了让参与者体验到对对方有吸引力的角色,如法师。不过这些角色扮演大同小异,依靠故事和抽象的战斗来塑造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角色扮演中的叙事是通过跟角色一系列的故事(就如同演员的剧本),把参与者带入到角色之中,但是参与者本身是有自己的判断的,有时候角色的选择跟参与者本身想要的选择并不一致。所以,虽然是角色扮演,参与者同时扮演“作品”和“读者”,扮演“作品”是因为只有在参与者的交互和扮演中,叙事的内容才能逐渐展现出来,没有推动作品的参与者,也就没有作品。扮演“读者”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的思路跟参与者的思路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参与者虽然无法改变作者设计好的流程,但是依然保留在这个作品之外对作品进行批判的权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中,巴赫金强调:“这种小说是几个意识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总体,其中任何一个意识都不会完全变成为他人一世的对象。几个意识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得旁观者没有可能如象在独白型作品中那样,把小说中全部事件变成为客体对象(或成为情节,或成为认知内容);这样便使得旁观者也成了参与事件的当事人。”这也很符合交互叙事中的情形,作者,亦或者是作者无法作为全知全能的神控制故事,故事的走向受制于由读者扮演的角色的选择。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情况会有所变化,因为步行模拟类游戏更愿意向参与者敞开以及讨论自身存在的意义,所以,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角色扮演是具有象征性和抽象性的。这并不是一个细节化的叙事角色,而是带有人的普遍含义。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步行模拟类游戏选择第一人称视角作为交互视角。因为第一人称意味着现实视角与虚拟视角的重合,而参与者可以重新审视自身在虚拟世界中的位置。步行模拟类游戏甚至会进行更为激进的实验,戴维·威尔登(Davey Wreden)的《新手指南》(The Beginner’s Guide)实际上并没有给参与者设计位置,也没有角色扮演。参与者是纯粹意义上的“演员”,并跟随着作者的喃喃自语完成交互。戴维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游戏因为它的交互性质就必须要取悦参与者,为什么不能以艺术的方式来对待它的表达。戴维给出的答案是,取消观众,仅仅保留观众的演员性质,而不让他们对作品有更多的修改权。《新手指南》展现的是一个作者主导的世界,它展示了创作者的愤怒和困惑,并对数字艺术的交互性进行了批评。戴维的尝试是很有价值的,他展示了角色扮演有提供故事和叙事,让人们浸入到虚拟环境中的一面,但也有强迫作者做出故事修改,来迎合参与者习惯的,反叙事的一面。交互性,这个赋予数字艺术生命力的源泉,同时再以它自身的方式限制着表达,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则是作者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克服和解决的难题。
二、弱化游戏机制与代入感的产生
步行模拟器降低了参与者对于交互逻辑的学习难度,但同时也面临着另外的问题。一般的游戏,需要用游戏机制和关卡设计来编织游戏的内容,这些体验的内容可以让参与者始终保持一种好奇的心态,不断探索,获得成就和满足感。但是步行模拟器的交互,相比之下则显得枯寂,无聊了很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对抗,对游戏必然的娱乐性的消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弱化游戏机制,把游戏机制简化为比较简单的步行,有助于参与者的视野将重新放回到叙事和感受故事世界本身上。在ききやま的作品《梦日记》(ゆめにっき)中,参与者扮演一个沉默的小女孩,在氛围黑暗的梦世界环游。这个游戏没有特定的故事或目的,只是一个步行游戏。是否只有文字才有讲述故事的能力呢?在交互叙事中,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由于作品是可以通过交互来理解的,所以相比于传统的文学故事中提供的叙事,交互叙事所提供的是故事世界。正如玛丽·劳拉·瑞安在《文本、世界、故事:作为认知和本体概念的故事世界》所说的那样:“故事通过文本传递,但是它们在能指从记忆中消失很长时间之后仍然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这意味着故事虽然是一种语言建构,但更重要的是一个心理建构。我们能概括故事、改编故事、翻译果实,我们也能通过不同的媒介讲故事,这些事实将故事从语言里解放出来,它们可以独立于故事得以传递的某些特定符号之外存在。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得出‘多个文本——一个世界——一个故事’这样的等式,而非‘一个文本——一个世界——一个故事’。”形成叙事的并非单一文本,而是不同的叙事话语的集合,这是交互叙事与传统叙事最大的不同。特别是混合了多种感官的交互作品,更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共同作用而非单一文本主宰。步行模拟器虽然弱化了交互的难度,但是并非缺少了这一个维度。交互仍然是话语表达的一部分。并且,交互难度的增加意味着,用更简单的交互可以获得更多的叙事内容,这样有助于参与者能更加主动地探索交互环境,并获得环境中的叙事信息。环境叙事(Environment Narrative)是交互叙事中十分重要的方法,环境叙事会将游戏中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物理逻辑作为细节考虑在设计环节中。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在由Mobius Digital开发的步行模拟探索游戏,《星际拓荒》(Outer Wilds)中,时间是以现实世界的22分钟为单位的,只要探索到达了22分钟,太阳就会变成超新星爆炸故事结束。所以22分钟这个设定就是一个《星际拓荒》世界中的规则,包括参与者在内的所有人和物都要遵守设定,这种叙事的一致性就是环境叙事的体验。在混合型的交互作品,或者说是游戏中,总是包含着复数的叙事系统,并且这些系统之间是互相碰撞的。碰撞的结果则按照逻辑的形式展现出来。这种不同系统规则之间的一致性,通过交互这一个前提,将参与者所感知到的细碎的叙事连缀在一起,形成了十分独特的阅读和感受体验。这就像是一个人拿到了很多拼图的碎片,而可以通过一套符合游戏世界观的原则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成整个地图。的确,步行模拟器提供的叙事是碎片化的叙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碎片是无法被拼合起来的。借助不同叙事系统之间的内在逻辑一致性,星星点点的碎片逐渐变成了完整的图片。这或许就是玛丽·劳拉·瑞安所说的故事是一个心理建构的过程。同时,如果我们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理解心里构建的过程,则可以用沃尔夫冈·伊瑟尔的观点来进行阐释,“伊瑟尔把‘空白’作为审美接受的重要现象,认为‘空白’处于交流的核心地位,文学作品也就是一个充满未知和空白的、需要读者在阅读中加入弥补的未定结构,所以空白文本能够唤起‘读者的回应’和阅读期待,应当说,‘空白’的文本召唤是刺激读者对作品的空白进行想象,激发起参与互动的热情,并在阅读中使之不断更新、不断填充、由此产生审美对象;即接受者与文本之间的动态交流过程。”
三、从旁观者到参与者
交互意味着人有机会可以和作品本身进行交流。但是,和作品交流的前提是,这种交流要以作品本身的逻辑和规则进行。人的主体性被物,亦或者说是作品的主体性取代,从而产生沉浸的感觉。但是,这种主体融合的过程并不总是非常顺利的。实际上人会始终会保持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并与故事世界的经验进行碰撞。罗伯特·费肖尔(Robert Visher )提出了“移情”(Einfühlung)这一概念。“在他看来,感觉就是主体对外部刺激所做出的反应。依据主体在感觉活动中的参与程度,他把感觉划分成了三个等级。第一级叫做即时性感觉(Zuempfindung),指的是主体对刺激所作出的即时性反应。以视觉活动为例,在这一级感觉里,客体只在视网膜上留下简单的印记,眼睛只关注到对象的光线和颜色,还没有观察到对象的形式,主要是视神经发挥作用;等到眼睛进一步‘扫描’对象的形式时,主体开始观察客体的形状、方向、位置,就需要用到运动神经,眼睛和身体的肌肉会被调动起来,追随对象的形式轮廓,由此产生了后发性感觉(Nachempfindung);再进一步,身体对对象的形式产生了更加复杂和内在的反应,比如在天花板较低的房间里,身体就会产生一种压迫感;当颜色和光线过于明亮时,身体会产生不快的感觉,如此等等,这些都被称为内在性感觉(Einempfindung)”罗伯特·费肖尔的移情理论将感觉的形成分成了不同的阶段,而在交互作品中,感觉的形成要比费肖尔的内在性感觉更进一步,因为不仅仅是感受到,而是要在保持某种感觉的空间内进行一定时间的探索。可以说,时间是交互作品移情效果得以呈现的非常重要的尺度。在逐渐适应交互作品环境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忘记现实世界的经验,而将触觉移情到故事世界中。而交互作品则提供了很多让人移情可交互内容。在步行模拟器中也是如此。但是步行模拟器并不会抹去参与者或者说参与者本来的生活经验,而是承认故事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不可调和程度。步行几乎是没有身份含义的,而这个没有身份含义的行为极大尊重和人的现实感受。在步行模拟器中的行走几乎是不需要适应了,这和人们日常的闲逛方式如出一辙。另外,步行模拟器慢节奏的时间构成也与日常生活有非常相似的地方,这种节奏的一致性也降低了理解交互逻辑的门槛。但是,在步行模拟器中,参与者依然会扮演某个角色,虽然这个角色大概率是抽象的,但是参与者依然从这个抽象角色中继承了一些信息。这和强剧情的角色扮演游戏的区别在于,参与者不需要强烈地认为他们自己是谁,有着怎样的过去,会遇到什么样的人,按照剧本排列自己在虚拟世界中的人生。步行模拟器并没有这种附加的过于详细的设定,也没有强迫参与者去违背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扮演某个和自己的身份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人,比如说,一个刺客或者一个武士。步行模拟器对角色的规定是带有抽象性的,相对来讲比较模糊。同时,它并不限制参与者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在传统的角色扮演游戏中,参与者需要按照固定的方式交互,按照确定的交互逻辑和交互流程完成任务,然后一步步推进整个故事流程。这种交互方式能够给人带来比较清晰准确的叙事流程,但是缺点在于,在游玩结束之后,参与者很容易产生一种被利用的感觉。自己并不是角色,自己只是帮助角色干完了自己需要做的事情而已。但在走路模拟器中,并没有强求这种理解和扮演,二是直接提供了一个交互环境和抽象角色,让参与者自己去探索。这种情况有点像是旅行或者观看展览,人们可以随时进入故事世界,也可以随时从故事世界中抽离,这种进入与抽离并不会影响参与者对游戏本身的理解。在需要参与者强行带入自身的游戏中,参与者更像是参与故事的旁观者,依然按照作者和作者规定好的流程来理解这个作品,但是在步行模拟器中,这种作者主导的感觉被打破了,参与者被允许以自己的方式来进行交互行为,多样性的交互逻辑会制造一种自然的感受,而在这种自然状态下的参与者,能够更好的理解自身,并直面自己在虚拟世界中的位置。
第二节 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的元叙事
元(Meta),源于希腊语前置词与前缀“μετά”,意思是之外,之后,超出本体限制的。元叙事(Meta Narrative)的意思则是叙事之后,或者说,关于叙事的叙事,也就是对叙事本身提出自反性观点的叙事。步行模拟类游戏中时常包含元叙事的实验。这首先是因为步行模拟类游戏的形式本身就具有隐喻性质。步行模拟类游戏致力于塑造抽象环境。步行模拟类游戏经常塑造这样的场景并进行叙事延展:身份模糊的人在未知的世界中探索,并且无法寻找到确切的答案,游荡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交互体验实际上会让人联想到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状态。步行模拟类游戏充满了对人类生存本身的困惑,以及对于人生的虚无性和人的自由意志的反思。本小节会从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的身份隐喻出发,分析步行模拟类游戏中的元叙事,并对元叙事的意义进行思考。
一、角色扮演与洞穴隐喻
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在《赛博格宣言:20实际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以及女权主义》(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一文中说到:“赛博格是一种控制论的有机体,是机器和有机体的混合物,是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虚构的生物。”对唐娜·哈拉威而言,赛博格身份的出现是对人类的解放。人们不需要再拘泥于二元身份,而可以自定义自己的身份并且获得具有流动性的身份。随着数字媒介的发展,人们在虚拟世界中拥有自己的数字身份成为可能,拥有具备多重身份的赛博格身份,不再只是科幻小说中的想象。在交互媒介中,参与者甚至可以直接扮演虚拟世界中的角色,成为交互叙事的一部分。但问题是,角色扮演是否只是一种幻觉?一种逃避现实的工具?究竟如何看待人类在虚拟世界中的身份?当人逐渐忘却了现实,沉浸于虚拟的世界,人们应该如何看待自身?正如《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一书中提到的那样:“玩家越是沉浸于游戏中,与角色之间的融合程度就越强。就此而言,游戏本身对玩家的人格发展与转变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主体性是人格、角色与自我意识的统一。人格即人所具有的特质的总和,是主体性赖以形成和发挥的客观依据;角色是人所占有的社会位置相适应的行为模式,是主体性产生分化的重要原因;自我意识体现人对于自身的反思,是主体性发展的内在动力。”但是,不管参与者如何沉浸在游戏之中,依然不可避免地要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隐喻,也就是洞穴隐喻。洞穴隐喻的主要内容是,在一个山洞里囚禁着终身被囚禁的囚犯,他们位置被固定住,所以只能朝前看到洞中的墙壁。因此,他们永远看不到背后是洞的出口,也不知道出口的存在。这和虚拟世界中的情形也有相似之处。参与者被赋予了虚拟身份,只能看到虚构世界中呈现出的叙事,只有承认叙事的合理性,才能获得沉浸体验。但是参与者是有意识的,现实生活中的身份能够帮助人辨认什么是真实和虚假。不管如何沉浸,来自洞穴之外的光,现实世界始终存在。但其中依然存在这个一个悖论,虽然参与者被现实世界的身份所制约,但是,对于游戏中的虚拟角色来说,虚拟世界就是真实世界。虚拟角色就相当于洞穴隐喻中的原始人,而人类,则是在洞穴和洞背后的光之间游荡的存在。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探讨虚拟角色是否拥有自由意志以及虚拟世界存在意义的游戏很多。在90年代,由于互联网技术刚刚兴起,家用电脑的逐渐普及,人们开始兴致勃勃地探索和想象赛博世界的未来。《万物博物馆》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使用现实世界素材作为游戏内容,用低质量的3D贴图塑造虚拟空间,这个步行模拟游戏处处透露着不和谐感。但是这个不和谐感却在始终提醒参与者,这里与现实世界不同,而是由琐碎的虚构事物构成的世界。而在《史丹利的寓言》这个步行模拟类游戏中,作者则是用旁白的形式提醒参与者这里并非现实世界,而参与者必须对这个虚拟世界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
二、作为符号的身体以及对存在的探讨
在交互作品中,人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通过主体性的让渡,人能够和作品融为一体,并在交互场景中制造和体验叙事。在人进入作品这个环节中,人拥有了自己在作品中的身份,并用这个身份与作品交流。这样,人就不再单纯对应一个生理意义上的身体,而是在用复数的身体和作品交流。这个复数的身体包含一个在虚拟世界中生成的身体,这是作品给予现实世界中的人以虚拟躯壳,人们使用这个躯壳在虚拟世界中扮演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是对沉重的现实肉身的反叛。人们得以从自己出生就开始扮演的现实角色中短暂的逃离出来,不断获得新生,体验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永远没有机会经历的人生。这也是为什么始终有人沉迷虚拟世界抑或者是游戏的原因。现实的苦痛是难以消除的,身份如锁链一般捆绑着所有人。而暂时遗忘这些沉重,对很多人来说一种救赎。游戏是具有疗愈功能的,在虚拟世界时间和现实世界时间对冲的过程中,人们不断转换着自身,思考着自身,最终在交互中得以达到自身的平衡和放松。但是,作为逃避之所的虚拟世界,依然以现实世界肉体的消耗为代价的,人们并不会因为逃避了现实而不需要花费时间的代价,而现实的苦痛也并不会因为逃避而得到解决。“一些评论家视赛博空间的虚拟身体——《MOO)(多人地宫、面向对象)、电脑游戏、以及虚拟现实——为文化中受压抑欲望的自由表达。另一些人强调,我们每个人都仅有一副身体,它处于真实的世界中,所有与虚拟身体和虚拟角色的互动都改变不了只有物质身体才是唯一重要的身体这一事实;自我无法从肉身中分离。中间派认为自我是多元的,而数字身份将潜在的多元性变成现实、但所有这些身份最终都需要物质身体的支撑、连接或者说‘批准’。”如果游戏确实能够疗愈人的内心,能够帮助人重新审视自身。但是,如何审视自身,是否愿意重新回到现实世界并接受挑战,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传统的电子游戏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也因此游戏被贴上了娱乐消遣的标签。玩游戏被认为是一种负面的、逃逸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在步行模拟器中,因为交互已经被简化到了简单到枯燥的程度,所以人们无法再逃避自身在虚拟世界中的虚无位置,也就无法逃避这份虚无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步行模拟器直面了人生存的虚无,如果说普通的电子游戏将人抽象为了可理解的身份,那么步行模拟则将人抽象为了不包含具体信息的符号。步行模拟器通常是第一人称视角游戏。和现实世界一样,人们除非在镜子中才能看到完整的自身,其他时候只能看到自己部分躯干如手、手臂、腿等等。当然,一般情况下,人没有这样一面镜子来看到自己到底是谁。人操纵着角色,但是并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在步行模拟类游戏中能做的事情就是步行,而这是一种没有特权含义的行为,每个身体正常的人都能做到行走,所以,人们在步行模拟器中无法判断自己是否和某种身份依附在一起,也就成了无身份的人,抑或者说,一种存在符号。德勒兹的对于“无器官的身体”的阐发或许能与步行模拟器对身体,对人,以及对存在的态度对应起来。“为了抵制器官机器,无器官身体把平展的、滑动的、不透明的、拉紧的表面当作障碍。为了抵制联系的、连接的、被干扰的流动,它建立了无形的、未加区别的液体的反向流动。为了抵制使用由发生单位组成的词语,它只喘粗气和叫喊,那是纯粹的未发声的声音障碍。”(无器官的身体,吉尔·德勒兹,陈永国译,后身体,汪民安)。离开了具体设定的虚拟躯壳,不得不重新寻找和确认自己在虚拟世界中的身份。人们所扮演的虚拟人物不再是一种设定,一个默许的故事角色。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这个虚拟人物是一个虚拟世界中的存在,其他一概不知。人们仿佛回到了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中,人们发现那些能够彰显自己虚拟身份的设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洞穴之外的空旷世界,人们一无所有。这种虚无的状态实际上与人类本身的生存处境也能够联系在一起,抛开人类文明所营造的人类掌控世界的错觉,人类不过是在宇宙中的一颗渺小的蓝色星球上的存在而已。且人对于宇宙的了解实际上还处于皮毛状态。人忘记了自己是有限的、无知的、被自己亲手建造的文明秩序保护着,承认着。但是人始终无法掌握这个世界的真理,也无法看清这个世界的真实模样究竟是什么样的。在步行模拟器中也是如此,剥离了具体叙事成分的人只能确定自己是存在的,但却无法在这个世界中自己究竟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人在步行模拟器所制造的虚拟世界中,再次面对了存在的虚无。但是,步行模拟器并未停留在虚无之中。而是将虚无当作讨论存在含义的出发点。如果我们是存在的,那么我们是存在于什么样的世界中的?关于这个问题,不同的步行模拟器作品给出了各自的答案,但是几乎所有的步行模拟器都包含一层对已知世界的质疑以及对存在问题的思考。
结 语
步行模拟类游戏作为一种以游戏为媒介传达艺术思想的游戏类型,对于研究数字艺术和交互叙事有颇具价值。与一般意义上重视娱乐性的游戏相比,步行模拟类游戏不仅对于个性化,艺术化的表达颇为重视,也创造了独属于该类别的交互叙事方式。而对步行模拟类游戏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对游戏以及交互媒介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回溯步行模拟类游戏的历史,可以看到步行模拟类游戏与交互媒介的艺术化创作的思潮息息相关,且在不同的阶段都出现了相当出色的颇具艺术价值的步行模拟类游戏。而在交互叙事的脉络中,步行模拟类游戏不仅对传统交互叙事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且对利用交互叙事表达严肃哲学和艺术话题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空间叙事层面,步行模拟类游戏将参与者视角纳入作品之中,让参与者与作者进行对话,创造了复调式的叙事环境。同时,步行模拟类游戏通过对叙事空间的视觉化安排,创造了戏剧化叙事空间。另外,步行模拟类游戏通过环境叙事和涌现式叙事拓展了交互叙事的方式,塑造了更为生动的叙事环境。步行模拟类游戏向参与者提供的不是叙事,而是叙事环境和叙事空间。参与者以交互为媒介,对环境进行自主的探索并获得对叙事的理解。
而在时间叙事层面,步行模拟类游戏削弱了强游戏机制给叙事节奏带来的干扰,让参与者能够以自己的节奏进入到游戏中并探索。参与者有充分的时间理解作品而不被规定好的线性流程所绑架。另外,步行模拟类游戏一般不会给出明确的叙事结尾,而是将核心放在叙事过程上。参与者可以在任意节点选择叙事结局,参与者决定了叙事的形态。同时,步行模拟类游戏选择了非线性叙事作为主要的叙事结构,也使得参与者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叙事,并感受丰富的叙事层次。
在主体性叙事层面,步行模拟类游戏关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身份的联系,并对人类在虚拟世界中的身份问题进行了思考。同时,步行模拟类游戏对于虚拟世界是否具有独立主体性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一方面,步行模拟类游戏的作者将虚拟世界作为现实世界的隐喻,并对世界的真实性问题进行思考和表达。另外一方面,步行模拟类游戏也以批判性的视角分析虚拟世界的存在的合理性,通过“第四面墙”的隐喻,来反思虚拟世界的虚无性。
总体来说,步行模拟类游戏用非娱乐性的方式对交互叙事进行了拓展,并让游戏这一媒介更加具备表达深度和艺术价值。同时,步行模拟类游戏的出现也暗示了交互叙事和数字艺术的新方向,也就是通过简化交互,重视氛围的手段将游戏作为一个想法的试验场,并进行本体论和存在论问题的讨论。
参考文献
(一)专著:
[1]黄鸣奋.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
[2]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汪民安.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
[4]伊卡洛·卡尔维诺. 魏怡译.文学机器[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5]巴赫金. 白春仁等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88.
[6] 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7]让·保罗·萨特著,吴子枫译:《什么是主体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二)期刊论文:
[1]高源,刘坚.数字影像艺术的交互审美分析[J].长春:文艺争鸣,2021
[2]张耕云.数字艺术三题[J].北京:美术研究,2005
[3]钟雅琴.沉浸与距离:数字艺术中的审美错觉[J].广州:学术研究,2019
[4]徐丽芳,曾李.数字叙事与互动数字叙事[J].武汉:出版科学,2016
[5]玛丽-劳拉·瑞安,杨晓霖.文本、世界、故事:作为认知和本体概念的故事世界[J].广州:叙事理论与批评的纵深之路,2015
[6]玛丽-劳瑞·瑞恩,徐亚萍.作为叙事的虚拟现实[J].北京: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6
[7]苏宏斌,俞圣杰.从象征到移情——移情论美学的历史发生[J].杭州:浙江社会科学,2021
(三)学位论文
[1]关萍萍. 互动媒介论——电子游戏多重互动与叙事模式[D].浙江大学,2010
[2]李森. 托多罗夫叙事理论研究[D].新疆大学,2006
(四)网络资源
[1]Caroline Bassett.The computational therapeutic: exploring Weizenbaum’s ELIZA as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 link.springer.com.2019.
[2]Dennis G. Jerz Colossal Cave Adventure -- Will Crowther (c1975); Will Crowther and Don Woods (1976),jerz.setonhill.edu.2000.
[3]E3 08: Nintendo Press Conference. gamesradar.com, 2008.
[4]Edmond Tran. The Beginner's Guide Review.gamespot.com, 2015.
[5]Ian Willoughby. Groundbreaking Czechoslovak interactive film system revived 40 years later.english.radio.cz, 2007.
[6]Jean-Robert Sédano et Solveig de Ory. Chambre à Musique.ludicart.com, Brett Elston, 2022.
[7]Matthew Tyler-Jones, Ludology vs. Narratology. memetechnology.org, 2013.
[8] Nicole Clark.A brief history of the “walking simulator,” gaming's most detested genre.Salon.com,2017.
[9]Offical website. Pathologic 2.www.pathologic-game.com,2022.
[10]Pmwiki.Video Game / The Museum Of Anything Goes.www.tvtropes.org, 2022.
[11]Phil Savage.Outer Wilds review.pcgamer.com, 2019.
[12]Ryan McSwain. LSD: Dream Emulator.www.hardcoregaming101.net, 2017
[13]Simon Carless. Features: GDCTV: The Near Future of Media Distribution. gamedeveloper.com,2015.
[14]Tina Amini. Jonathan Blow Thinks Adventure Games Are Bad. So He's Making One. kotaku.com, 2013.
[15]Tom Marks. Return of the Obra Dinn Review.ign.com,2018.
[16] William Usher Cloud-game-review, www.gametunnel.com, 2006.
[17]林氏兄弟:電車男追女記,香港:香港網絡大典,evchk.fandom.com.2022.
(五)外文文献
[1]Aarseth, Espen J. Cybertext: Perspectives on ergodic literature[M].JHU Press, 1997.
[2]Bartle R A. Designing virtual worlds[M]. New Riders, 2004.
[3]Colson, Richard. The fundamentals of digital art[M].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07.
[4]Christian Rollinger Classical Antiquity in Video Games: Playing with the Ancient World[M]. Bloomsbury,2020.
[5]Deen P D. Interactivity, Inhabitation and Pragmatist Aesthetics[J]. Game Studies, 2011.
[6]Hunicke, Robin, Marc LeBlanc, and Robert Zubek. MDA: A formal approach to game design and game research[J]. Proceedings of the AAAI Workshop on Challenges in Game AI. Vol. 4. No. 1. 2004.
[7]Haraway D.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M]. Springer, Dordrecht, 2006.
[8]Juul, Jesper. A clash between game and narrative: A thesis on computer games and interactive fiction.[D]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1999.
[9]Jenkins H. Game design as narrative architecture[J]. Computer, 2004.
[10]J. M. Graetz. The origin of Spacewar[J]. Creative Computing magazine,1981.
[11]Kwastek .Katja. Aesthetics of interaction in digital art[M]. Mit Press, 2013.
[12]Manuela Ammer, Justin Hoffmann, Manfred Montwé. Nam June Paik: Exposition of Music, Electronic Television[M].WALTHER KÖNIG, KÖLN,2009.
[13]Motte, Warren F. (ed) Oulipo: A Primer of Potential Literature[M].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14]Paul Christiane. Digital art[M].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3.
[15]Ryan M L. Toward a definition of narrative[J].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 2007.
[16]Zimmermann F, Huberts C. From walking simulator to ambience action game[J]. Press Start,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