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黑色,公園裡有的烏鴉
當我在寫《在巴黎的那場誤會》的系列文章時下的註解是「故事性散文」,一直以來都有爭論散文虛實的問題,因此我通常在敘述時會盡量少量的使用人稱,這篇文章寫的是《沒有狄多的迦太基》中的一篇。
想像巴黎這座沒有狄多的城市中的情景,但這裡確實沒有狄多,不用花多大力氣想像。
不確定這個敘述是不是正確的,記得那天在巴黎十八區的一處不知名的公園中看到一群黑色的禽類,應該是烏鴉吧?對了,無法確定這是真或假是我偶爾會把幻想、夢境和事實混淆,過了幾年後就無法記得這是否是真的。
烏鴉通常與死亡和厄運相關聯。黑色羽毛和沉重的叫聲使烏鴉成為象徵死亡的動物,與黑貓一樣是會帶來霉運的。可是烏鴉同時也象徵著變革與重生。在生態中清理屍體,促使新的生命得以生長。那天我看到了烏鴉,不知道是好或壞?
那時也有寫日記的習慣,只是不可能再翻閱了,所有的日記本都在搬家時遺失,抑或根本沒把這一天記錄下來。畢竟那也不是多特別的一天。
當時要從一處穿越到蒙馬特公墓(Cimetière de Montmartre),經過一區北非人開的商店,還有某個看似公共部門的建築物前有很多人排隊要登記領取福利,地上有被人丟棄的食物,有的被踩爛了黏在地板,烏鴉們飛得很低,在廢棄物的上空盤旋⋯⋯會有這畫面的印象是我記得自己一面走路,避開地上的污穢,一面躲著牠們。
自言自語的說:「這裡連鴿子都沒有嗎?」
不只北非人,還有膚色更深的西非人(我只敢在不真實的敘述中說他們黑),其中有的人以不友善的眼神盯著我,大概是我看起來有點緊張,那裡還有一間中國人開的越南河粉店,或許在前面兩個街區,一個斜坡上,裡面有穿著像是90年代末期青少年風格(色彩繽紛、字母T恤),捲著大麻的中年人,我相信他們從二十多年前的穿著到現在都是一樣的。
城裡很黑暗,至少在那個區域是如此。
我短暫掉入第三空間中,烏鴉成群的地方沒有其他人,所以才能自言自語走了一段路,想起《自殺專賣店》的畫面,腦中也播放著那首。
我們對整個城市都很有用
(他們對整個城市都很有用)
不管你的檔案是什麼
(我們的檔案)
忘記一切,平靜地死去
(我們忘記一切,平靜地死去)
再見生活,就這樣吧!
鴿子和烏鴉,我都不喜歡。我害怕任何會飛的東西,有羽毛的更讓我討厭。

一個流浪漢撿起地板上剛被丟棄的菸——很確定這是真的了——他抽起菸來,應該只能再抽一口就沒了。那天是為了思考某事才去蒙馬特公墓,我喜歡坐在墓園裡面發呆,一開始是假裝看得懂墓誌銘,然後會試著唸一下拉丁文,以分散注意力。總之,不管在墓園裡發生什麼事都會覺得特別平靜。
只要不遇到哭泣的人就好了,我心裡總是這樣想。事實上也從沒遇到。
蒙馬特是很多藝術家聚集的地方,公墓裡也大多是生前曾在此生活過的藝術家們,比起拉雪茲神父公墓中的故人認識的很少,也沒研究是誰長眠於此,我真的不是刻意在此寫了很多有色人種。
此時,我就是一個沒感受力的人,墓地就是墓地,我分不出這幾個公墓之間的氛圍差異,只是帶著一種要沉澱的心情上行於此。
每當計畫著要去一個地方、要做一件事,即使去墓地沈思這種事,都會特別有任務感,彷彿我「去了」就會完成一點什麼,然後又是一個經過洗禮後的我!因此,那天是亢奮的一路穿越十八區商店區,那裡的情景總是看起來灰暗,但一切對我來說都像過場的背景——用阿拉伯語爭吵或只是在講話的路人,推推擠擠的並排行走、蹲在店門口抽菸的非裔店主、色彩繽紛卻看上絕望的亞洲人美甲店——如果在夏天,都會覺得經過那就會沾染到一點「外來人氣味」——而我不應該這樣想,我有什麼資格說他們是外來人?
我走得很快,好像那些混亂的情景都與我無關,只想著要到公墓中,然後一切問題都會解開,不知道哪來的信心?也可能是我浪漫的一部分,但既然十八區沒有狄多,我也無法期待她的智慧能使這座城市繁榮昌盛,沒有女王就會失去一種生命力。
即將走到聖心堂的階梯前還遇到專門騙觀光客的吉普賽人,像是沒看到他們一樣的橫衝了過去,聽著他們對著我的背影一直說:「拜託!」。我能給他們什麼好處?被騙幾歐元嗎?
走最後一段上坡路時就開始落起大雨滴,不久後雨水像是一盆盆的倒下來,前面灰暗的印象是因為快下雨了,烏鴉也是因此才出現吧?全身被淋濕了,連右眼的隱形眼鏡都被沖地流出來,像是經歷了一場「洗禮」。
如果迦太基沒有狄多,那些被傳頌的故事就不會被寫下來,但那最終也只是史詩中的虛構,穿鑿附會的故事。
我摸著黑下坡,走回了住處。
字數:1831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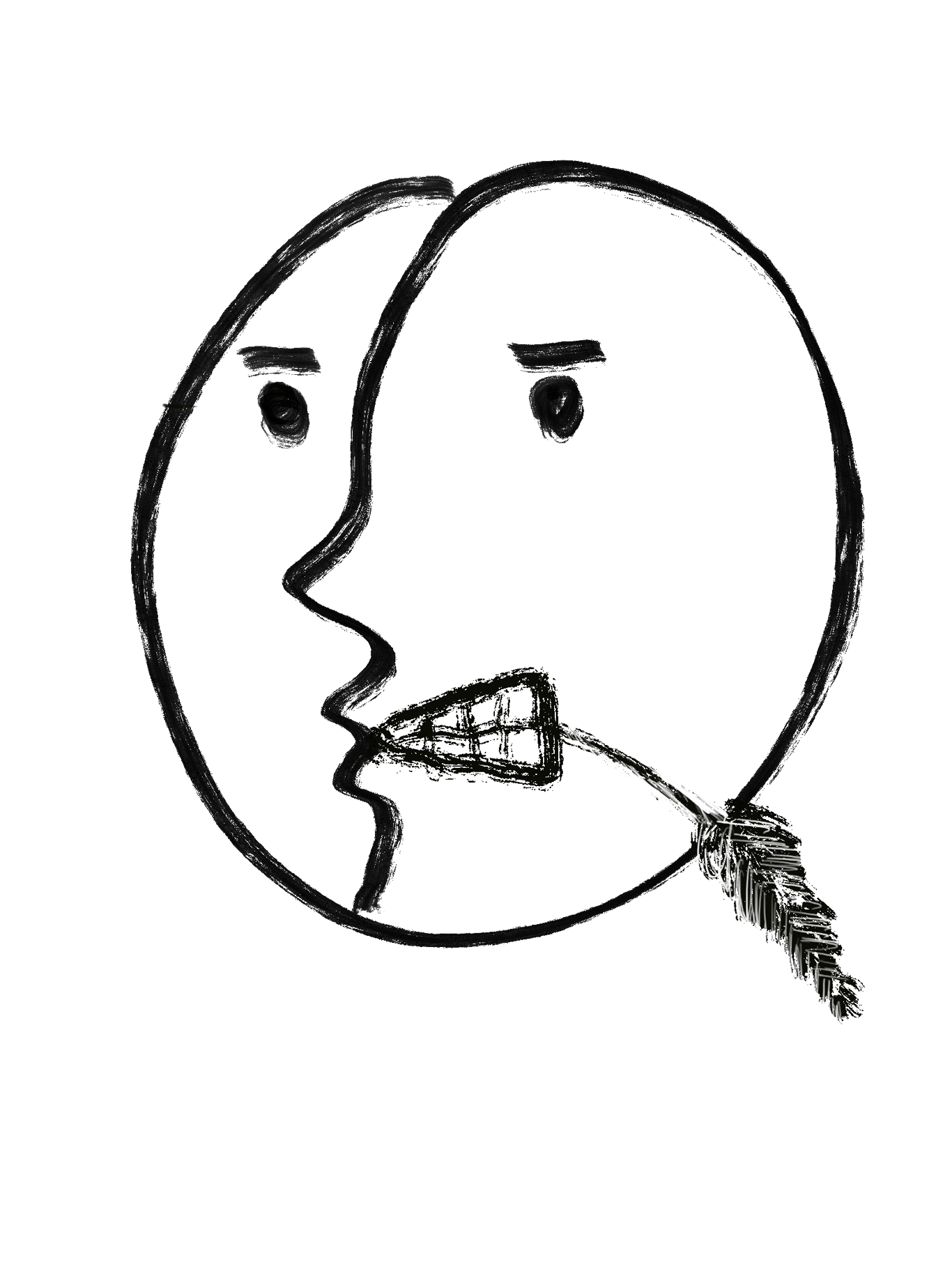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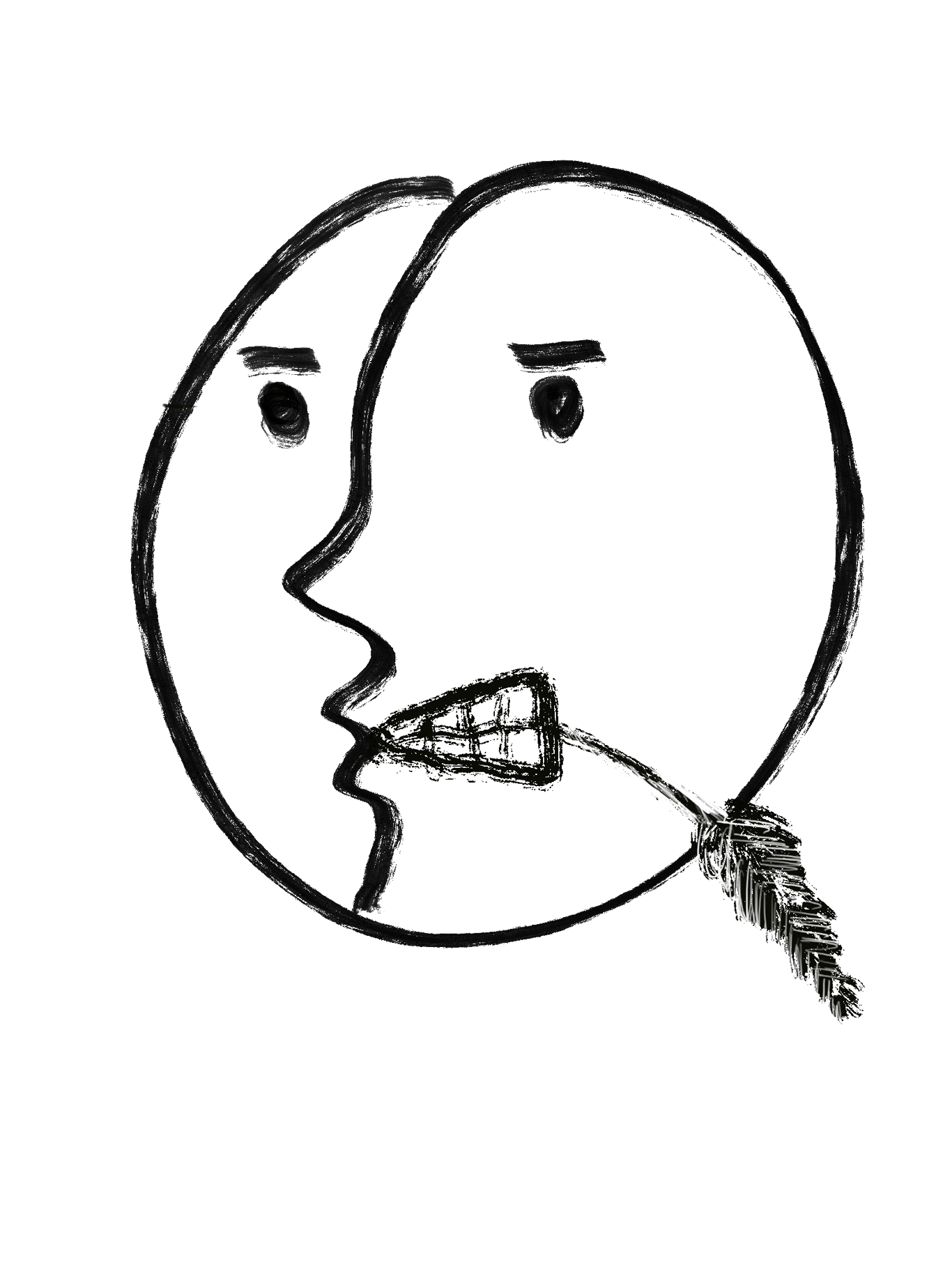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