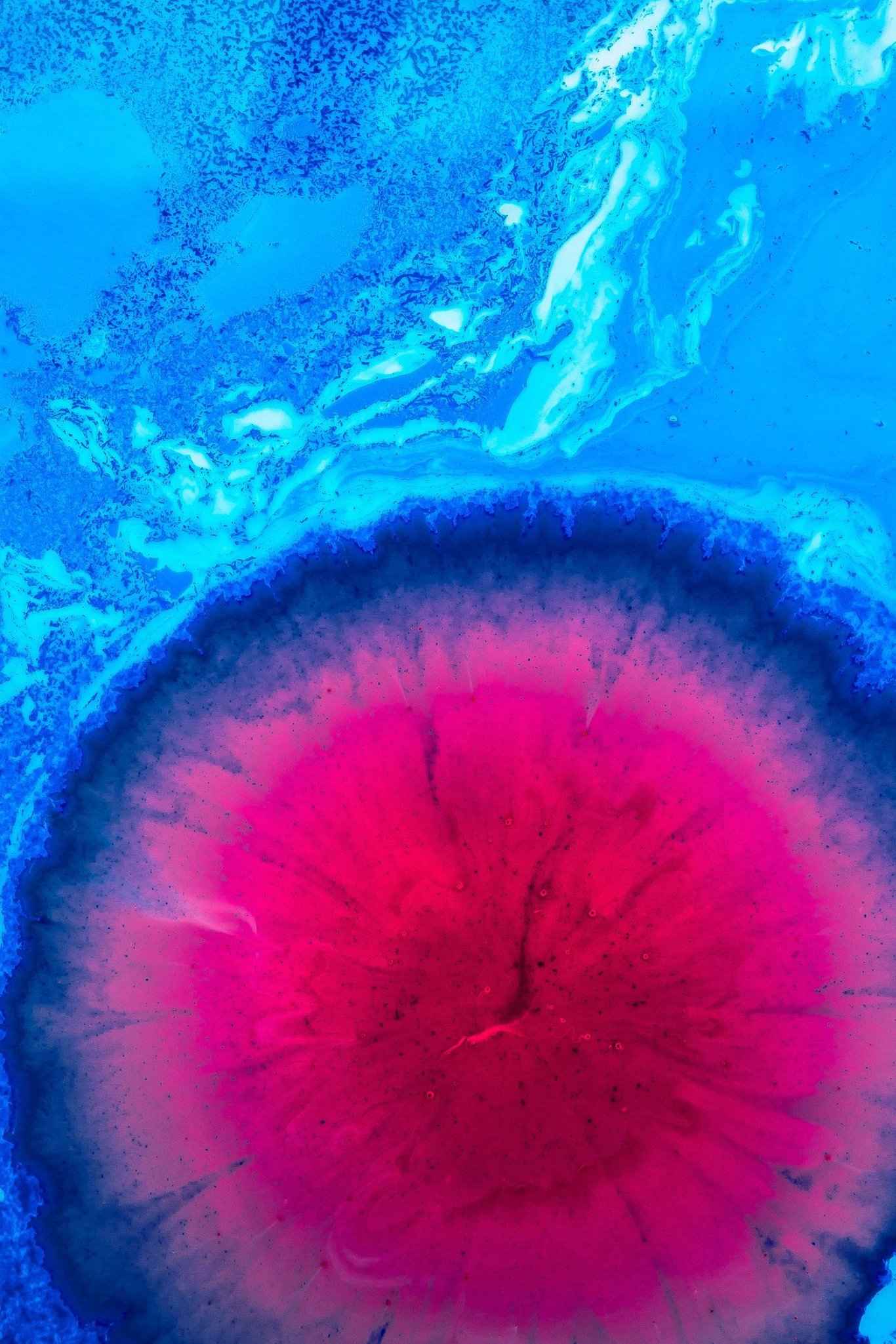背叛

我们做完爱,躺在床上休息。关北的房里堆了几堆宜家的干花散味,一股一股的劣质香精味涌来,渗进铺在床上津湿的毛巾里,毛巾黏着皮肤。
夜里凌晨三点半,关北把窗帘拉开,我躺在床上看着夜幕缀着城市灯火朝我似凉风刮过,高潮泄去,竟然打了个冷颤。我们做了多久?夜已经这么深,灯光仿若深海发光的水母,幽幽透着寂寞的颜色,我扯了扯床单掖了一下肚脐,传来关北打开游戏的声音,在屋里清脆地回荡。
初夏傍晚时分来他家,小区绿植还没被修剪整齐,那些冒出头的枝丫叶片,试探性地划过我的衣服。我来找他做爱,这些绿植们像极那些多嘴的街坊四邻,团簇在一起窃窃私语地谈论我的到来;又似乎在给我传递桃色的信号,暗示关北一个人在他家等我,迫不及待又窸窸窣窣地撩拨着我。
他男友每月出差一周,做药品外贸,去加拿大,他家里备很多prep,对我说吃这药可以无套,我们便无套。有些事你无法分辩清楚,概率的问题对于真实而言只有100%和0%,人都只活在剩下的区间里掷骰子,做爱是,工作是,认识一个人也是,失去同样。不用分辩,也无需分辨,于是只能把精力放到享受上,之前我犯急性肠胃炎,去医院打完点滴后转身拐进火锅店,周航拦都拦不住,一直冲我板着脸,直到我疼得冒冷汗脸色发白放下筷子,他冷言冷语地说,活该。
吃得很爽,火锅也够辣。但周航的态度令我又生气又无奈,他冷漠的模样和嘲弄的“活该”胜过了关怀的暖意,折损了我仅剩的一丝满足和快乐。关北听我讲完这件事,说恋人在一起久了不都是这样吗?最开始的时候觉得对方光芒万丈,在一起久了就发现那些光芒都是一些粗燥的毛发,顺得好你才觉得温暖,顺不好就呛鼻子,但总不是刺就好。
说完,他脱衣服示意我上床。我把浴巾丢到沙发上,然后转身趴上床抓住他疲软的下体送进嘴里。很难想象,现在网络上的人们会如此热衷形容生殖器的模样,它似乎已经成为更准确的社交定位——如果描绘一个人,形容他脸的样子反倒不如形容他下体的样子更容易表达事件和情绪。想到这里,我示意关北用手轻捏我的乳头。我听到他嘴里的喘气声逐渐变粗,并开始小声地爆着粗口。
像这样的偷情,相比他和他男友,我和我男友之间的性事有什么不同呢?回忆和关北做爱的场景,在第一次摸透对方的癖好后,我们对对方而言,越来越成为一个合格的性伴。当做一份重复性比较强的工作时,人会试图以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交差,床上这事也一样,合格的性伴意味着普通、正常、一般。周航和我做爱时有没有也曾觉得太过普通?
我们已经有些时日没有做爱了。自从上次他说完活该,我们有两天没说话。两天里我重新看了一遍《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在哭泣的时候故意放得大声。不需要安慰,难过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手机上的各种软件刷一遍就冲淡情绪了。世界的大事令你疲于应对,强奸、暴力、沉冤得雪,国家之间的争锋相对,商业之间的刀光剑影,一只猫在囹圄中被如何拯救,一群宠物却又在牢笼中被吸噬,无处安放的垃圾……我愤怒、嘲弄、无奈、自怜,情绪像走马灯,但我想到周航还没道歉,于是兴致缺缺地点了一份海胆水饺——是周航爱吃的。
一旦决定不去主动和解,我就开始变得不知所措,为什么哭,为什么愤怒,为什么吃他爱吃的东西,情绪和动作的目的开始相互掩盖、相互交织,厘清目的似乎便能洞悉宇宙的真相,而内心懦弱又意志缺乏的我,却只能任凭这些掺杂私欲、不忿、诡计的情绪,像染料一层又一层地洗刷心尖。我故意从周航面前经过,又故意在磕到床脚的时候发出长长的“嘶”,阳光如薄纱一样铺陈在客厅里,我看到内心戏被投射时的丑陋与怯弱。
关北抽插了十几分钟,我们从传教式换到后入式,他的力度渐渐慢了下来,硬度也渐渐软了下来。他说先歇会儿,拔出来后走去浴室,我抽了一张湿巾擦拭了一下后面转身躺到床上。记得年轻时候,对于性总有着过分的野心,也没有讲究过干净,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讲究起来,性的快乐似乎少了些许。我回想第一次和关北做爱,用一个不得体的比喻来形容,就像是烧开的水壶,他摸索着我的身体,从脖颈到尾椎,欲望的热气顶着壶盖,噗噜噗噜的声音是荷尔蒙的节拍,我们的舌头交缠在一起,唾液和着汗水是性欲分泌的润滑剂,腥味在鼻息间流淌。
然后是第二次,我们依然保持对彼此身体的渴望与热忱,水壶开始噗噜噗噜地作响,我说我去清洗一下吧,洗完出来时,水壶已经停止沸腾,不过水还烫,他涨起的下体闪着光泽。很久以后回忆,我们才发现自那时起,气氛已经不太服帖了。越试图得体,越试图准备充分,距离满分永远隔着距离。人的欲望总是很奇怪,哪怕满足99%,可只要有1%未达到,便心心念念。
胃是什么时候坏掉的,我也说不上来,刚开始的时候周航会照顾妥帖,烧热水,熬粥,叮嘱我吃药,习以为常后就不觉得是事了,就像感情相处久了,也不觉得是事了。只是多为自己考虑一下,就容易撕扯一下感情,一般分手,大多是没有心力去糊好那块幕布,既然扯掉了,就谢幕吧。
几次与周航的争吵结束后,我在凌晨时分沿河边走,夜色薄凉,路灯冷彻,河水在静谧中被夜风拨弄,像漫无目的的我漫无目的地起波纹。往哪儿走?行多远?都没有经验可谈。爱与不爱都是浅薄的问题,年轻人才关心,大多是不爱却依旧得往下走。所以谈谅解、谈相守都很荒谬,无非是秉着分寸感在每一次窝火中试图平息。路灯什么时候灭的我都没留意,天光不留情面,我得给自己留。
短暂的和解也许持续三四周,也许持续个把月。和解期间我和周航聊天、对话,你来我往亲密无间。夜里如果在外过夜,他提前和我说好,并叮嘱我记得吃饭,如果胃疼一定要烧热水喝,“真不让人省心,你说,没有我你怎么办”。有些话,出自本能的会接,“你爱我吗?”“爱”,有些话,你思索很久都不知道如何回答,否决会削弱他的存在价值,肯定却也换不到长久的安宁。好在对他来说,他这句话从来不是为得到我的回答,甚至讲这些话,更多是讲给自己听的,这点我尤为确信。
他第二日回来后,显得更加容光焕发,也容许我无理取闹几分钟,这是好事。当你逐渐的失去目的,并希望在情侣关系间得到一种平和,一定要拿捏好自由的分寸感。这点关北十分赞同。夜里十一点半,他男朋友从加拿大发来视频通话,关北故意给我一点镜头,对他男朋友说,“他和他男友吵架,来家里找我聊会儿天……我开导开导他,没事的……你在那边要休息好,等你回来,想你”。
视频挂掉后,他一把将我拽到身旁,将短裤扯到底问,想不想被我开导?想。喘息声很性感,令我情不自禁,“我想要”,我说,“我去快点洗一下,等我”。他涨挺的下体还有残留的唾液。
那段时间的和平,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下班回家刷美剧,他在书桌前看书,时不时回复信息,后来干脆合上书。我说,你拖一下地好不好?他锁屏后说好。我说吃点宵夜可以吗?他问我先吃点什么。我说上班太累了,领导最近更年期脾气很差,四十多岁将近五十岁的女人,手下一帮人哄着她。他说,中上层得到的不仅仅是社会的特权和物质的积累,精神上的满足也不会落下,他们压力大是真的,但收获总能抵消,你是一个职员,你想任性可以,成本太大。我说这不是还有你么。他说是的。
话容易说死,即便是好话,它甚至不如一句生分的“你是我,我是我”更得体。不置可否式的回答将这场戏砸的很彻底,像掴了你一巴掌,让你没法假装无事。我都忘记是怎么样去挑衅,争吵,质疑再到歇斯底里。“又不是分不开”,周航说完这句话,穿起衣服摔门而出。
我曾问过关北,“你是怎么和你对象在一起这么久的”?他思索了很久,说不知道,“你会遭遇困境,会被堵在生活的墙角,可再苦再难,都是一个人的事。但两个人的困境,两个人的无路可走,一定是哪里出了错才会遇到的,这和爱不爱都没关系,这怎么说……”他试图给我解释,“那种关系或者说那种感受,和你是不是单身,有没有恋人也毫无关系,有点近似生物躲避危险本能的选择”。
他的这一番话说的不明所以,就像那次吵架结束后,周航第二天回来抱着我失魂落魄地哭泣般令我不明所以。他的泪水那么汹涌,很快打湿了我的衣服,我不知所措间只好抱着他,安慰着他说,别哭了别哭了,昨晚对不起。他只是抽泣着,像失了玩具的孩子。
盛夏来的时候,我和关北断了联系,倒不是因为对彼此没有了性的冲动——我偶尔还是会怀念和他在床上共度的时光。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同时抵达高潮,有一段时间没有经历过这种倾泻透的快感了,瘫软在床上,我没有顾忌身上的汗水,钻到他的臂弯里,他问我,爽吗?我嗯了一声,问他,“你喜欢我吗”?他没有回答,起身去浴室开始冲澡。
那次之后,我似乎知道周航那晚发生了什么。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