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妖風》我們對民主失去信心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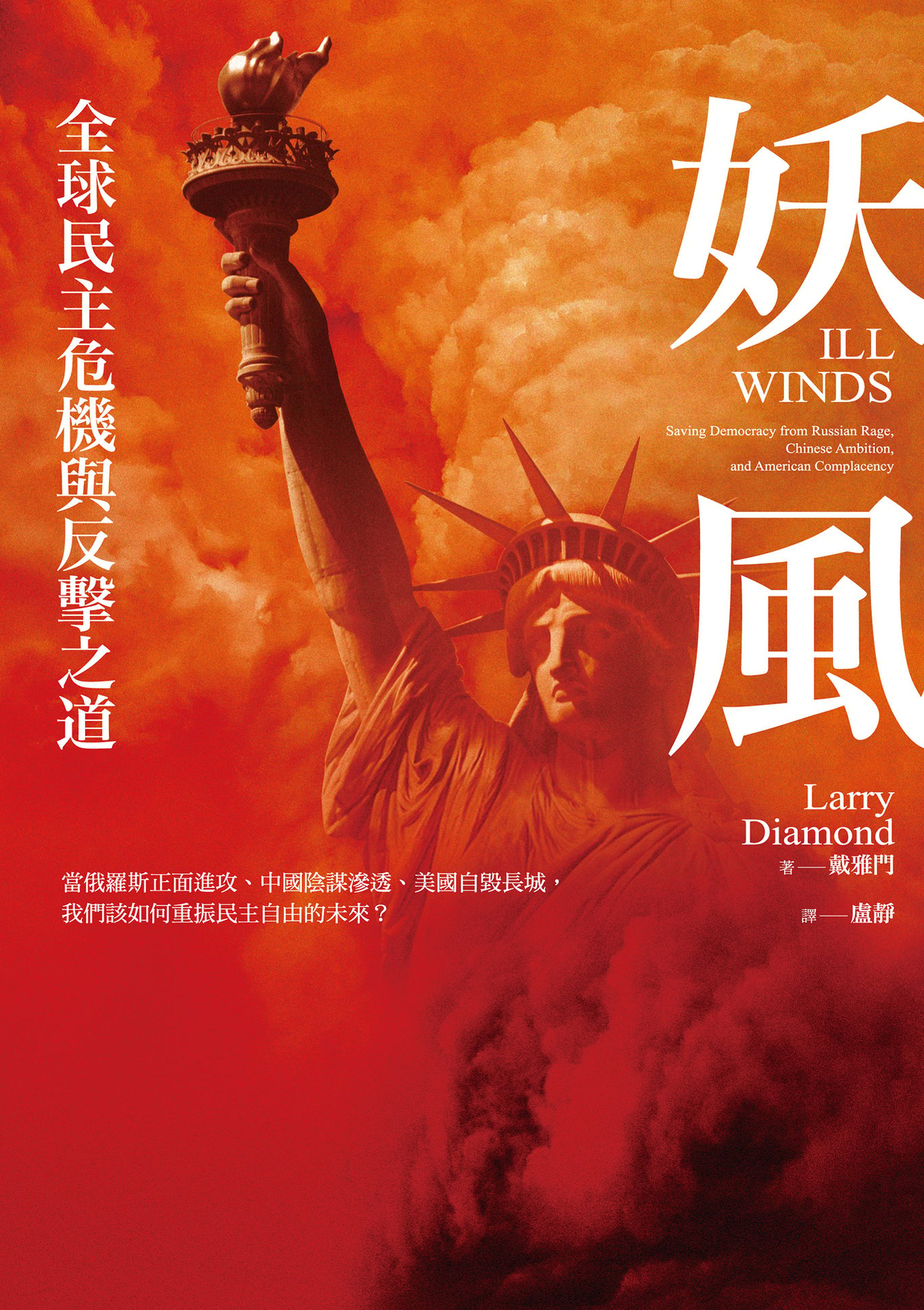
我們對民主失去信心嗎?
所謂普世價值,是指任何地方的人都有理由認定它有價值。
── 阿馬蒂亞.沈恩(Amartya Sen)
現在我們看到的不只是獨裁體制的攻城掠地,甚至是獨裁者也竟然自詡為當代的道德和文化精神標竿。無論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中東,甚至部分的西方民主國家,都有愈來愈多的菁英主張「中國模式」的威權國家資本主義才是未來的潮流。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只花兩個世代的時間,就帶領國家從貧困走向富強;當今的獨裁者也跟隨著他的腳步,主張經濟快速發展需要秩序勝於自由,而獨裁統治比自由民主更適合西方以外的文化。
但這是獨裁者治下的人民想要的嗎?老牌民主國家的公民又如何看待暴君的崛起?人民正在對民主失去信心嗎?
答案很簡單:並沒有。沒有任何大規模調查顯示民意對獨裁的評價有所提升。
然而,這不代表我們可以就此安心。在美國和其他相若的民主國家,對民主的質疑仍與日俱增,支持威權主義的資本顯然也愈來愈多 ── 當國家遭受挑戰時,反自由民粹主義者將能以犧牲自由為代價,號召更多選民。
這種山雨欲來的危機在巴西、墨西哥、菲律賓和突尼西亞等國家更令人有感,因為當地的民主制度並未有效消弭犯罪和貪腐。幸好,老牌民主國家的公民仍普遍認為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而獨裁者不論用什麼文化主張為自己辯護,比如「亞洲價值」、「伊斯蘭文化」或其他非西方價值,或託詞窮人忙著賺錢而無暇關注自由,都與堆積如山的證據不相符。實際上,在非洲這塊世上最貧窮的大陸,人民不只對民主展現驚人的高度支持,也重視許多自由價值和監督統治者的制度。即便在仍是民主荒漠的阿拉伯世界,數據也顯示人們普遍憧憬民主與可問責的政府。
如今對民主最大的威脅,不是人民的價值觀或意見,而是(包括許多民選)統治者的貪腐和權力慾,以及國會和法院等監督機構的積弱不振。
如果缺乏對民意的理解,就很難寫一本關於民治政府的書。然而要完整匯集全世界對民主的看法也不容易,因為不同的調查不僅進行時間有別,使用的指標也各異。不過,數據仍然是很有力的證據。而數據顯示,只要政治領袖可以實現經濟進步,並尊重民主原則和法治來治理國家,世上任何一個地方的人民都可以抗拒獨裁的誘惑,擁抱民主。
美國人民對民主態度的變化
《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在二○一六年刊登了一篇聳動的文章,由政治學者羅貝托.佛亞(Roberto Foa)和亞夏.芒克(Yascha Mounk)撰寫,挑戰了我輩專家一直以來的假設,那就是西方先進工業化民主國家擁有牢固的根基。在這些政治學者生活的世界裡,民主的正當性已經堅若磐石,沒有主要的政治力量膽敢以不民主手段獲取權力,也沒有政治領袖在試圖破壞民主制的規範、監督和平衡後,還能逃脫制裁,因此這些學者才會說民主已然鞏固(consolidated)。
在這樣良好的環境裡,民主當然是唯一的遊戲規則。但一個真正有韌性的民主國家,不只是菁英間要有這種共識,主要政黨、利益團體和大眾也都要有。只有無條件相信民主是最好、最公正的政府形式,才能讓民主樹大根深。而佛亞和芒克主張,如今開始衰弱的正是這種信念。
佛亞和芒克追蹤美國與歐洲社會對民主的態度已長達二十年,他們警告,西方輿論當中開始浮現一場「民主正當性的危機」。他們寫道:「在北美和西歐一些民主理應已然鞏固的國家裡,公民不只對政治領袖更吹毛求疵,也開始懷疑民主作為政治制度的價值,不指望自己能對公共政策發揮影響力,並且更情願支持帶有威權色彩的替代選項。」
雖然近期的調查證據顯示佛亞和芒克只說對了一部分,但我們還是有理由認真擔憂這件事。首先看看美國。我在二○一七年七月加入了獨立、無政黨背景的「民主基金會選民研究小組」(Democracy Fund Voter Study Group),和其他學者一起根據五千個代表性樣本調查美國人對民主的態度。
好消息是,美國民眾依然壓倒性支持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約有百分之八十六的樣本說民主是很好或非常好的體制,百分之八十二說生活在民主社會裡非常重要,百分之七十八說民主無論如何都「比其他任何類型的政府還要好」。華府雖然已變得兩極分化和失能,美國人卻也不如想像中那樣對我國民主感到幻滅。有六成的美國人對美式民主的運作或多或少感到滿意,比其他先進民主國家好一些。
但我們也得到一些壞消息。除了上述三個民主支持度的問題,二○一七年的調查也評估了人民對兩個威權選項的態度,一個是「不必受制於國會和選舉的強力領袖」,一個則是軍事統治。結果竟然有百分之二十四的美國人渴望強人統治。這比佛亞和芒克在二○一一年的調查結果低很多,但相較於同年皮尤研究中心對三十八個國家的調查,仍高於其他先進民主國家,比如加拿大只有百分之十七,法國為百分之十二,對悲慘的納粹歷史記憶猶新的德國更只有百分之六。
此外,美國境內對於軍事統治的支持也在穩定攀升,從一九九五年的百分之八,到二○一七年約百分之十八。這不只遠高於加拿大(百分之十)和德國(百分之四),也高於以色列(百分之十)和南韓(百分之八)等深切依賴軍隊的民主國家。(不過,選民研究小組在深入訪談中發現,美國受訪者對「軍事統治」的認知更接近由軍隊維持法律與秩序,而非讓軍方凍結憲法並直接治理國家。)
在表面的數據下,還潛伏著一些令人不安的趨勢。首先,美國人對民主的支持不如我們所希望的穩健。我們的調查小組在二○一七年的五個問題中,有三個關於民主、兩個關於威權,只有略過半數(百分之五十四)的美國人一貫地堅持民主立場。實際上,有百分之二十八的樣本在至少兩個問題中給了非民主傾向的回答。
更糟的是,民眾也趕上了當今嚴重兩極分化的政治情勢,對民主價值變得猶疑不定,甚至帶有敵意。當然,美國也曾流行過反自由的情緒。我們不知道有多少美國民眾在三○年代、或在五○年代歇斯底里的反共風潮中,願意支持獨裁者上台,而那些人數也可能比現在更多。但在那幾個過往時期裡,無論人們面對的挑戰是什麼,總統對民主的忠誠都沒有如此可疑。
在二○一六年總統初選中,川普支持者大體上更為支持「強力領袖」(百分之三十二),其他主要政黨候選人的支持者僅有百分之二十(或更少)有此偏好。而在該年大選中投給川普的選民,有此傾向者大約是投給希拉蕊的選民的兩倍(百分之二十九對十六)。至於二○一二年投給歐巴馬、二○一六年轉而投給川普的人,則是威權傾向最重的一群,支持「強力領袖」的比例高達駭人的百分之四十五。
在當今的美國,種族歧視和宗教不寬容,與獨裁支持度有非常高的相關性。令人擔憂的是,多達六分之一的美國人願意從種族的角度,甚至根本可以說是種族主義的角度,來看待美國人這個身份,亦即只有祖先是來自歐洲的人才算是真正的美國人。比起主張歐洲血統「完全不重要」的美國人,前面那些人支持「強力領袖」的可能性高出四倍,也更容易質疑民主。
在支持加強監控清真寺或對穆斯林加強機場安檢的美國人身上,也出現同樣令人擔憂的反應模式。這些受訪者支持「強力領袖」的比例,是強烈反對拿宗教信仰來為人貼標籤者的三倍。每當川普掀起文化論戰、挑撥反穆斯林仇恨、拒絕明確譴責白人至上論者、攻擊從加州眾議員瑪克辛.沃特斯(Maxine Waters)到籃球明星雷霸龍.詹姆斯(LeBron James)等非裔批評者的智力,靠的就是煽動這些潛在選民。
最後一個讓人憂心的模式同時發生於美國和其他主要民主國家:教育水準較低的人整體上更支持威權主義。
如同我們在第五章看到的,比起一百年以前,美國兩大政黨的意識形態更加涇渭分明、沒有交集,然而兩者也比過去更加勢均力敵。這樣的態勢使得美國政壇淪為一種兩黨之間你死我活、沒有合作可能的零和戰場。當每個人的政黨認同最終變質為敵對部落之間水火不容的鬥爭時,政治妥協的可能性就會降低,中間派要勸說同一陣營中的極端派和激進分子也會變得極其困難。對共和黨籍的國會議員來說,當最主要的踐踏規範者是政黨領袖和總統本人,要這麼就更難上加難了。
當然,社群媒體快速傳播錯誤、仇恨和極端訊息的能力,也加劇了美國民意中這股危險的趨勢,更不要說還有俄國等境外勢力,正居心叵測地利用美國政治的兩極分化與民心易受煽動這兩個弱點,準備扳倒美國的民主。
所以,真正的危險不是有大量美國人叛離民主理念;真正的問題在於,正當我們的民主政治受到前所未有的襲擊之際,美國人對民主認同的程度卻顯得搖搖欲墜,且囿於黨派之見。
窮人一樣渴望民主
美國國內的這些趨勢令人深感不安。但在世上一些生活沒那麼幸福的地區,我還是從民意中看到濃厚的希望。
有很長一段時間,專家都認為窮人不可能關心民主。一九四○年代中期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率先提出一個影響特別深遠的理論。馬斯洛主張全世界的人類有著相同的需求層次,最基層的需求是民生物資和人身安全,「更高層次」依序則是尊嚴、歸屬感和自我實現。該理論多年來經過不斷修正與強化,支持者主張貧窮、混亂國家的人民會著重「生存價值」,關注收入及安全,而富裕國家的人民則會追求「自我表達價值」,強調選擇的能力、尊重多元差異,並且不只是要求民主,還要求建立能讓自由及責任政治穩固成長的基礎結構。從這個觀點看來,社會經濟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前提:社會愈是繁榮,愈能將國家推往「自我表達價值」的方向,最後走向民主。
此一學派被稱為「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暗示較為貧窮的國家即使有了民主,也會缺乏必要的文化土壤,且其自由程度恐怕不及富裕國家的民主體制。這個理論主張,未開發地區民眾對民主的支持較為空洞、片面,對真正自由民主體制所需的自由、容忍、法治和制衡缺乏堅定信念。
這個理論在民調資料前是否站得住腳?它確實能合理解釋多數富裕民主國家為何能維持對民主的強烈支持。由於它著重在經濟富裕程度和民眾看待民主態度之間的關聯,故也能以「實質收入下降,貧富差距卻同時提升」來解釋美國和部分歐洲國家對民主的支持度的下滑。然而,事實上,在許多中等收入或貧窮國家,民眾支持民主的程度卻比一般假設的程度更高、更深刻,也更普遍。
首先,我們來看看民主國家比例最高的開發中地區:拉丁美洲。二○一七年,大型年度民意調查《拉丁美洲民主動態調查》(Latinobarometer)調查了十八個拉美國家,各國中大部分的人都仍然同意改寫自邱吉爾之名言的命題,即「民主或許有其問題,但仍是最好的政府體制。」從墨西哥的百分之五十四,到烏拉圭的百分之八十四,同意此觀念的比例平均為百分之六十九。
自二○一三年一度高達最巔峰的百分之七十九以來,拉美地區對民主的認同平均下跌了十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拉丁美洲的人民對民主的績效滿意度穩定下滑。墨西哥、哥倫比亞、秘魯和巴西都長期承受暴力或貪腐問題,這些國家的民眾對當前民主績效的滿意度不到百分之二十。只有百分之三的巴西人認為他們國家的施政是以照顧全民福祉為目的,而不是只為「少數有權有勢的群體」服務。
東亞的情勢更加慘澹,這從我參加過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定期民調數據可見一斑。如果我們比較東亞最富裕的三個民主國家(日本、南韓和台灣),和另外四個中等收入的民主國家(印尼、蒙古、菲律賓和泰國),也可以發現民主所獲得的支持也顯得有些淺薄,一如現代化理論所預期。
抽象地看,這幾個國家無論貧富,基本上都非常重視民主的價值。在二○一四到二○一六年間,這些國家平均有百分之八十九的人民都同意前述「民主或許有其問題,但仍是最好的政府體制」這個命題。但被問到對於威權的觀感時,幾個較貧窮國家的人民的立場就動搖了,或是更糟。當我們問到「我們是否應廢除國會和選舉,讓強而有力的領袖決定一切」時,有三分之一的泰國中高收入者和菲律賓中低收入者都支持這種強人統治 ── 菲律賓也真的在二○一六年選出強人總統杜特蒂。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也探查了亞洲人對言論自由、法治以及立法權對行政權的監察等自由價值的認同程度。這些問題旨在調查各國人民同不同意某些反自由的想法,包括讓政府「決定是否允許社會討論特定思想」、在重大判決上要求法官接受「行政部門的觀點」,以及政府「如果始終受立法機關監督」就無法「成就大事」。
這些問題的答案似乎因收入水準而有明顯差異。平均來說,有四分之三的日本人和三分之二的南韓及台灣人反對這些反自由的陳述。但在較不富裕的亞洲民主國家,人們就不那麼堅持這些原則。平均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印尼受訪者反對這些想法,而蒙古、泰國和菲律賓受訪者反對的比例僅略高於百分之四十。(這個比例和柬普寨、馬來西亞、緬甸和新加坡這四個鄰近的獨裁國家差不多。)
不過,世界上最貧窮的大陸 ── 非洲 ── 的民意卻讓老派政治科學家相當驚艷。我們可能會以為,比起中所得的亞洲,低所得的非洲比較不支持民主或言論自由和法治等自由價值。但事實並非如此。在二○一六到二○一八年間的調查中,近三萬名來自撒哈拉以南,從貝寧到辛巴威等二十二個非洲國家的受訪者,有很高的比例不但支持民主,也都認同民主的自由價值。這些國家普遍貧窮,但平均有百分之七十二的人民同意「民主永遠好過」其他的政府形式。
非洲人對民主的支持度雖然略遜於前面七個中高收入的東亞國家,不過那些國家不但富裕得多,實行民主的時間也超過一個世代。然而非洲人對自治政府(self-government)的熱忱卻遠高於拉丁美洲。非洲有許多人飽經獨裁和軍閥統治的荼毒,對威權的厭惡也不亞於東亞國家。平均有百分之八十五的非洲受訪者反對獨裁,相較之下,東亞受訪者則只有百分之六十九。至於對軍閥統治的唾棄程度,兩個地區都差不多是百分之七十五。
非洲如此強烈認同多黨政治、國會監察政府績效,以及媒體監督當權者等自由價值,讓老一輩的政治理論家大為吃驚。大約有四分之三的非洲人支持自由選舉和兩屆總統任期限制,還有百分之七十支持媒體監督政府是否有不正當的行為。更出人意料的是,非洲對這些自由政府的核心原則及民主本身的平均支持程度,從二○○五年以來就居高不下。
如果問一個普通的非洲人,他的國家有什麼問題,答案一定很清楚:是統治者。在二○○五年到二○○六年間,對十八個非洲國家的四次不同期調查一直顯現同樣的模式:百分之七十四的人要求民主,但只有百分之四十七的人期望民主會實現(來自二○一五年的數據),落差極大。
最後來談談阿拉伯世界。如果我們可以預期有哪個地方可能會鄙視民主,那大概就是中東了,那裡是全世界民主化程度最低的地方。雖然中東各地在二○一一年爆發了追求自由的起義行動,但除了突尼西亞這個小國以外,短命的阿拉伯之春在其他國家均以慘敗告終。
不過另一份區域性調查《阿拉伯民主動態調查》(Arab Barometer)的數據仍令人驚奇,因其顯示本區民眾同樣憧憬民主、憎惡威權統治。在二○一一年的十個受訪國家和二○一三年的十二個受訪國家中,平均有百分之七十二的阿拉伯人同意邱吉爾那段話,而在二○一六年受訪的六個國家中,同意的比例更高,平均為百分之八十一。被更深入問及能夠保障公民權、政治平等和行政可責性的民主體制時,阿拉伯人的反應更加正面:二○一三年,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受訪者贊成這樣的體制。
平均約有百分之七十五的阿拉伯人強烈贊成漸進而非立即的政治改革。但他們也不期望獨裁者將他們從混亂無序中解救出來。實際上,反對不受國會及選舉限制的「獨裁總統」的阿拉伯人年年增加,從二○○七年的百分之七十五,到二○一一年的百分之八十,再到二○一三年的百分之八十三(和二○一六年六個受訪國的平均比例相同)。阿拉伯人對伊斯蘭宗教獨裁也沒有多少熱情;各國絕大多數人都認為絕對「不宜如此」。
突尼西亞是阿拉伯之春後唯一繼續試行民主制的國家,但由於貪腐盛行又缺乏效率,人民對民選政府的評價愈來愈低。在二○一一年到二○一六年間,認為民主不利於國家經濟的突尼西亞人比率從六分之一增加到一半。但這些年間,認為民主是最好政府體制的突尼西亞人從百分之七十增為百分之八十六。或許人民並不像某些理論家假設的那麼缺乏耐心和重視物質。
各地的調查結果可以簡單總結成一句話:民主是普世價值。平均而言,世界上每個受訪地區的民眾,大多數甚至絕大多數都認為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而且同意有權無責的強人很糟糕。真要說起來,那些經常被評估為就算不支持獨裁、也對民主不感興趣的地區,支持民主和反對強人統治的平均程度與美、英、法、日等富裕的民主國家不相上下。
危機在於理想的幻滅
整體來說,全球的民意數據都清楚且令人驚喜地顯示,貧窮並非民主最大的敵人。柬普寨和緬甸這些亞非國家的窮人也渴望民主;他們只是渴望民主是為他們服務,而非為統治階級服務。開發中世界的公民仍不時會受到威權主義的誘惑,但被誘惑的與其說是窮人,不如說是理想幻滅的人。
經濟發展和公平公正對民主的成長至關重要。但大眾是否會長期穩定堅持民主,最重要的因素其實是當權者是否忠於自由體制的規範:透明化、責任政治、包容異己、尊重法律,以及確保反對黨發揮重要的監督職務。以民為本、信守上述價值的民主國家不只能讓國民安居樂業,更能讓大眾恢復信心,相信民主是人類所能想到最好的政府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