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獨裁者聯盟》脫鈎、去風險化與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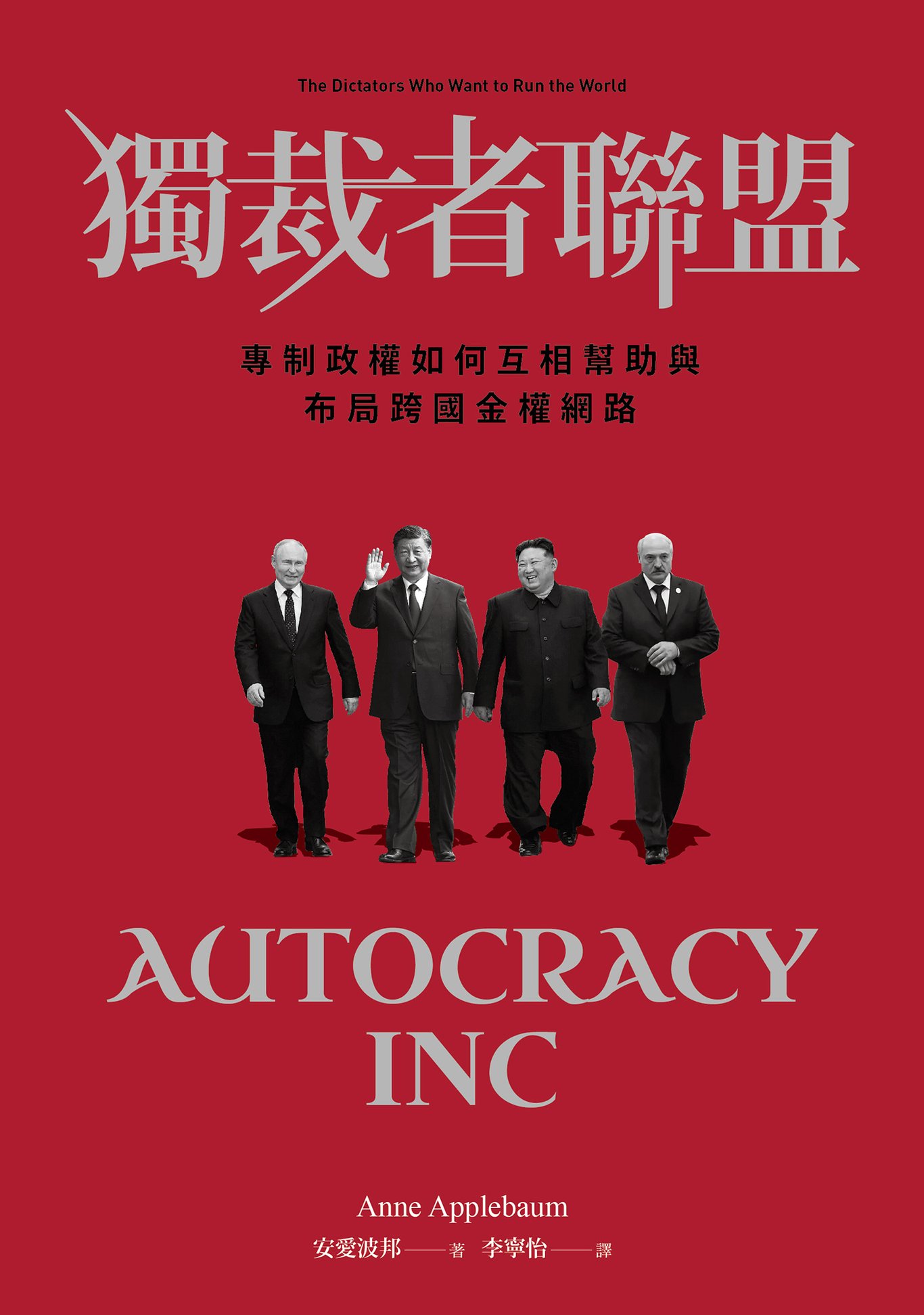
脫鈎、去風險化與重建
二○二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哈布斯堡狩獵小屋會議的五十五年後,歐洲的獨裁與民主相互依存實驗步向終點。一次大規模的海底爆炸後,又接連發生數起爆炸,炸毀了北溪天然氣管。四條獨立管道中有三條被摧毀,讓這整套耗資兩百億美元的建設毀於一旦。除了實體管道之外,這種破壞行為也摧毀了外界原本以為德國、歐洲或美國能藉貿易促進民主的想法。
俄羅斯自始就想讓北溪天然氣管達到徹底相反的目標:俄羅斯希望在德國推行盜賊統治,並且為俄羅斯控制烏克蘭奠定基礎。北溪二號的主要目的是將天然氣從俄羅斯直送德國,繞過波蘭和烏克蘭,使這兩國無法取得利益豐厚的天然氣轉運合約,還可能完全切斷烏克蘭的天然氣來源。甚至在協議簽署前,俄羅斯就已開始利用天然氣的定價與供應作為影響政治的工具,曾先後在二○○五至二○○六年與二○一四年兩度切斷對烏克蘭的天然氣供應,並操控價格,也在中歐與東歐地區藉天然氣議題來操弄政治。
北溪天然氣管也成為俄羅斯和德國之間一種新型特殊關係的基礎。參與北溪建設的俄羅斯企業開始融入德國的文化和政治。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資助了柏林的德國歷史博物館一場展覽,內容是被過度美化的俄德交往歷史;該公司也贊助了沙爾克足球俱樂部,正好是德國總統暨前外交部長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熱愛的球隊。這些公司也和德國與俄羅斯的政治人物關係密切。曾與普丁同時派駐德勒斯登的前東德國家安全部官員沃尼格(Matthias Warnig),就成了北溪公司執行長。[]當年同意興建北溪天然氣管的德國總理施洛德,卸任幾天後就接受普丁提議,成為北溪公司股東委員會主席。至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二○二二年為止,施洛德每年從北溪及俄羅斯天然氣相關企業(包括俄羅斯石油公司)賺得近百萬美元。並非所有與北溪相關的人脈關係都是腐敗的(施洛德堅決否認涉貪),但這些天然氣管既不符合德國的國家利益,也和歐洲的戰略穩定有所牴觸。俄羅斯二○一四年首度入侵了烏克蘭,但即使如此,繼施洛德後出任德國總理的梅克爾也沒有結束北溪天然氣計畫。普丁或許自此開始相信他獲得放行,可以繼續侵略行動。
很多人都曾猜測梅克爾的動機,但她的觀點其實與同時代幾乎所有民主國家領導人一致。她相信,互利互惠的投資加上一點點耐心,就能鼓勵俄羅斯融入歐洲,就像歐洲各國在二戰後學會相互融合一樣。她未能明白,俄羅斯的企業都不是民間公司,而是俄羅斯的國家代理人,在無數商業和政治交易中都代表克里姆林宮的利益。她未能了解,和那些不時接受中共補貼或指示的中國企業進行貿易,可能十分危險;她也不清楚,從稀有礦產到醫療用品等各種物資都仰賴這些企業,又存在怎樣的風險。
過度依賴與俄羅斯、中國或其他獨裁國家的貿易,不僅在經濟上產生風險,更關乎國家根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歐洲人才慘痛地意識到,依賴俄羅斯天然氣的決定讓他們付出多麼高昂的代價。改用更昂貴的能源導致了通膨,通膨又反過來引爆民怨。在俄羅斯假訊息戰的推波助瀾下,民怨升高使得德國極右翼的支持度激增。一旦極右翼政黨執政,戰後德國的本質就將面目全非。
二○二三年四月,拜登總統的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在華府一場演說中,談及過度依賴中國可能帶來的類似風險。他不主張脫鉤(意即美國經濟徹底與中國經濟脫離連結),而是主張去風險化:確保美國等民主國家不再全靠中國提供任何可能在危機發生時被當成經濟武器的資源。他舉了一些例子,包括美國「目前生產的鋰只能滿足當前電動車需求的四%,鈷則是十三%,鎳○%,石墨○%。在此同時,超過八成的關鍵礦物都只由一個國家加工,那就是中國」。他主張打造一套「供應鏈根植於北美,並延伸至歐洲、日本等地的綠能製造生態系」。
這件事必須更加大刀闊斧地進行,因為民主世界在礦產、半導體或能源供應上依賴中國、俄羅斯等獨裁國家,不僅會構成經濟風險,這樣的商業關係也在腐蝕我們的社會。北溪天然氣管並未如同當年德國總理布蘭特期待的那樣,深化商業關係並協助強化歐洲的長期和平,而是被俄羅斯當作勒索用的武器,並以有利於俄羅斯的方式影響歐洲政治。中國企業則利用在世界各地的存在來蒐集數據資訊,之後或可用於發動網路戰。俄羅斯、中國等國家的寡頭投入英美房地產的資金,讓大城市的房地產市場變得畸形,不只一位政治人物因此墮落貪腐。川普的首個總統任期內,就有匿名空殼公司購買川普品牌地產公司的公寓。這件事原本應該敲響警鐘,但事實不然,證明我們對盜賊統治的腐敗已習以為常。
我們與「獨裁者聯盟」之間的交易關係還帶來其他風險。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也在二○二三年春天的一場演說中表示,中國與歐洲之間的經濟關係「並不平衡」,而且「日益受到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所造成的扭曲影響」。說得更直接一點,中國政府會補貼最大的企業,幫助它們在國際間競爭。馮德萊恩呼籲「在透明、可預測和互惠的基礎上重新平衡雙方關係」,這是以禮貌方式表達我們需要實施關稅、禁令和出口管制,確保中國無法以政府資金削弱我們的產業。
警訊可能不僅於此,因為競爭的對手不只是中國,也不只是在貿易方面。當前的我們大約處在一個轉折點,必須在這個時刻決定如何形塑監控技術、人工智慧、物聯網、語音或臉部辨識系統以及其他新興技術,讓它們的發明者和使用者仍須向民主制度的法律負責,並遵守人權原則和透明度標準。我們已經未能監管社群媒體,因此對世界各地的政治造成了負面衝擊。舉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若未能在人工智慧扭曲政治對話之前實施監管,長期下來就可能產生災難性後果。民主世界應該再次聯合起來,提升透明度,制定國際標準,確保規則不會由獨裁國家制定,產品不會由獨裁國家塑造。
我們意識到這一切的時刻已經非常晚了。從莫斯科、香港再到卡拉卡斯,全球各地的民主運動人士一直在向我們發出警示:我們的工業、經濟政策和研究成果正在促進其他國家的經濟,甚至助長軍事侵略。他們是對的。
某些最有錢有勢的美國人和歐洲人在這些行業中扮演著矛盾角色。非常富有的人可以一方面與獨裁政權做生意,有時促進這些政權的外交政策目標,另一方面又與美國政府或歐洲政府做生意,同時享受民主世界自由市場中公民的地位和特權及法律保障。我們不能再生活在這樣的世界,是時候要他們做出選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