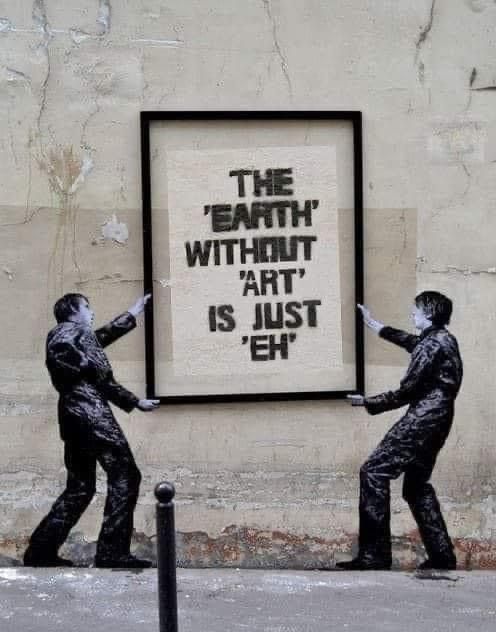自由人
第一次聽到“非暴力溝通”這個詞的時候應該是上中學。當時覺得發明這個概念的甘地很厲害,雖然並不真的理解這個概念的背景和語意,但能感受到,這應該是基於一套很深刻的哲學思想而延展出來的理論。我當時對於暴力的理解很簡單粗暴:就是打人。
1
大學時期我選擇國際政治作為專業。一個非常不實用但能滿足我好奇心的專業。我在歷史書中學到了非常多革命性的事件,它們幾乎無一例外都充斥著暴力元素,許多事件的終結也往往伴隨著一些關鍵人物的死亡。我曾想,如果我被迫捲入這場暴力事件中,我會做怎樣的選擇?妥協、對立、背叛、還是暴力終結?那個時候的我,一方面希望親眼見證歷史的滾滾洪流,另一方面又暗自慶幸自己不生在那個動亂時代。
很神奇的是,我在大學的四年裡(2009-2013),外部的環境非常動盪,但那又是我人生中最靜謐的日子。放學看書上課吵架,是我作為一名國際政治生的常態。課堂上,我們常常需要直面許多直擊人心的話題:比如中美關係、釣魚島、中日歷史遺留問題、台灣問題、香港問題⋯⋯每一個「問題」都能引發課堂上的唇槍舌戰,但是下課鈴一響,大家依然可以愉快體面地一起共進晚餐。我們專業的中國人很少,我算其中一個。每次提到跟中國有關的問題,我都能感受到大家的目光,好像我說的一切都來自背後那股強大的勢力。導致我每次發言壓力都很大,而且總會加上一句,“首先這屬於我的個人觀點”。我們專業的人好像有某種默契,就是下課時間只建立私人感情,至於觀點和辯論,全部留到課堂上。我的同學當中,大部分都是溫和的人,只有少數屬於「激進份子」,就是那些在私下交往的時候依然會因為我的國籍而對我排擠和陰陽怪氣的人。而大部分同學在畢業後,都只留在了Facebook裡。那個時候我認為,最大的對立,是國家塑造出來的意識形態,但這種對立在普通人的生活中,還牽扯不到暴力層面。
2
2014年,同樣也是因為意識形態而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動亂事件。當時我所在的教會在十萬八千里以外,那時候我們正在籌備復活節晚會。但所有教會成員為晚會所排練的話劇居然全部跟這場動亂有關,並且以神的名,要勇敢向敵人宣戰(但是在遠方)。我當場驚掉下巴,但也不敢多說什麼。畢竟作為一個外來者,我分分鐘會被貼上「敵人」的標籤,儘管我們信的是同一個上帝。再後來,我真的親眼目睹了一些團體暴力打壓事件。人們一次又一次帶著神的名義,號召其他人一起衝在前面,直接與「敵人」對立。而沒有直面對立的人,就被貼上“信仰不虔誠”、“信心太小”的標籤。這時候,「對立」有了一個具體的模樣,就是要做什麼樣的事,跟什麼樣的人站在一起,擁有一個怎樣的觀點,說怎樣的話。而「對立」的終極目標,就是對抗來自敵人的暴力打壓,以守護我們共同的信仰。
疫情幾年,飯桌上也常常是充滿硝煙的。我跟家人經常動不動會因為一些新聞和觀點吵得不可開交,非常不愉快。最後發現各自都無法退讓之時,默契地決定不聊這個話題了。從此飯桌上都是沈默的聲音。吃完飯轉向互聯網,無論是微博、朋友圈、小紅書、或者是牆外之網,好像不管發什麼,都有人會因觀點不同而抬槓兩句。而我也在這個環境中,掌握了許多陰陽怪氣的招數來對付那些喜歡抬槓的人,遺憾的是,他們當中很多是我的家人。我當時感到很絕望,是不是無論我如何努力,我跟家人之間始終有一道很深的鴻溝無法跨越,使得我們永遠無法真正理解對方?
3
前段時間播客圈有一則“塌房”新聞讓許多人津津樂道。有一個頂流播客,以談論文化、社會、結構性問題著稱,其中不少內容關於女性主義(主播都是女性)。他們被一位前實習生(更年輕女性)揭發了一系列關於拖欠工資、情緒操縱、壓榨年輕人,以及內部管理混亂等諸多問題,引來大規模吃瓜和圍觀。我並沒有耐心看完事情的來龍去脈,但這件事確實引發出了我從前許多不愉快的職場經歷。很諷刺的是,我也曾自詡為「女性主義者」,但在職場中我受到最多的不公平對待、打壓、冷暴力、背叛、陷害,全部來自女性上司或者女性合夥人,而她們也自稱是「女性主義者」。於是我開始思考,我所堅守的、擁護的這個「主義」到底是什麼?它是不是在不知不覺中創造了一些盲點,使得我所看見的東西越來越狹窄,從而我也從受害者變成了加害者,從而構建了一個新的暴力結構?説回播客頂流塌房這件事,從最開始的對立,到主播出來道歉,又引發了新一輪的對立,到有人發聲說“請不要對主播進行獵巫”而又再次引發對立,沸沸揚揚被討論了幾天。我知道就像眾多塌房的八卦新聞一樣,熱鬧過後很快會消散,再過幾年人們也不會記得當初誰被討論了什麼。
我也曾經做過幾年播客,那時體會到了不少來自陌生人的惡意。有時候也不知道是哪句話讓聽眾不舒服,對方就會寫下一條惡意滿滿的留言,有時候甚至還指名道姓罵人。這種新的體驗使得我終於可以像那些經驗老道的人說一句 “這個社會怎麼戾氣這麼重”,對立可以毫無關係,暴力可以毫不費力。做播客的那些年認識了很多我曾經很欣賞的人(大多數是所謂的文化人、知識分子)。可是近距離接觸下來卻發現,他們或許會為遠方的苦難和貧窮的人落淚,卻絲毫察覺不到身邊人的淚水。我意識到,暴力不一定要做什麼才算暴力,不做什麼也構成一種暴力。
我很喜歡「唐頓莊園」裡的一幕。當家裡的廚娘家裡發生危機時,管家竭力阻止家中的老爺介入,因為他認為廚娘的事情會對這個貴族家庭的聲譽帶來負面影響。但老爺知道了廚娘的困境之後,反而不顧家族聲譽,主動挺身而出幫助廚娘化解了危機。聲譽終究是虛無的,但人是真實的,關係也是。當我們所擁護的、追求的東西是虛的時候,對立會變的容易,暴力也會變的無差別。願我們都可以成為不被定義和主義奴役的自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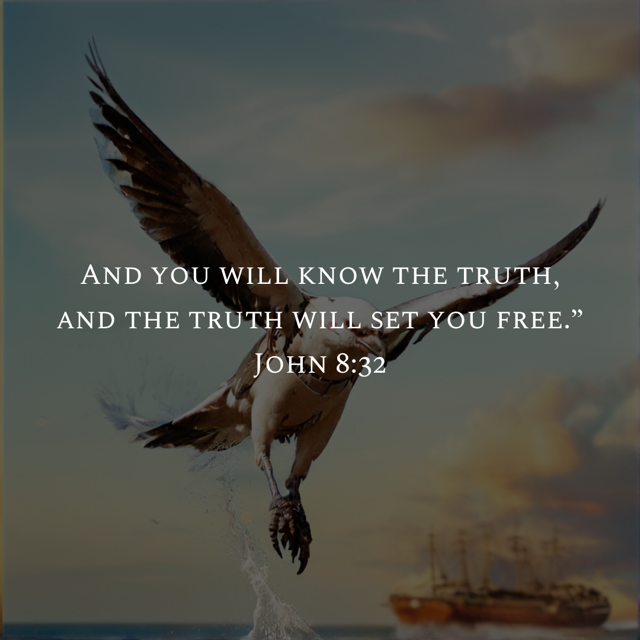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