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宾丨马克·贝辛格谈二十一世纪的革命



译按
马克·贝辛格(Mark R. Beissinger),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运动、革命、民族主义、国家建设、帝国主义、前苏联和后苏联国家。代表性个人著作有:The Revolutionary City: Urbanization and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Rebellion(2022)、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2002)。
就其去年出版的The Revolutionary City一书,马克·贝辛格接受了《雅各宾》杂志特约编辑克里斯·迈萨诺(Chris Maisano)的专访。专访原题“What Does Revolution Mean in the 21st Century?”,由《雅各宾》杂志网站发布于2023年8月10日。《雅各宾》,是一份在纽约发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的季刊,创办于2011年,旗下产品还包括同名网站等。
受访者回答中的斜体字(在本处为黑体字)为原文所有,书封图片为译者添加,小标题为译者添加。译者听桥,另对原文有多分段。
马克·贝辛格谈二十一世纪的革命
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的核心存在一个奇怪的矛盾。
自十八世纪出现以来,社会革命的梦想眼下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遥不可及。但与此同时,旨在推翻政府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像野火般席卷全球。即使只列出一部分经历过大规模街头骚乱的国家(和地区——译注),也是令人畏惧的: 阿尔及利亚、巴西、智利、捷克、厄瓜多尔、埃及、法国、香港、伊拉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波多黎各、俄罗斯、塞尔维亚、南非、苏丹和乌克兰,等等。当2010年代的世界历史被书写时,“阿拉伯之春”、“黑命攸关”和“占领华尔街”这些运动都将占据重要位置。
每一次抗议活动都吸引了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有时,他们甚至推翻了一个政府,或者将一位年迈独裁者驱逐出境。但他们的记录至多好坏参半。最成功的案例在带来更多民主或平等方面成效有限,而最不成功的案例则受到严厉的反革命镇压。
马克·贝辛格(Mark Beissinger)的近著《革命之城:城市化与反叛的全球转型》(The Revolutionary City: Urbanization and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Rebellion )帮助我们理解了这些“城市市民革命”,以及何以它们通常离开历史舞台和登上历史舞台一样快。
就本书的主题、我们所知的社会革命为何已经结束、革命的未来可能带来什么,贝辛格接受了《雅各宾》杂志特约编辑克里斯·迈萨诺(Chris Maisano)的专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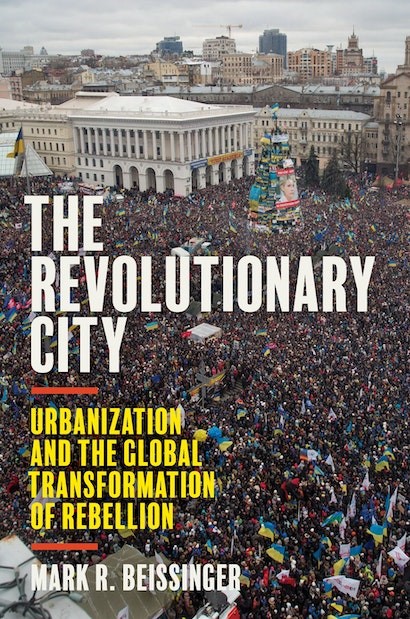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中期,社会革命主要成为农村现象
克里斯·迈萨诺:什么是革命?
马克·贝辛格:根据这个词在当今社会运动文献和一些更当代的革命研究中的使用方式,我给出了一个相当直接的定义:革命是指一个在位的政权被自己的民众大规模围困,旨在形成政权更迭,随后是形成实质性的政治或社会变革。正如列夫·托洛茨基所说,革命就是民众自下而起,通过大规模动员夺回对政权的控制。
自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现代革命首次出现以来,革命一直是一个不断演变的现象。关于古代世界是否有革命,存在争论。如果有的话,它们属于不同的类型,而且规模非常有限。
例如,有些人认为古代雅典发生过革命。但古代雅典的总人口,至少就自由公民而言,是很少的(最多有大约十万人)。雅典是一个城邦国家,规模与当代民族国家完全不同。但当我们谈论现代革命时,我们谈论的是大量民众的参与,和有领土野心、经济目标和大规模政治组织的现代民族国家。
历史上的革命被用于许多不同的目的。革命开始时主要是社会遏制君主篡权的一种方式。十九世纪,革命有所演变,增加了社会方面的构成,旨在改造社会的阶级结构。这一社会性元素长期占主导地位。但这一时期总有政治革命发生,而且革命的政治维度先于它的社会维度存在。
除了反君主制的革命,还有旨在获得民主的革命,旨在摆脱殖民统治或现有国家的独立革命,旨在颠覆种族等级制度或族群等级制度的革命,旨在将世俗国家改造为宗教国家的伊斯兰主义革命。这并没有穷尽历史上革命发动的各种目的。
我的书主要是关于革命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的。我没有详细研究所有不同类型的革命。我对社会革命的衰落和日渐边缘化,以及我称所称的城市市民革命的兴起特别感兴趣。社会革命在二十世纪中叶达到了鼎盛时期。但近几十年来,社会革命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旨在遏制腐败和高压独裁政权的政治革命成倍增加。与此同时,革命的地点出现了转向,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十九世纪,社会革命主要是一种城市现象。但在二十世纪中期,社会革命转移到了农村地区,并且主要成为农村现象。
城市市民革命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革命的主要形式
克里斯·迈萨诺:什么是城市市民革命?
马克·贝辛格:城市市民革命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革命的主要形式。城市市民革命力求在城市空间中心动员尽可能多的人,以便通过数目的力量而不是武器的力量实现政权更迭。因为他们试图动员尽可能多的人来扰乱政府,他们在支撑他们的联盟中是相当多样化的。城市市民革命之所以成为世界各地主要的革命形式,部分原因与过去一个世纪间数百万人涌入城市的流动有关,这一大规模的城市化已改变我们世界的性质。
事实上,直到二十世纪晚期,你才看到这种形式的革命,当时有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里。1900年,世界上大约有13个城市有一百万或更多的居民。今天,我们有548个这样的城市。因此今天形成相当多人群,并将他们当作实现政权更迭的基础,比起一个世纪以前要容易得多。
从传统上看,革命是一种武装现象。但因为国家在城市中拥有压倒性力量,城市中的武装革命通常是一个失败的命题。国家有更多的武装战斗人员、更好的武器和更好的训练,而且这些力量往往集中在城市,那里是政府的神经中枢所在地。十九世纪的革命者已意识到这一点。
例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道,城市里的武装革命分子相较于国家来讲处在很大的劣势,因为国家拥有压倒性的火力。这是二十世纪中叶武装革命从城市转向农村的主要原因。在这个过程中,社会革命者发现了农民的革命潜力,而他们以前被认为是反动的,主要关注于获得土地,而不是改造阶级结构的问题。
城市化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使城市市民革命在二十世纪晚期成为可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政府以非常暴力的方式对待手无寸铁的人群。二十世纪初,手无寸铁的革命人群死亡的可能性是今天的六倍,因为政府更有可能向他们开枪,或从他们身上骑过。所以革命者不得不武装自己,只是为了保护自己。
但今天,随着人群控制的“非致命”方法的发明,非武装革命的危险性已经下降很多。但还是有很大的风险。很明显,今天仍然有人在革命人群中遭到枪击并身亡。但与过去相比,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城市市民革命直到二十世纪后期才发生,还有技术上的原因。例如,二十世纪早期,因为没有音响放大系统,你在很远的地方就听不到一大群人中的人声了。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首次将声音放大技术应用于大型示威和街头游行,你才能听到十米以外人群中的声音。在早期,革命者也主要依靠高度本地化的社区和工厂网络动员民众,这也限制了人群的规模。
但到了二十世纪末,所有这些都改变了。随着电视和互联网的兴起,技术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向,这使得更多的人可以被动员起来。数字技术改造了革命的进程,加强了可视性和共时性,并以极快的速度跨越了政治边界。
政治和国际环境也在以也有利于城市市民革命兴起的方式发生转变。人口在城市中的集中使得基于数量的力量而非武器的力量的革命性挑战成为可能。因此,今天的革命与过去有着明显的不同:不仅在于它们向城市的转移,还在于它们的整个实施方式。
新自由主义改革引发了一些更具体的问题
克里斯·迈萨诺:在社会结构、自然环境、国内和国际市场地位等方面,城市本身也与几十年前或一个世纪前不同。我生活在纽约,现年四十岁了。现在和我小时候大不一样了。这座城市的性质已经发生了真正的转变,类似的过程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城市上演。
新自由主义时代城市社会生活的转变如何影响城市市民革命的发展?
马克·贝辛格: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城市的面貌、社会结构和性质发生了多方面的转变,这些转变影响到城市革命挑战的性质。回想一下十九世纪和工业化时期,典型的情况是,比如在巴黎,那里有非常密集、靠近权力中心的工人阶级社区。这些密集的工人阶级街区为街垒作战提供了有利的实体环境。
但为打击叛乱,政府拆除了这些社区。社区被清理出去,在它们的地方建起了大的开放空间。在巴黎,这与奥斯曼男爵有关,后来在世界其他地方得到模仿。伴随各国实力增长,它们还寻求在城市中建造大型的仪式性开放空间。随着城市的发展,更宽阔的街道和林荫道变得必不可少,只是为了人们的流动。这些宽阔的林荫道和广场对武装叛乱不是特别有利。但在今天,它们恰恰成了大量民众聚集在革命人群中的地方。(奥斯曼男爵,即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生于1809年,卒于1891年,法国城市规划师,主持了1853年至1870年的巴黎重建。——译注)
简言之,城市空间的开放提供了有助于城市市民反抗的实体环境。
新自由主义也影响到城市。一方面,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中产阶级化往往将穷人和工人阶级推向城市实体的边缘。相对于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城市贫困人口参与城市市民革命的数量通常不多。相反,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有不成比例的参与。我说的不是资产阶级,也就是资本家阶级。资本家通常不参与革命,因为他们没有适当的理由参与。他们通常与执政政权关系密切。但受过良好教育的服务阶级的参与确实不成比例。
在我的书中,我用了来自四个不同的城市市民革命的有代表性的全国性调查,研究什么人参与了城市市民革命。那些城市中,两个来自乌克兰,一个来自埃及革命,一个来自突尼斯。那些调查显示,在那四座城市中,相对于他们在社会中的数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和富裕人士不成比例地参与到了社会活动中。但那些调查也显示,不只在阶级形象方面,而且在政治观点方面,参与这些革命的人群是相当多样化的。城市市民革命是相当多样化的联盟。只有中上阶级,你不可能形成必不可少的巨量人群,去推翻一个政权。
这一多样性反映在他们的目标和要求中。那些目标和要求围绕消极联盟(negative coalitions),专注于驱逐一个腐败而高压的政权,而不是着眼于专门的一整套变革。在这方面,城市市民革命往往被解释为民主革命。但正如那些调查所显示的那样,绝大多数参与者对民主价值观的承诺较弱。此外,激励绝大多数参与者的往往是腐败和经济事务,政治和公民自由只是激励通常约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少数参与者的因素。
就新自由主义的后果而言,源自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城市人口实施,诸如强加于社会的公共服务缩减或价格上涨之类调整——的危机,已引发了相当多的革命。并非所有城市市民革命的形成,都是因为响应了新自由主义,但新自由主义改革引发了一些更具体问题。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还以一种新的方式将各城市联系了起来,使革命在全球的扩散成为一种更快、更广泛的现象。作为全球化的结果,革命在各国之间的扩散变得更加明显。
存在一种将远离革命作为一种实现变革方式的转向
克里斯·迈萨诺:“革命形势”这一概念,是革命研究的核心。关于革命形势是怎么回事,弗拉基米尔·列宁有一个三部分构成的概念。他认为,当统治阶级不可能维持其统治,被压迫阶级的苦难比平时更加严重,并且因为前两个条件,人民群众登上历史舞台时,那种形势就出现了。你怎么看这一概念?
马克·贝辛格:当代学者普遍超越了这一列宁主义概念。革命不只是冤屈深度或压迫层级的问题。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准确地预测过革命。研究表明,绝大多数人在面对冤屈时会默默忍受。冤屈当然至关要紧,但远远不足以解释革命。正如列宁本人可能会认为的那样,领导力至关重要。资源至关重要。机会至关重要。但即使是这些,也无法完全解释革命的爆发,众所周知,那是不可预测的。
至于什么是革命形势,今天的学者们反而从托洛茨基那里获得了启示。托洛茨基认为,当对同一个国家的主权要求出现竞争时,革命形势就是一种双重主权的形势。托洛茨基显然是在写俄国革命,在那场革命中,两个相互竞争的权力中心,即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在争夺主导地位。你到达两个正式的权力中心,它们声称对同一个政府拥有主权,这不总是事实。有时,在当代革命中,革命的领导权往往是分散的,只是人们拒绝在任政权的主权,同时对在任政权的替代方案更加含蓄。
这一列宁主义的概念是高度结构化的。但革命形势不只是结构性条件的问题。它们来自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互动,这一互动可以将改革或高压时期变成公开的反抗。多种可能性会发生在这些行情内,而且因政府和反对派回应彼此时做出的选择,革命中存在大量不可预测性。
这并不意味着革命背后没有一个结构性维度。正如我在书中所展示的,存在一系列结构性条件,可以准确预测大约80%的城市市民革命的出现:高度的腐败,中等水平的镇压,长期掌权的领导人,缺乏石油资源,中低水平的发展。
但这些条件也严重高估了革命的可能性。基于这些条件,你会期望看到比实际发生的更多的革命。那甚至考虑到了某些已知会触动革命的因素,如价格上涨、金融危机或国际战争。
支撑革命的结构性条件过度预测了革命,因为政府与反对派的互动在革命的出现中发挥了作用。例如,要回应一项挑战,政府的做法可以是拉拢,或者,可以实施改革或展开镇压。这些做法有时会在革命性挑战获得动力之前将它们驱散。
反对派内部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使他们无法展开跨团体的合作。在本书中,我勾勒出几个例证,这些例证出自这样一个国家:基于在其他地方至关重要的结构性条件,它存在高于正常水平的革命风险。但革命没有发生。而且我研究了何以风险升级了,但革命没有发生。我发现,在这些情况下,起作用的是代理和选择。
革命是一种结构化了的现象。它通常发生在我们会期望它发生的地方,且是在一组特定的结构性条件下发生的。但革命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人们的选择,且这些相互作用的发生往往伴随相当不可预测的结果。革命争论中的错误也相当常见。出于所有这些原因,革命通常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克里斯·迈萨诺:你有没有发现,相较于更常规的政治争论模式,革命在实现目标方面多少是成功的?
马克·贝辛格:很难说。我们并没有像应付革命那样应付所有常规的争论和改革运动,革命是一种远为少见的情形。例如,我不能说改革运动在实现实质目标方面多少比革命成功。改变很难。
但我认为,我们可以说,对某些类型的目标来讲,存在一种将远离革命作为一种实现变革方式的转向。举例来说,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以来,就夺取权力而言,还没有出现过成功的社会革命,而且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寻求社会阶级转型的新的革命事件出现得相对较少。但我们确实知道一些非革命的运动,它们的目标是,改造已经通过票箱掌权,或通过其他方式影响了政府的社会阶级结构。
革命或许已经成为改变社会的社会结构的一种不太有用的方式。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改变社会的社会结构往往会分裂社会,诱发大量暴力抵抗,使社会革命更加暴力,且更加难以实现。
城市市民革命要成功,往往需要一个外部威胁
克里斯·迈萨诺:我们更近距离看看乌克兰,这是你在书中详细研究的案例之一。乌克兰现在是新闻焦点,因为那里正在发生战争。2004年的橙色革命和2013至2014年的广场革命,乌克兰城市市民革命的这两个大事件,是如何阐明你书中的一些主题和论点的呢?
马克·贝辛格:对我来说,橙色革命是典型的城市市民革命。这场革命发生了,是因为一个腐败、高压的政府试图实施选举舞弊,以维持权力,这引发了社会广泛领域的强烈反对。它试图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在城市中心空间,在大的开放地区,实现政权更迭。它在动员大量人群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在基辅市中心聚集了上百万人。
但后来,主导革命的消极联盟掌权后很快就分裂了。它极其多元,无法加以团结。它也没有以任何方式推开或改造那个它继承的国家,腐败继续猖獗。这导致了一种局面: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这位在最先引发革命危机的选举中竞选的候选人,在六年后的2010年当选总统。于是,正是那些被革命从权力中驱逐出去的人,因革命后出现的执政联盟的失败,没过太久之后就通过投票箱再度掌权了。
持久性缺乏,是城市市民革命的典型特征。这种革命缔造的政府极度不安分。这部分是因为它们有非常简约、消极的目标,寻求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它们很大程度上是要驱逐一个高压、腐败的政府,更多是关注动员民众起来反对什么,而不是为了什么。假如你打算依靠数目的力量,你就必须拿出能够吸引大量人群的诉求。假如你靠数目的力量生存,你就会死于数目的力量。
当然,乌克兰发生了第二次革命,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第一次革命没有结束引发第一次革命的腐败和高压。第二次革命,即广场革命,某种程度上更成功地改造了这个国家。但乌克兰在这一过程中也经历了相当多的挣扎,主要是因为第二次革命继承了亚努科维奇建立的腐败国家。当然,当代乌克兰面对的部分挑战源于战争。但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和入侵团结了乌克兰社会,而革命之后多半不会有这种情形。那使得泽连斯基周围出现了一个严厉打击腐败的新联盟。
克里斯·迈萨诺:埃及局势中不存在这样的地缘政治因素,那里也有一个非常广泛的消极联盟,成功推翻了穆巴拉克。
马克·贝辛格:没错。埃及的这个联盟在面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时也无法保持团结。它分裂了,最终,事态恶化到这样一个地步: 曾与穆斯林兄弟会结盟驱逐穆巴拉克政府的自由派自己与穆巴拉克军队的残余结盟,为的是将穆斯林兄弟会赶下台。这个故事是埃及革命的悲剧,我们知道今天正在那里发生的大规模镇压的后果。
城市市民革命要成功,往往需要一个外部威胁来保持革命联盟的团结,因为它们的自然趋势是在掌权后分裂。
城市抗议变得更加暴力,但更多是街头暴力,而不是内战
克里斯·迈萨诺:你这本书的关键方面之一是暴力和革命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正如你在本书中记录的那样,革命性的暴力长期以来一直在减少,特别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但你也注意到,近年来,革命变得更加暴力了。
乌克兰正在发生可怕的暴力战争,那里的局势似乎反映出这一点。乌克兰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它的地缘政治维度影响了那里的革命争论吗?或者你认为,它预示着某些事情会到来,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大国对立在国际舞台上重新出现的时候?
马克·贝辛格:总的来说,革命中的暴力,长期看已经减少了。与二十世纪上半叶或冷战时期相比,革命性的内战已经变得不那么常见了。即使在这些战争中,死亡人数也较少。哪怕在非武装革命中,致命的暴力也减少了。
考虑到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引发战争的方式,乌克兰局势中有一个独特的元素。但在革命中的暴力长时间下降后,今天的革命再次变得有些更加暴力了,尽管方式有所不同。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内战,不如说是更多的暴力,尤其是在城市里。你在广场革命中看到过那种场面。那起初是一场典型的城市市民革命,动员了非常大量的人群,主要是为应对政府的镇压,但后来演变成了暴力街头骚乱。但城市市民元素无法驱逐亚努科维奇政府。
一般来讲,城市市民模式依其自身条件看都相当成功,但近年来,这一模式所应用的目标却变得越来越难以推翻。抗议者面对的是更加高压的政府,数目的力量不大容易撼动这些政府。它们已学会如何处理城市市民抗议,如何在空间上管理这些抗议,以及如何等待抗议活动结束,直到人群筋疲力尽。你在白俄罗斯也能看到这种情形。
数目力量的这一失效已将一些抗议案例推向更加暴力的形式。所以,是的,它们变得更加暴力,但更多是街头暴力,而不是内战。
大量人口迁入城市为革命的城市市民模式创造出有利环境
克里斯·迈萨诺:你认为,社会革命的时代,至少是像我们所了解的那样的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只是冷战结束和苏联集团解体的副产品,还是有其他动态在起作用?
马克·贝辛格:苏联集团的解体无疑是一个因素,但事情没那么简单。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有关社会革命的经典作品《国家与社会革命》一般被认为是关于这一论题的学术典范。以本书为例,斯考切波认为,社会革命植根于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即她所称的农业科层社会(agrarian-bureaucratic society)。那是这样一种社会:在其中,农民生产的剩余,基本上由政府和与政府结盟的贵族或地主精英共享。这是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容易受社会革命影响的典型社会。(西达·斯考切波,生于1947年,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国家与社会革命》初版于1979年。——译注)
因此,社会革命历史上与土地不平等和土地获得机会缺乏密切相关,通常发生在农民社会。哪怕社会革命中的动员发生在城市,主要由城市各阶级领导,农民元素依旧是突出的。但到二十世纪晚期,农业科层社会已经开始衰落。
发生了什么?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国家经历了共产主义革命,那些革命将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阶级一并清除了。其他地方因存在社会革命的威胁而发生了土地改革,目的是削弱革命的潜能。世界各地的土地不平等依旧相当普遍。但在许多地方,大量土地已被重新分配给了民众,这缓和了社会革命冲动的元素。
然后是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那些流动到城市生活的人是谁?通常是年轻人,也就是最有可能参与武装叛乱的同一些人。当他们移居城市时,他们将相当高比例的老年人和女性人口留在了乡下,那里通常仰赖在城市赚取的工资和汇回的钱款。于是,获得土地不再像生计来源那样重要,通常是在城市中挣得工资的渠道取而代之了。此外,农村地区有一些绿色革命这样的发展,在一些国家提高了农村地区的生产力,这样人们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最后,贵族阶级的主要溶剂之一是民主化。研究表明,通过民主改革,拥有土地的贵族精英的权力往往会被削弱。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破坏了农业科层社会。所以我们传统上了解的社会革命就不再发生了,这不只是因为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苏联没有形成社会革命。苏联的作用本质上是为革命者提供武器。相反,支撑这些革命冲突的条件已经恶化,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人口迁入城市。大量人口迁入城市的这一运动,反而为革命的城市市民模式创造出有利的环境。
新的社会革命模式将不得不与众不同
克里斯·迈萨诺:在一种更城市化的背景下,社会革命可以变成一种活生生的可能,能否预言这样一种情形?在这些条件下,社会革命是否有必要加以彻底重新构想?
马克·贝辛格:是有必要重新构想。社会革命的农业科层模式不再有效。但是社会不平等依旧凸显,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变得更严重。因此,在城市化的社会中,支撑社会革命的那些问题并没有好像是消失了。农业科层社会的黯然失色使那种社会革命模式退化和边缘化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社会革命模式不会被发明出来。
考虑到城市社会的特点,这一模式比较可能不得不依赖数目的力量,而不是武器的力量。因此,它不会像早期的模式那样被严重意识形态化,也没有那么全面绝对,早期的模式通常寻求彻底改造社会。同样,假如你打算依靠数目的力量,你必须想办法如何吸引相当多的人,而那会削弱你的诉求。此外,因为国家的强制力量集中在城市,城市的武装革命就成了一个失败的命题。简直无法起作用,至少在大量案例中是那样的。一个新的社会革命模式,一个打击阶级不平等的模式,将不得不与众不同。
目前,绝大多数这些问题都是通过投票箱解决的。一般来说,民主是革命的重要溶剂,因为假如几年后,你可以通过投票箱来改变政府,那么你确实没有理由在街头冒生命危险。
克里斯·迈萨诺:你书中的一张图表让我印象深刻。那是一张线性图,显示了社会革命事件的发生频率如何在到达国内生产总值和民主化的某些临界点之后,基本上下降到零。
马克·贝辛格:在这方面,是所有革命事件。一般来讲,达到一定程度的民主之后,就不会有革命了。民主国家偶尔发生革命,但非常非常罕见。中等程度的镇压下最容易发生革命:不是在最开放的政权那里,也不是在最高压的政权那里,尽管最高压的政权确实比民主国家更经常经历革命。
这正是民主倒退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今天不知道民主的未来是什么。它目前饱受怀疑,处在威胁之中。我们已见证了全球范围内民主国家的倒退,和一场向更威权政权发展的运动。假如民主国家确实回归了威权的政府形式,那可能让革命成为更具魅力的命题。
克里斯·迈萨诺:你所说的倒退,是指选举民主并没有被完全摧毁,而是被操纵了,以至于无论人们如何投票,基本上都不可能改变政府或其政策?
马克·贝辛格: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但独裁权力的壮大会更加如此,这种权力无视任何对行政的限制。有在那些情况下发生革命的案例。真正的疑问是,民众在投票箱那里有多大的影响力来抑制这些倾向?假如有这样做的意愿,他们能够通过投票箱改变他们的政府吗?
1月6日国会山事件更像是暴动,不是革命
克里斯·迈萨诺:在现代,革命的概念已经几乎完全被等同于左翼、民主、进步的政治传统。但今天,革命的重心似乎正在某些方面转向右翼。1月6日事件发生在美国,而在巴西,博索纳罗的支持者在他输掉选举后效仿了1月6日事件。你看到革命争论的政治效价发生了转变吗?(博索纳罗,生于1955年,2019年1月至2023年1月担任巴西总统。——译注)
马克·贝辛格:从历史上看,我们偶尔会有右翼革命。那不是完全没有发生过的现象。墨索里尼的崛起就可能被解读为一场革命,事实上,在我的书中,我确实把那当成了一场革命。所以很有可能。
我不认为1月6日事件是一个革命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是由一个已经掌权的人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而实施的。另一方面,它缺乏一个革命事件的信念,只是一次性的。我会说那个事情更像是暴动,而不是革命。围困意味着某种承诺: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心向往之并持之以恒,以实现政权更迭。
在1月6日事件中,他们捣毁了国会,然后就回家了。其他人称1月6日事件为“自我政变”,也就是拉美人熟知的autogolpe,我认为是正确的。那是指一个领导人通过发动反对自己的政府的政变或起义,试图永远掌权,主要是为夺取对那个政府的永久控制权。
幸运的是,1月6日的自我政变被挫败了。博索纳罗在巴西的尝试也是如此,缺乏对大规模围困权力的承诺和信念,更像一场骚乱,而不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旨在让博索纳罗永久掌权的自我政变,而非针对现政权的群众反抗。
克里斯·迈萨诺:希望未来他们不会试图实现你描述的那种围攻。
马克·贝辛格:那是可能发生的。革命是一种可以被所有不同社会力量利用的现象:它不是左派或自由派的唯一属性。相当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