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代简中人的割席感
割席一词,最早是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事件里听说。
作为一个在广东出生长大的女性,即使从小母语是粤语,也得益于广东省居民前往港澳的方便和从小能实时收看TVB电视,但在19年反送中事件发生时,也很难完全共情香港人的处境。
反送中时期,墙内外的新闻和社媒论调基本呈两极分布:墙内的公众号和微博,多的是批判讨伐论调,不齿香港青年受境外势力煽动,争取其实从未被赋予过的民主;墙外在Facebook和Instagram,认识的香港朋友们却持续多日表达愤怒和抗争,很多换上了全黑的头像。
当时的自己,没有明确表达过立场。
一方面情感上同情共饮一江水的香港人,感念于粤语能维持影响力几乎完全是香港的贡献;另一方面在墙内的生活和政治环境,导致我几乎无法摆出坚定支持他们的理由。
港人内部也逐渐分化,有一系列口号和暗语表达在运动后期不同的行动态度,比如“Be Water”,“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其中也包括“割席”。
还记得当时的对立激烈到,连在深圳打开Tinder刷到对岸的香港人时,十有八九都会在profile上标上个黄丝带,或者写“黄丝勿扰”。之前在香港参加青年交流活动认识的朋友,也不动声色在Instagram上取关了我。
不在一个语境下生活,缺乏公共话题讨论经验,甚至是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都让我对香港青年的理解尝试变得困难。也可想象在香港的朋友,每天身处漩涡中心,却在社交媒体刷到我在大陆岁月静好时,内心的落差感和割席的愤怒。现代通讯科技发达的一个悖论在于,让有一面之缘的人有了长期联系的手段,却无法对维系长期有意义的关系有任何保证。既然已不在彼此的生活里,突发事件所暴露的共时性差异随时能成为敌对的导火索。
终于由于今年三四月在上海亲历封城,自己突然懂了当年香港友人们的感受。
在4月4日,我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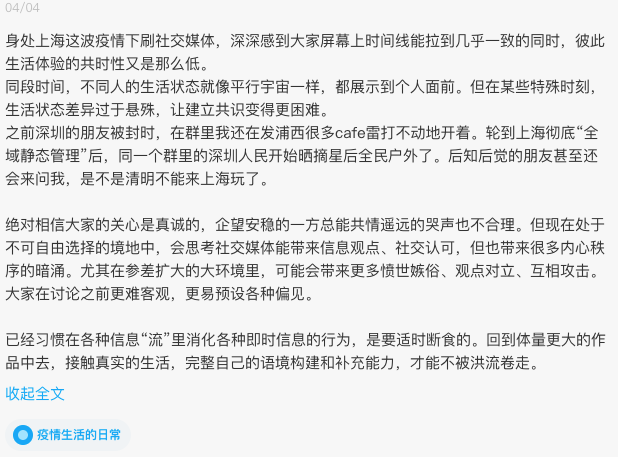
现在看来,是对友人无法共情自己的无奈,也是无法抵抗大环境的消极躲避。
很大程度上这是一次政治扩大影响的次生灾难,因为不准异议、不可细究、不得追问,身处其中受苦的人只能被迫以激进的方式发声。一种小时候在家里家长不准顶嘴的委屈感,真真切切地在集体公共生活中发生了。上海在6月1号儿童节全市解封,仿佛是一个隐喻:在儿童节给你自由,是因为一直把你当儿童看。
在外面的人还有点看懵了,这不是病毒无情吗,怎么还养出了一帮刁民教领导做事?回头再看,我们当时觉得香港青年极端,有没可能是他们也受了我们看不见的委屈?更不忍联想到,上海和香港尚且还有发声闹一闹的资本,远在边疆的少数族群,他们或许只能含泪歌舞升平。
很多之前以为能和朋友们达成的共识,都在这两个月后瓦解重构了。解封后见或不见,心理距离就在那里——各自对这两年防疫政策的看法,已在心里分成三六九等。不必互相解释太多,都体现在润不润、生不生、买不买的行动里。身不由己的选择自然是有的,只是有时甚至都不用聊,都能在社交媒体里看出是不是同路人。
上海解封后,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是另一起激起舆论浪潮的新闻。几位不幸女性拒绝骚扰后被残害,全过程监控录像曝光后,引发简中世界对女性权益保护的又一次讨论。因为铁链女、西安地铁女、拉姆遇害新闻后的不了了之,以及女权主义这两年被泼脏水成打女拳,早已对内地的女性议题讨论失去信心。但我还是在微博上转发了几条自认相对克制的发言,其中一位现实朋友看到后,对我另一位共同好友发问:我什么时候加入了打拳?是不是之前在上海被关太久,现在有心理问题?
而这位朋友,还是一个女性。
共同好友跟我转达信息后,说自己也不认可她的说法并隐晦表态了。身为一个女人,自己不发声就算了,还倒戈相向,实在是难以理解。没有办法再和那位说我打拳的朋友讨论她的真实想法,我和共同好友只能一起分析了下她的处境来理解——大概是一个曾经受过苦的文艺女青年,终于在老公开了公司经营得小有名气,自己也一起成为了小小资本家后,享受着雇人缴税的道德优越感,来批判她曾经熟悉的群体。
我只是疑惑,她曾经是念艺术史在美术馆工作的先锋女青年,怎么之前工作和读书接触到的思潮理念,没有留下一点印记?
朋友说,大概是她从来没有相信过。
我突然懂了,为什么之前香港反送中事件,她也那么早旗帜鲜明地对香港青年发出谴责和鄙夷。
她的精明在于能站在为自己获得现实利益的一边,全然抛弃自己的过去所学和性别身份,甚至将知晓的理论见识用于批判他者;同时还十分幸运地不会轻易共情自己同类的苦难,免遭情感和认知的冲突。一种经世致用的个人哲学,实用至上的精英主义。
她给我理解现在的简中群体,提供了一个典型:正正因为体会过资源的匮乏,又抓住了一波阶级跃迁的轮动,对今天来之不易又其实带着莫名其妙的所得会更抱死不放。此时维护自己相对优越的需求,远远压过理解关心其他社会弱者的能力。尽管偶尔的事件会传来摇摇欲坠感,但隐隐的不安只会让他们更本能抓住当下,维护那套叙事,在不合理的威权下仍然寻求自洽,以期在动荡中自保并抓住未来可能又一次机会的优先权。
我们其实都是同一代,出生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时期,成长于最早发展海外贸易的南方,潜移默化接收过很多主流叙事外的文化教育。但近年社会上的一系列事件,大浪淘沙般让我们逐渐分道扬镳,价值观取向已不可同日而语。
简中人的割席,大概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