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門佳片|《唬爛三小》——青春就是唬爛唬爛著,然後就沒了

一部鮮為人知也被低估的紀錄片,是20年前隨手記錄下來和同學的閒聊唬爛
前幾天花蓮鐵道電影院請來了黃信堯導演分享製作紀錄片的歷程,並在早上放映了導演的《大佛》也就是《大佛普拉斯》的前身,短片版,以及比較少人知道導演的早期的作品《唬爛三小》,也是《同學麥娜絲》角色的原型。
《唬爛三小》是一部從1998年拍到2004年(?不確定)的紀錄導演的高中同學每天泡在泡沫紅茶店裡唬爛聊天,講些「沒有意義的話」,從大學到出社會的變化,直勾勾的將普通人從青春到步入社會的快樂、失意、黯淡、無奈到接受的過程一一展現,頗有早期VHS時期的家庭錄影帶風格,影像粗糙對話細碎,配上導演標誌的台語口白。一開始是因為考上藝術大學練習拍紀錄片,想從身邊熟悉的人開始拍起,後來因為其中一位同學意外離世便決定認真整理剪輯成一部片以此紀念彼此的青春。
由於年代較早,可以通過這個片子看到很多過去我們參與或者沒參與過的細枝末節,都成為了這個片子有趣的看點:在那個年代裡,最新的相機像素是300萬(現在手機像素最高到4000萬),泡沫紅茶店是青少年最愛喇賽的地方,騎機車不戴安全帽還是很普遍。導演提到原本拍了八位同學因為不同的原因最後集中紀錄其中四位,有的可能是因為太成功而不適合他想拍的那種「掉漆」的人生的主軸。
整部片是一種荒謬的、嬉鬧的節奏在紀錄著同學之間互相聚在一起抽煙、打牌、喇賽、當兵被兵變出來買鞋還撲空、同學自殺沒成功卻因為其中荒謬的細節最後卻成為了「笑話」,而後從青蔥無煩惱的歲月慢慢轉化成各自步入社會的憂愁:為了房子、錢、工作、欠債種種現實的問題,滿滿消磨了許多的年少那樣的光彩,雖戲謔但溫柔,那樣淡淡的憂傷貫穿著片子,沒有特意營造的情緒化,但卻因為它的真實、欲言又止、點到為止而耐人尋味,從頭到尾是平平的敘事,加上導演招牌的黑色幽默的旁白,平淡甚至幽默的方式敘「憂愁」反而更讓人心有戚戚焉,導演曾提過自己不愛讀書,也不會深奧的寓言,喜歡直白的、貼近生活的語言(下圖),我認為就是因為這樣的敘事使其的電影常常會被認為「淡淡的憂傷,後勁十足」「有種難以言喻卻又有什麼滿到溢出的感受」「道出中年的無奈」。
我個人認為這樣的方式是很「高級的」(雖然覺得這個詞也不恰當但是也找不到更恰當的詞),我一直認為如果我有天想要說故事,不管事拍片或是創作,我想要達到的敘事的境界就是這樣的,越重的故事越要要輕的、淺白的語言敘述,更打動人。不是說悲傷的事情就一定要被攝者嚎啕大哭更有力,而那種無聲的沈默、不語、呆滯,反而傳達了更多無以言喻的感情。
真實的人生已經夠荒謬、夠戲劇,夠美麗、夠悲傷
看完這部片有種莫名其妙的感受:就是感覺挺白目的,但是真的很好看,而且很觸動(不是感動)。這讓我感到很有趣,一個這麼「粗糙、細碎」的紀錄片,何以讓人覺得好看?又什麼是個好看的紀錄片?怎麼樣可以讓觀眾沒經歷的故事卻能觸動觀眾?
我想就是它足夠粗糙、真實、純粹,「真實」聽起來好像很普通,但其實真的很珍貴,真實誠實的創作者、真實的創作並不常見:那晃動的鏡頭(我猜想那時候的攝影機沒有防抖功能,現在連手機的防抖功能都是基礎的功能),大概是360p的畫質(這幾年很流行低畫素VHS的畫質,復古成為了一種風尚),未經思考的鏡頭(拍褲襠那裡印象深刻),無意義的對白、復古的細枝末節(泡沫紅茶、不戴安全帽),因為朋友之間彼此很熟幹話、髒話一堆,因為不了解紀錄片所以拍起來無所顧忌(其實是另一種境界),創作往往會顧及很多,顧及越多越不純粹,往往在什麼都不懂的時候可能反而更容易。
細碎的日常片段,好像都似曾相識,但是又不太相識,明明我沒有過這樣白爛、瀟灑、不守規矩的青春,沒有這樣的同學,但是好像跟著片子也認識了這些人,也經歷了這些事,也共情了一些感受,留下了一個淡淡長長的憂傷。作為觀眾也順便一窺「那個年代」的年輕人的生活和煩惱,同時又覺得好像每個年代的年輕人都差不太多。《唬爛三小》的評價普遍很高,大家都不約而同的覺得很受觸動,可能使其想起逝去的青春,步入社會的無奈,人事萬物變化的無常。影評提到覺得導演是用腦內記憶在剪輯這部片,可能很符合我們想起一些人的時候的碎片記憶,也許我們記得的都是細枝末節?所以看起來格外有趣。
再來看《同學麥娜絲》很難不被表演的痕跡所影響,發覺自從我開始看越來越多紀錄片,再看回劇情片的時候就很難不注意到「演戲」的痕跡這件事,看劇情片越來越艱難,片子也越來越挑。而紀錄片有時候看著看著都會懷疑「這真的是真的嗎?」荒謬到無法相信的事實,有趣的是,真實的人像在演戲,演戲的人在想演真實。
後來也明白紀錄片的的魅力所在,誠如以前在看脫口秀的時候,也發現那些講生活中真實發生的故事的段子(通常都是因為善於觀察生活細節)通常比硬編的段子更好笑,寫實生活本身就已經夠荒謬、夠戲劇。 我想看過足夠多新聞事件、深度調查案件,也會有同樣的感受,編劇是來源於生活,但真實發生的事情很多時候連編都編不出來,想都想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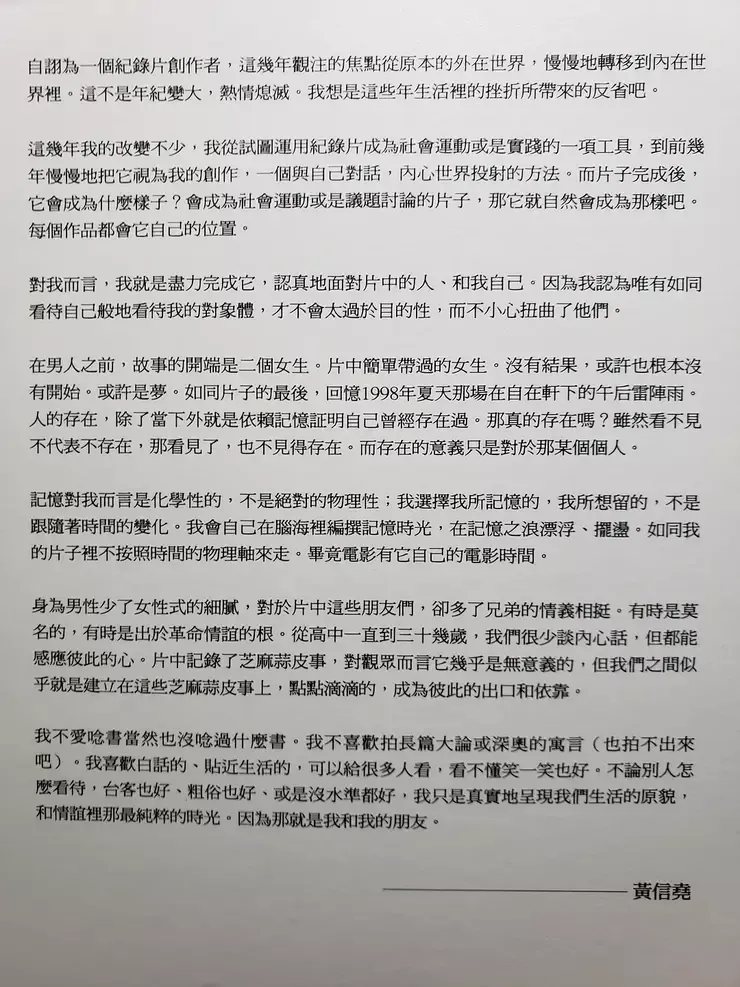
2005年再回頭看這一場雨,
卻發現時光像雨水般流逝,
而記憶卻也擋不住滿天的雨點。
——《唬爛三小》結尾
職業倫理不是人人都有,就像同理心一樣
這部片在當年公映之後獲得了一些認可,導演坦言這部片因為是紀錄身邊的人的「不堪」而造就的精彩,讓他心裡很過意不去,所以很少公映這部片,在拍攝倫理的問題上,不同於曾經要他「拍攝時要一直挖到對方痛哭流涕最好的」前輩的「教導」,導演選擇的是將心比心,在片中對處境低落的朋友選擇了點到為止的敘述:「如果是我,我都不願意說為什麼要別人說?」,如果對方不願意再說不會再挖。導演說從這部片以後,再也沒有拍過以人物為主的紀錄片,因為儘管在紀錄片裡他盡可能的中性化角色的一些缺陷,但仍然無法避免觀眾對他的同學批判。
提到這裡時我想到曾經也有一名導師跟我們說過類似的話,如果要採訪一定要「一直問到想問的,一直挖」不得不說,我看到的很多的採訪者也是這樣的屬性,可能對罪犯是有用的,對那些惡劣屬性的當事人,為了逼供一些證據出來,或者調查刑事案件,當事人做偽證、路人有重要線索但怕惹事不敢說實話,逼到對方不舒服,是合情合理,但是當我們遇到一個創傷者、要說出自己不堪回首的過的時候、不管是什麼原因要說出自己不喜歡提的往事的時候,我是不知道為什麼憑什麼這個人一定要為了成全採訪者個人的成功甚至是一片精彩的報導而犧牲掉自己的「不舒服」和沈默的權利?我想那個導師不在意,很多人不在意,因為他們只在意自己的文章、自己的名聲,採訪完了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對他們來說,扒了受訪者的創傷讓他們PTSD多少年跟他們沒有關係。這時候就會有職業倫理課,但是倫理如何教?教了就可以讓原本會這麼做的人不這麼做嗎?也許有一點點用吧,但我覺得倫理這種東西是在長久的文化裡、教育裡、社會的觀念裡,就像同理心是需要培養的一樣。
社會上的人文關懷也是需要培植發展,所以當導演說他覺得他的片子(《同學麥娜絲》)沒什麼意義,我不太認同,它無形中讓更多人種下了一些會關注一些平常不會特別注意的人、角落的小種子,甚至只是身邊的人。這個社會真的需要更多這樣人文關懷的影片。
「拍片不要去想形式,會侷限住,形式是拍完之後就自然產生的」
當年導演因為不了解紀錄片而無所顧忌,不知道當技術越來越純熟,或者知道越來越多理論的時候,會不會有更多的枷鎖反而很難拍出一種純粹?要隨時在意鏡頭晃不晃、收音有沒有弄好......好像在很多領域的創作者都會經歷這樣的過程,而後再追求一種當初那樣無所顧忌的狀態,然後就有人覺得是「藝術」,有人覺得在「亂搞」。
最近剛好翻到一個很多人都在推薦的一個YouTube頻道,一直讓我聯想到《唬爛三小》,叫Andy's iphone ,節奏和紀錄的方式都很像《唬爛三小》裡面那樣隨意隨手、分享有趣有時候是憂傷的故事,但都是源自身邊的人,它有別於很多台灣的youtuber拼了老命的追求特效、綜藝字體、奇怪的音效、浮誇的節奏和假嗨的主持人、千篇一律的風格和跟風,它這些通通都沒有,但有字幕,而且只是用iphone拍攝(iphone收音真的專業),就只是紀錄身邊玩獨立樂團的朋友發生的小故事,也可能只是一些小片段,沒什麼意義甚至有點莫名其妙但卻「很好看」,和看完《唬爛三小》有同樣的感覺。
從這次的座談和過去的訪談中,不難看出導演是有自己一套人生哲學觀:「電影不能改變社會」、「拍片不要去想形式,會侷限住,形式是拍完之後就自然產生的」、「人生沒什麼意義,拍片也沒有,(想拍再拍)也不一定要拍片,不拍片也不會怎樣」、「好好活著就好了」(人生就像洪流自有安排)、「人生就是有很多的錯過,很多的沒拍到,但拍不到不一定是壞事,有時候你拍到的很好的畫面用不上也沒有什麼用」、「沒有能力的時候不要設目標」(沒有能力沒有錢的時候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這種很道家的順其自然的無為思想看似很「喪」「負面」,卻也是一種佛系、禪意,其實也是一種極致的悲觀就成了樂觀,悲觀的樂觀主義者,在經歷很多無力無奈無以為繼發現既然生活這麼爛了,也不太改變的了什麼,那就要好好活著每一個當下。
這也是我翻滾了很多之後的想法, 可能就是源於看到了很多的不得不和被迫的無奈,漸漸覺得人如果能有自己的節奏,並能不會被外界的聲音干擾,能按照自己的節奏過人生,就也很足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