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若是一條河
自去年底開始在台北當上班族。在日常裡撿拾著晨間與睡前的小塊時間,嘗試把碩論重新編修成書。那些可以埋頭讀書的日子沒法回答的大哉問,如今還是依然卡住。
於是,想到或許可以重拾七日書那種「先不管了,有什麼思考的碎片都先寫下來」的動能,在小小塊的時間裡,記下一些什麼。
今日讀到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趙恩潔老師一篇有趣的文章<如果在台灣,一個穆斯林:文化作為意義之流>(收錄在2020年出版的《南方的社會,學:她者亦是共同體(上)》)。
其中她討論不同歷史時期遷移到台灣的穆斯林的文化認同和實踐,提出這樣一個關於「意義之流」的描述:
「翰納茲(Ulf Hannerz)卻認為最重要的就是社會分布。因此,他堅稱文化不是紀爾茲(Clifford Geertz)說的『意義之網』,而更像是一條河流,河裡的所有水流、生物鏈、流向、流量,隨時都會或大或小的改變,但長期來看,那仍是一條河流。重點是研究者如何在不同的定點上,去抓住這些河流的分支與主支之間的關係。」
趙恩潔認為「文化」應被看作是一種意義之流,不需要刻意追求一種僵固的文化大傘,而應將關注重點放在次文化社群。
「不只看宏觀結構,也注意個人的生命歷程。並加入『水循環』的譬喻,以理解河流生態的長時間變遷。」
.
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到最近在Threads上馬來西亞華人與台灣人的小論爭。
台灣人質疑,馬來西亞人喜歡稱自己是「華人」就是擁抱了中國和大中華主義;馬來西亞人則不解,為什麼台灣人不能承認自己是「華人」?
過去,我以為這種「不理解」只會在英文語境裡面發生。因為英文裡只有一個字Chinese,卻同時指涉了中華(更抽象的「文化」)、中國(國家與政治實體)、華裔(更類似一種血緣與民族)、華文(語言)等等非常不同的概念。
殊不知,過去中文語境沒發生,可能只是因為我們其實並不真正有過大型的相互遭逢的現場。到台灣或馬來西亞旅遊的人,大概也沒有太多機會跟路人就這樣的問題來好好吵一架。
若用趙恩潔或Ulf Hannerz理解文化的方式去閱讀這個網路小爭鬥,會發現是Threads讓原本分佈不同位置上的人,流到了一起,才形成這樣的漩渦。
.
我又自然而然地去想,那麼我是一滴怎樣的水?馬來西亞(華)人或馬來西亞作為一條「意義之河」的話,它是一條怎樣的河?我們如何抓住分支與主支之間的關係?
馬來西亞華人如何可以不只是相對於中國的「文化失傳」抑或「重新擁抱」,而可以有一種不同的理解?(在習近平最近剛剛訪馬,這種發問突然變得好像挺有深意!)
在一種相對於強權國家的邊陲,而也是同時更久遠的洋流必經的地理坐標上,我們如何在大量大量的遭逢與混雜裡,或許早已長出一種自己尚且沒有語言精準描述的樣子?
我說著自己母語的時候,中國人、台灣人、任何人都似乎還是可以理所當然地說,我有口音;做新聞的時候,工作場域各個國家的英文母語者,都可以不假思索地說,我有口音。
無論如何,我都不是任何文化、語言、認同的正典。
但我卻發現,我或許其實蠻喜歡一種能隨著環境與遭逢,持續改變形態的狀態,而存在本身即是否定定性、否定正統、否定清澈純淨的樣子,卻毫不意圖成為一種新的正典。
沒有什麼別人期待的文化本質的狀態本身,可不可以也是一種本質?
(我對自己的狀態找不到更貼近真實的描述)
.
現時當下,當在中國人正在潤、重新進入逃散狀態(我爺爺是歷史裡逃散的一個水分子),所謂的「華人」又正在從新的移動與相遇裡長出了什麼不同的樣子,整條大河又再經歷怎樣的變化?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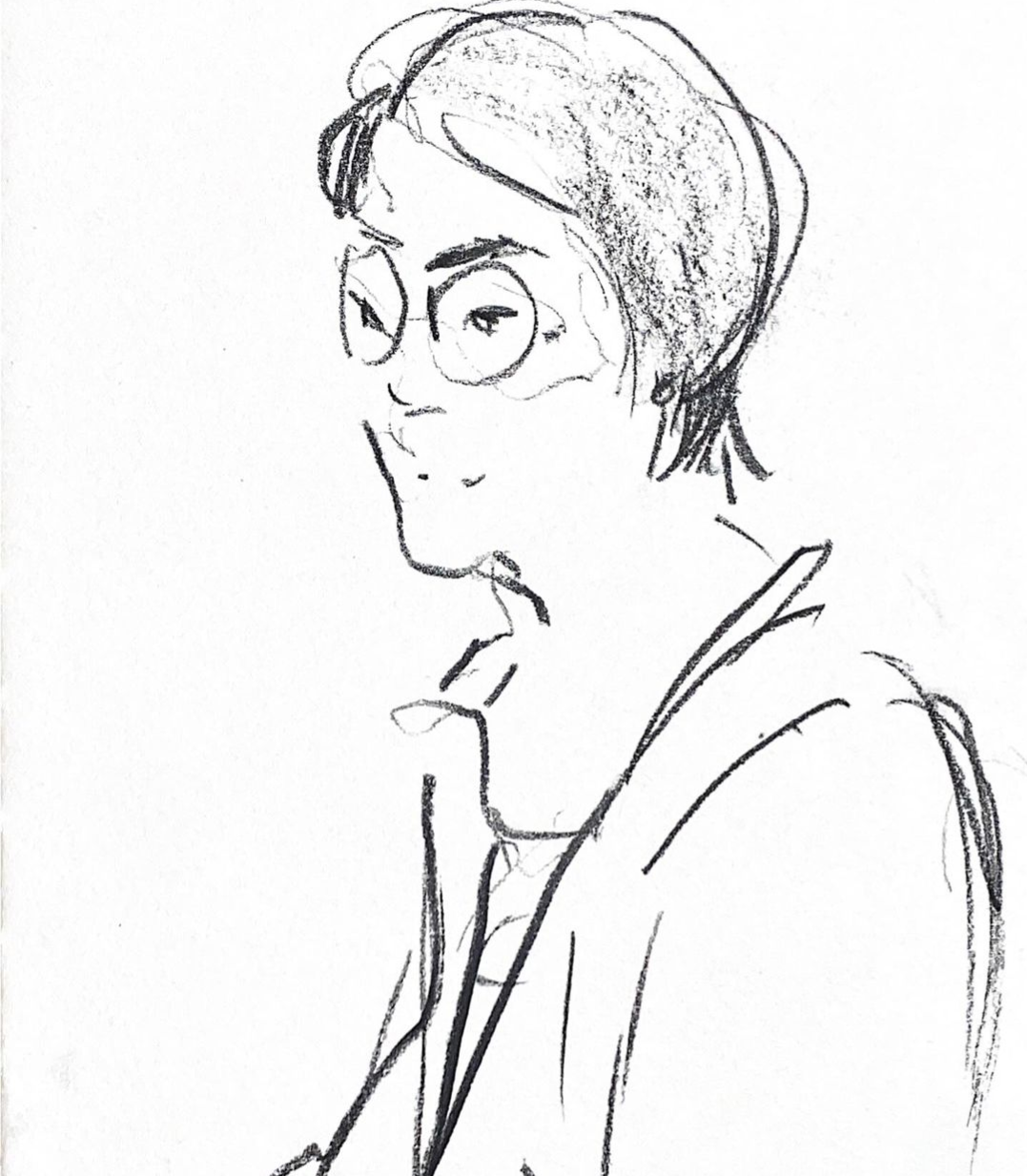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