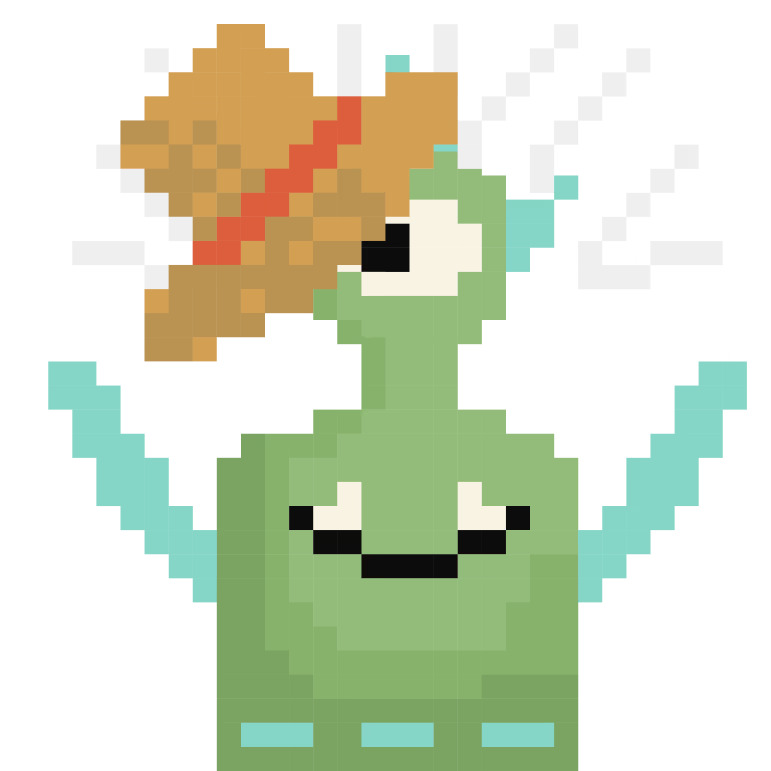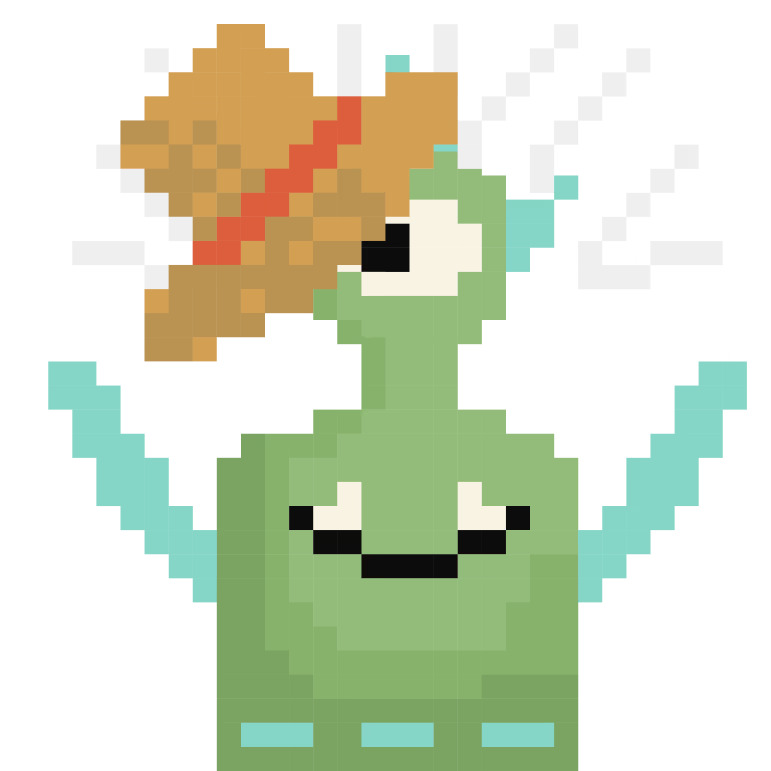一个潮汕女孩,决心飞往自己的山
本文首发于【青年志】

00 不得不写的冲动
我的出生是不受欢迎的。
妈妈离婚后,才发现自己怀孕。当时娘家人都劝她打掉孩子,但她向来容易心软,终究还是不舍得。在我出生前,听说生父在斗殴中丧生了。
几年后,在媒人的介绍下,妈妈认识了一个同样带着孩子的男人。这个人成了我的继父。
上学前班时,我跟堂姐在家门口玩耍,她笑着说“你不是你爸生的”。我没多想就怼了回去,“你才不是你爸生的!”后来我才知道堂姐说的是实话。
小学四年级,妈妈跟继父爆发争吵,我从妈妈口中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没有任何哭闹,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只在继父下班回家后,心里冒出一句话,“他不是我的爸爸”。
日子还是像从前那样流逝,没有分别。
大学暑假回家,妈妈常常要我陪她去湿地公园散步。有天傍晚,我们走在木板桥上,聊到她的婚姻。我说,“重新组建家庭,对我来说是好事,但对你来说不是”。
作为一个父亲,他实打实地支持我上大学,一定程度上帮我摆脱厂妹的命运。但作为一个丈夫,他屡次家暴妻子,给她带来数不尽的痛苦。
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关于女性命运,关于出走,关于人的灰度。如果一个女性努力飞往自己的山,但没有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那这个故事还值得书写吗?我不知道。只是它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了3年,让我流泪,让我失眠,让我不得不写下来。
写自己的故事是最困难的,我总担心自己不够客观,被个人情绪干扰。时常要跳出来,站在其他人的视角观察。跟家人关系缓和的时候,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过分了,为什么要外扬家丑?气得想拉黑他们的时候,我又想“哼!你们根本不值得我给予那么多理解!”情绪反复变动,找不到坚定的叙述角度。
文章初稿写于2023年9月,写作期间,我哭过好几回。但今年再拿出来,自己改稿的时候,我已经平静下来了。现在我能够坦然接受每个人的局限性,包括我自己,同时也不遮掩真实发生过的伤害。
01 工厂、童婚、留学
小学三年级,妈妈开始要求我去工厂干活。按照她的说法是,“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赚点钱”。
我生活在一个以电子垃圾闻名的乡镇,塑料工厂遍布在各个村落。工厂老板不知道从哪里,用三轮货车运来以吨为单位的塑料。通过碾切、沉淀、过滤、分拣等流程进行处理,再卖出去,赚取中间差价。
从那时开始,我的生活被分成两半。周一到周五,我在村里唯一的小学读书。周末和寒暑假,我就在工厂分拣塑料。
工厂是一个由铁棚搭建出来的空间,大概能容纳二三十个人。铁棚顶部悬挂着三只大风扇,摇摇晃晃地旋转,试图驱散夏日的燥热和困倦。
我的工作就是按照颜色、韧度等特征,给塑料分类。拿到一块塑料后,要先观察它的外观,有的一眼就能看出类别。要是分辨不出来,再试着掰折塑料,感受它的韧度,结合断裂口的颜色、透明度,基本能做出判断。
这些是常用的方法,足够应对日常情况。如果还不管用,就只能拿打火机点燃塑料,观察火焰颜色、嗅嗅气味。
工厂靠近田野,分拣塑料时,常常会遇到蜈蚣、蚯蚓、蟑螂等生物。我曾经在一个下午,遇到六十多只小蜈蚣。它们在我的脚下四处乱窜,我怎么都踩不完,吓得差点哭出来。
傍晚下班回家后,我疲惫地瘫在地板上,梦见大蜈蚣追着我跑。惊醒后,睁开眼,距离不到10厘米的地方,有只小蜈蚣在缓慢爬行。我累得不想起身,只是平静地抬起旁边的塑料凳子,用椅腿轻轻压住它。
工人里有像我这样一边读书一边打工的,也有早早辍学出来谋生计的。高声聊天的大多是男生,他们热衷于谈论酗酒、斗殴和黄色笑话。
我也跟某个男生打过架,在他主动挑衅,扇了我两个耳光后。我怒不可遏,紧紧追赶了他几个来回。如果他以为我是软柿子,那么他完全错了。最后他实在怕了我,被迫站在原地不动挨打。我也扇了他一耳光,但力度出乎意料地轻,怎么会这样?其实我不习惯使用暴力,只是想出一口气。
几乎同时,妹妹就带着爸爸过来了,准备给我撑腰。“没事,我已经打回去了”说完,我又转向那个男生,“你走吧”。
大多数工厂都以家庭作坊的形式运作,家庭成员是工厂的基础劳动力,再辅助雇佣村民。为了降低人力成本,老板偏爱雇佣童工。
那是2009年前后,我一天工作八小时,工资只有15元。之后的五六年里,工资缓慢上涨,但始终不超过30元。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学校和塑料厂之间徘徊。而堂姐们则在小学毕业后,选择了内衣厂。她们开20分钟的电动车,去隔壁乡镇打工。
那里被称为“中国内衣名镇”,有完整的内衣生产链。一捆捆不起眼的布料,经过女工的手,变成花式精美的内衣,销往全球各地。

堂姐们早早辍学进入社会,社会时钟也因此加快。她们在外认识了心仪的男孩,十六七岁的年纪就结婚生子。
童婚,在乡村里并不少见。
2020年,“广东一18岁高中生迎娶14岁初中生”事件冲上热搜。视频画面中,两人在红方桌前吃饭,红烛摇曳着明亮的火焰。在新闻报道中,事件以“政府部门已对双方家长进行法制教育,责令女方回归家庭”告终。
但事实并非如此。男孩是我们村的,听妈妈说,后来女孩还是嫁过来了。“生米煮成熟饭,还能怎么样?”女孩已经怀孕了。
与辍学、童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的表姐们在985学校读书,甚至出国留学。毕业后,她们在医院、证券公司、翻译机构工作。表姐们普遍比我大十几岁,处在完全不同的人生阶段,因此我很少有机会能见到她们。
我只记得,舅舅在村里建了四层楼房,家里打扫得很干净,空气也异常清新。每次我跟着妈妈去做客,都要脱掉鞋子,光脚踩在地板上。
他们的冰箱里还放着清甜的芒果汁,妈妈从来不买,我以为那是很贵的饮料,长大后才知道一罐只要4块钱。我还眼馋表姐的白熊玩偶,上初中后,家里有了第一个玩偶,是在路上捡来的。
辍学、童婚、留学,从小我就生活在一个割裂的环境中。一道无形的选择题,悄悄地横亘在我的生命中,在懵懂无知的年纪。
从小妈妈就跟我说,“女孩子没必要读那么多书,关键是以后嫁个好老公。”按照她的规划,我应该在初中毕业后,找一份能糊口的工作。然后等待运气降临,有个经济优渥的男人看上我,自此我成为衣食无忧的家庭主妇。
“为什么不对男孩这么说?为什么不说男孩没必要读那么多书,关键是以后娶个好老婆?”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女性主义,只是凭着朴素的公平观,提出质疑。
你说女孩没必要读那么多书,我偏要。这很大程度是出于逆反心理。在此之前,我对读书毫无兴趣,有时还会背着父母,逃课跟朋友去疯玩。
误打误撞间,我在选项A画上勾。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02 在题海中盼望、挫败
上初中后,我开始花费大量时间在课业上。每天放学回家后,我就把书桌搬到天井,开始做作业。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我还要求自己复习当天的课堂笔记,预习第二天的课程内容。
随着科目增多,我学得越来越晚,有时甚至能学到晚上十一点。当我合上课本时,家人都已经进入梦乡,鼾声连连。我胆子小,一进入黑暗环境,就会忍不住想象各种牛鬼蛇神。但又不得不去卫生间洗漱,就会在心里默念些别的东西,转移注意力。
我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只能剔除吃饭、睡觉、学习之外的“非必要”。我频繁拒绝朋友的邀约,隔绝人际交往。这一度导致后来我想交朋友时,反而不知道该从何入手。
努力很快得到了回馈。我的成绩直线上升,从年级六十到三十、第十。初三的时候,我顺利进入学校里唯二的尖子班,一度考到年级第二,比第一名少三分。
发小在另一个尖子班,她听见同学议论我,“这个人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们是年级前三的常驻选手,没听过我这号人。
我的优绩主义开始外溢。那时我是历史课代表,需要帮老师收作业。有个男同学一直不交作业,我就去他的座位堵人,堵不到的时候,还跑到篮球场找他。
初中的男生最爱起哄,一边用暧昧的眼神看我们俩,一边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但即使这样,都没能阻止我。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时的自己有多么讨人厌。
我心心念念想去区一中,但是中考的时候,我发挥失常,跌出年级前十,只能靠着“指标生”的身份,去排名第二的公立高中。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很大的挫败。
为了摆脱耻辱,我只能逼迫自己更加努力。高一的期末考,我终于考了年级第一。但不管我考得多好,我永远觉得自己只是做了“鸡头”而已。时常忍不住想,我的成绩在一中会是什么水平呢?
缺乏参考系,我陷入了无限内卷。看到舍友挑灯学习,我会焦虑得睡不着觉,只能起身拿出课本,躲到厕所,小声背诵知识点。即便厕所的味道,让我感到不适。
早上六点,宿舍区会播放起床音乐,但我听到的次数越来越少。因为焦虑迫使我在五点半就起床,六点的时候,我已经到了教学楼。
我的时间观念逐渐扭曲,连洗头发、剪指甲都成了非必要。在学校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处于紧绷状态。一不小心在学习之外的事情,多花了点时间,我都会陷入无限自责、愧疚。仿佛是在佛像面前虔诚祈祷的信徒,生怕自己稍微有点分神,就会遭到报应。

暗恋的男生问我,“这样不会太辛苦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没法停下来,否则焦虑会像潮水一样淹没我。当然,他也不知道我的情感。在学校和自我的洗脑中,恋爱变成危险的罂粟,让我避之不及。
午后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光晕大到我看不清他的脸,但那一刻时间好像静止了。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心动的含义。这时,我的理性跳出来大喊,一见钟情是不可靠的!不要相信!
越压制弹簧,它弹开的力量越大,人也一样。临近高考,我开始毫无理由地厌倦学习,周末回到家里,我就沉迷追剧,不断拖延复习进度。
不管我再怎么掩饰,成绩总不会说谎。高考二模,我的排名跌到六十多。一个月前的一模,我还是年级第一,比第二名高出二十多分。
班主任吓了一跳,喊我去办公室谈话。他试图弄清发生了什么,但我只含糊地表示,会调整学习状态。我知道自己出了问题,但崩坏的弹簧怎么也回不到初始状态了。理所当然地,高考的时候,我没能考上表姐的985学校,去了一所双非一本。
我对那个男生的情感,意外地延续到了大学。我一直试图分析,他吸引我的原因,最后发现其实是——他做了我想做却不敢做的事。
我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高考上,生怕踏错一步,但他不是。他可以一边听课,一边玩手机,还能取得不错的成绩(虽然还差我一大截)。碰到感兴趣的事,他会毫不犹豫地尝试,例如参加飞行员招考。所以,与其说是喜欢他,不如说是我把理想的自我投射在他身上。通过靠近他,间接实现自己脱轨的愿望。
高三时,我曾经萌生演员梦,想考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这是我第一次发自内心,想做一件事,无关成绩名次,无关他人的认可。但当我向家人表达这个想法时,他们说“别异想天开了”“拿镜子照照自己吧”“我们一分钱都不会给你的”。
是的,我是个长相普通的女孩,丢在人群里不会被注意到。肢体也不协调,连广播体操都跳不好。可是,我想要一个训练的机会、一个检验自己的机会,即便最终结果是“你没有当演员的天分”,那我也认了。但是艺考培训费用动辄上万元,甚至更高,对我们家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成为演员,更不是体力劳动者出身的父母,能理解的职业选择。所以,我的梦也短暂地结束了。
03 日常的家暴
妈妈一直认为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提醒我趁年轻,好好把握机会。但事实上,婚姻从来没有给过她幸福,不管是世俗意义的生活无忧,还是精神上的陪伴,她都不曾拥有。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选择跟前夫分开,但是在第二次婚姻中,她遭遇了此前未曾经历过的家暴。我亲眼目睹过三次,或许我在寄宿学校念书的时候,她经历了更多。
上小学的时候,我看见继父把妈妈推倒在地上,骑坐在她身上,用拖鞋接连不断地扇耳光。妈妈动弹不得,发出痛苦的哭声。
事后,妈妈责怪我,为什么站在一旁什么都没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辩解。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明白,是无形的恐惧将我钉在原地,剥夺了我的行动能力。
有天晚上,我在睡梦中被哭声惊醒。跑出房间,看见妈妈被禁锢在沙发上,继父用衣架抽打她。来不及思考,我直接扑在妈妈身上,阻止他的殴打。“走开,走开!”男人怒吼了几声,我没有挪开身体,他气得踹了一脚沙发,扬长而去。
上初中后,邻居违建设施,占用了大片公共巷道,给我们的日常通行带来麻烦。妈妈想让继父去跟邻居交涉。但他只是沉默地扒着碗里的饭,没有任何回应,于是妈妈一个人去了邻居家。
回家之后,妈妈指责继父窝囊。他一怒之下,开始追打妈妈,从厨房打到客厅。妈妈手中的饭碗也在躲避中摔碎了,饭菜洒落在地面。
躲进房间后,妈妈偷偷拨打了110。没多久,一群警察来到家里。但他们并没有像妈妈希望的那样,逮捕男人。相反,在男人的安抚下,他们围坐在客厅喝茶。最后留下一句“清官难断家务事”就离开了。
妈妈绝望了,她不知道还要经历多少次殴打,不知道还有谁能帮自己。于是,她拿起一条蓝色的跳绳,悬挂在房梁,然后站上红色的塑料凳子,试图自杀。不过她没有成功,被嫂子劝了下来。后来嫂子在转述事情时,发出轻笑,笑话婆婆果然还是怕死。
在我生活的乡镇里,根本没有家暴这个词,人们普遍觉得打老婆是正常的。丈夫殴打妻子,不仅发生在我们家,还发生在邻居家、叔叔家、舅舅家……
前年春节,我们像往常那样在家里的饭桌聊天。我和妹妹一起告诉继父,家暴是错的,不允许他再打妈妈。“可是她骂我,不能打吗?”“不能!你可以骂回去”“……好吧”。
不知怎么的,又说到养老问题,他说“我只能依靠你哥了......他和你们终究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我不服气地问道,他没说话,于是我替他回答了,“是因为没有屌吗?”继父震惊地看着我,露出尴尬的笑,显然没料到我会说出如此直白的话。
小时候,妈妈曾经想过送我去练武术,这样以后我就不会被丈夫欺负。但是如果男人都这么坏,为什么还一定要跟他们结婚呢?面对不堪的生活,村庄里的女人只会默默忍受,从没想过直接掀桌,不玩婚恋游戏。
大学毕业后,妈妈时不时会发多条长语音,催促我找对象。甚至不经同意,就把我的照片发给媒人,推送我的微信给陌生男人。
我不堪其扰,反问“你也结过婚,你觉得自己的婚姻幸福吗?”我知道这是在戳她的痛处,但如果不这么说,她还会继续打着为我好的旗号,推我进入婚育轨道。
“我遇到的男人不好,不代表所有男人都不好,还是有好的”妈妈还试图劝说我。
“你遇到坏男人,不是因为你运气差。恰恰相反,遇到好男人,才需要运气。你不能逼我去赌博!”听完我的话,她一时语塞,发了一个捂脸哭的表情包。
事实上,家暴的阴影,从来没有离我远去。在跟前男友恋爱期间,我们发生过争吵,看起来他好像要被怒火吞噬了。“我现在不敢离你太近,怕控制不住自己”,这是他的原话。后来,我假装语气平淡地问他,“你会打我吗?”他笑了,估计以为我在开玩笑,但——我不是。
我见过男人最凶狠可怕的模样,对婚姻早就没了滤镜。而且我好不容易才离开那个闭塞落后的地方,绝不可能再走回头路。
04 去广阔的世界
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没有延续理科生的路子。我打心底里觉得,自己做不了科研。我曾经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后来才明白其实是骨子里的自卑在作祟。即使在裸考的情况下,获得广东省生物竞赛三等奖,我依旧无法认可自己。
我选择了新闻传播,正如大多数学生调侃的那样,“没有一本《看见》是无辜的”。我对调查记者满怀敬佩,憧憬着自己也能深入新闻一线,揭开被遮蔽的真相。
不过后来我走向了非虚构写作,这是我理解自己的一把钥匙。我写的第一篇深度报道是《十六岁的“自由”婚姻》,写一对姐妹怎么走上童婚的路,分析背后的家庭和社会原因,以及童婚给她们带来的影响。其实她们就是我的堂姐。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怎么在岔路口失散,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自从上高中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络。为了写这篇文章,大三的时候,我重新回到家乡,采访她们。那时,她们已经有了两三个孩子,肩上扛着不小的经济压力。一边跟我聊天,一边脚踩缝纫机,争分夺秒地干活。说话声和机器的“哒哒”声交织在一起。
我意识到,相比堂姐们,我算是幸运的。虽然生活在重组家庭,但至少爸爸没有苛待我。小时候半夜发烧,也是他背着我去诊所。赤脚医生打针特别疼,我趴在他的怀里,忍不住张口咬了他的手臂。但他什么都没说,没有因疼痛而喊叫,也没有斥责我。
堂姐们接连辍学后,他说,只要我想继续读书,他就会支持我。从血缘来讲,我跟他的关系是最疏离的,但我却是家里唯一有大学文凭的人。
虽然妈妈口头上不支持我读书,但是每次学校有活动邀请家长参加,都是她出席。高考录取成绩出来后,学校举办了小型的颁奖仪式,奖励所有考上一本的学生。
我在台上接过奖状的时候,看见她流泪了。下台后,我问她“你怎么哭了?” 她摇摇头说“没什么”。
而堂姐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因为婶婶忍受不了家暴,选择离家出走。采访过程中,我问堂姐会不会想念妈妈,她反问道,“如果你妈抛弃你,你还会想她吗?”
压抑的家庭推着堂姐往外走。当有男人展露体贴和爱意时,她们迅速沦陷,“喜欢一个人可以倾其所有”。《十六岁的“自由”婚姻》标题有两层含义:一是,婚姻是她们获取“自由”的方式;二是,指出这是在法律之外的“婚姻自由”。
她们的逃离,是从一个男人,走到另一个男人。而我,更相信自己。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林屿”,谐音“零屿”,意思是我不会寄希望于别人给我一个家,他们也给不了,我就是自己的岛屿。
大四的时候,我拿到大厂的实习记者offer,去了从来不敢想的北京。从我们家到中关村,跨越了约2137公里。

在那里,我写了潮汕丁克、子宫腺肌症,试图展现生育文化的束缚,和女人们的抗争。主管在选题会上说,“有些老师总是写女性议题......”他看向了我,“可以适当写些别的,毕竟我们不是一个女性向账号”。
那时,我才后知后觉,原来自己一直在写女性议题。我想,这是根植在我的生命里的东西。在对女性主义一无所知的时候,我已经走上了这条路。我没法回避自己的生命经验去写作。
除了女性议题外,我还跟着编辑去到综艺录制现场,采访明星。第一次突破荧幕见到真人,我紧张得脑袋空白,磕磕巴巴地提问。不过,丢过一次脸后,再做艺人采访,心理状态就好多了。
在向外走的同时,我也在试着直面原生家庭,进行漫长的人生补课,努力弥合两种生活的沟壑。
大学的时候,我买过一个黑色双肩小背包,室友说这好像是某某品牌,我完全没听说过,只是觉得好看就买了。背包是在街边店铺买的,只花了二三十块钱,无疑是冒牌货。当时我羞愧不已,甚至想扯掉背包的logo。最后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品牌说到底是人为建构的体系,我也不一定要遵守那套体系。
朋友约我去按摩,我以“不感兴趣”为由拒绝。其实不是不感兴趣,而是在我的消费观里,按摩似乎是奢侈的。我能想象,躺在按摩床上,我获得的不是舒适,而是局促。
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有跟朋友聊过自己的原生家庭,担心他们会用怜悯的眼光看待我,直到一次偶然的聊天。
当时前男友在追求我,我们无意中聊到原生家庭话题。一般情况下,我会假装自己生活在正常的家庭,但那时我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他知难而退。这是我第一次暴露自己的家庭一角,但他表现得很平淡,也可能是手机屏幕阻隔了他的情绪。
不管怎么样,我开始觉得也许我的家庭没有那么不体面,长久以来的自卑得到一些缓解。我慢慢去直面自己的生活,也会主动预约学校的心理咨询,倾诉自己的困扰。
有些人排斥长大,因为长大意味着承担责任。可是,我太喜欢长大了。这意味着,我可以随心所欲买冰淇凌和玩偶,可以去别的城市,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大学毕业后,我在北京的自媒体工作过一段时间。碰巧在社群里看到一篇推文,有个女性行动小组在招募新一期的话剧演员,那是一部女性题材的话剧,叫做《阴道之道》,关注月经、妇产科疾病、性暴力等议题。
我立马提交报名表,进入试戏环节。第一次演戏,我选择了一个跟自己心理状态相近的角色——一个被导师性侵的女生。那时,我正在职场遭遇PUA。虽然这是不同的事件,但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权力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欺凌。
试戏的时候,每个人轮流表演片段,然后由其她人投票。同剧组演员说,她看到我突然摔倒在地上,蜷缩身体的时候,吓了一跳,心想“(这个角色)就是你了”。
经过三个多月的排练,秋天的时候,我们在北京的剧场演出了四场。没记错的话,话剧票是80元,每场开放60个座位。演出结束后,有女观众说“你好像房思琪......”听到这个反馈,我终于可以跟17岁的自己说,“你没有异想天开”。
读书的时候,我的英语成绩一直都不错,但同时我也有隐隐的困惑:学英语有什么用呢?我又不可能去国外。小镇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但现在我想的是,为什么不可能呢?说不定等到三十岁的时候,我会在欧洲呢? “去广阔的世界,见识更多有趣的人和事”这是我在23岁许下的生日愿望,也是我未来的人生愿望。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