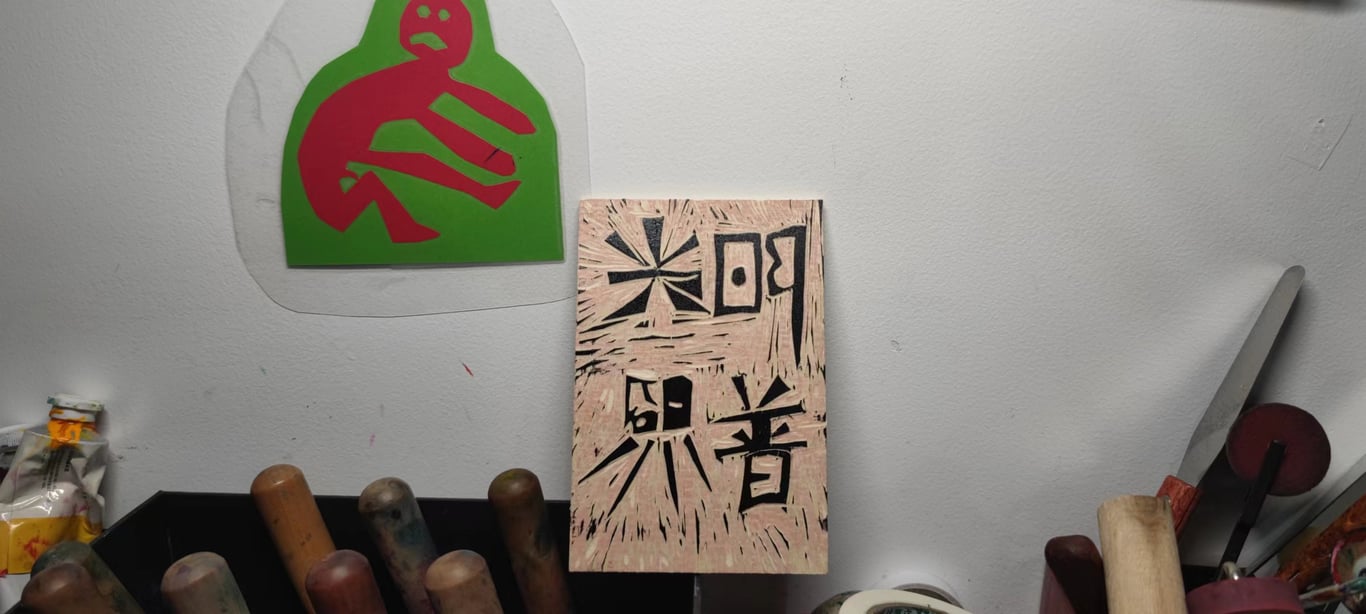盛最多水的容器

那就是一个没有春天的城市,三月就满是暑气,每日百分之七八十的降雨概率。说来,前一年的三四月我也在那里,那年雨水好像更多,困了我更久,雨热同期,来来去去倒也没长记性。
那几个月,一日日装做忙碌,实际只是重复,读书、写作、吃饭睡觉,总是淋雨,却没能清清昏沉的脑袋。不情不愿地去面试,佯装得心应手,他们问我,你打算在广州待多久呢?要长待了。其实,我在那儿多待一天都挺疲累的,夜间燥热,白天烦闷,因这春夏不明,总是昼夜失神。
—— 南国潮湿的三月,是我记忆里最美的季节,某一天,满城的榕树一夜之间抖落一身黄叶,捂出新生的长长的根须,焕出碎碎的嫩芽,引得来往路人痴痴地望着那新绿发呆。你没法适应的回南天,是我不可剥离的记忆。三个月后,同样的潮热才轮得到上海。在上海的这些年,我总觉得梅雨季可亲近,近到重回故里。
你从上一个雨季来到这一个雨季,在这里,你又停留多久呢?感觉我们这些人,永远在研究别人怎么活,说到底还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怎么活。
总有些不明事理的期待,因为想要去感受一种强烈,才会把自己困在一个又一个雨季吧。挑了这个时节才回来,同样睡了雨,醒了也雨,但这个昏天黑地的六月,还是比广州舒服多了。
这家咖啡店以前有段时间我每天都会来坐坐,走过两个路口,裤脚湿着进店,干了再回去,透过雨水纵横的玻璃呆看着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行的,经理是怎么从新德里来上海的,店里晚7点之后打折的面包他们自己也会吃吗?他们也是在一刻不停地表演吗?
当然,这个地方离你那儿也近,想着你来也容易。诶,你怎么在这里还停了这么久呢?
——他那会儿刚从剑桥回国,他的同学也就是我的好朋友叫上我们一起喝咖啡,也就认识了。后面也就喝了几次咖啡,我们进入了一种亲密关系,也可能只是我这么默认了。我租住的地方那样小,想要待久一点就只能去他那里了,只是他从不许我留宿。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向家人出柜,谨慎的很,不想自己好好藏住的这部分被父母撞见。我们日常见面不过从一杯咖啡到另一杯咖啡,深烘浅烘各色风味都尝了个遍。
后来,在那栋他妈给他的大房子里,就算是脱光了,总觉得也是隔着好几层皮肤。不知道为什么,不可做的触摸比可以做的深入更诱人,我此前以为的试探,以为的有所克制,不过是不为所动,我们躺在一起,背着对方自慰。我不知道他接受我是有多少爱在,还是只想要人陪着。
在这里,至少有一部分的我可以不必藏的,在他那里整个我都被藏起来了。我们可以聊新展古籍、聊远方的非正义,但是我没法说自己藏在这个“租界”角落的生活,我总是晚上去挑街角档口的菜,给他带的手工司康不是什么有机品牌只是我自己做的,每份精致的生活都是我一点点计较出来的,可是对他来说是不必使这份力的。
我想,我的停留仅仅因为自己不必躲藏的那一部分吧,而他给的那一部分太容易化掉了。
诶,你怎么没能停久一点呢?
因为,他先走了吧。因为一时雨糊住了窗,一时满世界的水啊,我装不下。
看,外面这雨要是再大一点,就都走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