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到来
2024年国庆回到父母所工作的浙北县城。
还是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每年暑假来到这里度过一个又一个夏天。持续有15年之久。那大概是在2000年至2015年之间。
浙北的县城临近上海,印象中在2006年左右它的繁荣便超过了其它中西部的小城市,是一个文旅、经济都很发达的城市。
2024年,肉眼可见的水泥路面老化了,从城南到城北的距离也比小时候近很多。更直观的感受是人也少了,中学时代的夏天来到住所附近的篮球场,2024年国庆再来时显得更小、更旧、甚至衰败一些。
更多人在老去,这是最能感受到的地方。更多中老年人行走在街道上,她们银发铺满头顶、步履缓慢。
更多商场寂寥无人。曾经的那些商场总是人头攒动,热热闹闹的。现在的这些商场只剩下骑手穿梭其中、步履匆忙。
回到老家,视角转向曾经出生长大、充满许多眷恋和温柔的原乡之地。
曾经熟悉的奶奶、大妈、叔叔、大伯(村里对长辈的通称)等长辈都肉眼可见的老去。奶奶们脸上皮肤低垂、眼神黯淡、白发生长。
一代人正逐渐老去。
这个事实在我心中生根发芽。
更多的是失落。曾经童年的伙伴都已长大,早已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原来在我想要去更远的地方行走在路上,在我在城市为就业和工作而苦恼、为生活意义而冥思的同时,在另一个小小的地方正有人订婚、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开启了属于他的新的生活旅程。
这种失落还体现在空间上。这几天得知屋后的邻居们一家已移居县城,也只在每年元月——和其他外出务工的人们一样回来过年,又在正月元宵节前离开。原来他们也过上了这种两地生活的日子。
这种离开老家去县城、去南昌、去深圳、去广东的人们正形成一种趋势——一种早已被社会学领域称之为“城市化”的进程。只不过他们的住所离老家更近,我们更远。从时间上看,无论屋后的邻居还是外出务工的我们,我们更多的时间都在外地而不在家乡。家乡好像一个子宫,持续孕育男性女性们,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断有人离开(偶尔回来)。
说到底,我们都是“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
时隔两年没有回来,村里今年过年的感受向着两个极端发展。一面因为村里逢上20年一遇的“修谱”,请来戏班子的那晚同时燃放烟花和爆竹,其热闹和欢乐胜于以往许多个新年;一面是烟花升空璀璨过后,留下了寂静无声的黑夜——“修谱”第三日许多人便已离开,只剩下平日里白天冬日冷冷的光。第四、第五日村里便只剩漫长的寂静。这种事情的发展达到高潮便迅速结束的状态,让人怀疑像做了一个梦。按理想状态,我们都应好好庆祝这短暂相聚的时刻,我们不应急着相互告别彼此再去度过漫长的一年。
入夜睡前时,我在想故乡之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城市化之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城市化的进程中,氏族在式微、家族在衰弱,对我们的一生来说,幸福是什么?年轻一代伴随城市化进程的理念是为自己负责、创造财富过更好的生活,无力负担另一个生命时绝不轻易兑现,只有个体的幸福才是真的幸福。
长一辈的人继承着上一辈人的人生理念:一个人需要结婚成家,需要生儿育女,需要传宗接代,这种繁衍生息、不断发展的生活方式是为之秉持的。
这会是一种伴随失落而来的理想吗?
年复一年。冬天会过去,春天会再来。更多的人在老去,更少的人在年轻。
无论经济发达省份的县城还是经济不发达省份的乡村,失落的感受都伴随着我。潜意识中,我一直很喜欢并向往定居栖息在美丽的小地方,并形成一个亲密熟悉的人际关系。在河边、在湖畔、在乡镇。
但离开的人充满眷恋,而生活在家乡从未离开的人也伴随着失落。他知道我们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他知道更多的人在离开这里去远方定居,他知道大部分时间只有他的小家庭以及其他留在此地的亲人在。
失落是相互的。
故乡会有失落吗?
故乡的规模扩大了,故乡的基础设施更好了——有了水泥路、有了精致装修的楼房、有了自来水、有了更亮的路灯。蜿蜒过故乡的河流更安静、更清澈。
故乡会有失落吗?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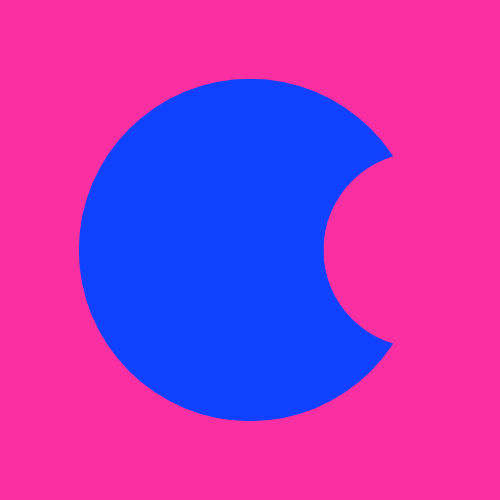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