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美中貿易戰,戰什麼?》美中供應鏈的合與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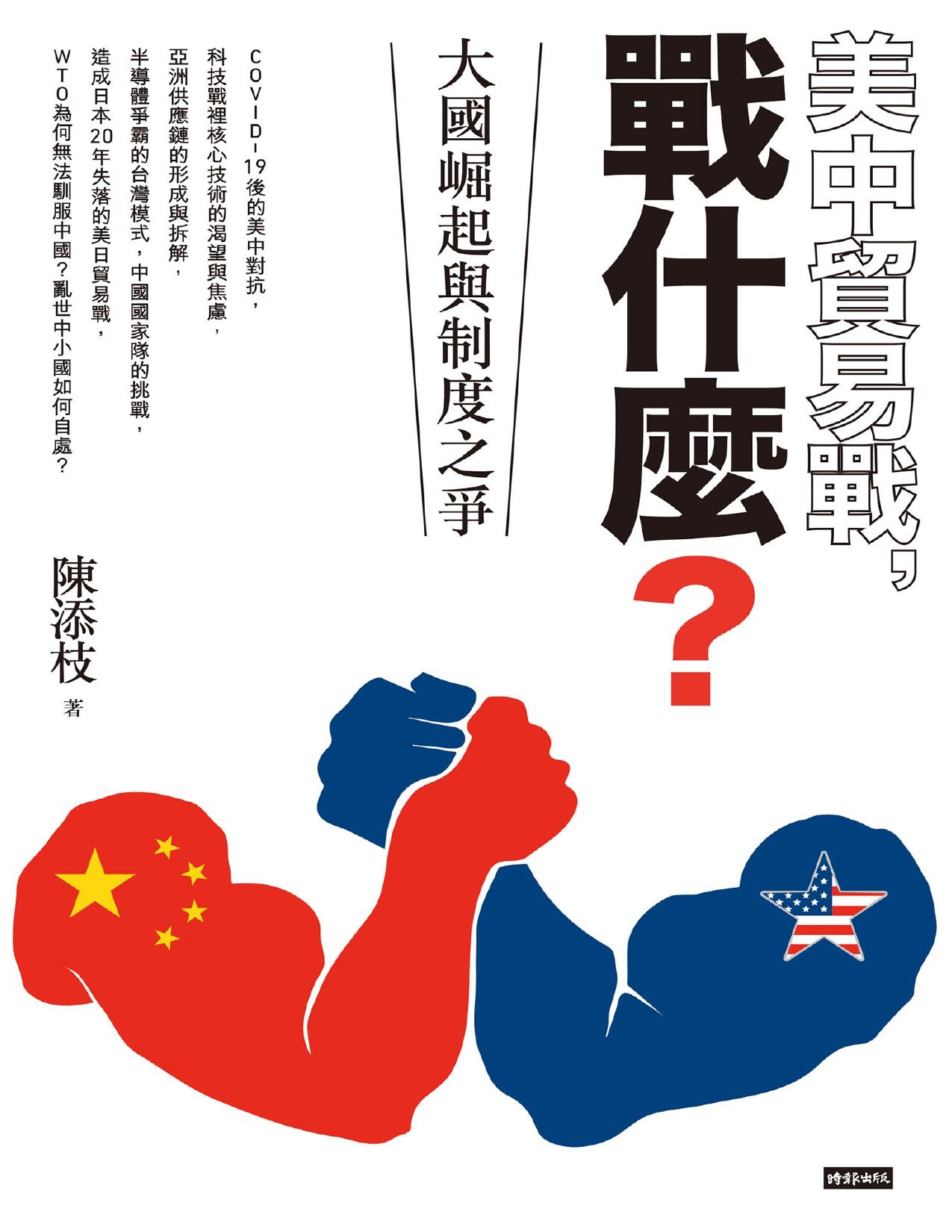
美中供應鏈的合與分
中國自一九七八年實施改革開放以來,逐漸融入全球生產分工的體系,成為全球供應鏈的一環。中國廣大的勞工和優越的投資環境,吸引西方的企業,紛紛在中國打造生產的基地,有的是自行投資建設工廠,有的是透過代工廠生產。經過四十年的累積投資,中國成為全球供應鏈最密集的地方,幾乎什麼產業中國都沒有缺席,而且上、中、下游的生產鏈段落都存在,甚至有些產業全部集中在中國生產,別無他處的替代基地。供應鏈的集中,使中國成為世界的工廠,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家。中國大量進口生產所需的原料和中間財,加工以後再出口,形成大進大出的貿易型態。
全球供應鏈的形成,本來是國際大廠運用國際資源,進行全球競爭的安排和布局的結果。有效率的供應鏈使國際大廠可以更快速、更大量、更便宜的提供產品給全世界的消費者。然而過度集中於中國的供應鏈,也造成西方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緊張。供應鏈的效率高,固然使企業競爭力提升,獲利增加,卻犧牲了國內就業的機會,深化了西方國家內部資本主和勞工間的矛盾,演變成棘手的政治問題,連帶使中國成為眾矢之的。另一方面,供應鏈也是生產利益分配的平臺,中國雖是全球供應鏈匯集之地,中國的企業和勞工,為多國籍公司提供各種資源、鞠躬盡瘁,但他們從供應鏈獲得的報酬卻少得可憐。中國政府意識到想要改變生產利益的分配,無法像過去一樣,進行無產階級革命,而是必須提升自己在全球供應鏈上的地位,於是有「中國製造二○二五」這類企圖打破現狀的宏大計畫。中西雙方都對全球供應鏈的現狀不滿,企圖加以改造,摩擦自所難免。
亞洲供應鏈的形成
美國的企業和它們的代工廠,是協助中國融入全球生產體系的要角,也是構建中國供應鏈的工程師,在過程中中國政府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他們只熱衷於招商、急著累積更多資本、推升生產的總量、提高GDP的數字,對於美國企業所擘畫的產業地圖甚少關注。如果說今天佈建在中國的生產鏈構成美國的威脅,不論是市場競爭的威脅或國家安全的威脅,只能說這都是美國企業自己造成的,自業自得,和中國政府無關。或許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當初和中國合,是為美國利益,現在要和中國分,是感覺威脅大於利益。
美國企業佈建全球的供應鏈別無其他目的,只為了市場競爭,而競爭大多來自國外的對手。我們就以海外布局最早、全球化生產程度最高的電子產業來加以說明。美國電子業的對外投資,從一九六○年代就開始,但積極的從事海外生產鏈的佈建則是從一九七○年代開始,而主要的推力是來自日本電子業的競爭壓力。從消費性電子產品如電視、音響、影印機、傳真機,到半導體的晶片、材料、生產設備,美國企業受到日本企業崛起的全面挑戰,只能以海外生產來降低成本,保住競爭的優勢。大型的企業偏好以直接投資、自行生產的方式來降低成本,小型企業沒有海外投資的能力,則以委託生產的方式直接自代工夥伴獲取低成本的產品。海外生產或海外取材(offshoresourcing)也受到政策的鼓勵。美國貿易法(TariffActof一九三○,八○六/八○七條)對於委託海外加工再進口的產品,只針對海外產生的附加價值課徵關稅,美國廠商提供的中間材料是免稅的,這項優惠稱為海外加工條款(offshoreassemblyprovision;OAP)。雖然大部分的OAP進口來自鄰國墨西哥,卻也鼓勵美國的半導體廠早早的把半導體封裝移轉到亞洲各地,如馬來西亞和臺灣。
一九八○年代中期是日本製造業的巔峰時期,日本各項產品的全球市占率節節上升,引發當時美國雷根政府的緊張,美國陸續與日本在鋼鐵、汽車、工具機、半導體等產業達成貿易協議,強迫日本採取出口自動設限(voluntaryexportrestraints)與擴大進口的措施,作為減緩美日貿易逆差的手段,和今天美國對付中國的手法如出一轍。最終使日本崛起的浪頭突然消沉的是一九八五年的「廣場協議(PlazaAccord)」,該協議引導日圓大幅升值,此後日本政府一連串錯誤的總體政策,使日本經濟陷入長期的衰退,再也無能力挑戰美國產業的龍頭地位。
政策的干預讓美國廠商獲得喘息的機會,但並無法自動恢復其競爭力,除非企業進行生產的變革。經歷一九八○年代的生死存亡之戰,美國電子業在一九九○年代以後逐漸復興,更藉著網際網路的興起,如浴火鳳凰,重新站上全球市場的領先地位,主要原因是美國電子業建立了一個舉世無敵的全球供應鏈。它們改變了過去的營運模式,不再拘泥國內生產,不再堅持自製關鍵零組件,它們透過對外投資、委託海外生產的安排,創造新的全球分工體系,不僅運用全球各地資源來降低成本,而且運用各地資源來創新。經過多年努力,美國終於在全球電子產業重新取得主導地位,反而把日本企業收服成抬轎的供應商。
今天我們看到的全球供應體系,並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有跡可循、逐步累積的,其中一九九○年以後到今天的變革最為劇烈。回顧美國電子產業開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至全球供應鏈體系的形成,大約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晚期,美國企業開始對外直接投資,以海外生產降低生產成本;第二階段是一九七○年代晚期至一九八○年代中期,美國企業逐漸深化與投資地(尤其是亞洲地區)的供應鏈關係,開始採購當地零組件;第三階段則是從一九八○年代中期至一九九○年代初期,美國企業的海外營運擴大到技術合作領域,海外生產漸漸被賦予供應全球市場的重責大任。此後,供應鏈的架構與分工逐漸優化,形成一個全球研發、採購與生產的完整體系,其中亞洲企業扮演關鍵角色一。
在第一階段,美國的代表性電子大廠,開始對外尋找合適的組裝生產基地,主要目的是降低生產成本。當時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亞洲國家,如臺灣、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憑藉著低廉的勞動成本,成為美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首選。例如最早來臺投資的通用儀器(GeneralInstrument)公司於一九六四年在高雄設立二極體的生產基地,RCA於一九六九年在桃園設立電視機零件的生產基地。這一階段的海外取材(offshoresourcing)以直接投資為主要型態,技術來自美商,生產管理也是由母公司派員負責,零組件由美國供應,在本地採購的比率很低。
在第二階段以後,除了母公司直接投資以外,委託生產變成另一種型態,這是因為亞洲本土廠商的技術能力提升了。雖然在生產過程中一般仍有客戶的技術支援和監督,代工廠已經可以自行管理和設計生產的流程。代工廠由最末端的組裝工作開始,慢慢向上延伸至中間財與零組件的生產,開始學習更複雜的技術、生產更高階的產品,包括電子設備所用的零組件、螢幕、電源供應系統等。同時由於產品規格的統一及模組化技術的發展,代工廠透過替不同客戶代工製造,合併起來,可以達到規模經濟的效果。這種發展讓小型的品牌企業,也可在亞洲找到代工夥伴,不需進行直接投資。
委託生產的逐步擴大,創造出一種垂直切割、高度專業分工的全球生產樣態。美國廠商只專注於產品設計,和關鍵零組件的製造,其他的生產工作都由亞洲廠商代勞。這種分工型態使美國廠商的投資規模變小、投資效率提高,承受市場波動的風險減少,因為它們不需投資和維持下游的產能,卻可以隨時取用這些產能,取用時甚至還有多個工廠可以選擇。美國的電視機、計算機、個人電腦及其附件等都在這段間紛紛走上委託海外生產的道路。
到一九八○年代的中期,亞洲國家,如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等主要美商的海外生產基地,已經實現初步的工業化,而被稱為「新興工業化國家」(NewlyIndustrialEconomies)。他們正積極擴大國內的基礎建設、充實教育體制、提升勞動力品質,同時提供財政與租稅誘因,促使美國企業擴大投資,並設定國內產業升級的目標。有些國家的企業更把握與美國企業技術合作的機會,除代工生產之外,並致力於零部件及其周邊產品的設計與生產,於一九九○年代開始迅速擴大該類產品的全球市占率。例如臺灣廠商藉著代工生產個人電腦的機會,自力開發出主機板、滑鼠、掃描器、螢幕、鍵盤等產品獨立在市場上進行銷售,獲得很好的成績。
到一九九○年代,可說是全球生產供應體系成熟的時期。由於亞洲製造能力的躍升,美國企業開始專注於新世代產品的創造與設計,及其所需技術與軟體的開發,其他工作都委諸亞洲企業,甚至連關鍵零組件都放棄自行開發生產。例如個人電腦的廠商,連主機板也開始委外設計及生產。另一方面則賦予其亞洲的供應鏈伙伴更深一層的任務,除代工外增加了部分產品設計的任務,同時肩負協調全球市場產品供應與生產的責任。例如蘋果電腦於一九八一年在新加坡成立蘋果電腦新加坡分公司(AppleComputerSingapore,ACS),並設立產品組裝線;一九八九年,ACS獲得美國母公司的授權,負責設計與生產蘋果電腦的部分零組件;一九九○年開始,ACS獲得指定負責幾款蘋果麥金塔(Macintosh)電腦的設計、生產與全球銷售任務。除微處理器仍由美國製造提供之外,其他包含外觀設計至零組件製造與最終產品的組裝等,皆於亞洲完成。
其他美國企業在亞洲建立的生產與銷售體系也與蘋果的運作模式相當類似,包括康柏電腦、惠普、摩托羅拉、AT&T、IBM、希捷(Seagate)、威騰電子(WesternDigital)、德州儀器、英特爾等。隨著這些美國電子大廠陸續在亞洲建立生產基地和生產網路,獲得生產訂單的代工廠如臺灣的華碩、宏碁、廣達、仁寶等也因此獲得快速成長的機會。
中國加入供應鏈
經過一九七○年代和一九八○年代和日本企業的激烈廝殺,美國電子業陣亡了一半,但另一半卻更加茁壯。陣亡的一半是消費電子,包括電視機、冰箱、音響等,大半江山都被日本和後起的韓國企業搶走。越戰越勇的一半則是工業電子,包括電腦、半導體、通訊器材等。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日商和韓商呼應中國的「市場換技術」政策,早早就進入中國投資,但不出二十年光景,中國的國家隊透過快速的技術學習和國家政策的明幫暗助,就光復了電子消費的市場。在工業電子的領域,日商和韓商也採取類似的策略,目前在個人電腦和通訊器材(含手機)也遭逢相同的潰敗宿命,只有半導體的領域,市場和技術都還掌握在日韓廠商手上。半導體的市場和技術的特殊性,我們將另章論述。相對於日韓廠商,美商對於進出中國市場態度較為保守,他們大舉進入中國市場,是在中國加入WTO(二○○一年)以後,在此之前,美國對於來自中國的貨品在貿易上是否給予和他國平等的「最惠國待遇」,還須國會逐年批准。
美國品牌廠的製造因為已經全部委託亞洲的代工廠承攬,因此其進入中國,也是由代工廠代行。例如個人電腦,幾乎全部由臺灣的廠商代工,因此美商進入中國,等於是臺商的對中國投資。臺灣政府自一九九一年起,開放臺商赴中國投資,逐漸在中國建立綿密的電子產業供應鏈。但迄二○○○年止,筆記型個人電腦仍然禁止對中國投資。美國個人電腦的大廠和臺商聯手施加政治壓力,才迫使臺灣政府在二○○一年開放筆電對中國的投資。臺灣政府的政策易弦,反映的是美商的政策轉換。
在政府開放筆電赴中國投資後,臺商代工廠在中國建立大規模的生產基地,使電子產業供應鏈更為完整,中國提供的規模優勢和成本競爭力,使其他地區的電腦生產完全失去生存機會,臺灣筆電的生產線紛紛熄燈出場。美商利用這天下無敵的生產網路,很快把日本品牌逼出市場。在大投資伊始的二○○一年仍有NEC和東芝兩個日本品牌位居全球市場銷量的前五名,十年以後的二○一一年,已經沒有任何日本品牌名列前五名,今天NEC和東芝都已經完全淡出個人電腦的市場。美國品牌借臺灣代工廠之力,利用中國的豐富資源,徹底摧毀了日系對手。
由美國企業主導在中國建立的全球生產網路,實在太過強大,今天全世界的個人電腦幾乎都由中國出貨。這個網路不止納入美國和臺灣的供應商,而且納入亞洲其他國家的供應商,包含日本和韓國。日本的品牌廠被打敗了,日系的供應鏈就被收編了,日本擅長的機殼、硬碟、記憶體、化學材料等產能也變成這個生產體系的一環,畢竟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市場了。這個生產體系,如海納百川,而且不斷去蕪存菁,自然日益壯大。為什麼它有這麼大的包容力,因為這是一個模組化的開放架構(modulararchitecture),只要依循系統的原始設計架構,新的部件就可以融入系統中。個人電腦的開放架構,最早是由IBM設計的。
模組化的開放架構有強大的資源整合能力,降低了參與者加入的技術門檻,使分工變得容易,而且產品演化的速度更快。因為是開放系統,進入的門檻不高,而且整個系統在中國本土完整呈現,中國企業很快學會如何運用這個系統。他們憑藉著廣大的內需市場和政府的政策支持,找臺商代工生產,很快建立自有的品牌。中國的品牌聯想,原是日本東芝的代理商,由銷售進入生產,最後建立自己的品牌Lenovo,並在二○○五年收購了IBM的個人電腦部門,二○一四年又收購了摩托羅拉的手機部門和IBM的伺服器部門,使同年個人電腦的出貨量超越HP,成為全球最大的個人電腦品牌。除了個人電腦之外,在其他領域,如通訊器材,中國企業也有類似的發展。中國品牌在逐漸壯大後,也開始培養自己的供應商及代工廠,於是紅色供應鏈崛起。紅色供應鏈一方面從美系的供應鏈取得養分,一方面和美系的供應鏈競爭關鍵技術的主導權,因而引起美國的疑慮。
中國製造二○二五
美國企業所建立的這個供應鏈體系,加入容易,使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成為「世界的工廠」,製造業的產值領先全球。但中國政府很快就發現,如此巨大的生產價值,真正屬於中國、分配到中國人口袋的比率其實很小,因為中國的企業在整個生產鏈占據的位置不重要。以蘋果的智慧型手機iphone七為例,全部的組裝工作都在中國完成,但中國分到的報酬估計只有八.四六美元,包括工資和一顆國產的電池,占iphone出廠價(報二四○美元)只區區三.五%,如果以零售價(超過五○○美元)對照,則不到二%。如此辛苦為人作嫁,但報酬如此微薄,是因為中國沒有掌握關鍵零組件之故。掌握重要零組件的國家,都獲得較高的報酬,例如日本得到六八美元(半導體元件和面板等),臺灣得到四八美元(CPU代工和鏡頭等),韓國得到一七美元(記憶體等),都比中國高出許多,當然賺最多的還是蘋果公司本身。
供應鏈不只是生產整合的平臺,也是一個利益分配的平臺,而主導整合和分配的都是供應鏈的牽頭廠商,或者旗艦廠商,在以上的例子中,Apple就是旗艦廠。它是品牌廠,它決定什麼供應商提供什麼零件、做什麼工作,獲得多少報酬。技術強、難以替代的供應商,獲得比較好的報酬;技術普通、容易替代的供應商獲得比較差的報酬。旗艦廠商擁有生殺大權,因為它是產品價值的主要創造者。供應商無論多厲害,只是幫助實現價值創造的抬轎角色,沒有蘋果的創新,再好的技術也英雄無用武之地。當蘋果使用金屬機殼時,臺灣的金屬機殼製造技術價值連城;當蘋果改用塑膠機殼時,這些廠商立刻由雲端跌入谷底。
中國首先學到品牌的重要性,沒有品牌,無法行銷,無法掌握市場。中國自身擁有廣大的市場,在所得水準不是很高,而政府有各式各樣干預市場的手段,中國品牌在中國市場有絕對的主場優勢。美國企業佈建在中國的這個開放式生產網路,使中國的品牌進入市場的技術門檻降到極低的水準,因為所有生產零件在市場上都可以輕鬆取得,如果需要組裝,也有人可以代勞。只要產品賣得出去,產品就做得出來。中國的本土品牌在主場優勢的庇護下,幾乎在所有行業都勢如破竹,在短時間內把原來外商壟斷的市場搶回來。以智慧型手機為例,蘋果的第一支iphone手機在二○○九年進入中國,初期中國的智慧型手機市場都是外國品牌,包括蘋果和三星,但不出十年,本土的華為、小米、Oppo、Vivo等品牌,就光復了這個市場。到二○一九年,只剩蘋果在中國市場仍有能見度,約有九%的市占率,其餘外國品牌,像三星,已經不足掛齒;三星甚至把中國的生產線完全撤退。中國的品牌廠所以這般神奇,是因為外商自改革開放以來,在華南地區所建立的電子業供應鏈,歷經山寨機時代的淬鍊,發展成為孕育正規品牌的強大生態系統。今天中國的本土智慧手機品牌,幾乎都來自山寨的故鄉──深圳。
建立了品牌,掌握了市場,坐上了王座,固然獲得精神上的滿足,但不見得就創造了價值。中國品牌廠的關鍵零組件和生產設備,仍然依賴外商的供給。例如智慧型手機的各種晶片、記憶體、銀幕、鏡頭等仍然無法自製,即使手機賣得好,也可以自主利益的分配,在市場的競爭下,除少數例外,中國品牌廠獲利仍然有限。比起臺灣的代工廠,中國品牌廠可能神氣許多,但算起錢來,就不見得神氣得起來。技術雖然對品牌建立的影響不大,但對價值的創造影響重大;光有品牌,沒有價值創造的能力,也無法主導供應鏈的資源分配。關鍵供應商把產能優先給了蘋果,次級品牌廠只能尋找生產網路上剩餘的產能。
面對這樣的困境,中國政府在二○一五年提出《中國製造二○二五》計劃,立志要在十年內把中國由一個「製造大國」變成一個「製造強國」,重點就是要掌握關鍵的製造能力。計畫強調製造業的創新、資訊化(數位化)發展和工業基礎能力的建構。其中,創新和數位化是順勢而為,是中國製造業升級必須走的道路;工業基礎能力的建構則是彌補現狀的不足,也就是「補短板」,減少對全球供應鏈的依賴。這個方向和中國迄今為止的發展軌跡相悖離,也是造成與美方衝突的主因。
根據工信部長李毅中的說法,所謂「工業基礎能力」,包括核心基礎零部件、先進基礎工藝、關鍵基礎材料、產業基礎技術的「四基」,目標是提高產業自給率,要由計畫啟動時(三二○一五年)的二○%自製率提高到二○二五年的七○%。《中國製造二○二五》的重點領域包括新一代資訊產業、高階數控工具機、機器人、軌道交通裝備、航天設備、電力設備、新能源汽車、奈米高新材料、醫療設備等。政策工具則包括補貼國內研發和生產,海外併購、吸引外人投資等;在外人投資部分可能搭配美國指控的強制性技術移轉。
《中國製造二○二五》基本上是進口替代的策略,針對高階的設備、材料、核心零組件,以國產取代進口,然後進一步推動出口。工業後進國家的日本、韓國都採取過類似的策略,而獲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為什麼中國這個計畫推動不到三年,還看不見太多的成效,就遭遇川普總統的強烈抵制?固然是因為中國的經濟量體遠大於日韓,但更重要的是開放性的生產網路,使中國可以取得的資源更容易,而付出的代價更少。
日韓在一九六○年代、一九七○年代進行進口替代時,必須以高關稅建立貿易保護牆,隔絕進口的競爭,提供國內產業技術學習的機會。關稅保護增加了國內下游產業的生產成本,傷害了下游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這是技術學習的代價。此時如果引進外國投資來加速技術學習,還必須容忍外國企業享受高關稅保護下的超額利潤。中國政府因為WTO的承諾,無法築關稅的保護牆,只好以國內市場為槓桿,用行政手段強迫外國企業合資、強迫技術移轉,或者提供本國企業低廉資金,在國際市場上狩獵有高技術含量的外國企業。這種以行政力量巧取豪奪先進技術的新型態產業政策,不受WTO傳統規則的約束,被美國視為是不公平的競爭手法,因此川普政府選擇了封鎖策略,要把中國排除在全球供應鏈之外,阻絕中國技術學習的門道。
美國的出擊
美國對中國供應鏈的出擊,採雙路夾攻的策略:一路對來自中國的進口課徵懲罰性關稅,一路利用貿易管制的法令(ExportAdministrationRegulation)限制對中國的出口。在進口方面,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根據二○一八年三月的三○一條款調查結果,確認中國實施不公平貿易,包括強迫技術移轉、竊取智慧財產權等,因之啟動對中國的關稅制裁措施。目前已經執行四波的加徵關稅措施,第一波始於二○一八年七月六日,針對進口值約三四○億美元(以二○一七年進口值計)的八一八項中國產品加徵關稅,產品包括化學品、儲存元件、面板、工具機、產業用機械等;第二波始於二○一八年八月二三日,針對進口值約一六○億美元的二七九項中國產品加徵關稅,包括鋼鐵、半導體、塑化產品;第三波始於二○一八年九月二四日,針對進口值約二,○○○億美元的五,七四五項中國產品加徵關稅,包括工業電腦、電腦零件、網通產品、汽車零件,還有一些消費產品;第四波於二○一九年九月一日起徵,涵蓋約一,二○○億美元的三,二三三項中國產品,以電視、相機、智慧手錶、成衣等消費品為主。前三波的關稅率都是二五%,第四波的關稅率是一五%。迄今為止,只剩手機、筆電、遊戲機、電腦顯示器、部分玩具、鞋及服飾等約一,六○○多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尚未被加徵關稅(原定在第四波課稅範圍,後因談判而暫緩),還有自始即列為排除項目的藥品、醫材、稀土等項目。
美國前兩波共五○○億美元產品清單,都是為反制「中國製造二○二五」而選取的重點產品,第三波也涵蓋部分的「中國製造二○二五」項目。美國的策略是希望透過懲罰性關稅的課徵,讓國際廠商將生產線移出中國,以解構中國的供應鏈,使進口替代策略難以施行。在中國境內為「中國製造二○二五」而生產的外商,很少是純為中國的進口替代而設立的,他們大部分是服務全球市場的,包括美國市場,因為中國政府的優惠措施或者因為中國生產鏈的完整性,使中國生產具競爭優勢,因而吸引他們的投資。美國的策略是運用關稅的懲罰,逼他們退出中國。貿易戰發動後,二○一九年美國自中國全年的進口額減少了一六.二%,同期美國進口總額減少一.六七%,可以看出懲罰性關稅的效果。
貿易戰已造成許多國際廠商將生產線移出中國。各國外商轉移生產據點以母國、東南亞、墨西哥等地為主。以臺商為例,根據投審會資料,截至二○一九年底,臺商承諾回臺投資金額達七,一二一億臺幣,投資廠商家數一六五家。這些回臺的廠商大都以生產網路通訊、電腦伺服器等產品為主要。即使尚未被加徵關稅的筆電和手機,也開始做分散生產的布局。據《日經新聞亞洲評論》報導,蘋果已經要求其主要供應商進行成本評估,包括:iPhone組裝商(富士康、和碩、緯創)、MacBook製造商(廣達電腦)、iPad製造商(仁寶電子)和AirPods製造商(英業達、Luxshare-ICT、Goertek),規劃將其產能的一五%至三○%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的可能性。雖然緯創從二○一七年來已經在印度生產較低階的iPhone手機,鴻海自二○一九年起也開始在印度組裝iPhone,但產量不多。目前逾九○%的蘋果產品仍在中國組裝。蘋果供應商們承認,在其他地方複製生產網路需要一些時間,至少需要兩年或三年才會產生網絡效益。而且即使部分產線轉移,未來中國很可能仍然是蘋果最重要的製造基地。蘋果供應商考慮中國部分產能轉移的新生產基地,包括墨西哥、印度、越南、印尼和馬來西亞四。
除了蘋果公司之外,美國重要的筆記型電腦廠商,如惠普(HP)、戴爾(DELL)也都要求代工廠評估將二○~三○%的產能移出中國,而可能的生產基地包括越南、菲律賓、印尼、臺灣。因為這兩家公司的全球市占率合計高達四○%,而中國製造的產品約有四○~五○%是出口美國市場,高額關稅對廠商的營運影響很大;而日商夏普也考慮將其出口美國的筆電Dynabook由杭州移往越南生產。
美國另一路的進擊,是利用出口管制的法規,針對中國特定的企業,封鎖其敏感性設備和零組件的供應,最明顯的案例就是華為。美國政府把華為和其相關企業列入「實體清單」後,所有來自美國的半導體產品,都必須取得美國商務部的許可證,才能出貨給華為。所謂「出貨」,包括出口、轉口、再出口各種交易型式。二○二○年五月,商務部擴大法律的解釋,修正「直接產品法則」(directproductrule),規定凡採用美國技術或軟體所製造的產品,不論在何處生產,都列入出口管制的範圍。
這項規定,使台積電也被迫停止替華為生產華為自家設計的晶片。但這項新規定,對於不是替華為量身訂做的產品,如三星或聯發科所生產的泛用性晶片,是否可以續賣給華為,語焉不詳。二○二○年八月,美國商務部再發出解釋令,規定凡採用美國技術或軟體所製造的產品,不論是否為華為所設計或量身打造,一律不准賣給或轉賣給華為。這一來,華為使用第三方晶片的道路也被阻絕了。
美中供應鏈脫鉤
美國對中國的關稅制裁及技術圍堵,是否會使中國的供應鏈和全球生產網路完全脫鉤(decoupling)?這是現在大家關心的問題。美國的強勢措施,將使中國既有的供應鏈體系產生巨大變化,應是無庸置疑的,但會變成什麼樣態仍有許多未知數。原則上,以供應美國市場為主的產品,有些生產將移出中國,而供應中國及其他非美國市場的產品則還可以繼續留在中國。
這是分散與分流,但並非脫鉤。多國籍公司在中國已經建立的產業鏈,不論是效率及成本都是全球最優的,除非萬不得已,廠商是不會放棄在中國生產的;但集中中國的風險十分巨大,尤其在新冠肺炎衝擊下,更顯突出,有必要分散。至於外移的供應鏈,以東南亞及印度為主,生產鏈將根據客戶及代工廠的需求及各地的生產條件,分散在不同國家。
其實近年來,中國本身的勞動成本上升,勞力密集產業自中國移出已經是大勢所趨。例如成衣、製鞋、玩具、家具等,中國事實上已失去生產上的比較利益,在貿易戰發動之前,產業鏈已漸次外移到東南亞及南亞各國,貿易戰將加速其移動的腳步。有些產品,如筆電和智慧型手機,中國雖仍擁有生產上的比較優勢,但因為美國戰略上的安排,也將迫使其移出中國。但無論前者或後者,因為中國本土的市場龐大,中國對產業的保護仍未消除,產業鏈只是部分移出中國,並不會從中國完全消失。而且中國這些年來所建立的強大生產聚落,仍有能力支援其他國家產業聚落的運作,因此不會和外移的生產鏈完全脫鉤。例如成衣業紛紛外移到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地生產,使中國在美國成衣市場的進口占有率已經降到三○%以下,但中國卻是這些取代國最大的布料供給來源。
受貿易戰的影響,可以預測大部分的生產鏈,不論有無戰略意義,都會相當幅度的由中國移轉到周邊的國家,包括東南亞和南亞。這些國家的人口總和,足以和中國相抗衡,因此也有足夠的能量可以吸收自中國移出的生產需求。而且許多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的人口結構十分年輕,正可接棒逐漸老化的中國勞工。這一條在東南亞向南亞延伸的新生產帶上,因為近年的區域經濟整合(如東協自由貿易區、東協+一自由貿易區),彼此間的貿易障礙已經降低,因此生產鏈的串連並無太多障礙,貨可暢其流。這條生產帶上的國家經濟因為發展程度不同,產業的差異化也高,未來可吸收來自中國不同產業的供應商,形成較為分散化的產業聚落,不再像過去一樣,全集中於中國一地。新聚落一方面和西方的市場相連,一方面和中國的生產聚落相銜接,形成一個「前店後廠」的態勢。
在短期內,這個生產帶上的勞動力供應無缺,但技術性勞動力,尤其是研發人才將面臨嚴酷的挑戰。要取代中國,只有一般勞動力是不夠的,技術性勞動力才是生產力高低的關鍵因素。因此未來這個生產帶上的技術性勞動供給能否大幅提昇,才是生產鏈可以移轉到什麼程度及移轉後的生產樣態之主要決定因素。
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圍堵是有針對性的,美國圍堵的產業挑明是「中國製造二○二五」的目標產業,美國圍堵的對象是中國國家隊的企業,也就是承擔政策任務的國家級企業(nationalchampions)。美國的政策目標是要把這些中國國家隊排除在美國所建構的全球技術體系之外,但對其他中國企業則沒有相同作為的必要,它們仍可繼續參與這個開放性系統的運作。例如美國排除華為於系統之外,但並沒有排斥小米、OPPO、VIVO這些公司持續和西方供應系統合作,畢竟合作是彼此互利的。
因此,所謂美、中產業供應鏈脫鉤的問題,應只限於「中國製造二○二五」的項目,而且只限於中國國家隊的企業。這些企業在美國的技術圍堵下,未來不得不發展自主性的技術,不得不建立自主性的供應鏈,以規避長期暴露於美國貿易制裁的風險中。如果自主技術發展成功,它們將形成一個獨立的體系,和美國的系統有所區隔。但中國的體系將是封閉式的,因為中國以其現有的技術能量主導一個開放性的技術體系仍力有未逮,而且願意抬轎的企業也不會是技術先進國家的企業。與其說這是中國與美國的供應鏈脫鉤,不如說中國是被迫「自立門戶」,但他們不會因此放棄從美國的技術系統中汲取養分。如果美國企業受政策限制,不能和它們合作,他們仍可以和亞洲其他國家,或歐洲企業合作。
一個技術體系的建立,要有長期基礎科學研究的支撐與全球資源的互補,才能與時俱進,維持市場的競爭力。在短期的未來,仍不易看到中國有獨自建立這種技術體系與美國分庭抗禮的能力,而且這樣做將耗費龐大的資源,也不是政策上的好抉擇。中國雖然在技術自主方面有強大的企圖,但應該不會忘記計畫經濟時代「閉門造車」的慘痛經驗。政府雖然繼「中國製造二○二五」後提出「中國標準二○三五」的計畫,也只是企圖參與國際產業標準的制定,爭取主導權,提高自主性知識產權的價值,還沒有自大到要建立一個自己可以掌控的技術系統。今天連美國也必須整合別國的技術力,才能形塑一個完整的技術系統。因此美中的技術之爭,不是系統之爭,而是同一個系統下的主導權之爭。
臺灣夾在美中兩強爭執中間,一邊是石頭,一邊是鐵板,十分難受。臺灣在短期內固然可以承接一些自中國移出的產能,但因為臺灣的土地及勞動成本均高,不可能成為大規模生產的基地,臺商只會將高階及附加價值較高的產品移回臺灣生產,但大規模量產的產品,例如筆電及手機等,則只能選擇在東南亞及印度生產,這種調整,將強化臺灣在全球資通訊產業供應鏈的角色。因為臺商在中國以外的國家已有所布局,對建立新的產業聚落也有經驗;只是在其他國家建立供應鏈體系,會比在中國花的時間更長,效率可能也不一定可達到中國一樣的水準。中國以外的供應鏈因為較為分散,各國將根據自身的條件及產業基礎,吸引不同的供應商及產品落地,彼此互相支援。非中國系統的亞洲區域供應鏈,將聯結日商、韓商、歐商、美商的力量,重塑一個新的跨國供應體系。
臺灣在這個非中國體系的亞洲供應鏈的建立上,將扮演拓荒者和連結者的角色。臺商迄今仍是中國出口到美國的主要貢獻者,臺商的移出中國因貿易戰已勢不可擋。有些臺商動作快,有些臺商動作慢,這是因為他們的客戶(品牌廠)有不同的考量的緣故。在東南亞及南亞重建生產基地,對臺商來說,應該不是十分艱難的任務,他們其實在一九八○年代末期也曾經做過類似的事。臺商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技術人力相對缺乏的亞洲新生產鏈上,建構完整而有效率的技術支援體系,使其生產效率不遜於中國。要因應這個挑戰,臺商必須在臺灣本土建立更強大的技術支援能量,包括研發能量(而不是生產能量)。這個技術支援中心,必須和主要客戶進行密切的研發合作,並且和日本、韓國的技術伙伴有細緻的分工和戰略支援的安排,從產品開發設計到生產設備的提供、生產材料、關鍵零組件的取得、製程技術的開發,從頭到尾的技術支援體系必須完整無缺,而且可以落實到新的生產據點的生產線上。亞洲生產鏈的再構築,將是未來十年亞洲產業發展最重要的課題。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