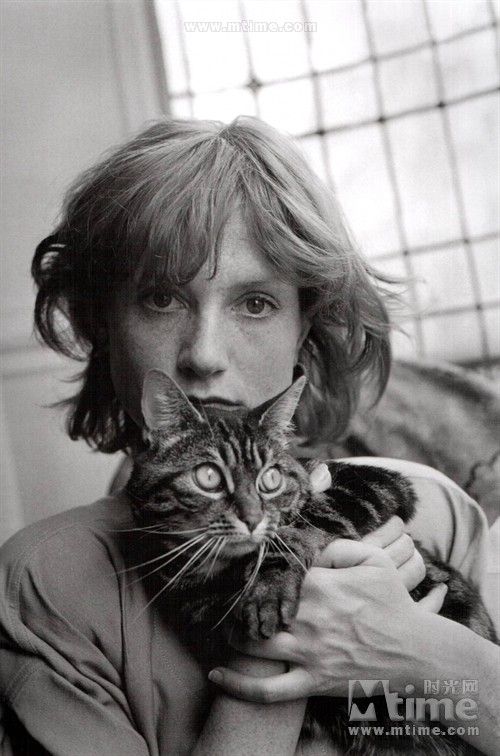疫情之下的安庆农村
原文以标题《疫·安庆|瘟疫不管你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首发于《城市中国杂志》/ 2020.03.02
————————————————————————————————
1
坐在我旁边的女人转动的眼珠,停在了我搽鼻涕的动作上。紧接着,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引得车厢里的人扭动着脖子,循声望向一位坐在靠窗位置的老人——待上下起伏的胸腔平稳以后,老人低下头继续刷手机。
在这列开往上海的高铁上,所有乘客都戴着口罩的情形,与我1月22号(腊月二十八)回安庆老家的那天截然不同。那天的车厢里,只有少数年轻的乘客戴着口罩。戴口罩者的数量,也随着我回家经过的地方——大城市(上海)、小城市(安庆)、镇上、乡下,而相应地减少。
我所在的村子,只有几个从城里打工回来的年轻人戴着口罩。其他的村民则毫无防护地为腊月二十九小年夜的祭祀忙碌着。即便是平常,也鲜少有留守的村民在家看新闻联播,电视已然沦为晚饭时的背景声。有手机的村民们通过抖音知道武汉有人因感染新型肺炎去世,一传十,十传百,基本上大家都知道这么个事,但武汉——离我们太远了。
我刚把行李箱放下,母亲忙不迭地与我报告村里的大事——玉莲奶奶走了。说是前几天高烧不止,吃了退烧药也不管用,后来话也说不出,傍晚的时候,她家里传出哭声来......
我问母亲她家里人怎么不打120急救电话。“年纪那么大了,哪个愿意花钱?”我又问玉莲奶奶是否有咳嗽的症状。“咳吧......我昨天去看她,见她哑了,就凑在她枕头边唤她的名字,看她还认不认得我——”
如果母亲描述的症状属实的话,那玉莲奶奶极有可能感染上了新型肺炎。我继续追问村里是否有从武汉打工回来的人去看过玉莲奶奶。母亲想起村里有个在武汉读书的男孩,回来有些时日了,但并未出现任何症状。“有潜伏期的”,我叫母亲少出门,非得出去的话,戴个口罩。我在上海买了两袋一次性口罩,省着点用,应该能管够。“我不戴,人家看了要笑死!”母亲拒绝道。“你是要命还是要脸?”母亲选择了“脸面”,说她不习惯戴口罩,又说得不得病,都是命中注定。
不久后,串门的父亲回来了。我把叮嘱母亲的话跟他重复了一遍,得到了相同的结果,父亲叫我别听风就是雨,说我们农村没这个病。
“这瘟疫又不管你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
父亲或许是存在侥幸心理,或许是真糊涂了。从前大家都在村里务农,如今大家都去城里打工,况且安徽省与湖北省紧邻,去湖北打工的安徽人肯定不在少数。
2
1月23日,我和表妹去镇上买东西,顺便陪姑妈去银行。
到了镇上,狭窄的街道挤满了卖东西的小贩和买年货的村民,戴口罩的人甚少。表妹看到有小贩在卖野鸡之类的野味,甚是奇怪,她拉着我和姑妈绕道而行。
好不容易到了银行,等候大厅里又是挤满了没有戴口罩的人。表妹取了号,叫姑妈等着排队,并叮嘱她“口罩不要摘下来,不要跟别人讲话。”
我们把买来的东西拎到银行给姑妈看着,转头去了药店。跑了好几家,总算在最后一家药店买到几个N95口罩,一个15块,我顺道买了一盒维C泡腾片。
回家的路上,表妹说她初一不到我家来拜年了,理由是我爸妈不戴口罩到处乱跑,还有我家有太湖、望江的亲戚过来拜年,不能确定那些人是否去过武汉。
姑妈对表妹不去拜年的决定颇有微词。我说我无所谓,但我爸妈肯定不这么想。表妹想了想,说她下午过来看看奶奶,跟我们家那些亲戚错开。
3
“你拿个口罩给我。”准备去祠堂祭祖的父亲对我发出了指令。
这个时候,村东头的男人们已在堆满三牲福礼的桌前,在大炮仗放得震天响的间隙里,仔细聆听是否轮到他家祖先的名字。然后烧香,给祖先斟酒倒茶,再扔出一挂鞭炮。尔后行跪拜礼,敲一声罄之后,端着托盘,拨开烟雾缭绕的人群,忍受着呛鼻的硫磺,踏出祠堂的门槛,回到家中。
不知道父亲要戴口罩是因为祠堂里乌泱泱的人,还是因为燃放鞭炮烟花弥漫在空气中的硫磺味。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戴口罩总是好的。
我凑到父亲跟前,盯着他脸上的口罩,提醒他戴倒了,却被他怒声打断——“难道我还不晓得戴口罩!”好心提醒他,却像是冒犯了他一样。我想父亲生气的原因,大概是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连戴个口罩都不会。
4
大年初一早上5点钟,我被连绵不绝的鞭炮声给吵醒了,在床上辗转反侧到7点钟,窗外又响起广场舞的欢快音乐声。
一下楼,迎接我的是一客厅来拜年的亲戚。在这欢欢喜喜过大年的浓烈年味里,我只能听天由命,自求多福了。
晚上,表妹发来的微信消息一条接着一条——邻村封路的视频,他们村微信群开会讨论封路的截图,以及县政府下达的红头文件。接着,父亲和母亲陆续接到两个亲戚的电话,说村里封路,不能过来拜年。
就这样,初二早上村口的大喇叭响了——“正值新春佳节,村委提醒大家确保做好个人防护.......少聚餐少拜年.......”
母亲见没有亲戚登门拜年,说根本不像过年,一丁点年味都没了。我安慰她,省去了给亲戚烧饭的劳累,她不是落得轻松么。“我还要去洗衣裳,还要去摘菜......”母亲列举着她做不完的家务活。
5
村里安静了。没有鞭炮的响声,没有走亲戚拜年的人。然而,村里总有像父亲一样在家里待不住的人,嘴里叼着烟,手里揣着保温杯,在村里四处蹓跶。
不知道是因为过于紧张,还是受了风寒,我感冒了。在“丁香医生”查看了感冒与新型肺炎的区别,确定自己只是普通感冒过后,才安下心。
虽然春节假期延长了,但我并没改变回上海的时间。父亲见我要走,叫我给他留几个口罩,说他回无锡的路上用。我把剩下的口罩分了三份,一份给父亲,一份放在母亲床头的抽屉里,自己带走了一份。
在去车站的路上,没有像以前那样出现堵车的情况,一路畅通无阻。表妹望着车窗外的婚车,说:“他们真是不怕死。”
到了安庆站,门口是“进站必须戴口罩”的大字提示。进站之后,是穿着防护服的人拿着体温枪对准每一个乘客的前额。而在终点站等待我到来的还有一系列表格的填写。
6
1月28日到了上海之后,父母亲常常电话过来,关心上海粮食和蔬菜的供应情况。母亲跟我说,我们镇上已经有4个人确诊了,又说一房的五叔骑着摩托车想去镇上的医院看风湿,被人堵来堵去,风湿没看成,还把自己给摔了。
过了两天,母亲在家族微信群里发了一个视频——玉莲奶奶的棺木立在祠堂里,没有道士做法事,没有锣鼓喧天,也无亲人哭丧,只有几个戴口罩的男男女女跟在一个打锣的男人后面。打锣的男人学着道士的模样唱了几句,惹得众人大笑不止。
母亲说,奶奶担心自己的葬礼会像玉莲奶奶一样,亲戚没法过来奔丧,少了热闹,道士没法过来做法事,她的灵魂升不了天。
“叫外婆多活些时日吧。”表妹在群里如此回复道。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