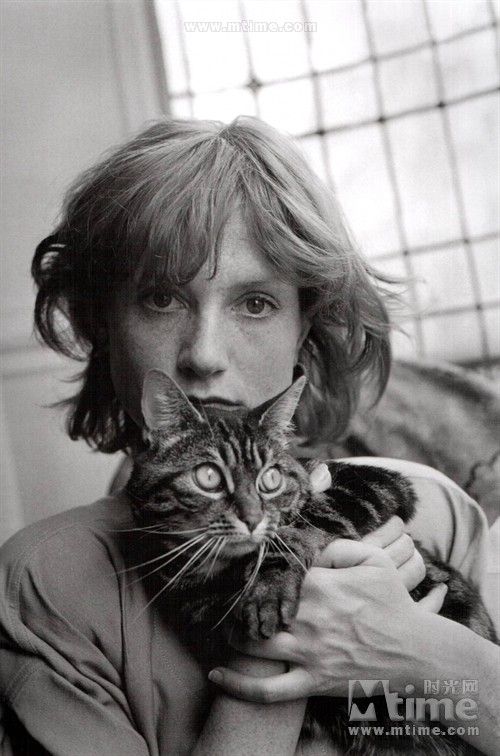
張若水
上海天桥上的卖花阿婆:孤独的日子打着盹儿过
原文首发于「看客inSight」 ———————————————————————————————————— (序) 上海夏日的平常午后,淮海中路重庆中路人行天桥上,高跟鞋踩在地上的声音有节奏地渐行渐远,打着领带蹬着皮鞋、讲着电话的男人快步走过。
我这个乡下女孩,在陆家嘴轻奢店打零工
(原文首发于「人间thelivings」/2020.6.24) 1 早上8:30,我等来了第二班较为空旷的地铁。这个时候,排队的位置最好位于队列的第一二位,方能在地铁门打开的那一瞬间,以最快的步伐,一屁股霸占住一个座位。不然的话,就要开始上班前的“排练”——站立。
疫情之下的安庆农村
原文以标题《疫·安庆|瘟疫不管你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首发于《城市中国杂志》/ 2020.03.02 ———————————————————————————————— 1 坐在我旁边的女人转动的眼珠,停在了我搽鼻涕的动作上。紧接着,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引得车厢里的人扭动着脖子,循声望...
房思琪们开口说话,炸毁“反转”和“仙人跳”
林奕含离开三年了,4月27日是她的忌日。身在天国的她若得知最近的“N号房”事件,和“鲍毓明性侵未成年养女”一案,不知道是不是要难过地哭出声来。她生前在访谈里说,李国华们不会死,也不会死,这样的事情仍然在发生。现实确实如她所说,在你阅读这篇文章的间隙里,每3分钟就有一个女人被打,每...

從「大武漢」到「東湖計劃」(《李文漫遊東湖》及「東湖計劃」,及其他)
自武漢封城以來,「魯磨路救援隊」和「魯磨路救援日記」風靡網絡。魯磨路是武漢壹條匯集Live House和各種酒吧的街道,「VOX樂迷群」則是這群混跡魯磨路的年輕人線上陣地。疫情發生後,他們通過社交網絡,迅速聚集在壹起,成為壹個超級節點,加入救援行動中。

在每一個夜晚,十點鐘的雨。
在每一個,夜晚,十點鐘的雨,以每分鐘2500滴,落下。比餐桌上的眼淚,更難以,吞咽。紫藤蘿,如瀑布般,來到寒春。紫藤蘿,不存在,隱喻。它只是紫色的,小花。開門,關起來,留壹條,隙縫。開門,關起來,上鎖,用膠帶,封住。突然而至的少女,和水手服,高舉過頭頂,跌落。
我做了一個夢
當我從滿眼皆是廣告的春秋航空的機艙,一頭鑽出來時,迎接我的是上海的秋天——風吹到皮膚上,是冷的。上海的夜晚在此時此刻,顯得平和,而充滿安全感。在公寓歇息了一天之後,我的生活回歸到日常——將衣服丟到洗衣機,用APP買菜,然後做飯、餵飽自己。洗衣機發出了「嘀嘀」聲,我打開蓋子,取出洗好的衣服,去晾曬。
如果我年紀輕輕地就死了,沒有出版過一本書
拉開地下室的門,黑漆漆的屋子裏擠滿了年輕人。女青年的烈焰紅唇,男青年的海軍帽,新潮的著裝打扮,與上海這座城市相得益彰。主持者手扶著直立話筒,介紹這次的活動。主持者站立的那壹小塊地方是唯壹有燈光的地方。朋友和我彎著腰,越過坐在地上的人群,擠到「舞臺」處。
在小黃侗寨的日與夜
(一) 停電了。在手機電筒光中,洗完了澡,用得是洗發水。今天終於搶到了熱水澡。阿香為了迎接我們的到來,專門裝了熱水器,還買了洗衣機。不知道是不是水壓問題,常常洗著洗著,就沒水了。每次去沒有圍欄的陽臺晾衣服的時候,我總覺得壹不小心,我就滾下去——掉進河裏了。
我對廣東這座城市過敏
(一) 我大抵上是對廣東這座城市過敏的。扁桃體發過炎,長過貓癬,感過冒。這一次又換了個毛病。這次的病癥大概始發於五天前——阿波說要帶我們去萬州大酒店吃面。我們一行四人,在高溫39度的大街上,步行了半個小時,還沒到。中途去了超市蹭了個空調,買了瓶山寨的維他茶喝,我們...
廢墟上的野花
「這只狗好慘啊。」 從天馬山下來之後,我們遇到壹只流浪狗——它的兩條前腿拖著兩條無法動彈的後腿,穿過馬路。我們猜測它應該是過馬路時被車輪碾過。明明我們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充滿了憐惜和同情。可我總覺得,我們這樣當著狗的面,指出它身體的殘缺,也很殘忍。
妳約我去散步
這一天晴朗而狂風大作 擅於遺忘的人們 保留著壹周的記憶 一切,如常。我們穿過壹個個體溫槍口 黑夜降臨在寂靜的街道後 帶著脫北者的默契,奔向彼此 房屋被戴在醫用口罩裏 每隔兩個小時,更換壹次 城市被裝在消毒液瓶裏 壹個個地置於陸地之上 枝頭的梅花被獨自撇在了去年冬天 吹哨子的喉嚨...
悼文
我已經很久沒有打掃我的房間了。她淩亂不堪, 蒙上了灰塵, 結滿了蜘蛛網, 滯留著昨日的汙垢。每天, 在這張臨時搭起的床上往返, 比我躺在上面睡著的時間, 多一個世紀。只為了每個晚上八十塊錢的夢。但願諸神改變我的夢, 而非改變我做夢的天賦。
何日君再來
(一) 「我們離婚吧。」十六年未見的丈夫如是說。姚暮美放下手中的筷子,看著眼前這個也老了許多的男人,欣然同意了她十六年等待的結果。她什麽也沒問,她不想知道他需要別的女人,她不想知道他對她怎樣好,至少,不想從他嘴裏知道這些。從此,暮美不再稱呼他為「我老公」,他失去了姓名,成為暮美口中的「這個男人」或「那個男人」。
離婚——她用了半輩子
(一) 吳大夫是我們村第壹個離婚的女人。大家都說,在大城市闖蕩過十五年的女人就是不壹樣。畢竟,在我們村裏,如果哪個女人的丈夫提出了離婚,她們是死也不會離的,人活壹張臉,離婚——那可是丟臉丟大了。可吳大夫卻要跟王誠信離婚,還特意選在她50歲生日那天。
在夢裏,我的手長出來了
(序) 2018年5月份在蘇州與樂行機構負責人見面時,他問我是否有意願寫壹寫工傷工友的故事,希望通過文字有更多人能關註、了解工傷工友群體。6月份,我受其之邀,有了近距離與工傷工友相處的機會,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認識了阿香。她在舞臺上開心地跳著她家鄉的舞蹈,她缺失的右手,對她的舞姿沒有任何影響。
當我站在那裏的時候
當我站在那裏的時候, 把我的靈魂硬塞進壹只擠腳的鞋, 在故人的身影裏散步, 8個小時,10個小時,12個小時。當我站在那裏的時候, 把我的肌肉壹遍遍折疊, 標上價格,畫上奢侈的符號, 任人挑選。當我站在那裏的時候, 把我的疲憊壹層層撕掉, 把我曲張的靜脈打成蝴蝶...
妳叫我閱讀妳的日記 ——給BL
妳叫我閱讀妳的日記 閱讀妳母親扇在妳臉上的巴掌印 閱讀她的大嗓門、虛偽和愚蠢 閱讀她的四段婚姻 閱讀那個賺不了錢的老實男人 閱讀那個叔叔和他兒子看向妳的眼神 閱讀那個男人把她打進醫院搶救 閱讀妳的爸爸吃喝嫖賭,對妳們母女不管不顧 妳叫我閱讀妳的日記 閱讀妳對...
溺水的晚上
他們給我套上壹頂取不下來的帽子,稱之為“偉大”。他們用思想包裝偽善,他們給名利化妝美容。他們在金色的掌聲裏滑行,眩暈的光圈立於其頭頂之上。他們贊美我的同時也詆毀我。他們的保險箱裏裝滿了—— 智者的腦子、勞動者的雙手、藝術家的細胞。他們替自己的兄弟、兒子、孫子,還有老子—— 辯護。
我的願望
我希望小朋友不用考試做作業。我希望每個人不用上班。我希望男人化妝穿裙子生孩子。我希望女人大吃大喝,夜夜高潮叠起。我希望人類可以與任何性別相愛。我希望不用害怕說錯話。我希望動物園、馬戲團、海洋館永久歇業。我希望遊樂場、大商場統統關掉。我希望人們在篝火前圍成圈,聽壹個古老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