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打零工的我,是“名校废柴”吗?
我打零工的经历可以追溯到三年前。
本科毕业以后,失去学生身份庇佑的我,终于没法心安理得地继续过着无所事事、毋需自食其力的日子。为了生存,我决定出去打工搞钱。这期间,我做过许多 “hit-and-run” 式的零工,包括但不仅限于画室模特,精神病房的临时会议协调员,群演,充场人员,超市促销,发模,演讲稿代写,小学生托管等等,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在形形色色的打零工经验里,我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无论何种性质的工作,总免不了因为性别的原因出现区别对待。除了某些岗位偏爱或直接限定男生,体力劳动男女差价工资,女性附加外貌形象条件等等之外,还有一些是性别刻板印象造成的隐性差别。
比如我在一家教育机构当中学助教,负责人会跟我说:“明天答疑的是高中理科,你们女生应该都不如男生擅长,所以明天安排了两个男大学生。” 而到了核对数据的时候,听到的则是:“这种不能出错的步骤就交给小姑娘完成吧,毕竟心细”。
这些话相信大家已经司空见惯。我还碰到过另一些 “老生常谈” —— 一次是和我妈提起去画室做了模特,她紧张兮兮地问:“没做裸模吧?女孩子坚决不能做”;还有一次是打算去应聘深夜的兼职便利店员,被提醒说深夜时间段遇到店内安全问题 “可能一个女生无法妥善处置”,遂作罢。
找零工的女性里,与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并不多。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和四十往上的中年女性往往是主力军。其中一个原因是,除去某些以女性特征为筹码的工作(例如礼仪,模特等),许多临时兼职以体力负担为主,对女性而言并不轻松,而且此类工作多半缺乏严格的规范制度,年轻女性多会担忧安全保障和权益维护的问题。
除了性别,打零工还令我思考起学历和教育这件事。名校文凭几乎是每个中国小孩梦寐以求并为之努力的,但在零工世界里,它毫无用处 —— 或者说,它的作用就是避开这些工作的 “垫脚石”。当被偶尔问起在哪所学校读书时,我不得不编造蹩脚的谎言 —— 我的大学虽然称不上殿堂级高校,但它的知名度也足以令我躲在背后小小虚荣一番;也正因此,在这种环境下提及自己的出身,“名校废柴” 的尴尬感也就呼之欲出了。
在世人观念里,体力劳动与精神生活有云泥之别。但在我打零工的日子里,我意识到,象牙塔里获取的知识除了赋予某种非常虚幻的、形而上的支撑感之外,它能提供的作用实际是微不足道的。接触这些简单机械劳累的劳动之前,我一直执拗地认定,自己是脱离庸俗世界的 “精神性” 的人,因此只能投身于精神世界的生产活动:一切与美和艺术相关联的、凝结了人类情感共鸣的表达都令我着迷。我应该去做人类灵魂后花园的建筑者,或是艺术界的抽象思辨领袖!
在表达欲的冲动下,我去到一家零食公司做新媒体文案策划,最后只坚持了一个月。放弃的缘由,跟大多数以笔谋生的文学青年没什么区别:既对商业性迎合观众的表达深恶痛绝,又想自己的表达被大众认可,最后因质疑绝大多数观众的欣赏水平而止步不前。匆匆办完离职,我的第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就结束了。
在这之前,我还接连搞砸过 “高薪优待” 的培训机构教师与专业对口的证券公司客户经理两个工作,离校后无处可去只得逃回家赋闲。在家里那段日子里,虽然有生存的焦虑,但更令我无法想象、极为恐慌的是:我究竟该如何投身成为社会链条上运转的一分子?一切招聘、面试、体制考试相关的消息,都令我头痛欲裂。我像一只搁浅在海滩上的软体动物,只要缩进暗无天日的硬壳然后往沙子深处一钻,就可以如愿以偿地失去与整个世界的关联。
现在想来,我逃避的是什么呢?大概是所谓的 “主流生活” —— 毕业、工作、组建家庭,环环相扣,从我们成年之后就被套上命运的枷锁,被牵引着度过一生。未来的轨迹早已被周遭的人推着设定完毕,要做的无非是在这条道上走一遍。每个被推进去的年轻人其实都心知肚明,社会共识加于我们身上的许多框架,需要我们削减个性以适应,并为了普世意义上的成功而承担许多不快乐的代价。
对于我周遭圈子的 “主流” 来说,放弃找正式工作,转而去做零工女孩,显然是离经叛道、不可理解之举。这意味着我并没有被某一社会身份收容,虽然同样付出的是劳动。跟旧识的人提及现状时,我不得不承受一些误解与不恰当的评价;当朋友善意地劝我回归 “正轨” 时,我也只能是报以感谢。即使自食其力努力打工显得狼狈不堪,但我恰恰在此间找到了与自己本性相符的姿态。
我设想过,如果是曾经的我,对这样的生活也会心存不解与质疑。唯有亲身经历过零工生活游离于规则之外的动荡,才能真正体会到,那些因为沉重的精神负担而自愿放弃 “正常人” 的轨迹,在大众认可的生存方式之外游荡的人,是一种更多元的生命形态。
当然,这绝对不是说零工的世界里是宽容的。恰恰相反,在这里你能体会到多种多样的社会规训和歧视。例如穿了 JK 水手服去参加充场活动,听到来自活动主办方窃窃私语的议论;为了做发模(为新手美发师练手的角色)染了一头宝石蓝,结果因为发色 “不够正统”,被教育机构以 “影响不佳” 为由拒之门外。还有一次是负责精神障碍会议协调的短期工作,第一次和与我对接的负责人姐姐进入精神病院的病房,出来时她在背后悄悄问我:“你怎么这么淡定啊,我都紧张得不得了。”
那一瞬间我的心情其实相当复杂,不晓得怎么用简短的语言解释大众对精神病的刻板化、污名化,也不想大方承认我亦定期拜访这家医院的门诊部,期间早已观察过形形色色的病患群体。我便无意识冒出一句 “我不怕,又不是没见过”,反应过来后立刻接上一句 “以前陪别人探望过。”
打零工的日子里,我周旋在曾经试图躲避的外部世界,已经习惯于自己的格格不入。但有一次经历,令我这个从精神到身体的 “边缘人”,竟然意外获得与周围陌生人的联结感。当时我去剧组当群众演员,经过一番被审视和挑选,我入选了,成为十几名 “年轻、微胖、女孩” 中的一员。到达场地之前,剧组还特意叮嘱我们化好妆,衣服要 “穿得漂亮一点,最好有女孩子的感觉”。
那是为数不多的、能见到那么多与我同龄女孩的机会,而且她们还与我分享相似的身体外形!(出于剧情需要,招募条件是 “体型偏胖的女生优先”)。辗转三辆公交车赶到拍摄现场以后,我们这十几个群演女孩坐在帐篷旁天南地北地闲聊,聊身材超重的顾虑,妆容与衣服的搭配,正在经历的生活,还有虚无缥缈的未来。因为逃避社交的缘故,我快已经与同龄女生脱节了,甚至连 “是一个女孩” 这层意识都快模糊了。但是在那次的场景里,我感受到了水滴落入汪洋的归属感。
在等待剧组布景、安排戏份的空当,我蹲在沙滩上大口吞咽着工作盒饭,望着远处天色渐暗的海平线发呆。看到旁边的女孩子点了根烟,我把脑袋凑过去:“可以给我一根吗,谢谢。”



两年多的零工生活结束了,我回到学校继续念书,结束了那段充满随性的 “混乱” 经历。即使到现在,我也还会时不时陷入 “这次毕业后能否融入工作环境” 的自我怀疑中,我清楚地知道,学生身份只是延缓我与世界磨合进程的一道缓冲带,而不是我能躲避一生的安全区。加上疫情的冲击,更让我感受到零工维生状态的脆弱:它只是勉强维持住了我的生活,却无法抵御任何突发事件。
但无论如何,我在二十出头的年纪,用尚有活力的生命从主流里逃逸了一回,总归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2021.08.04 | BY Asakusa |
BIE别的女孩致力于呈现一切女性视角的探索,支持女性/酷儿艺术家创作,为所有女性主义创作者搭建自由展示的平台,一起书写 HERstory。
我们相信智识,推崇创造,鼓励质疑,以独立的思考、先锋的态度与多元的性别观点,为每一位别的女孩带来灵感、智慧与勇气
公众号/微博/小红书:BIE别的女孩
BIE GIRLS is a sub-community of BIE Biede that covers gender-related content, aiming to explore th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emales. Topics in this community range from self-growth,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gender cognition, all the way to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art. We believe in wisdom, advocate creativity and encourage people to question reality. We work to bring inspiration, wisdom and courage to every BIE girl via independent thinking, a pioneering attitude and diversified views on gender.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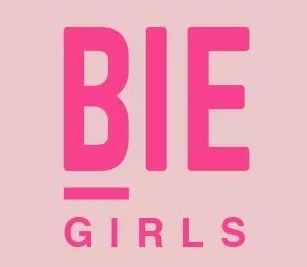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