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槍炮與時代浪潮
我們經常看見有人抱怨中國社會原子化程度嚴重,由於公民社會缺失,社會團結和社會自組織能力受到破壞,整個社會像一盤散沙。人們一邊悲嘆現實一邊心灰意冷,覺得沒有希望改變現狀就只好得過且過。但是你知道嗎,中共政府也注意到了社會原子化問題。你知道中共政府是怎麼做的嗎?
本期影片將首次嘗試解析中共政府克服社會原子化危機的努力及其內在困境。作為「新國家道路與中國民主轉型」系列第二期節目,本期影片首要目標是解釋把社會運動主戰場從街頭轉向社會的原理。公眾需要明白對抗原子化危機的緊迫性關系到我們如何與中共競賽以及如何扭轉局勢,而這條由斯多葛主義和哈維爾主義構造而成的新賽道還將開啟一個時代浪潮。
現在我們首先要問:什麼是社會原子化?中國的社會原子化是怎麼回事?要解釋社會原子化,我們必須先了解社會原子論。
關於社會原子論,有一個比較經典的解釋來自美國哲學家伊麗莎白·沃佳思,她在1987年出版的《正義的語法》一書中提出存在兩種社會原子論,一種是霍布斯式的,另一種是洛克式的。霍布斯式社會原子論的典型特點就是:每個人都受到激情驅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既表現出人愛自由的天性,又表現出人愛主宰他人的天性,其結果就是人們像氣體分子一樣各行其是,互相碰撞、互相沖突,形成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大混戰。在洛克式社會原子論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並不是天然就處於戰爭狀態,人們大體上可以和平共存,但是由於存在道德墮落的風險,人們結成社會契約,讓渡一部分權利給政府用來防范道德墮落;但是人本性上通常不需要政府約束,政府的政治權力是個體授權的結果,人們既可以授權保留政府權威,也可以撤回授權重新選擇新的政府權威。
在洛克式社會原子論中,政治權威的基礎是個體的獨立和自主,而人們締結社會契約是充分尊重個體權利才做出的選擇。在霍布斯式社會原子論中,人們出於生存安全考慮才創立政府,人們把政府保護集體生命安全作為不推翻政府的底線。
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在洛克式社會原子論中,人首先是一個道德動物,因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道德約束;但在霍布斯式社會原子論中,個體的天性就是與任何人為敵,因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相當弱化,乃至不存在道德約束。現在我們明顯可以看出:洛克式社會原子論是現代社會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觀念的原始根基,其國家功能是既保障個體生命財產安全,又保障個體自由權利;而霍布斯式社會原子論則具有典型的威權主義特點,其國家功能僅限於保障集體生命安全。
根據中國官方流行的一種說法,生存權和發展權就是首要的基本人權,這種表述就是非常典型的霍布斯式威權主義表述,因為把國家功能簡單看成是保障集體生存;而普通中國民眾想象的忍受政府壓迫的底線,剛好也是不餓肚子、不死於戰亂。但共產主義國家的大飢荒歷史告訴我們,以生存權為底線的社會實際上等於沒有底線,為了生存而忍受壓迫的人只會無窮無盡地忍受壓迫,即使餓死也不會觸及到他們的底線。這就毫不奇怪國民在談論社會原子化的時候,通常默認中國存在霍布斯式社會原子化,也就是說,默認人與人之間存在潛在的敵對關系或者無效關系,並且缺乏有效的道德約束。
根據中國社會學家田毅鵬和呂方在2010年的研究,中國的社會原子化指的是:由於人類社會最重要的社會聯結機制「中間組織」解體或缺失,而產生個體孤獨和無序互動狀態,以及道德解組、人際疏離、社會失范等社會總體性危機。依據田毅鵬和呂方的說法,中國的社會原子化表現為社會聯結機制缺失,結構層面斷裂,出現了無社會聯結的群眾,社會成員之間缺乏有效互動,公共生活匱乏,公共性孱弱;社會陷入無序和混亂,道德共識瓦解,底線失守。在個體層面,則是「普遍的漠不關心」,即對公共問題缺乏熱情,寄希望於個人的努力而對與他人合作共同解決問題缺乏信心和興趣,陷入狹隘的個體主義情緒;在消極中生存,而不思考或者看不到解決共同問題的可能途徑;道德感模糊,公益行為艱難;在社會階層序列之外出現了組織程度極弱的松散個體,陷入生存和發展的「組織貧困」狀態;中產階層雖然出現了一定的公益熱情,但由於缺乏以結社形式發揮積極作用的訓練和支持而表現出混亂無序。社會原子化危機的實質在於中間組織缺失,即個人直接面對組織化的權力,表現出精神上的孤獨無助和思想行為上的混亂,以及個體之間缺乏積極的、建設性的集體行動的資源和能力。
然而我們並不能完全同意田毅鵬和呂方點到為止的表述,尤其他們把中國的社會原子化看成是一般只在社會轉型期才出現的危機。比如田毅鵬在2012年一篇論文中說,中國的社會原子化是由單位體制消解、城鄉二元體制沒落、鄉村社會衰落、社會人口流動性加劇造成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改革開放初期至胡錦濤時代的社會危機。這種問題取向,沒有解釋毛澤東時代通過大規模群眾運動破壞農村和城市的社會結構、消滅社會階級、鼓動無政府暴亂,最終粉碎了中國的社會紐帶,直接促成了社會原子化。那時候告密之風盛行,人人互相舉報,此外,學生毆打老師、親友反目成仇、鄰裡變成戰場、家庭人倫關系遭遇滅頂之災,只有中國人共同的精神領袖毛澤東在形式上維系一盤散沙的社會。
中共政權雖然一度利用依托計劃經濟體制的單位制度來實現資源分配和社會整合,但是單位制度的真正用途不是用來克服社會原子化,而是用來強化社會控制,社會控制最多是約束原子化的個體而不是消除原子化,而單位制度解體不過是撤銷控制和約束,把原本已經原子化的個體釋放出來。
另外,田毅鵬和呂方的解釋,也無助於說明後轉型期中國是否還會存在原子化問題。我們看到他們所描述的社會原子化特征至今也十分典型,所以現在中國到底是處在後轉型期還是處在一眼望不到盡頭的轉型期中?不論如何,我們都必須承認中國社會至今飽受社會原子化困擾。
隨著社會矛盾尖銳化,社會戾氣逐年升高,無差別襲擊和報復社會案件層出不窮;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對民主運動的敵意越來越深;犬儒主義橫行,憤世嫉俗泛濫,甚至連反對政府的民間人士也一樣對民主運動充滿戾氣和偏見,用民小來諷刺一切改變社會的努力,就好像什麼也不做只要詛咒社會就是唯一的智慧;不管是親政府還是反政府,人們都顯露出相當粗鄙的暴戾習氣,人們漫無目的地互相攻擊、互相指責,還有認知錯亂無休止地擴大社會敵對情緒……基於種種亂象,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的社會原子化危機正在演變成肉眼可見的災難,小到反復催生孤狼式恐怖主義,大到制造暴政循環,除了一邊勸人移民一邊鼓吹打擊華人移民之外,沒有人關心如何改變現狀,到處都是憤世嫉俗,有人甚至打著基督教幌子宣揚針對本民族的種族仇恨。
現在我們要問:中共政府做了哪些努力來克服社會原子化危機呢?我們前面引用的田毅鵬2012年論文說,單位體制消解、城鄉二元體制沒落、鄉村社會衰落、社會人口流動性加劇等因素,是造成中國社會轉型期原子化危機的重要原因。其中單位體制解體趨勢從改革開放初期就開始了,但在江澤民時代達到高潮,根據中國經濟數據庫相關統計數據顯示,1995-2003年間國企改革導致約4400萬國企職工下崗,約佔國企職工總人數40%。另據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家李路路2013年統計,國有和集體單位就業人口佔城鎮全體就業人口比重,從1980年的99.2%下降到2009年的20.5%。公有制企事業單位就業人口大批流失,確實是單位體制解體的具體表現。
伴隨著單位體制解體趨勢,1994年分稅制改革還加劇了地方政府之間的GDP錦標賽,這個GDP錦標賽催生出嚴重的土地財政問題,而征地和拆遷還引發了尖銳的社會矛盾。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從最遲1993年起中國社會的群體性事件開始呈現逐年暴增趨勢。中國官方所說的群體性事件主要指集體上訪、集體抗議、集體維權、乃至中小規模暴動,由於圍繞具體糾紛、不關心普遍權利訴求或者缺少政治訴求,這些群體性事件稱不上是社會運動。
其中除了拆遷糾紛之外,從公有制企事業單位下崗失業人口,也是這些群體性事件的重要參與者。這些群體性事件圍繞具體糾紛,遍地開花、但是彼此孤立,沒有串聯成席卷全國的社會運動,這種特征是社會危機原子化的典型特點。9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多次爆發針對美日韓法等國的示威活動,這些活動也是當局定性的群體性事件,但它們是排外活動,與公民運動無關。
另外,中國大陸也有零星的社會運動,比如2011年中國大陸響應過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2012年許志永等人發起過新公民運動,還有2018年佳士工人運動,這些也屬於群體性事件,它們的發生方式也具有原子化特點,最終都沒有形成全國響應,其根本障礙還在於社會過度原子化。
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家應星據相關部門不完全統計,中國社會的群體性事件從1993年1萬起,逐年增長至2004年7.4萬起,年均增長17%;參與者從73萬增至376萬,年均增長12%。2007年群體性事件則高達8萬余起。據清華大學社會學家孫立平推算,僅2010年一年群體性事件就高達18萬起。人民網2009年援引不完全統計稱,2005年群體性事件高達8.7萬起,2006年超過9萬起,而2008年數量和規模都要超過以往,但當局不便公開具體數據。由於群體性事件逐年攀升,中國國家統計局後來停止公布有關數據。
與此同時,中國同期信訪數量也在逐年攀升。根據中國社科院于建嶸教授2009年的說法,從1992年起,中國信訪總量連續11年攀升,並在2003年形成了信訪洪峰。于建嶸拿到的統計數據是:2003年全國信訪部門共受理1272.3萬件次信訪。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還曾表示,每個月有800-1000封舉報信經過層層篩選上報到他手裡。
信訪案件和群體性事件暴增,從不同側面折射出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了應對日益升高的社會矛盾,1998年江澤民政府成立了中央維穩小組,2000年又升級成中央維穩辦,直到2018年並入中央政法委。維穩系統以政法系統為中樞,
滲透到各級政法機關、安全部門、信訪部門和企事業單位,一方面充當動員協調機制,另一方面同時用於強化中央對各級部門的直接控制和調度。維穩課題成了胡錦濤政府重中之重,胡錦濤政府的標志性執政理念「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都是圍繞維穩來設計的。維穩系統每年開支堪比軍費,就像是一場針對人民和鎮壓內亂的游擊戰爭。除了鎮壓邏輯之外,胡錦濤政府的另一手准備,就是重新樹立一套價值體系來克服改革開放以來的三信危機。所謂三信危機是指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對共產黨的信任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三信危機是意識形態根基動搖造成的,這使得胡錦濤政府從一上台就特別重視意識形態重建工作。
2002年12月,才接任總書記的胡錦濤就立即趕往中共革命聖地西柏坡朝聖。胡錦濤在這次朝聖過程中,故意援引毛澤東「兩個務必「來表態支持毛澤東政治遺產,尤其是胡錦濤故意輕描淡寫江澤民三個代表思想最重要的第一點,即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胡錦濤特別強調三個代表的民粹主義層面,即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個側重點顯然有意緩解當時日漸尖銳的社會矛盾,這與後來提出和諧社會理念一脈相承。
胡錦濤的表態被認為是公開偏離江澤民的重商思想,有意將工作重心放在意識形態重建工作上。中國國家行政學院竹立家教授曾對香港《南華早報》說,胡錦濤政府執政十年就算不是十年倒退,也是停滯的十年。期間人民與政府之間的不信任已經達到了沸點,隨著當局不斷壓制公眾輿論,公眾對政府的信心也在崩塌。竹立家說,胡錦濤政府提出了一大堆問題,但是並沒有真心實意解決任何一個問題。像改革停滯和改革倒退這類說法在胡錦濤時代非常常見。
2012年12月,新接任總書記的習近平選擇的第一個朝聖地點是深圳,這一度被認為是重新啟動改革開放的信號,盡管後來我們發現:即使習近平集中這麼大權力,改革開放依舊推行不下去,反而批判習近平政府開改革倒車的聲音淹沒了先前對胡錦濤政府的批評。胡錦濤政府在2006年就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但直到下台也沒有取得進展,胡錦濤只在十八大報告用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給自己沒有建樹的十年畫上一個潦草的句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要用意識形態來克服三信危機,但胡錦濤和習近平兩屆政府都沒有取得進展。
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說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習近平稍後在2013年1月5日用「兩個不能否定」來響應胡錦濤說的「兩個不走」。不管是胡錦濤還是習近平,兩屆政府都明確表態:不與毛澤東時代切割,避免重蹈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導致蘇聯意識形態根基動搖的覆轍。
以上我們講了這麼多,就是為了說明:胡錦濤和習近平時代重新祭起意識形態大旗,是為了應對不斷升高的社會矛盾和迫在眉睫的原子化危機。客觀來講,習近平政府在意識形態工作上比胡錦濤政府更有建樹,現在人誤以為胡錦濤政府更開明,恰恰是因為胡錦濤政府提出了一大堆問題卻不解決問題。公眾並沒有意識到胡錦濤政府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視程度,等看到習近平政府大刀闊斧地復活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斗爭,公眾才恍然驚覺意識形態的幽靈又回來了,但實際上這個幽靈在胡錦濤時代就已經回來了。
國際學術界還注意到,從改革開放初期到胡錦濤時代,中國社會存在嚴重的社會動員障礙。社會動員機制失靈,跟權力碎片化、市場碎片化以及中央集權體制失能有直接關系,但是從根本上來說,問題根源仍然出在社會原子化程度過高:迫於對專制政權的恐懼,國民被動生存,盡管有諸多不滿,但是習慣性逆來順受;一方面對公共事務缺乏參與熱情,另一方面既不信任自己也不信任其他人有能力改變令人失望的社會現狀,結果只維持一盤散沙狀態。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江澤民政府開始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來動員社會。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中國社會的民族主義情緒在隨後的抗議活動得到初次檢驗。後來在胡錦濤時代,中國大陸接連爆發三次大規模反日示威浪潮,更是把民族主義推向歷史高峰。但不管是民族主義還是意識形態工具,中共政府都沒能夠有效調動社會克服原子化危機。
我們必須在這裡說清楚:中共政府克服社會原子化危機的動機不是創造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是專制統治的敵人,中共政府只希望創造更好的專制統治土壤,讓國民更積極支持和維護專制統治,摧毀國民的反抗信心,保障特權階級利益不受挑戰。習近平政府采取多重復合手段,一邊軟硬兼施地動員社會,一邊推行更加嚴酷的政治高壓。政治高壓這一點是所有人最直觀的感受:在網絡審查、出版審查、新聞審查和社會控制等方面,習近平政府比以往歷屆政府都更加嚴厲,同時還加強了互聯網封鎖技術,控制信息流通;還有打擊維權活動、抓捕人權律師、迫害記者和媒體人、設立征信系統、推行網格化管理、實施大數據監控、取締和驅逐非政府組織等等。這種白色恐怖所制造的寒蟬效應是立竿見影的。才十幾年時間,中國社會就翻出了壓箱底的祖傳手藝,主動進行自我審查和互相舉報,還有全民獵巫式的社會揭發和社會批斗,直追毛澤東時代的動亂傳統。
另一方面,習近平政府也軟硬兼施地動員社會,比如發起針對習近平本人的學習活動和個人崇拜,不僅鼓勵社會背誦習近平語錄,還強迫學校和各級黨政機關使用「學習強國」等軟件積分打卡,這種動員形式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動員性質。中共還有很多動員手段,比如2021年的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像這類動員活動在習近平時代非常常見,有時候以座談會、學習小組、討論會、主題教育活動、學習活動等不同面目出現。中共的策略就是通過反復社會動員來克服人心不齊和政令不暢的困境,最重要的是,每一次社會動員都是向社會的各個環節灌輸意識形態。
我們先前引用過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家麗莎·魏丁的說法,意識形態本身就是一套不靠內容說服、而是側重從形式上馴服的政治手段。這些社會動員就是意識形態本身在發揮凝聚社會力量的作用。除了利用意識形態動員社會之外,習近平政府多次發起群眾運動,比如垃圾革命、廁所革命、餐桌革命和污水革命,這類社會動員形式是從毛澤東時代群眾運動中借鑑過來的,其目的就是激活國家對社會的動員能力。
一般民眾看見這類動員活動成了爛尾工程,以為沒有什麼社會影響,但是在中共中央眼中,每一次動員都是對官僚系統和社會各界的反復考驗、試探和馴化,就此而言他們肯定達到了目的。
中共還利用工會和工商聯合會來強化社會組織動員和對內統戰工作。通常人們忽視工會在中國的作用,因為中國的工會並不是獨立工會。但是由中共把持的工會具有強化社會控制和協助社會動員的功能,也就是說其職能既是監控和鎮壓工人運動,也是中共備用的社會動員手段。至於工商聯合會,除了作為統戰機關外,其機構功能也包括控制和動員工商業界。
不僅如此,習近平政府還反復動員年輕人去西部、到農村、下基層,評論界諷刺這種政策是復活毛澤東時代的「上山下鄉」運動,這種揣測引起不少恐慌,但這項動員缺少強制手段,青年群體對此反應冷淡,這與毛澤東的強大動員力不可同日而語。習近平政府鼓吹新「上山下鄉」運動具有多重政治用義,人們猜測最多的是解決城市就業人口壓力,防止失業人口在城市聚集成為動亂隱患。
但是站在政策制定者角度來看,中共當局的決策意圖還有另外三個方面:一是農業人口大規模流失對農村地區造成不可逆的破壞性影響;二是經濟落後地區人口向大中型城市流動,加劇區域發展不平衡和大城市人口壓力;三是中共推行的農村基層民主選舉試驗宣告破產,這意味著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道路已經行不通了。
面對這些難題,中共當局的反省是向農村和基層輸送新鮮血液,利用年輕人來重新組織社會結構和重新進行改革試驗。
我們在前面引用田毅鵬2012年研究,說農村社會變化也直接促成了轉型期的社會原子化問題。中共推行的農村政策是一邊著手發展農村政治經濟,一邊著手重塑農村社會結構。向農村輸送新鮮血液,且不論現實中有沒有可行性,但理論上確實既有利於振興農村經濟,也有利於農村基層改革實踐,還有一個更隱蔽但同樣重要的意圖是利用年輕人來改造農村社會結構。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和同年發布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曾提出過一個新概念叫鄉賢。所謂鄉賢,大致包括宗族權威、經濟權威和文化權威三種形式。在中共建政以前,地主和鄉紳通常扮演著現在所謂的鄉賢角色,他們在實際生活中組織動員和領導鄉村社會。
中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曾經注意到中國社會存在雙軌政治。有人將之總結為:皇權不下縣,縣下行自治。也就是說過去皇帝權力只統治到縣一級,縣以下則實行地方自治,而士紳、地主和宗族長老通常就在縣以下實際領導社會。中共官場至今還在說處長治國或縣長治國,這說明這種雙軌政治至今仍然存在。
以前士紳、地主和宗族長老不僅是基層社會的實際領導者、組織者和動員者,也是地方社會的凝聚力量和道德權威,也就是說正是因為有這些人在,中國傳統社會才不是一盤散沙的原子化社會。但是中共建政以來大力推行土地改革,對士紳、地主、富農和宗族長老進行物理消滅,徹底毀壞了中國農村的傳統社會結構。形象地說,就是把農村原本的有機結構碾成了粉末,造成道德真空和原子化的個體。毛澤東的個人統治就建立在打倒一切權威、只以毛本人為唯一權威的基礎上,因為一盤散沙的社會更有利於毛澤東推行個人崇拜和極權統治。毛澤東的個人權威不僅直接下達到農村,甚至直接登堂入室進入到每家每戶,這種情況被認為是終結了雙軌政治,實現了單軌政治。
但是到了改革開放時代,不再推行個人崇拜了,單軌政治隨即崩潰,一盤散沙的社會不斷造成新的治理難題,我們前面提到的各種原子化危機就是這麼來的。現在中共當局意識到這些問題,就想在基層重新塑造階級來穩定基層社會,但是因為基層社會高度原子化,已經普遍不存在傳統的社會凝聚力了,於是中共就想借助「鄉賢「來重新組織基層社會結構。現在中國就處在單軌政治崩潰、新的雙軌政治沒有完整建立起來的階段。
我們看見中共設法向基層輸送新鮮血液的嘗試並不是完全失敗的,大學生村官越來越多,基層公務員高學歷和名校背景也越來越多,這些現象都是在為培養新鄉賢做准備,即使這些年輕人30歲以後可能升職調到縣裡,但還會有其他年輕人源源不斷地填充上來。這就是中共要達到的目的:中共希望借助新鮮血液重新改造縣以下社會,增強其內在凝聚力,從基層遏止社會動亂源頭。
回顧中共應對原子化社會危機的策略,其關鍵就是一手鎮壓一手動員,那麼其成功率有多大呢?我們看到中共在鎮壓和動員方面有著非常充實的工具箱,這些政治手段有著強烈的功利主義色彩:與其說它們是要增強社會團結,不如說它們是要保障社會時時刻刻服從於中共的政治權威。中共做的事情非但不是促進社會團結,反而是加深中國社會的原子化程度。
中共統治手段的最典型特點就是煽動社會仇恨:一方面利用黨國宣傳機器和虛假歷史敘述,煽動民族主義仇外情緒來團結底層社會;另一方面則挑起群眾斗群眾,利用狹隘的愛國主義來攻擊社會內部的假想敵。不僅如此,中共官方喉舌使用的暴力語言也不斷影響社會,給普通人造成暴力內化的效果,中國民間日漸高漲的社會戾氣就跟這種暴力內化有直接關系:不止是中共政權支持者直接沿用喉舌媒體的暴力語言,連中共政權的反對者也一樣充滿暴力意識。中國社會彌漫的語言暴力和暴力語言,與中共政府及其喉舌自身粗暴的用語習慣密不可分。習近平要求反腐敗運動刀刃向內、刮骨療毒,蔡奇清理北京低端人口時要求敢於刺刀見紅硬碰硬,這種殺氣騰騰的用語習慣在中共看來是表示決心和果敢,但他們意識不到這是一種刻骨的暴力習性。中共喉舌近年更是學起潑婦罵街,央視和《人民日報》接連幾天大篇幅謾罵美國前國務卿彭佩奧,《北京日報》罵彭佩奧是肥豬、罵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是腦殘,中國駐法大使館還公開罵批評者是瘋狗。中共把粗暴表態視為一種斗爭姿態,其支持者聽到直呼霸氣過癮,其反對者往往也以粗暴語言回敬。中共使用的粗暴用語也滲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用語中,像比如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中國人不吃這一套、你沒有資格、嚴厲打擊、堅決反對、抹黑、造謠、雙標、恨國、潑髒水、甩鍋、扣帽子等等。這類詞匯塑造了中國網民的思維模式,人們一遇到不同意見就立刻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樣做出條件反射。
簡單粗暴的語言與簡單粗暴的思維和簡單粗暴的觀念,這三者互為表裡。這樣一來,民眾很容易就形成非此即彼的二極管思維,而社會戾氣和社會仇恨就借助暴力環境瘋狂生長。社會戾氣是指這樣一種文化環境,在其中人們不僅暴躁易怒,還習慣性用最壞的惡意和最大的敵意來揣測他人的動機,並且首先考慮用暴力來解決一切問題。在這樣的環境中,個體不僅被原子化了,還不再信任社會、不再信任其他人,還很容易就與人為敵。也就是說,中共雖然通過一系列手段來遏止原子化危機,但其同時也在煽動社會仇恨、塑造暴力意識、助長社會戾氣。中共還嚴厲禁止社會團結,禁止社會自發組織和自主動員,嚴密控制社會各個環節,尤其是環環相扣地監控學生運動,不允許大學生自發組織和影響社會。社會不僅喪失了自組織能力,還無法實現有機團結,這樣不僅社會原子化程度更深了,還削弱了社會自發反抗專制統治的能力,加之社會不公和安全感缺失,把絕望和幻滅變成了時代病。
原子化社會與公民社會不同:公民社會是有機整合的,即使是多元化的,其社會團結沒有遭到破壞,社會可以不受政府控制,自發組織、自發動員;但是原子化社會是一盤散沙,其社會團結遭到嚴重破壞,社會不僅難以自發組織和動員,甚至政府也可能無法有效動員社會。
我們看見習近平政府反復動員社會,實際上反而是因為動員障礙太大才需要反復動員,如果每次動員都取得大成功,反而沒有反復動員的必要了。所以如果沿著中共的統治邏輯來看問題就會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越是想要動員社會就越是沒辦法動員社會。如果我們也沿用這套邏輯,也會掉入這個陷阱。如果我們要學中共去動員社會,情況對我們會更不利,我們只會更被動、更無力引起響應。
現在我們要追問:我們具體要怎麼做才能克服社會原子化和開啟時代浪潮呢? 托克維爾、孔德、涂爾干曾經解釋過社會原子化可能造成暴政和極權主義,而漢娜·阿倫特則淋漓盡致地分析了由社會原子化促成的極權主義災難;在冷戰期間,極權主義的社會原子化也被認為是共產主義政權的一個重要特征。我們不得不合理懷疑,中國社會在習近平時代向極權主義國家的大踏步倒退,與中國社會的原子化危機也有著深層次關聯。
田毅鵬和呂方認為是聯結人類社會的「中間組織」解體或缺失造成社會原子化。這個「中間組織」通常指以結社、集會、游行和非官方出版物等形式參與公共生活。在民主國家,獨立工會也起到同樣的作用;但這些在極權主義國家是嚴密監視和打擊對象。
那麼,除此之外,是不是沒有其他辦法來克服中國社會的原子化危機了?我們感到迫切需要升級當前的社會運動理論,因為革新運動形式仍然可能重建有意義的公共生活。
我們看見中東歐和波羅的海等前共產主義國家,在擺脫共產主義政權前夜就成功克服了社會原子化,捷克出現了七七憲章運動,波蘭出現了團結工會,波羅的海出現了長度超過675公裡的人鏈,還有一系列大大小小難以統計的社會運動在冷戰晚期此起彼伏,連綿不斷。
社會運動此起彼伏恰恰是社會自組織能力恢復、社會團結加強和主動抗拒社會原子化的表現。但是在缺少社會運動引領的俄羅斯,民主轉型失敗了,其嚴重的社會原子化危機至今仍飽受詬病。1993年俄羅斯憲政危機期間,高度原子化的俄羅斯社會一潭死水,莫斯科居民湧上街頭,像看戲一樣看葉利欽指揮坦克炮打白宮,也就是俄羅斯議會所在地。從那以後俄羅斯社會轉型希望徹底覆滅。在最需要公民社會干預總統和議會斗爭的時候,絕大部分俄羅斯民眾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反而憤世嫉俗地期盼政治斗爭造成兩敗俱傷。俄羅斯民眾不理解自己的苦難是什麼造成的,蘇聯的灰燼還沒冷卻,俄羅斯人就已經開始懷念蘇聯時代,他們比誰都盼望強人政治回歸,恢復蘇聯榮光。
差不多在中東歐和波羅的海國家醞釀社會變革風暴的同一時期,韓國和台灣也經歷了大大小小無數次社會運動,這些運動都是頂著政治高壓進行的。現在很多人只記得1987年六月運動,忘記此前韓國民眾為重建公民社會組織過多少次社會運動。即使在朴正熙鐵血統治的最黑暗時代裡,韓國大學生也一樣冒死組織學生運動。在全斗煥血腥鎮壓光州民主化運動之後,韓國大學生反而越挫越勇,並沒有像六四運動被鎮壓以後的中國大學生那樣偃旗息鼓。光州事件以後,韓國大學生繼續發動此起彼伏的學生運動,而且這些學生運動不再僅僅以反政府為目的,而是致力於建立一個以科學和民主為導向的社會,也就是說反政府只是手段,民主化才是目的。1984年和1985年韓國接連爆發兩撥大規模學生運動,甚至還干脆把光州起義的口號跟訴求原封不動地打出來,堂而皇之地挑釁全斗煥政府。從70年代到80年代,在幾代學生運動前僕後繼的引領下,韓國社會運動也遍地開花,全斗煥政府也一樣毫不留情地殺人,但是嚴酷鎮壓也成就了付出巨大犧牲的社會運動,最終韓國民主運動通過持續不斷的斗爭徹底改變了當時韓國的政治環境,把獨裁逼到了窮途末路。
現在人們紀念台灣1990年的野百合運動,也忘記了在野百合之前還有一系列學生運動、人權運動、勞工運動、原住民運動、女權運動、環保運動、農民運動等抗爭活動在台灣遍地開花,期間還爆發了震動台灣社會的中壢事件和美麗島事件。也就是說,台灣社會連綿不絕的抗爭運動即便在白色恐怖時期也沒有停止過,這與韓國很像,與此相反,中國的社會運動在遇到一次流血鎮壓以後就幾乎偃旗息鼓。國民黨政府對於社會運動的鎮壓絲毫不比中共政府心慈手軟,除了大搜捕之外,國民黨政府也一樣利用特務和黑道勢力實施暗殺活動,一些密謀起義的政治犯還被判處死刑。只要人們不主動屈服於白色恐怖,白色恐怖就沒有能力扼殺社會的反抗決心。不見得只有中共政府的子彈才殺人,其他獨裁政權的子彈也一樣殺人,但是死亡沒有嚇退韓國人和台灣人,根本原因就在於層出不窮的社會運動把社會組織起來了。
有人抱怨說,那些成功實現民主轉型的國家是先有公民社會根基才有社會運動。這種論調是顛倒了因果關系,因為韓國和台灣的案例告訴我們:公民社會從來不是獨裁政權恩賜的,而是透過一代又一代人持續不斷抗爭得來的。1980年代中國曾經短暫形成過公民社會,這是1986年學潮和1989年學潮的時代背景,其序曲是1978-1979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從那以後,中國社會陸陸續續出現了大量民間結社、集會、游行和非官方刊物,包括自由派陣營在內多個社會思潮都有自己的輿論陣地,這些情況恰恰是公民社會興起的表現。相比之下,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和軍政府獨裁下的韓國,根本沒有中國1980年代的寬松環境,反而刺刀跟子彈仍然壓不住韓國和台灣社會層出不窮的抗爭運動。
1989年六四運動被鎮壓以後,中國的公民社會逐漸解體,非政府組織紛紛遭到取締和驅逐,自由派輿論陣地包括《世界經濟導報》、《炎黃春秋》、《南方周末》等等,要麼被強行關停,要麼被整頓噤聲。韓國和台灣的公民社會反復解體又反復重建,這與堅持抗爭團結社會息息相關。中國的公民社會解體之後就再也沒有大規模社會運動來重新集結社會。民間對自由派人士怨恨日益增加,國民不僅不理解社會運動是現代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反而把社會運動說成是暴亂和外國代理人。反智主義、犬儒主義、認知混亂、社會戾氣和各種形式的狹隘主義大行其道,傳統社會結構被共產主義革命毀壞,加之公民社會解體,這才造成現在中國的社會原子化危機。現在中國人自暴自棄、得過且過,比起1980年代那種自信和朝氣,不可同日而語。
時代精神的落潮不是平白無故的,連續幾代人萎靡不振與社會原子化程度密切相關。公民社會的形成條件絕不是因為執政當局突然開明起來,而是社會通過反復集結和反復抗爭,恢復了自我組織、自我動員能力,重新為形成和傳播社會思潮創造條件。也就是說社會克服了原子化狀態,人與人之間克服了普遍的不信任和敵對關系,人們學會了合作,人們不再濫用犬儒主義、反智主義和社會戾氣來撲殺社會思潮,人們停止內耗,轉而把政治熱情轉移到挑戰專制權威和推動社會變革之上。現在的中國民眾不僅忘記了公民社會的樣子,還忘記了自己具備重建公民社會的能力。
不管是什麼樣的社會運動,哪怕是每一次都失敗,只要層出不窮地爆發出來,每一次集結起來都會鼓舞社會。在白紙運動之前,許多人不敢想象參加社會運動是什麼體驗,但在參加過一次之後,人們發現自己不但受到了時代精神感召,還變得更加勇敢、更加堅定、更能夠與社會共情,更重要的是,更懂得團結和協作。
參與社會運動讓我們忘記了平庸生活的全部猥瑣和卑微,參與社會運動讓我們變得自信和勇敢起來,參與社會運動讓我們意識到我們不僅需要同伴也被同伴所需要……我們看到人們在街頭喋血,我們看到人們流著淚前僕後繼,我們看到不斷有人說這是我的責任,我們看到有人站出來大聲疾呼引來熱烈喝彩,我們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明知道會失敗的社會行動中,我們的勇敢引起熱烈響應。這就是社會共情,是社會運動重新鼓舞我們、重新把我們聯結起來,是社會運動教會我們互相掩護、共同進退,是社會運動教會我們每個人對其他人負有道德責任。
社會運動就是這樣,它把每一個人的政治熱情匯聚起來變成時代浪潮。這些就是社會運動突破社會心理障礙、克服社會原子化的基本原理。我們在這裡要再一次強調我們在本系列影片第一期講到的情況,社會運動並不簡單等同於街頭運動,一場成功的社會運動應該發生在街頭運動之前,否則街頭運動要麼鼓動不起來,要麼每一次都變成孤注一擲的豪賭。這是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運動和哈維爾思想給予我們的最重要啟發:改變社會必須先克服社會原子化和結束一盤散沙的社會現狀,這就是先於街頭運動的社會運動原理。
我們在第一期影片講要把社會運動主戰場從街頭轉向社會,就是這個原理。把社會運動轉向社會意味著我們要跟社會原子化作戰,我們要結束無窮無盡的精神內耗,我們要一起面對我們共同的敵人。我們的敵人是關押記者、律師、企業家、政治犯和良心犯的極權國家。把社會運動主戰場從街頭轉向社會就像是用玫瑰戰勝槍炮,這裡不是說把玫瑰插在鎮暴軍警的槍口上,而是說把玫瑰獻給普通人,玫瑰代表我們和解,玫瑰代表我們停止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大混戰,玫瑰代表我們願意重新締結社會契約,玫瑰代表我們撤回向中共政府授權,玫瑰代表我們決心結成社會聯盟來推動時代變革。
我們當然會遭到來自當局的污蔑和抹黑,我們為每一個國民的權益斗爭,總會有人跳出來上綱上線大罵你是殖人、漢奸、走狗、賣國賊。但是我們並不在任何地方暴動,我們並不代表外國政府,國家沒有一寸土地屬於人民,甚至連我們自己的財產都得不到安全保障,我們沒有什麼可以拿來出賣的,我們每個人只代表自己。我們要結束社會原子化和人與人之間的泛戰爭狀態,我們要重建人的自信和尊嚴,我們要恢復社會信任、強化社會紐帶、對抗社會潰敗……這些行為沒有一樣是犯罪。
我們沒有過剩的仇恨需要宣洩,我們不卑不亢地面對來勢洶洶的反對者,我們要用玫瑰來迎接匕首,我們要像時代浪潮一樣前僕後繼地沖刷不寬容的社會。憤世嫉俗的犬儒主義分子一樣會在我們背後插刀子,他們習慣性冷嘲熱諷,他們是社會運動落潮之後長期看不到社會出路造成的,他們也曾對中國社會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今我們要爭口氣來改變社會的時候,他們反而朝我們丟石頭,成了阻擋社會變革的障礙。過剩的怨恨和不信任橫亙在他們與現實之間,使他們主觀上放棄了改變現實的動機。他們用一種玩世不恭的游戲態度嘲笑一切價值,他們沒有方向,他們漫無目的地攻擊所有人,最終他們也互相攻擊。憤世嫉俗、玩世不恭和懷疑一切都不是政治,政治家的品格是寬容它們,而不是成為它們。政治理性和政治智慧總是能夠自我克制的。隨心所欲地發洩情緒,隨心所欲地耍小聰明、抖機靈,這類行為無法代替政治智慧來履行社會責任。我們更加信任那些懂得克制、具有政治家品格、並不熱衷於挑起內斗的伙伴,因為我們相信只有穩定可靠的肩膀才能肩負起重大的社會責任。
而憤世嫉俗只會撕裂社會、不會團結社會,憤世嫉俗無助於結束社會原子化,反而加劇人與人之間的敵對關系,這反而才是犬儒主義最脫離現實的地方:他們既不滿於現狀,又反對改變現狀,甚至攻擊一切改變現狀的努力,他們的桀驁不馴底下掩藏著很深的精神痛苦。
我們看到甚至連中共當局也在設法解決社會原子化問題,那我們就更要引起警惕了。因為解決社會原子化問題就是兩種路線的競爭:如果中共率先達到目的,強化了社會對其政權的忠誠和團結,那麼暴政和極權統治就會越來越穩固;相反,如果是我們率先達到目的,形成了反對派政治,那麼社會變革的時代浪潮就勢不可當了。在接下來的幾期節目中,我們還要詳細探討我們該怎麼做才能把社會運動引向社會,我們將挨個攻破阻擋在我們面前的社會心理障礙,把行動原則和信念播種在每個人心裡,最重要的是要讓每個人明白:將自己與他人的命運聯結起來關系到我們共同的未來。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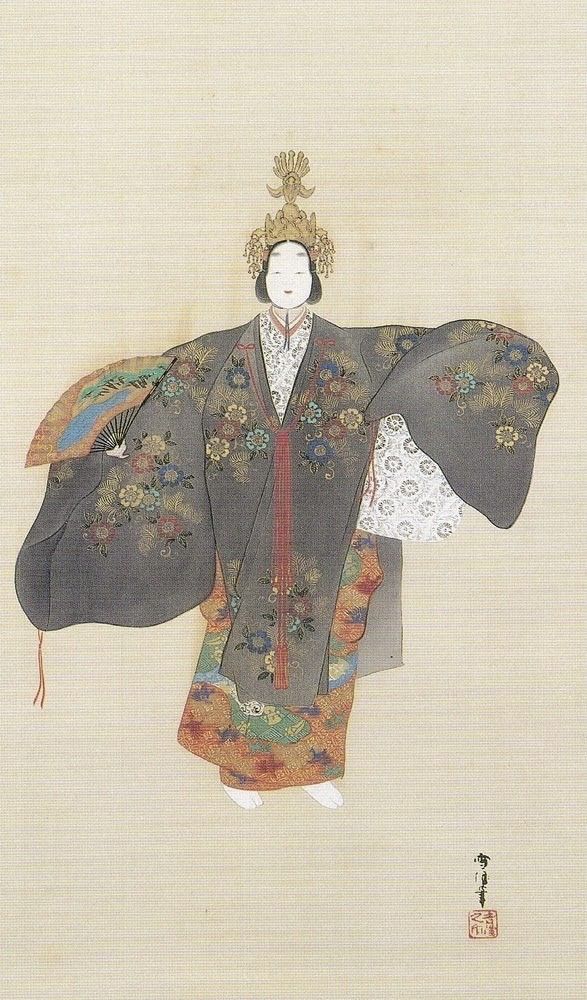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