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重大辯論 Ep. 6】Descartes vs. Bacon on Rationalism vs. Empiricism & “Man’s Conquest of N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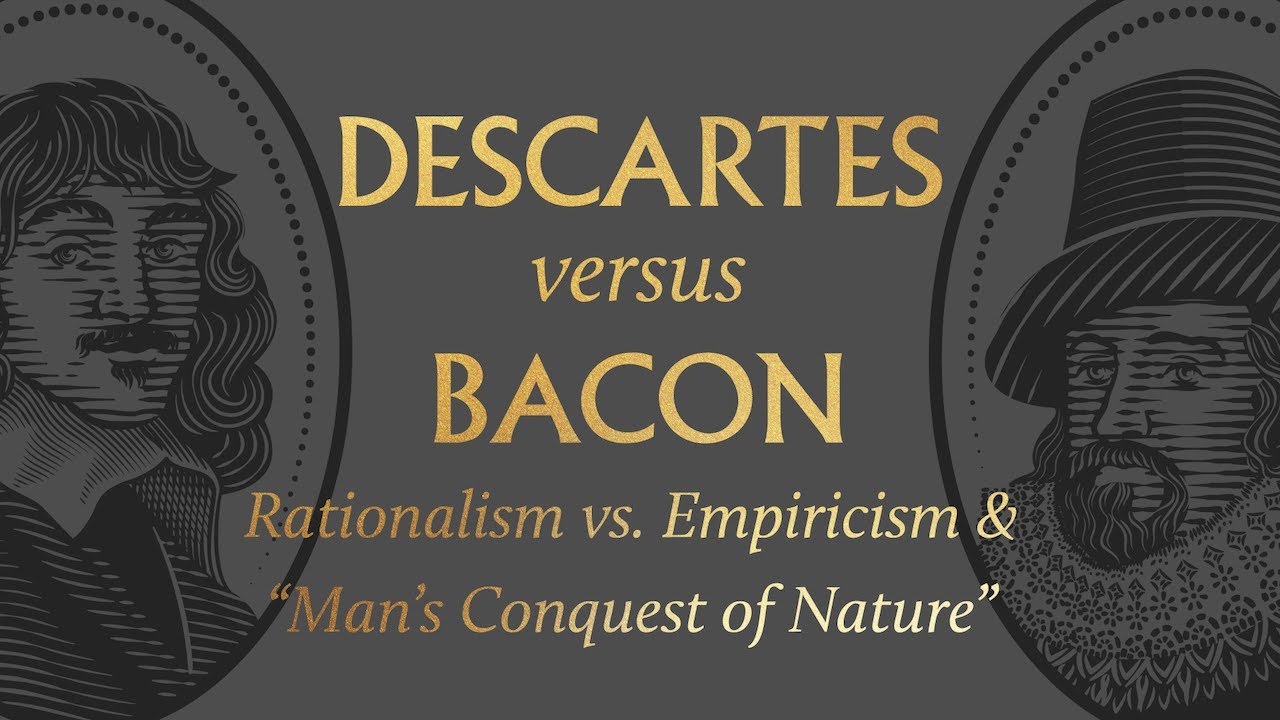
簡介
In lecture 6, Dr. Kreeft contrasts Descartes, who is universally known as the father of modern philosophy and a rationalist, and Bacon, who is an empiricist. These two philosophers, though taking opposite epistemological approaches, find agreement in their view of the greatest good of human life—the conquest and mastering of nature.
在第六堂課中,克里夫博士(Dr. Kreeft)對比了被普遍認為是現代哲學之父和理性主義者的笛卡爾,以及經驗主義者培根。這兩位哲學家雖然在認識論方法上截然不同,但在對人類生活最大善的看法上卻不謀而合——即征服和駕馭自然。
頻道Word on Fire Institute - www.youtube.com/chan...
Youtube影片列表連結 - youtube.com/playlist...
Youtube影片連結 - youtu.be/1WX3X_OIKvg...
影片官網 - www.wordonfire.org/v...
影片
全部內容
第六講是關於笛卡爾與培根的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以及人類對自然的征服。
蘇格拉底是整個西方哲學之父,但勒內·笛卡爾被普遍認為是現代哲學之父。 在許多方面,他是一個新的蘇格拉底。我認為有五個主要原因導致了這種情況,即他為什麼是新的,以及他如何在現代與前現代之間劃清界限的重要性。 這五個原因都密切相關。 幾乎所有早期的現代哲學家在這些新的思維方式上都遵循笛卡爾,即使他們在哲學的具體細節和教義上與他有不同意見。
首先,他體現了西方文化中普遍的人類思想的主觀轉變,尤其是在哲學中。 笛卡爾像一個青少年,他首先想知道我是誰,而前青少年則更不自覺,對客觀世界、客觀真理(自然和超自然)更感興趣。
其次,因為笛卡爾非常自覺,所以他對確定性問題著迷。 像一個青少年一樣,他問他的老師:你怎麼知道? 因為他的第一個問題不是達到客觀真理,而是個人的確定性,所以他很批判。 也就是說,他從一種方法上的懷疑論開始,他稱之為「普遍懷疑」(Universal Doubt),而不是從信仰、經驗或常識開始。 為了用他新的、更強大的理性把他們帶出懷疑的深淵,他像一條梯子一樣,先下到懷疑的深淵。
大多數 17 世紀初最聰明的哲學家事實上都是懷疑論者,像Montaigne。 即使是現代最偉大的宗教辯護者帕斯卡爾(Pascal),也寫了他的《思想錄》,尤其是他的著名《Pascal’s Wager》,是為懷疑論者寫的。
詩人William Butler Yeats寫道:「現在我的梯子沒了,我必須躺在所有梯子開始的髒破舊貨店裡。」笛卡爾試圖駁斥懷疑論,但如果那個梯子倒塌了,他就會陷入他故意採用的懷疑論的深淵他不會從數據、經驗、常識、傳統、任何形式的信仰或任何權威開始。如果他的文化,也就是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現代西方文化,在這方面跟隨他,那麼也許文化也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第三,當笛卡爾找到他的第一個確定性時,它不是上帝或世界,而是他自己。他對懷疑論的回答,以及他整個哲學的基礎,是他著名的論點:「我思故我在」,笛卡爾將自己置於他思想的中心。如果前基督教的異教徒是宇宙中心的,而中世紀的基督徒是神中心的,那麼現代後基督教的人類是人本中心的。
第四,笛卡爾關注方法,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獲得確定性的新方法,這本質上是將科學方法應用於哲學。他最受歡迎的書是《方法論》(Discourse on Method)。科學方法事實上是科學史上最大的發現,因為它打開了所有其他科學的門鎖,就像一把萬能鑰匙一樣。笛卡爾觀察到在他那個時代,由於這個新方法,所有其他科學都取得了驚人的進展。所以他將這個方法,或試圖將這個方法,也應用於哲學。
第五,因為這是他中央的追求和問題:他從認識論開始,而不是形而上學,從如何認識真理開始,而不是真理本身是什麼,從思考思考開始,而不是思考存在。這很清楚地區分了現代哲學與前現代哲學。笛卡爾在建造建築之前檢查他的工具。他在使用理性之前檢查了理性本身。這個計劃的問題在於他除了理性之外不相信任何東西來檢驗和驗證理性。理性如何驗證自己?如果所有論點都在受審,那麼其中之一如何成為法官,並宣布自己和所有其他受審的論點無罪?
認識論是哲學的一個分支,研究人類思想或理性本身,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可能是最不有趣、最抽象、最薄弱和僅僅理論化的哲學分支。
認識世界和人是更具體、更實用、更有趣的,因為它涉及到我們如何獲得知識,而這只是認識論的一部分。
但認識論會影響哲學中的其他一切,就像形而上學一樣,這也是大多數人不感興趣的原因,因為它具有同樣兩個特點:抽象和不具體,以及理論而非實用。 然而,我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認識的例子,因此屬於認識論,正如我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現實或存在的例子,因此屬於形而上學。
認識論的核心問題是你如何知道? 這意味著兩件事:對確切性的探索和對方法的探索。第一是懷疑論的駁斥,即否認我們可以確定。第二是達到確切性的積極路線圖,一路上的步驟。古典現代哲學的根本爭論,從笛卡爾到黑格爾,從17世紀初到19世紀初,是我們所擁有的兩種認識能力之間的正確關係,即理性與感官。
理性主義以三種方式優先考慮理性。首先,在時間上,它說理性首先存在,我們有先天的想法,先天的邏輯原則,這些不是從經驗中學習的。 像非矛盾律和因果律這樣的原則。我們知道這些原則正確,但我們不是從經驗中得出它們,而是將它們帶到經驗中。第二,在批判上,它說理性判斷感官。 這是理性主義的精髓。第三,它說理性是無限的,不受經驗限制。
相反,經驗主義在所有這三個方面都優先考慮我們的感官經驗。 首先,在時間上,它說感官經驗總是首先存在。 其次,在批判上,它以所有科學(除數學外)中的數據來判斷理性理論。第三,在擴展上,它說理性受經驗限制。
因此,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在三個相關的問題上相互矛盾,比較理性與經驗。
第一個問題是哪個先來?
第二個問題是哪個是判斷另一個的標準?
第三個問題是理性是否受經驗限制。
理性主義者說理性比我們想象的要大,經驗主義者說理性比我們想象的要小。
笛卡爾是一位理性主義者,柏拉圖也是,Spinoza、Leibniz和黑格爾(Hegel)也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約翰·洛克(John Locke)和大衛·休姆(David Hume)是經驗主義者。亞里士多德在這場爭論中處於中間地位,就像他在幾乎所有爭論中一樣。他避免了極端。他非常反極端。他通常被稱為軟經驗主義者,而不是硬經驗主義者,因為他說所有人類知識都從感官經驗開始,但並不受其限制,因為它可以從具體例子中抽象出普遍、不變和確定的原則。硬經驗主義者在認識論中否認這一點,在形而上學中,他們幾乎總是名目主義者(nominalists)。也就是說,他們否認普遍性是客觀真實的。中世紀形而上學中現實主義者和名目主義者之間的爭論在認識論的反射池中由理性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之間的現代爭論所反映。
康德(Kant)試圖避免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他分別稱為教條主義(dogmatism)和懷疑論(skepticism)。他所指的理性主義主要是笛卡爾,他所指的懷疑論主要是大衛·休姆,休姆從他的經驗主義前提中非常邏輯地推導出了激進懷疑論的後果。 他的經驗主義前輩如弗朗西斯·培根和約翰·洛克並沒有這樣做。 康德以一種與亞里士多德完全不同的方式避免這兩種極端,即他所謂的哲學的「哥白尼革命」,這本質上是重新定義真理為將外在物體與心靈內在結構的認識的符合性,而不是相反。 他說我們並不從對真實世界的經驗中得出我們的範疇。 相反,我們潛意識地將它們強加於世界,因此我們像藝術家一樣構建世界,而不是像科學家一樣發現世界。我在第三講中比較了亞里士多德的認識論與康德的認識論。
在本講中,我們將做兩件事:首先,我們將比較笛卡爾的認識論和方法論與培根的;然後,我們將看到這兩位哲學家之間更深層次和更有趣的統一性——不在認識論中,而在倫理中最重要的問題上,即人類生活中最大的善是什麼。
笛卡爾在他的《方法論》中從重新定義理性的含義開始,並使其要求更加嚴格。在人類思想的歷史上,這至少發生了八次。
第一次,蘇格拉底要求提供邏輯證明,而不是簡單地接受權威或傳統的觀點。
第二次,柏拉圖要求對所謂的柏拉圖理念、柏拉圖形式或永恆本質進行定義。
第三次,亞里士多德通過將理力的力量視為感官經驗的X射線,將理性與感官結合起來,從而從具體物質的例子中識別和抽象出普遍形式或物種。他給柏拉圖的形式一個新的、更世俗的地址。
第四次,中世紀的基督教哲學家將對超自然的神聖啟示的信仰添加到人類的自然理性中,作為通往真理的道路。 這將神聖啟示引入了哲學,並將哲學探索引入了信仰。
第五次,笛卡爾通過將科學方法應用於哲學,或至少該方法的數學方面,特別是要求他所謂的清晰而明確的想法,將理性縮小到科學理性。換句話說,這些想法在兩個方面更像數字,它們是清晰的,也是明確的。數學是唯一普遍且無歧義的語言。通過這種新方法,笛卡爾希望結束一直困擾哲學家的爭論,正如他觀察到所有其他科學在科學中秘密結束爭論一樣。不用說,這沒有發生。
第六次,像休姆那樣的硬經驗主義者和所謂的實證主義者將理性限制在對感官數據的排序上。他們採取了科學方法的另一方面,即使用經驗數據來判斷所有假設。
第七次,康德重新定義理性為構建其對象而不是發現它,將形式強加於物質而不是從物質中抽象形式。他是一種內外翻轉的亞里士多德。這通過使人們甚至無法擁有關於客觀現實或事物本身的可能知識來縮小理性。
第八次, 計算機革命越來越多地導致人類將理性(reason)重新定義為推理(reasoning)或計算(computation)。這也是數學和數字的。計算機不能理解質素(qualities),只能理解數量。它們不能理解類比(analogies),類比是直覺(intuitive)的。 除了數字外,所有語言中的所有詞都可以用於類比。
以下是笛卡爾對理性的重新定義。他稱之為「常識」或「良知」,並說它不僅普遍存在於所有人中,而且在所有人中都是平等的。但顯然,智慧或理解或直覺,或我們可以稱為的哲學共情,並不在所有人中平等。
這就是為什麼哲學家不會像科學家那樣達成一致的原因。科學方法不依賴於或訴諸於這種右腦直覺,而只依賴於感官數據、確切的量化測量和邏輯計算。確實,所有人都有能力做這三件事,因為我們都有相同的感官、相同的數學和相同的邏輯規則,但我們沒有相同的理解或直覺智慧。
理性主義的收窄是科學達成一致的方式,笛卡爾認為他也可以將它應用於哲學,從而結束意見分歧,甚至結束戰爭,而戰爭總是從看似無法調和的深刻意見分歧開始,但如果我們都同意使用這種新、更窄、更嚴格、更科學的理性版本,也許它們並不存在。 這基本上就是所謂的「啟蒙」(Enlightenment)的信仰。 笛卡爾觀察並因三十年戰爭而受到創傷,該戰爭是關於新教德國和天主教法國之間的宗教分歧,笛卡爾在從戰場回家的路上受到啟發,創造了他的新哲學。
如果笛卡爾今天活著,知道了拿破崙戰爭、1848年的戰爭、布爾什維克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整個世界進行的戰爭,導致數百萬人死亡,幾乎沒有任何原因,以及隨後的恐怖事件,如共產主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大屠殺和超過5000萬的傷亡、廣島和毛澤東,意識形態上殺害了1億名非戰鬥人員,以及波爾布特,他殺害了所有柬埔寨公民的三分之一,以及伊斯蘭恐怖主義和我們當前文化中不斷加深的意識形態分歧和文化戰爭,你認為笛卡爾會說什麼?
笛卡爾是否不得不承認,這個新的理性與科學的神,作為地球上和平、進步和天堂幸福的源泉,確實像尼采所說的老神一樣,「已經死了」。
笛卡爾強調了科學方法的數學和演繹方面,而培根強調了經驗和歸納方面,這一差異是早期現代哲學家之間的主要問題,即理論問題的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但他們所有人,除了帕斯卡爾這個顯著的例外,都對科學方法不僅能改變哲學,還能改變人類生活本身充滿了希望。這個問題——實踐問題的人類幸福、倫理學和善惡——比認識論的理論問題更重要。在這個問題上,理性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一致,共同反對前現代對所有倫理問題中最重要的問題的答案,即最高善的問題,幸福或福樂的意義,對「我們在這個世界能做的最好事情是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
在《方法論》的結尾章中,笛卡爾給出了對這個問題的答案,這與培根的答案相同。他新的答案是文化中從未發生過的重大變化,因為這不僅僅是關於任何手段的變化,而是關於目的的變化。這就像一個人為了娛樂而駕駛帆船,決定加入海軍,並同意成為一名間諜,使用他的船。或者相反,一個間諜決定用他的船來娛樂。在任何情況下,他改變主意的不僅僅是如何駕駛,而是為什麼駕駛,關於最終的、終極的目標和目的,以及他做的一切其他事情的理由,從導航到油漆到清潔。
以下是笛卡爾關於他整個哲學的結束和目標和目的,以及他採用新的科學方法的原因,他希望將這個方法應用於哲學。 當然,方法只是手段,哲學也是。 就像培根所說,真理本身也是。 它是實用主義的(utilitarian)。它只是最終目的的手段,這個目的不是真理本身,而是它帶給我們的對自然的力量,換句話說,就是技術(technology)。
以下是笛卡爾的話:
「我們可以獲得非常有用的生活知識,並且可以找到一種實用的哲學,取代中世紀學校教授的思辨哲學(speculative philosophy),通過這種哲學,我們可以了解火、水、空氣、星星、天空和周圍所有其他物體的力量和作用,就像我們理解各種工匠的技能一樣,我們可以同樣使用這些物體來實現它們適合的所有目的,從而使我們自己,仿佛是自然的主人和擁有者。」
笛卡爾這裡所說的思辨(speculative)並非指不確定(uncertain),而是為真理本身而尋求真理,作為目的,而不是作為使用的手段。當笛卡爾談到「自然的主人和擁有者」時,他是在呼應培根,培根明確地說,人類在地球上的目的不是首先是認識真理,這只是一種手段,而是人類對自然的征服,或者權力,這是目的。就像尼采在他的想法中更激進地擴展了這一點,即最終的目的只是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尼采甚至質疑了對真理的意志(will to truth)。
C.S. 路易斯(C.S. Lewis)在他的預言性傑作《人類的廢除》(The Abolition of Man)中非常清楚地闡明了這一點,我認為這是整個現代時代最重要的書籍之一,因為它清楚地向我們展示了現代性的隱藏內心導致了什麼,我們走在哪條路上。他從糾正關於數據的常見錯誤開始,關於現代與中世紀之間的歷史差異。
他說:「關於現代科學的誕生,人們誤解了真實的故事。你甚至會發現一些人寫關於16世紀的內容,好像魔法是中世紀的遺留物,而科學是新的東西,進而掃除了魔法。那些研究這個時期的人,像路易斯自己,他寫了這個時期文學的標準作品,即《16世紀牛津英語文學史》,他們知道得更好。中世紀的魔法很少;16世紀和17世紀是魔法的高潮。嚴肅的魔法努力和嚴肅的科學努力是雙胞胎:一個病弱並死去,另一個強壯並蓬勃發展。但他們是雙胞胎。」
路易斯然後非常清楚地闡明了我們的文化與人類歷史上所有其他文化之間的差異。他說:「魔法和應用科學都有共同點,那就是技術,而將它們與早期時代的智慧分開。對於古老的智者來說,人類生活的主要問題是如何使靈魂符合現實。解決方案是知識、自我紀律和美德。對於魔法和應用科學來說,問題是如何使現實屈服於人類的願望。解決方案是一種技術(technique),也就是技術(technology)……本著這種精神,培根譴責那些將知識作為自身目的的人;對他來說,這就像將應該用於生產的配偶用作愉悅的情婦。真正的目標是擴展人類的力量。培根拒絕魔法,只是因為它不起作用;他的目標與魔術師的目標相同。」
換句話說,他是薩隆(Sauron the Great,自作品《魔戒》),他的權力戒指(ring of power)是技術(technology)。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魔戒》中從未見過薩隆,因為薩隆是我們自己。
我們如何分類事物可以告訴我們很多關於我們的思想。當小孩子被要求將玩具放入兩個盒子時,他們有時會將所有球放入一個盒子,將所有其他不同形狀的玩具放入另一個盒子。他們是結構性思維。那些功能性思維的人會將棒球、棒球棒和棒球手套放入一個盒子,將冰球、冰球棍和冰球網放入另一個盒子。
讓我們看看我們如何分類四個人類企業,其中三個仍然嚴肅,所有四個在培根和笛卡爾的早期現代時期都存在,爭論不休。 我們如何分類科學、技術(technology)、魔法和宗教?
幾乎每個人都會將科學和技術歸類在一起,將宗教和魔法歸類在一起,有兩個充分的理由:科學和技術都使用科學方法,都只訴諸自然,而不是任何超自然事物,而魔法和宗教都超越了科學方法和自然。
但更深層次的分類,更深層次的統一,是魔法和技術之間的統一,以及宗教和科學之間的統一。因為,正如路易斯指出的,魔法和技術都尋求對自然的權力。雖然一個使用超自然手段,另一個使用自然手段,但兩者都渴望權力,而科學和宗教都渴望真理。科學和宗教都尋求使人類靈魂符合客觀現實。雖然科學關注心靈並試圖使它符合自然的現實,而宗教關注意志並試圖使它符合上帝的現實。
但目的比手段更重要,因為它們是由心、意志和愛選擇的。 而愛比技術更重要。因此,最重要的是差異,不是超自然魔法的技術手段和自然科學技術的技術手段之間的差異,而是它們的共同目標或愛,即對權力的愛。 另一方面,科學和宗教有不同的技術和方法,但它們有相同的目標,即符合客觀真理,符合現實。 科學使心靈符合自然的真理,宗教使心靈、情感和生活符合上帝的真理。
在《方法論》的最後一章中,關於笛卡爾希望通過這種方法實現的烏托邦結果,他透露了自己希望通過未來技術的無限潛力回歸伊甸園,或進步到烏托邦。他說:「這不僅僅是為了無限的裝置,這些裝置將使我們能夠無痛地享受地球上的果實和其中的所有財富,而是……我們可以擺脫無限的疾病,無論是身體的還是心靈的,甚至可能是衰老的虛弱,只要我們充分了解其原因和自然為我們提供的所有藥物。」
在私人信件中,笛卡爾坦承了他對征服自然王牌,即死亡本身的最激進的夢想。他寫道:「人們不應該懷疑,如果我們知道適當的藝術,人類的生命可以無限延長。」
在這裡,笛卡爾準確地預言了路易斯在《人類的廢除》中警告的內容,即對自然的征服可以成為對人類本性(human nature)的征服,對所有疾病的廢除,甚至是死亡本身,從而預言性地預見了硅谷(Silicon Valley)中所謂的超人類主義者(transhumanists)的黑暗夢想和裝置,他們正在認真地努力地發展征服自然的王牌,通過基因工程實現人工永生。
如果這確實發生,我認為這將引發耶穌再臨和世界的結束。因為在這個墮落的世界中,不朽的種族,用他們自己墮落、愚蠢、自大的肉體,將像未孵化的爛蛋。 他們會關閉自己teleology(目的論)、自己的結局的大門。再引用路易斯一次,「我們現在就像雞蛋,你不能永遠只是做一個好的雞蛋。 你必須要麼孵化,要麼變壞。」
約書亞,耶穌的前任和同名者,在以色列民即將進入應許之地時,給了上帝所選的人這個最根本的選擇。他說:「你們今天要選擇要事奉誰,是事奉迦南神,還是事奉埃及神,但就我和我家而言,我們要事奉耶和華。」這是擺在西方文明和其中每一個人面前的重大選擇的最終意義。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