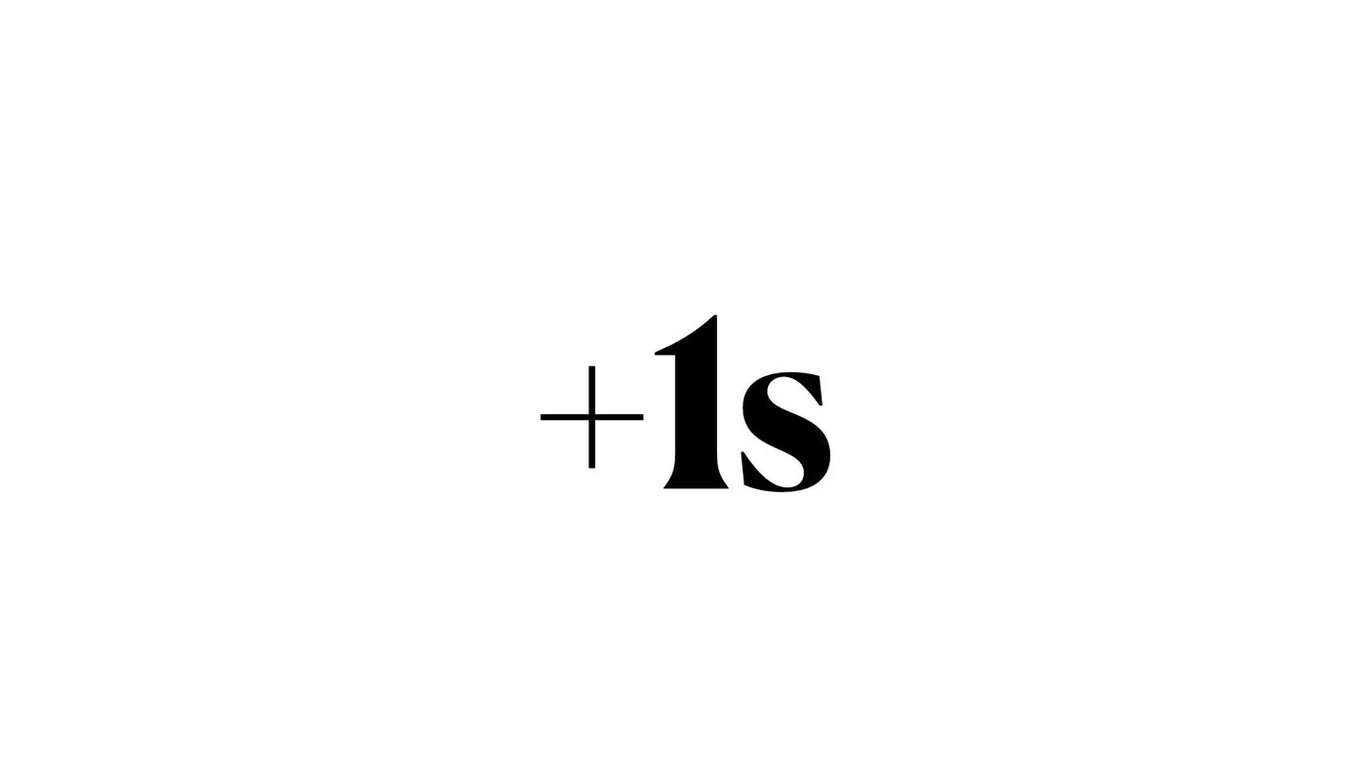一个刺头的诞生
IPFS
和朋友聊天讲到ta小时候,因为总是被班主任讨厌,被认为是刺头,建议ta这种人“适合到外国去读书。” 听到的时候是笑了,因为这或许是很多小时候“不乖”的孩子都有的经历,自己多半被这么说过,没有明确的印象多半是因为,当时的处境完全没有想到最后会去美国。
上一辈的家长或者老师说这种话,必然是出于一种对外国(尤其是美国)道听途说的想象,而里根时代个人主义盛行取消放开政府管制的美国也理所当然最符合在集体主义浩劫中长大,喜迎改开的上一代国人的憧憬。
这个外国,或具体地说,这个美国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如Cuomo著名的“双城记”演说),但也是属于过去的。原来的刺头到了美国也会反过来拥抱如今美国左派的集体主义。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有意和无意之中,无意是真诚信奉或者皈依了左派政治清教徒式的信条,有意则是迅速掌握了一套游戏规则下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人精,他们找到了组织,和组织能赋予的归宿和权力。这些刺头,这些无法被同化所以被流放的逃兵,并非反对集体主义本身而是反对他们认为“错”的集体主义。
所以这才让我与他们渐行渐远。诚恳地说,我对现在面对着性别种族的种种荒唐言论,又挣扎在同化与否的精英体系下的人,尤其是学生,深表同情。对着政治书言之凿凿的信条,真诚地想要理解,想要相信,似乎和你的人格正直善良息息相关,却始终有这里那里让你坐立难安的自相矛盾,让你浑身不舒服,你不知道,你根本不需要相信,有的是人说一套,做一套,说得比唱的还好听,如鱼得水扶摇直上,就算知道了,也无能为力。这正是我从小经历过的煎熬。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