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米兔”一周年 行动者表示从未放弃 (旧问重发)
原文于2019年8月12日首发于自由亚洲电台(责编:嘉远 网编:洪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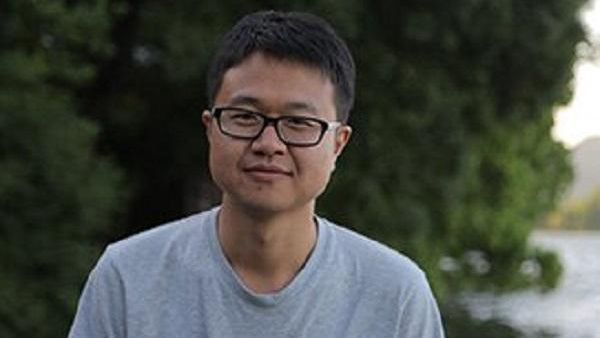
2018年7月23日,一封举报信将中国公益明星雷闯推到了风口浪尖,由此掀开了从中国公益圈到媒体圈的米兔运动。米兔运动延续了美国的#MeToo反性骚扰运动,受害者在运动中打破沉默,曝光施害者的行径。一年过去了,这场中国本土的米兔运动怎么样了呢?
行动者:356封信的坚持
2018年7月23日,女生花花在自己的朋友圈曝光,乙肝“权益斗士”雷闯在数年前倡导乙肝权益的徒步活动期间性侵了自己。雷闯随后发布声明,承认性侵,承诺会去自首。
但是雷闯至今都没有自首。他将自己的朋友圈设为三天可见,有时还晒出自己孩子的照片。一年前的性侵丑闻似乎毫无痕迹。
对此,全程参与了这场米兔运动的公益法律人士梁小门说:“灰心丧气的感觉没有,生气愤怒倒是比较多。”她告诉本台记者,有一些行动者至今都在关注雷闯性侵案的后续,通过微博、微信群和寄纸质信的方式,每天督促雷闯实现自己的自首承诺。“其它行动者持续不断的行动虽然没有很多人关注,但是仍然很振奋人心。”
一位行动者在公开发表的自述中写道:“到现在为止,负责寄纸质信到亿友办公室的人还是只有我一个,而我已经做了整整一年了。” 亿友公益是雷闯所在的机构,这一年来这位行动者一直给他们寄信,连出差的时候也没有遗漏,直到今年7月25日,她已经给亿友办公室寄出了三百六十五封信。
她在声明中表示,寄信的过程很繁琐:打印、装信、写提示板、拍照,但她会坚持下去。
施害者:没有证据定罪难
然而,即便雷闯自首了,法律也很难定罪。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长期从事性侵害公益援助的律师告诉本台记者:“性侵是刑事案件,定罪需要以证据为基础。如果只有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一致的口供,但没有其它物证也很难入罪。”
由于事情发生时间较久,性骚扰或性侵未遂的情况下 很难采取证据,取证难必然导致定罪难。被控施害的一方经常抓住这一点,对受害者和他们的支持者提起名誉侵害的诉讼。
在这一波“米兔”浪潮中,媒体人邹思聪、美国卫斯理大学教授王敖都曾为其它受害者公开发声,并因此被对方以“侵犯名誉”为由告上法庭。此外,原告都申请了不公开审理。
原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认为:“法院审理的是公开发表的言论有没有捏造的事实来诋毁原告,这其中涉及的其他人员他们也已经公开了,不存在隐私问题。”
状告邹思聪的《凤凰周刊》记者邓飞是人人口中的“公益圈大佬”。他被曝光曾性侵实习生未遂,且受害者可能不止一人。邓飞申请案件不公开审理后,被传出利用新华社和网信办来威胁被告方,试图动用自己在权力体系中的关系来恫吓发声者。
本台记者曾试图联系邓飞的代理律师求证,但没有成功。邹思聪的代理律师徐凯则拒绝了本台记者的采访,希望舆论把焦点放在邓飞性侵未遂这件事本身。

法制:仍需完善对受害者的支持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反性骚扰机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梁小门说:“中国‘米兔’运动绝对改变了影响了官方政策对性骚扰问题的态度。” 她补充道,现在检察院和地方教育部门会登记有性侵未成年人的教师名单: “这样的措施既有预防也有惩治,但是这样的措施缺少民间的问责和公众的参与,它依靠的永远都是 上级部门去进行惩治,并没有第三方进行权力的制衡。”
珍妮弗-斯瓦茨(Jennifer Schwartz)是美国奥登-戈登律师事务所(Outten&Golden)律师,在处理性骚扰方面的案件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她告诉本台记者,美国的“米兔”运动中法律为受害人和其他参与者提供了完善的保护:“有一些新的立法,也有公益机构和政府部门通过包括公开就业平等委员会等方式,还有个人和集体诉讼等,都为美国的‘米兔’运动做了很大贡献。”
她补充道,美国很多州都有反策略性诉讼法,在“米兔”运动中指控他人有性骚扰或性侵害行为的人,都可以用相关条文来保护自己,避免吃到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