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重大辯論 Ep. 7】Pascal vs. Descart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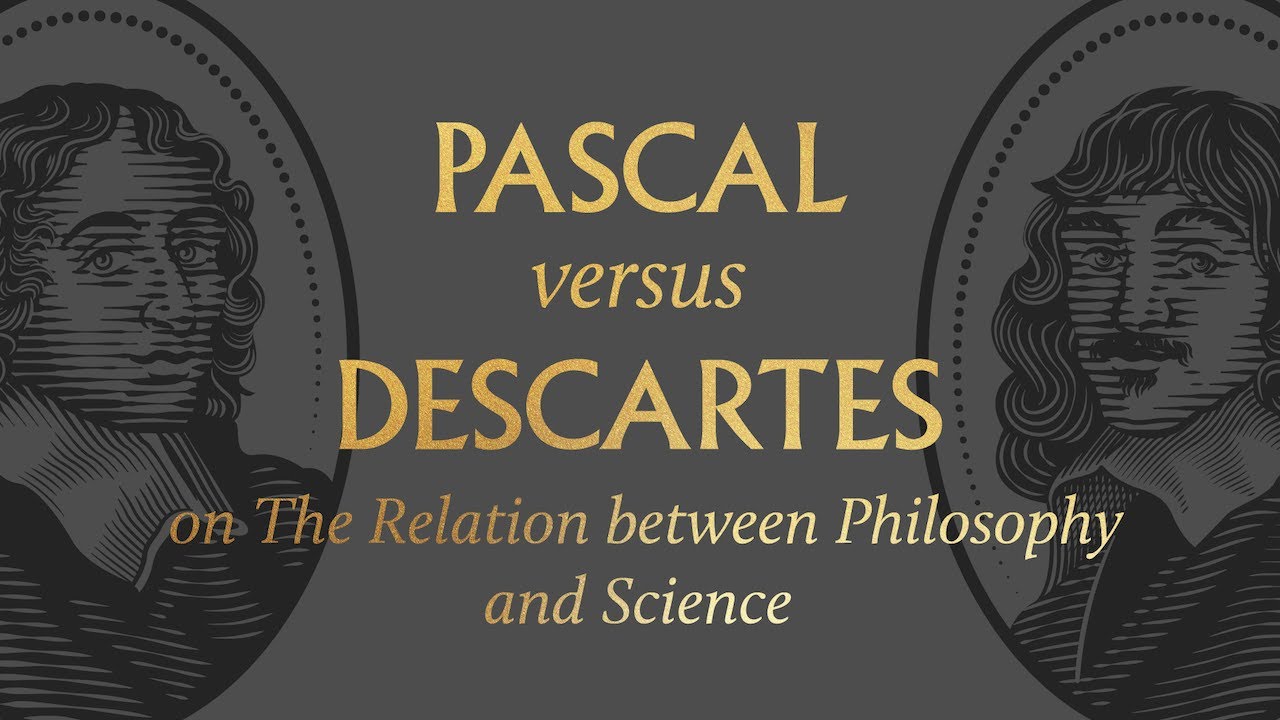
簡介
In lecture 7, Dr. Kreeft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ascal and Descartes on just about everything—though both were believers and practicing Catholics. Pascal was a great scientist and mathematician who saw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while Descartes tried to make philosophy like mathematics, formulating clear and distinct ideas aimed at achieving absolute certainty.
在第七堂課中,克里夫博士(Dr. Kreeft)討論了帕斯卡爾和笛卡爾在幾乎所有方面的差異——儘管兩人都是信徒和實踐天主教。帕斯卡爾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和數學家,他將哲學視為一種生活方式;而笛卡爾則試圖讓哲學像數學一樣,制定清晰而明確的概念,以達到絕對的確切性。
頻道Word on Fire Institute - www.youtube.com/chan...
Youtube影片列表連結 - youtube.com/playlist...
Youtube影片連結 - youtu.be/T0BEfI9ei2E...
影片官網 - www.wordonfire.org/v...
影片
全部內容
第七講是關於帕斯卡爾與笛卡爾在幾乎所有方面的差異。
我們還沒有完全討論完笛卡爾(Descartes),因為在上一講中,我們僅僅將他作為理性主義者與經驗主義者培根(Bacon)進行比較。然而,比知識論上的爭議更根本的對比是笛卡爾與他的同時代人帕斯卡爾(Pascal)的對比,帕斯卡爾既不是理性主義者也不是經驗主義者。帕斯卡爾並沒有涉及知識論的問題,尤其是對確切性的追求,他只尋求反駁他所謂的教條主義(理性的確切性主張)和懷疑主義,正如蘇格拉底所做的那樣。
那麼,如何歸類帕斯卡爾?
我會稱他為第一個基督教存在主義者,如果奧古斯丁沒有已經寫了《告白錄》(Confessions)的話,這本書對帕斯卡爾的傑作《思想錄》(Pensées)影響最大,僅次於《聖經》。事實上,當帕斯卡爾知道自己將死時,他把自己龐大的圖書館中的所有書都送出去了,只留下這兩本書。
早期現代哲學方便地設定了時間範圍、重點和選項。它可以從1637年笛卡爾出版《方法論》開始,到1831年黑格爾去世,他是最後一位偉大的系統建立者。它的重點是知識論問題,有三個選項:大陸理性主義(continental rationalism),尤其是在笛卡爾、Malebranche、Spinoza和Leibniz;英國經驗主義(British empiricism),在培根、洛克(Locke)、伯克利(Berkeley)和休謨(Hume);以及德國理想主義(German idealism),在康德(Kant)、Fichte、Schelling和黑格爾(Hegel)。
帕斯卡爾並不符合這三個範疇中的任何一個。
在接下來的兩百年裡,每一位重要的哲學家都跟隨笛卡爾的腳步,試圖將科學方法的某個方面應用於哲學,除了帕斯卡爾。笛卡爾試圖讓哲學更像數學。他要求清晰而明確的想法作為內容,確定的演繹論證作為方法,以及絕對的理性確切性作為目標。
帕斯卡爾,就像笛卡爾一樣,自己也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和數學家,尤其是在概率論方面,帕斯卡爾還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原始的、可工作的計算機,但他將哲學視為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僅僅思考,並認為它依賴於心靈和頭腦。
他最著名的計算性和準數學推理是嚴格實用的。那就是他著名的《Pascal’s Wager》,他用這本書不是要證明上帝存在,而是要證明相信上帝是我們唯一幸福的機會,也是世界上最合理的賭注,因為,正如他說的,如果你贏了,你贏了所有東西,如果你輸了,你什麼都沒輸。
在中世紀,信仰(faith)與理性(reason)的婚姻在帕斯卡爾身上還沒有完全離婚,就像在Hobbes或休謨等無神論者那裡,也沒有完全分離,就像在既是基督徒又是哲學家的笛卡爾那裡,但他絕對不是基督教哲學家。在帕斯卡爾身上,信仰與理性的關係確實變得鬆動了。笛卡爾和帕斯卡爾都對信仰和理性進行了限制。一方面,笛卡爾將理性的含義縮小到科學理性,一種完全無個性的東西;另一方面,帕斯卡爾將信仰的含義縮小到非常個人化的東西。他對證明上帝存在的論證持懷疑態度,因為他尋求的不是他所謂的哲學家的上帝,而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聖人和神秘家的上帝,不是概念,而是火焰。
這兩位哲學家在他們對哲學本身的看法和哲學的起點上也是相反的。帕斯卡爾從經驗開始,事實上從普遍的人類經驗開始,即不可否認的普遍經驗的四重數據,我們都渴望確切性和幸福,而我們無法實現我們所渴望的這兩點。笛卡爾根本不是從經驗開始,而是從普遍的、有系統的懷疑開始。他聲稱在著名的「我思故我在」中僅通過理性思想就找到了確切性,並聲稱從這點出發推導出他哲學的其餘部分。
他們的模型或影響也是相反的。帕斯卡爾在他的傑作《思想錄》(Pensées)中寫道,他把除了《聖經》和《告白錄》以外的所有書都送了,這兩本書是他模仿的對象。相比之下,笛卡爾說他在大學裡學習的唯一讓他滿意的科目是數學,這就是他哲學的模型。帕斯卡爾說這樣的哲學值得大約半個小時的工夫。笛卡爾認為他的新哲學是建立新科學的基礎,這個新科學將把世界變成烏托邦。
這兩位哲學家的差異並非完全。他們都是有信仰、實踐的天主教徒,都是成功、原創、出色的科學家和數學家。帕斯卡爾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實用的計算機、世界上第一套公共交通系統和吸塵器,以及概率論的許多內容。笛卡爾說他整個哲學的目的是證明上帝的存在和人類靈魂的現實性和不朽性,所以這兩位哲學家並不完全不同。但儘管他們相信相同的科學和宗教,他們的哲學卻像頭腦和心靈、邏輯和信仰、客觀和主觀、理論和實踐、古典和浪漫、理性主義和存在主義、科學和人文學科一樣不同,這兩種文化今天分割了我們的靈魂和世界。
奧古斯丁的兩隻手,開放的書本和燃燒的心,在現代由兩位不同的哲學家呈現,而不是由一位。笛卡爾是奧古斯丁的書,沒有心;帕斯卡爾是奧古斯丁燃燒的心,沒有書。《思想錄》不是一本書,它包含大約一千條關於一本書的簡短筆記,如果這本書確實寫出來了,它會像老子的《道德經》那樣,是一本反對書籍的書。
托馬斯·阿奎那(Aquinas)的信仰與理性的婚姻中的兩任配偶已經分居,雖然還沒有離婚。笛卡爾和帕斯卡爾從未談論或相信那個偉大的現代神話,所謂的「科學與宗教之間的戰爭」,這是在歷史中最虛假的戰爭,因為它沒有任何傷亡。沒有任何宗教教義被任何科學發現所推翻,這是一個從未曾被反駁的歷史事實。這個神話只能在我們將科學和宗教這兩個模糊的抽象概念,與具體的宗教教義和具體的科學發現區分開來時才可以被相信。
為了展示帕斯卡爾和笛卡爾之間的差異有多麼普遍,我將簡要地從十二個不同的哲學領域對這兩位哲學家進行對比:他們的哲學的目標或目的、他們的哲學方法、他們的哲學的邏輯結構和進展、他們的知識理論或認識論、他們的哲學人類學或人類本性哲學、他們的宇宙學或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他們的形而上學、他們的哲學神學、他們的倫理學或個人善、他們的社會倫理或政治善、他們的邪惡哲學,以及他們的死亡哲學。由於我們在之前關於笛卡爾的講座中已經觸及了其中的一些內容,我將對笛卡爾的概述更簡短,對帕斯卡爾的概述更詳細。
對笛卡爾來說,哲學的目標非常高遠。他將哲學視為所有其他科學的基礎和正當性,因為哲學為人類理性本身提供了正當性和有效性。雖然,正如我們在之前檢視笛卡爾時所看到的,理性如何證明自己,就像任何人如何引起自己一樣,這並不是很清楚。即使上帝也不是自因的,而是無因的。對笛卡爾來說,人類理性的哲學正當性是科學這座摩天大樓的基礎,而這座摩天大樓的應用技術是人類的新家園,最終是一種地球上的烏托邦。對笛卡爾來說,哲學非常重要,但不是為了它自己,而是為了科學,而科學反過來主要是為了培根所說的人類通過技術征服自然,笛卡爾相信這在應用到人類生活和甚至死亡方面是無限的,我們很快就會看到。最終,笛卡爾預言,科學將回答所有理論和實踐問題,消除所有無知,解開所有謎團。我們將不再需要蘇格拉底來提醒我們的無知,也不需要上帝來提醒約伯,人生是一個該透過生活去體驗的謎團,而不是要解決的難題(life is a mystery to be lived, not a puzzle to be solved)。
帕斯卡爾或許是對這種理性主義做出有意識的反應,他寫道哲學值得大約半個小時的麻煩。我們有權這麼說,但只有在我們寫了一本像帕斯卡爾《思想錄》那樣好的書之後,而不是之前。帕斯卡爾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真正的哲學智慧不是他們寫的,而是他們如何與家人和朋友相處。對帕斯卡爾來說,最根本的哲學問題,上帝的問題,不應該通過抽象和無個性的證明來回答,無論這個證明多麼有效,而是通過具體和個人的賭注,一個賭注,一個信仰和希望的飛躍,這不是由頭腦(mind)完成的,而是由心靈(heart)完成的,不是由理性,而是由意志和它的自由選擇。
對於帕斯卡爾來說,四個最重要的哲學問題是自我、上帝、生命和死亡的意義。而我們現在或未來能給出這些問題的唯一充分答案是耶穌基督。帕斯卡爾說:「認識他,就是認識這四個問題的意義;不認識他,就不認識這些意義。」(To know him is to know the meaning of those four things, and not to know him is not to know those meanings.)
那麼,哲學的目的是什麼?笛卡爾將哲學視為一種強大且無限成功的手段,用於人類征服自然的最終目的。帕斯卡爾將哲學視為一種微弱且非常有限成功的手段,在他自己的手中,用於上帝征服人類的最終目的。由於方法取決於目的,由於笛卡爾和帕斯卡爾在哲學的目的上存在根本性的差異,因此他們在方法上也存在同樣根本性的差異。
對笛卡爾來說,這是一種科學方法,它在所有其他科學中都證明了如此成功,笛卡爾很自然地試圖將其應用於哲學。笛卡爾提出的四個基本規則是指:從普遍懷疑開始;要求清晰而明確的想法,就像數學一樣;從簡單到複雜進行演繹,因此使用分析,而不是直覺或綜合;最後,通過普遍回顧來彌補任何遺漏或錯誤。笛卡爾假設,這在哲學中是可能的,就像在其他科學中一樣,而且在其他科學中,就像在數學中一樣,是可能的。當然,這些假設在實踐中從未得到驗證,很少有哲學家,更少的普通人,還相信它們在理論上有效。
相比之下,帕斯卡爾的方法,他說,就像彈風琴的方法。風琴是人,正如他說的,你必須知道按哪些鍵。這是耶穌和蘇格拉底使用的方法。由於目的個人化,方法必須是個人化和實踐化的。你不能先學習然後再去實踐;唯一學習方法是在實踐中學。但耶穌和蘇格拉底,這兩位最偉大的教師,並沒有忽視邏輯、無個性和客觀的維度。沒有人能在一場辯論中擊敗他們,也沒有人在他們的推理中找到過謬誤。
他們也使用一種科學方法,但更基本。帕斯卡爾在這點上跟隨他們。他們的方法首先是歸納而不是演繹。它從經驗開始,而經驗是複雜的,而不是簡單的。所以方法不應該從簡單到複雜,像笛卡爾的演繹,而應該從複雜到簡單,像歸納。
在除了數學以外的所有科學中,所有假設、理論或原則都應該通過我們經驗的數據進行測試和驗證。帕斯卡爾首先總結了我們自己和我們生活的經驗給我們所有人提供的四個最重要的數據:我們都追求幸福,我們都發現不幸,我們都追求確定的真理,我們都發現錯誤和懷疑。換句話說,用最著名現代哲學家最著名的話來說,你不能總是得到你想要的,我還不能知道滿足。音樂哲學不多,但音樂本身有很多好哲學。任何沒有解釋或甚至沒有嘗試解釋這四個數據的哲學都不值得我們花時間。任何不適合這個鎖的鍵都是無用的。而一個適合的鍵值千金。基督正是那把鍵。所以帕斯卡爾首先探索鎖,也就是我們的壞消息,然後是鍵,也就是上帝的好消息,福音,以及鍵和鎖之間的契合。
帕斯卡爾被譽為悲觀主義者,因為他探索了我們不滿、虛榮的走廊,就像後來的無神論和基督教存在主義者,以及所有早期的存在主義者,就像《傳道書》的作者和聖奧古斯丁。為什麼他要做這件悲觀的事情?因為這些數據需要被解釋。
傳統的上帝存在論證通常從好消息開始,正面的完美,如宇宙中的秩序和設計,或道德法則和我們對它的認識以及對永恆真理的認識。從設計中,我們推斷出超人類的設計者,從法律中,我們推斷出超人類的立法者,從永恆的想法中,我們推斷出超人類的永恆心靈。
但帕斯卡爾卻與之相反,他從消極數據開始,我們的不幸和不確定性,這些問題更深地咬住我們,並需要實際和理論的解決方案。這不是悲觀,這是現實主義。笛卡爾的方法,科學方法,假設我們是冷漠的觀察者。帕斯卡爾的方法假設我們是問題的參與者。
那麼,我們用什麼標準來比較這兩種方法?為什麼不問哪個假設是真實的?由於方法上的差異,笛卡爾和帕斯卡爾在哲學的邏輯進展或結構上也存在差異。笛卡爾的哲學是一連串理論問題解決的邏輯演繹,幾乎像歐幾里得的幾何學。而帕斯卡爾的哲學像一次探索未知的旅程,一個英雄的旅程,像所有偉大的故事,尋找打開人類悲慘、無知、虛榮和不公正之鎖的鑰匙。
笛卡爾的進展以預測人類通過科學和技術創造的地球天堂而結束。帕斯卡爾的進展以人類通過信仰向基督投降而結束,這是一個信仰的飛躍,他不是通過演繹,而是通過賭注來邏輯地證明。
笛卡爾的哲學是演繹,帕斯卡爾的哲學是戲劇。
認識論(Epistemology),哲學中關於知識如何運作以及如何應當運作的科學,與方法緊密相連。笛卡爾的認識論是理性主義和演繹性的,並且是數學的。他告訴我們,數學是他大學裡唯一讓他滿意的課程,因為他最想要的是確切性。笛卡爾聲稱驅逐了神秘。帕斯卡爾則沉浸在神秘中。笛卡爾想要一個上帝的視角來看待事物,而不訴諸信仰或神性啟示。他是系統建立者,建立了一座語言的塔(Tower of Words),對帕斯卡爾來說,這是一座巴別塔(Tower of Babel)。帕斯卡爾並不試圖用一座偉大的建築刮天頂。他像洞穴探險者一樣向下鑽探,他挖掘我們經驗的土壤。笛卡爾探索本質(essences),帕斯卡爾探索存在(existence)。帕斯卡爾的認識論是理性的,但不是理性主義的。它沒有忽視或貶低理性、邏輯和論證,但它以經驗和直覺為中心,以心靈的眼睛為中心。他著名地說:「心靈有它的理由,理性不知道。心靈有眼睛。」(The heart has its reasons which the reason does not know. The heart has eyes.)
人類學(Anthropology)是關於人的科學,是關於人類(anthropos)的科學。那麼,認識論取決於人類學,因為人的認識取決於人的本質。笛卡爾的人類學是一種靈智派理性主義(Gnostic rationalism),將人與心靈相等,心靈與理性相等,理性與邏輯相等,邏輯與定義和演繹相等。帕斯卡爾也使用邏輯論證,但他認為人以心靈為中心,他說的心靈,不是賀卡或流行心理學所說的,而是聖經所說的。不是情感(feelings),而是情感和思考(thinking)、意願(willing)和選擇、愛的預功能根源(pre-functional root)。
我說我的思考、我的感受、我的意願、我的愛。那個「我」是誰?好吧,心靈是所有分支的樹幹。所羅門寫道:「你要用一切勤勉守住你的心,因為生命的泉源就從心裡流出。」(Keep thy heart with all diligence, for out of it are the issues of life.)心靈首先是愛的源泉。
帕斯卡爾在奧古斯丁的影響下寫作,他認為愛是人的本質和人的命運。「Amor meus pondus meum」,奧古斯丁說,「我的愛是我的重力。」這就是為什麼帕斯卡爾在《思想錄》中說,傳教士和護教者必須首先讓我們渴望相信基督,首先展示他的可愛性,然後展示這份愛是真實的,而不是反之。
希臘人告訴我們要根據理性去愛;聖經告訴我們要根據愛去理性。因此,笛卡爾區分了自我兩個層面,身體和心靈,帕斯卡爾區分了三個:身體、心靈和心靈,或者生物學、理性與慈善;生命、光和愛,也是三個聖經類別,以及聖約翰對上帝的三個最喜歡的詞:Zoe、logos和agape。
正如認識論取決於人類學,人類學取決於形而上學。正如人的認識取決於人的本質,人的本質取決於存在,於真實,於存在的意義。那麼,笛卡爾和帕斯卡爾在形而上學上有什麼不同?
既然笛卡爾和帕斯卡爾都不是唯物主義者或唯心主義者,他們都相信現實的試金石和標準是上帝,是同一個上帝。他們都是有信仰的天主教徒。所以我看不出這兩位哲學家在形而上學上有任何不同,這很令人驚訝,因為哲學中的其他一切都取決於形而上學。然而,這兩位哲學家在幾乎所有其他方面都存在根本性的差異,但在形而上學的內容上卻沒有不同,儘管他們在形而上學的價值上存在差異。笛卡爾在這裡花了很多時間,而帕斯卡爾卻很少,因為帕斯卡爾認為大多數人對形而上學幾乎沒有任何感動。
顯然,哲學其他分支對形而上學的依賴不是演繹的依賴,不是結論依賴於前提,因為如果是這樣,那麼笛卡爾和帕斯卡爾就會有相同的結論,因為他們有相同的形而上學前提。換句話說,哲學家們通常不會從形而上學開始,然後從它演繹出一切。他們通常從另一端開始,從結論開始,然後找到前提來證明它們。
他們從對更具體問題的信仰開始,關於人和價值觀和愛,然後建立抽象的形而上學原則和前提來支持這些結論。換句話說,愛和心靈事實上首先存在。帕斯卡爾知道這一點,而笛卡爾不知道。我認為,這可能是他們在形而上學上的最大差異。這不是內容上的差異,而是焦點上的差異。
兩位都是超自然主義者,不是自然主義者,但帕斯卡爾專注於超自然,而笛卡爾專注於自然。他們都相信上帝,但對笛卡爾來說,上帝只是理論上的興趣,不是實踐上的興趣。他只用上帝作為他自己知識與世界知識之間的橋樑,這是他開始和結束的地方。他首先證明了自己的存在,然後證明了上帝的存在和自然的存在。但上帝在其中。他不讓上帝成為他整個哲學的阿爾法和歐米伽,開始和結束。他也不把上帝作為解決人類生活問題的方案。他沒有將他理論上的上帝與他實踐上的人類生活聯繫起來。帕斯卡爾做到了。這就是為什麼帕斯卡爾不僅談論上帝,還談論基督。基督是上帝的現身,上帝在人中和人類生活中。
在認識論中,帕斯卡爾呼籲上帝、祂的神聖啟示和我們對它的信仰,作為我們不確定性的唯一解決方案。在人類學中,帕斯卡爾呼籲上帝、祂的承諾和我們對它們的希望,作為我們虛榮和絕望的唯一解決方案。在倫理學中,帕斯卡爾呼籲上帝、祂的神聖慈善和我們接受它和反映它的行為,作為我們不幸和悲慘的唯一解決方案。這個計劃影響了帕斯卡爾的形而上學,並產生了與笛卡爾在內容上的唯一重大差異。
因為在笛卡爾的形而上學中,他只有兩個層面的現實,物質(matter)和心靈(mind),而帕斯卡爾有三個:物質、心靈和慈善(charity),神聖的愛,Agape,他明確說這超自然,與自然和自然理性不同,這是他形而上學的其他兩個層面。
在他們的神學哲學中,帕斯卡爾和笛卡爾對上帝有不同的看法,雖然他們都不是明確的神學異端。笛卡爾看到上帝和上帝在人中的形象主要是心靈,而帕斯卡爾看到上帝和上帝在人中的形象主要是心靈和愛。當他經歷了改變他一生的神秘體驗時,帕斯卡爾,像摩西一樣,看到上帝不是光,而是火。那是他的詞,火。因為根據上帝自己的話,上帝是愛,而愛根據那些不僅僅是愛的學生(students of love)而是愛者(lover)來說,是火。
帕斯卡爾奧古斯丁的心靈和愛的首要地位不能僅僅是人類學,它還必須在他的形而上學中產生後果,因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創造的。
在倫理學方面,笛卡爾沒有任何倫理學,除了一些純實用和暫時的建議,關於如何在做真正重要的事情,即科學和技術的同時,以最少的麻煩生活。康德填補了笛卡爾理性主義哲學中缺失的部分,通過建立純粹的理性倫理學。事實上,這是一種幾乎數學的理性倫理學,沒有形而上學和哲學人類學或心理學,這兩點都使康德的認識論不可能,因為他的哥白尼革命在哲學中否認了我們對事物本身或客觀現實的認識。因此,忠實於笛卡爾的理性主義,康德的倫理學不訴諸普通的經驗性經驗,不訴諸人類本性,不訴諸習慣、美德和惡習,正如亞里士多德和帕斯卡爾所做的那樣。
在政治方面,笛卡爾的哲學的主要影響是他聲稱在哲學中使用科學方法將結束所有哲學分歧,包括政治哲學。法國在所有其他領域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功,因此笛卡爾希望它在社會倫理或政治方面也能做到同樣的事情,這將結束戰爭。
這個希望有一個非常個人和經驗的來源:笛卡爾在從德國回法國的路上,在一個被雪困住的夜晚,做了一個他認為來自真理之靈的神秘夢境後,提出了他的哲學,他當時剛剛經歷了三十年戰爭的戰場,這是一場宗教和意識形態的戰爭,以非戰鬥人員的災難性後果而聞名。
不必說,笛卡爾的和平夢想還沒有實現。
另一方面,帕斯卡爾,一如既往,以現實主義和經驗觀察者的身份,而不是理性主義和理想主義者的身份,談到了人類正義的虛榮和真實的自然道德法與人類思想和行為的荒謬之間的差距。他讀過奧古斯丁《上帝之城》的第19章。在集體、社會和公共方面,以及個人和私密方面,他首先告訴我們沒有上帝的人類不幸的消息。然後他告訴我們有上帝的人類幸福的好消息。他將這些標記為他這部經典《思想錄》的兩個主要要點,兩個主要部分。政治在第一個部分中被提及,但在第二個部分中沒有被提及。
所以帕斯卡爾隱含地認為政治是我們問題的一部分。笛卡爾隱含地認為政治是我們解決方案的一部分。當然,作為基督徒,他們都會同意基督的話,我們應該把凱撒的歸成凱撒,把上帝的歸成上帝,但他們會以不同的方式劃分這條分界線。
這兩位哲學家對罪和道德邪惡有什麼看法?
Chesterton說,原罪教義是唯一一個可以簡單地通過閱讀日報來證明的基督教教義。帕斯卡爾在《思想錄》的一半中給我們提供了關於罪、邪惡、惡行和虛榮以及其導致的痛苦在人類生活各個領域的經驗證據。罪是人類生活中的主要問題,是上帝來到地上要拯救我們的事情。天使沒有對約瑟說:「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或救主,因為他要救你免於政治不正確,甚至免於痛苦。」
笛卡爾對罪有什麼說法?他只提到過一次罪或道德邪惡,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罪的唯一一次是在談到他在物理學中的科學發現時。他寫道:「我認為我不能隱藏它們而不犯下巨大的罪。」犯下對什麼的罪?笛卡爾在下一句話中回答了這個問題:「對培根的至高善:讓我們成為自然的主人和擁有者。」然後他在這個背景下談到了無限或無限制,這是一個上帝的屬性,他沒有在談到上帝時明確提到。
他寫道:「這不僅僅是為了發明無限多的裝置,讓我們能夠在沒有痛苦的情況下享受地球上的果實和所有在這裡找到的財富,而是主要是為了維持健康,這無疑是第一大善,是這個生命中所有其他善的基礎。因為心靈極大地取決於身體的體質和器官的處置,如果有可能找到一些手段讓人們更聰明,我相信我們應該在醫學中找到這個手段。事實上,目前實踐的醫學幾乎沒有什麼有用的,但在這個領域,我們所知道的一切與我們所不知道的相比,幾乎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們能夠充分了解它們的原因,我們可以擺脫無限多的疾病,無論是身體的還是心靈的,也許還可以擺脫因年齡增長而造成的衰弱。」
好吧,我們今天知道年齡增長的原因是遺傳性的,我們破解了遺傳密碼,我們正在學習如何用我們自己的編碼取代上帝和自然的編碼。如果我們這樣做,通過消除不僅是疾病,還有死亡,我們將徹底重新解釋John Donne的虔誠詩意預言,「死亡啊,你要死去」(Death thou shalt die),以便將死亡的征服放在我們的控制下,而不是基督的。
這將是以幾乎完全相同的方式扮演上帝,就像一個母親,她為墮胎自己的孩子辯護,當她扮演上帝並徹底重新解釋基督的聖餐話語,「這是我的身體」。她說同樣的話,但要奪走生命,而不是給予生命。
這是我的身體!
撒旦喜歡褻瀆,他沉迷於將地球上說過的最神聖的話語翻轉過來,以表示反基督的行為,而不是基督,德古拉奪走我們的血液,而不是基督的行為,基督將他自己的神性血液和身體賜給我們。
《科學怪人》是史上最受歡迎的故事之一,儘管它遠非文學傑作。為什麼它如此受歡迎?因為我們本能地知道,科幻小說最終會成為科學事實,為什麼人工永生技術應該是這個規則的例外?
笛卡爾告訴我們要懷疑一切,但他寫信給Burnham說,不應該懷疑人類生命可以「延長」,如果我們知道適當的藝術。延長?多長時間?為什麼一定要有結束呢?
為什麼不完全征服自然,征服死亡本身,自然的王牌呢?我們有沒有發明過一種新的藝術或力量,我們不想使用它?實際的科學發現和發明,當然是核彈。笛卡爾會怎麼看待這美妙的進步?他會不會驚訝地看到它在廣島和長崎的後果?大多數有理智的人,意識到基督教所說的原罪,都會喜歡將這個精靈重新關進瓶子裡,如果他們能的話,關閉由我們的驕傲和對權力的貪婪打開了的潘多拉魔盒。但一旦那個蘋果被吃掉,它就不能被吐出來。當死亡之門關閉時,天堂之門也關閉了。如果那發生了,帕斯卡爾將被證明是太天真和樂觀了。讓我們祈禱那不會發生。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