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記_《終極警察國度》揭開中國反烏托邦的駭人真相_推薦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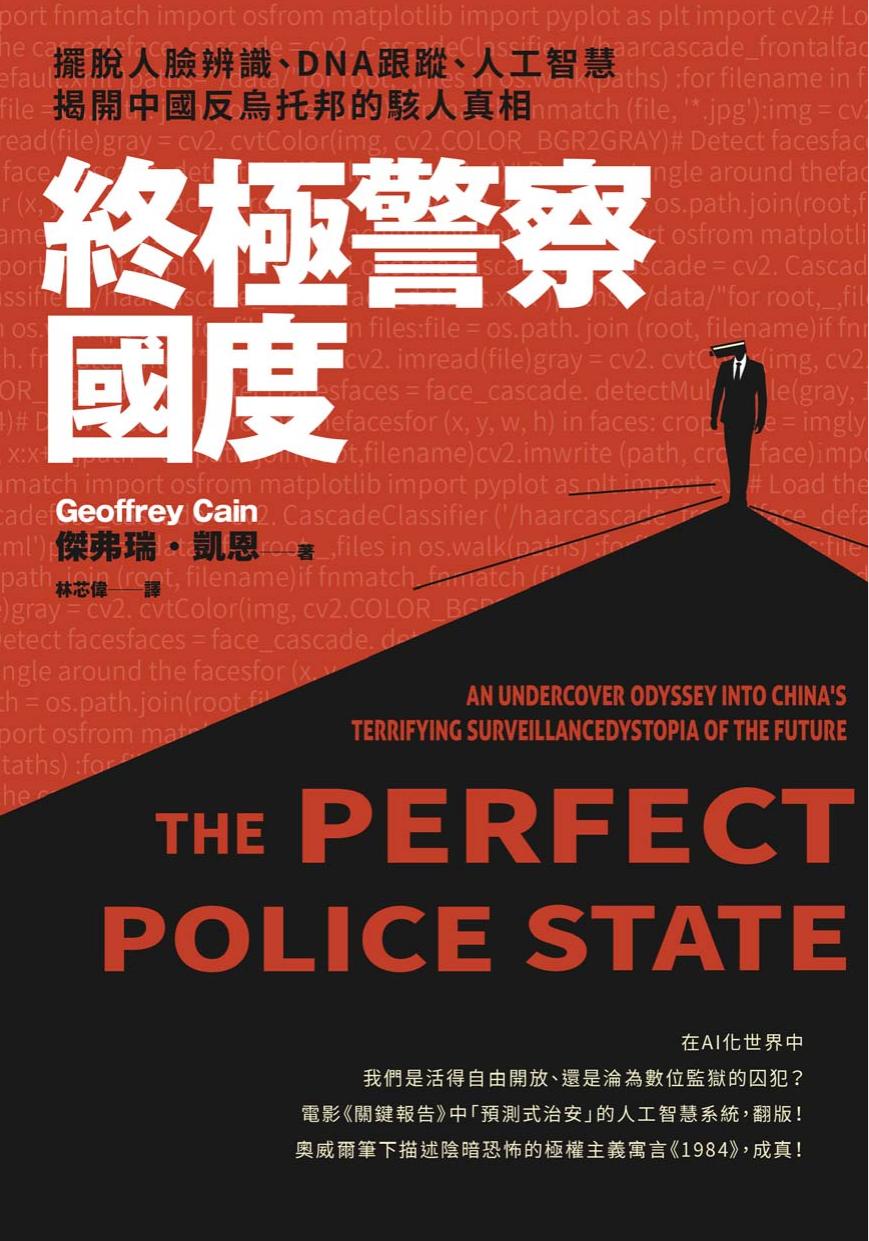
當威權主義政體擁有大數據: 如果蘇聯能夠進行大數據監控, 可以避免崩潰嗎?
沈旭暉博士 **國際關係學者**
不少學者談及,今天中國、俄羅斯等政體,表面上,並非昔日教條式極權主義、純粹高壓的「獨裁者1.0」模型,更多是表面上賦予了人民一定空間、其實卻是用這些假象來合理化專制統治的「獨裁者2.0」。
以往極權主義主要形容二戰前的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共產蘇聯等,指政權的權力無限制,並追求絕對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以蘇聯為例,史達林死後,就算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上台,推行「去史達林化」運動,普遍被認為是較開明的領袖。然而,赫魯雪夫政權對黨內反對者、政治異見者的打壓,雖然沒有史達林時期般明顯,但對人民的監控卻伸延至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立陶宛學者巴洛茨卡伊特(Rasa Balockaite)提到,莫斯科在「後史達林時代」開始,把注意力由政治打壓轉移到社會和經濟控制,成立一系列有別於傳統黨政機關的非正式組織,以一個更廣闊的網絡去監控人民。整個管治手段,比以往來得去政治化、去中心化:一方面,人民對政權的討論固然少之又少,也沒有多少把柄可被掌握;另一方面,透過這些網絡,令人民在政治生活以外的個人行為、習慣,也逐漸掌握在黨的資料庫當中。
冷戰結束後,前蘇聯陣營各國的祕密警察檔案陸續解密,可見這種監控的精細,已是相當科學化的工序。東德祕密檔案的公開,以及電影《竊聽者》的情節,尤其令世人震撼。
理論歸理論,這種去政治化、去中心化的監控,雖然已看出與科技結合的雛形,但畢竟受當時條件所限,要紀錄國民生活細節的行政成本,始終較高,而且充滿漏洞。當時至少需要人力物力去搜集、紀錄對象的生活日常,再一層一層向上級彙報,即使有基本竊聽、監視設備,也未能做到對全體公民無孔不入。加上人民非常清楚政治環境,定會理性作出口不對心的表述,假如單單依靠公開表態,往往令監控結果的準確度下降。可見舊式極權雖然設法掌控生活每一個細節,但未竟全功,否則冷戰也不會這樣結束,那些政權更不可能不戰而敗。然而,這些不足之處,在大數據年代,統統已不成問題。
中國大陸「芝麻信用」這類信用評級機制,並非橫空出世,翻閱文件,一切有跡可尋,例如中國國務院2014年發出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當年中國政府仍未將社會信用系統與網路結合,但已為推動這些政策,建立了理論基礎。綱要指出,「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石」,為推動經濟改革,必須建立信用系統,達致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14年前,中國大陸的信用市場以央行作主導,但此後流動付款普及至日常生活,信用系統進入了市場化階段。2015年,中國人民銀行印發《關於做好個人徵信業務準備工作的通知》,要求包括「芝麻信用」、「騰訊徵信」在內的八家企業,為徵信業務做好準備。自此,這些經常被提起的信用系統,便擴展到人民生活的不同層面。
某程度上,這現象自然也不是中國大陸獨有,世界各國發展大同小異,不過以中國人口基數最高,漠視人權的特徵也最明顯而已。至於如何計算每個人的「信用」,這些科技公司都以大數據、雲計算這些詞彙說明計算方法,但具體公式一直未有公布。不過,他們倒是說明了哪些事情影響評分,例如「芝麻信用」其中一項基準是用戶是否準時提交電費、水費,是否準時還清貸款;「騰訊徵信」的用戶分數,則基於消費、財富、安全與守約的大數據,其中「安全」是指用戶有否實名登記、數位認證等。推廣時,這些公司都提供不少誘因,例如租用「共享單車」、訂酒店不需保證金、低利息分期購物等,令一般人都樂於個資被收集;而兜兜轉轉,用戶是否適當鎖上「共享單車」一類行為,又會成為評分大數據的一環。
大數據、雲計算收集的資料,涉及的範疇比以往更廣、更準,所需人手亦因少了抄寫、彙報的過程而減少,用戶的一切行為、消費習慣、個性隱私卻都一覽無遺,而且超越了公開表態的漏洞,能進入每人心底裡最真實的一面。這些數據資料如何被分析、使用、推算,除了是近年商家、政界的研究範疇,自然也是威權政府希望掌握的資訊。在商業層面,最簡單的例子自然是根據搜查關鍵字、瀏覽過的網站推銷產品,更進一步是基於所收集的數據,以「助推」(nudge)用戶的行為,如消費決定等;在政治層面,投票取向同樣能這樣「助推」。
來自丹麥技術大學的學者利曼(Sune Lehmann)與斯派斯基(Arek Stopczynski),曾研究能否透過收集學生數據,分析並助推他們的行為,達致更好成績,甚至精神健康。推而廣之,助推自然亦可應用於社會、政治,從而使國民作出符合當權者的良好行為。收集大數據的目的已不止於監視,而是控制,也就是更貼近威權主義的終結理念。
不少人以為,假如減少使用網路、智慧手機,就可避免被過度收集資料。不過,這已經是偽命題了,因為科技公司正大力推廣「物聯網」 (IoT),也就是將物理世界數位化。這世界相信很快就完全成熟,屆時即使關上電話不用,你曾到過的地方、習慣偏好、健康狀況等,亦會因你日常使用的智慧家具,如電燈、電視機、冷氣,24小時全天候被收集。
面對這情景,不少學者均討論過人民處於民主與威權國家的分別。但其實真的有分別嗎?在較民主的國家,當然都有定立法例,規範可收集的數據範圍、使用方法等,表面上有較透明的制度,讓市民了解數據去向。不過,即使以上機制健全,政府與私人公司信守承諾,我們也不能排除駭客、恐怖分子取得數據,而這些新聞在近年屢見不鮮,屆時已超出如何規管數據、透明度與道德的問題,結果我們日常的一舉一動,也是在一些機制掌控之中。何況從史諾登的案例可見,即使是民主國家如美國,以「國家安全」名義,同樣可以進入一切大數據庫,對所有人的檔案一覽無遺;而川普團隊如何利用大數據「助推」潛在支持者出來投票,乃至怎樣利用人工智慧在討論區造勢,更已成為學術研究課題。這一切在威權國家,更是理所當然。
假如希特勒、史達林活在今天,領導各自的國家,還有倒台的一天嗎?特別是冷戰時代有這些科技,共產主義國家可否實現計畫經濟、全面監控,以鞏固其統治?蘇聯的崩潰,可以避免嗎?
要討論這個命題,得先了解計畫經濟當年的運作。眾所周知,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絕大部分時期,都實行計畫經濟,生產原料、企業都是由國家擁有,勞動力也由國家分配,以生產出計畫目標的產品數量。這些國家的供求非由市場主導,而以追求不同的「五年計畫」為目標,消費者的需求沒得到重視,因國家盼藉計畫經濟推動工業化、現代化及農業集體化,以追上西方資本主義的生活水準。
理論上,「五年計畫」由蘇聯國家計畫委員會(Gosplan)制定,經歷不同領域、不同級別的機構、官員、企業,再由國家計畫委員會修改,最後在黨代表大會通過。然而,在實際操作上,政治局成員、以至總書記在過程中,究竟參與多少?
他們有否明示或暗示應訂下怎麼的指標?這些指標是科學化的指標,還是抽象的指引?這些問題難以說清楚。蘇聯治下的烏克蘭大饑荒、中國的大躍進,都是計畫經濟沒大數據支援下的災難性後果。
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本質的問題,在學術界自然討論多時。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埃爾曼教授(Michael Ellman)是研究這範疇的權威,他提到社會主義經濟體經常生產消費者不需要的產品;但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必需品、商品總是存貨短缺,但當局對商品庫存的數據並不充分,甚至不準確。即使最低層的數據準確無誤,在匯報過程中,官員因存在升職的誘因誇大成果,或技術官僚因循失責,而令上級難以掌握實情,這些情況,至今依然,不見得是歷史。
由於計畫經濟未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在社會主義國家,往往出現「第二經濟」(The second economy)。學者森遜(Steven Sampson)指出,「第二經濟」由非法生產或交易產生,亦包括企業、工廠為追求生產目標,而產生的非正式或非法活動、地下工廠等。這些活動在冷戰時期的東歐、蘇聯相當盛行,在今日極權主義的最後代表北韓也同樣出現,導致經濟活動無法準確統計,官方數字準確性成疑。基於以上因素,美國從不輕信蘇聯官方公布的數字,中央情報局會自行統計相關數據,不少人認為CIA的數字,較蘇聯官方公布更可信。
那麼在現代社會,有了資訊科技革命,又是否可以避免以上制度上的缺失與人為錯誤?
正如早前談及,大數據、物聯網等,是一個全天候收集個人數據的機制,問題只在於不同軟體的權限、如何儲存或傳遞相關訊息、誰人能掌握等,但技術本身,毫無懸念。假如政府決意收集全國國民這些資訊,首先就可以解決「第二經濟」無法被紀錄的問題;而每一個紀錄,也不用經過官僚系統逐級向上匯報,政府高層可輕易掌握準確數字,第一個問題,也可以大部分解決。
舉一些實質例子,中國大陸網購龍頭阿里巴巴每年統計「雙十一」的交易資料,除了是大數據,還是即時性的數字,避免使用滯後數字作決定。以往這些技術只會用於金融業,如股票、期貨等交易,但現在就連到便利商店購買一包紙巾,也可以立即反映到不同伺服器內。又如美國的Amazon Go,連「客人拿起商品」這個動作本身,甚至不涉及具體金錢的購買行為,也可以被紀錄。當這種技術被推而廣之,不止是股票買賣,幾乎所有日常消費、零售行為,均可被統計。
在自由市場,這些資訊可以令政府、企業清楚了解需求,但對蘇聯一類國家而言,假如當時有這些技術,就可以利用更準確的數據,制定「五年計畫」。唯一未能改變的是決策者會否忽視實況,作出不切實際的目標;但相信在大數據年代,一切透明,領袖要「逆天行事」,即使在極權政體內部,也不容易為所欲為。
在經濟層面以外,這些技術同樣可用於政治層面,假如蘇聯的國家安全委員會(KGB)有了大數據,就不只是如虎添翼。作為情報機構,KGB主要對不利蘇聯的行為進行情報工作,而正如早前提及,自赫魯雪夫起,蘇聯的情報工作就出現「去政治化」、「去中心化」的監控,人民在社會、經濟層面的舉動,均被非常規組織監察。但與此同時,只要行為並非超出政治層面,當局也不會作出行動,而且基於人手問題,備受關注的往往是異見者,他們會被入屋搜查「反革命」證據,而普羅大眾,則大致生活如常。
不過隨著科技發展,人民的生活與網路緊扣,蘇聯的繼承者俄羅斯,就公然嘗試掌握國民在網上的行為。根據《維基解密》公開的文件,俄羅斯有一套名為「SORM」的情報系統,自1990年代起就對國民全方位監控,由電話、短訊開始,到近年的網路、社群媒體、信用卡交易、智慧手機等,無所不包。對比蘇聯時代,這個系統可更快、更有效掌握全國人民的行為,而作為KGB培訓出來的領導人,普丁對這一套,自不會擱下不用。
我們也許認為網上行為自我約束,便可逃避監控,但現在天眼處處,加上人臉辨識系統發展迅速,結合大數據的應用,離開家園後的一舉一動,幾乎都被紀錄在案。在中國大陸國內,不少新建社區、廠房,已使用具人臉辨識的保全系統,能輕易辨認住戶人臉,並顯示如年齡、身高等基本資料,就連出入次數也可紀錄。即使放下電話,你的日常生活,依舊暴露於監控系統當中。個別人臉辨識系統更聲稱具有「深度學習能力」(deep learning),與昔日的舊式閉路電視不可同日而語。目前這些系統仍處於早期階段,社區、門市的保全系統,未必與官方機構的互聯互通,但要將不同系統連結一起,技術上並不困難,幾乎肯定會有這一天。
假如史達林活到今天,蘇聯在推行計畫經濟、資源分配上,政府應可掌握更廣泛、更準確的數據,以實現他心目中的工業化、現代化;政治上,亦可更微觀地監控民眾。最大挑戰反而是擁有大數據的一群,會成為吉拉斯(Milovan Djilas)所說的「新階級」,甚至取代領袖的地位,總之,平等社會依然難以實現。但只要接受了這一點,假如這制度在中國大陸一類國家令一般人過得安穩,又能容許走過場的、預先知道結果的「民主程序」,威權政體是否對一些人比民主政體更「吸引」,如果我們不認同、又可以做什麼,正是此刻全世界人民都要思考的嚴肅抉擇。
原文發表於《信報財經新聞》,經作者更新改寫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