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能孕育出薩依德式的知識分子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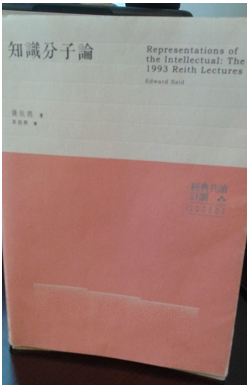
——評《知識分子論》(Edward Said 著,單德興 譯,2011)
從事文學與藝術評論者,對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這個名字應不陌生。然而,他最廣為人知的,卻是對中東與伊斯蘭世界的評論,尤以「中東評論三部曲」——《東方主義》、《巴勒斯坦問題》與《採訪伊斯蘭》——最為人稱頌。薩依德生於耶路撒冷,父親是巴勒斯坦的希臘東正教徒,後來皈依聖公會;母親則為浸信會信徒。自幼浸潤於英語與阿拉伯語雙語文化,使他形成獨特視角,並未如許多基督徒般盲目親近猶太傳統。
1967年中東戰爭之後,他開始密切關注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壓迫;1993年,他更明言「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 是對巴勒斯坦人不公平的「凡爾賽和約」。這二十多年來,薩依德在美國頂尖大學任教,於學術與政治關懷的辯證張力中,逐漸孕育出中東評論三部曲。他以知識分子的道德責任為使命,甘冒「暴力狂熱分子」、「反猶主義者」的罵名,說出了伊斯蘭世界具體的一面,與西方大眾媒體所塑造的平面伊斯蘭世界 —— 不是恐怖分子就是難民形象 —— 大相逕庭。
1993年,英國廣播公司(BBC)邀請他擔任李思講座(Reith Lectures)主講人,講題便是〈知識分子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之後集結成書出版,中文譯名為《知識分子論》。與其說這是關於知識分子的理論探討,不如說是薩依德的現身說法:他不是體制內的技術員或學術專家,不為任何政府、企業、媒體或權力系統服務。他堅持,唯有脫離受聘結構的侷限,知識分子才能自由發聲、獨立思考、揭示真相、對抗壓迫。他稱這為「再現」(re-presentation)—— 就是把被掩蓋、被壓制的現實重新呈現,讓人重新看見。
然而,對薩依德而言,「再現」不僅是知識分子的職責,更是一種生命的形態。真正的知識分子不隸屬任何單一陣營,今天可站在受害者一方批判強權,明日若這一方成為壓迫者,他也毫不猶豫轉而批判之。因此,批判強權往往沒有重複的故事可依循,每次都要從新的角度呈現自己。因此,他經常無法歸屬於任何派別或機構,注定成為邊緣人、流亡者。
讀此書之時,我心中不斷浮現一個問題:基督教能孕育出薩依德式的知識分子嗎?
表面上,似乎難以並存。薩依德式知識分子不承認任何終極權威,而基督教則以上帝為權威。然而,若我們放下對「權威」的狹隘理解,便會發現,聖經中早已有薩依德式知識分子的先驅。
舊約的先知們,豈不正是這樣一群人?他們不畏強權,單憑上帝的啟示,指責列國與以色列的罪惡。他們不倚靠任何制度,只倚靠上帝的話語,因此其生命也是一個不斷「再現」的生命:他們不擁有重複的自我敘事,他們每一次宣講信息,都是基於上帝的話臨到時,所得全新的使命。今日傳平安,說不定明日就要傳責備的信息;他們流離失所,甚至被殺害,只因忠實於神的話語。
不僅是先知,歷代的聖經翻譯家與宗教改革者——如威克里夫、丁道爾、馬丁路德、加爾文等——同樣背負著再現上帝話語的使命。他們也經歷了逃亡與逼迫,只為叫神的真理被世人看見。他們雖然為信仰而戰,卻未將信仰變為政治工具,而是以信仰作為對一切強權說「不」的根基。
因此,我們不能斷言基督徒無法成為薩依德式的知識分子。誠然,我們有上帝為最高的權威,但正因如此,我們才不應服從世間的任何權力、文化潮流、意識形態、甚至教會的體制。我們不以黨派為義,不以民族為義,只以基督為義。
我們跟隨的,不是薩依德,而是耶穌基督。祂無枕首之地,我們便也成為無所依歸的流亡者;祂背負十架,我們便也當不惜一切代價,承擔見證真理的使命。若我們願意如此走上「再現真理」的十架道路,那麼,在今日世界的邊緣處,或許就能看見新的、屬神的知識分子正在興起——他們不是從體制中出來的權威者,而是從曠野中走來的見證人。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