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稱複數|複語術
接續多年前,看陳昭如《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2014,即將再版)後,去年參加人本基金會與台大合辦的「校園性犯罪」研討會(2019),到看完台灣電影《無聲》(2020)之後,憤而寫下這篇心得,投到關鍵評論網的讀者投稿。
寫完後才從台灣障礙研究學界的師長那邊得知,這部電影不但沒有真實呈現性平事件應有的程序,也沒有真實呈現聾人世界。人本基金會與陳昭如,也於今日聯合澄清,表示與《無聲》製作團隊完全沒有合作關係。
《無聲》雖然警醒了社會大眾,卻為了電影的戲劇張力而扭曲了校園性犯罪的真實,是福,還是禍?我們又該如何評價這部電影?我還需要時間好好沈澱,還不夠好,也值得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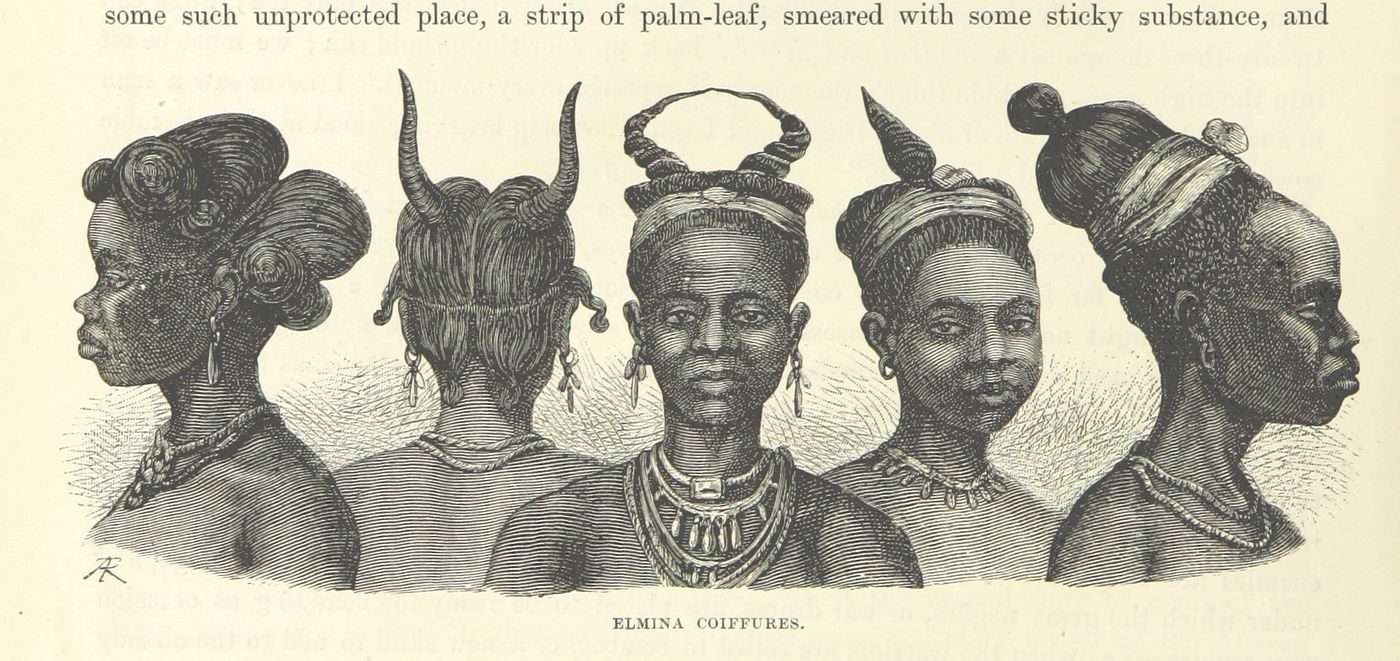
隨著國片《無聲》在戲院上映,不但好評不斷,也相應催生許多影評與讀後感。很多人已經指出,《無聲》與九年多前,台南某啟聰學校性侵案件高度關聯[1],更有人聯想到三年前的林奕含事件[2],令許多觀眾走出戲院後仍心有餘悸。
我想藉著《無聲》談幾個問題。
障礙是誰的問題?
啟聰學校原是為了補足聽障學童在教育資源上的不足而設立,卻導致聽障學童不但被聽人社會排除出去,甚至害怕「回歸」健全社會。聽障到底是誰的問題?
長久以來,障礙的觀點一直被所謂的「個人模式」主導,也就是覺得障礙是個人的問題,需要別人才能解決。個人模式分為兩種:慈善觀點與醫療觀點。持慈善觀點的人主張:障礙者是值得同情的對象。他們認為障礙者不可能自立生活,必須仰賴社會捐助與善意才能生存。比方說啟聰學校就是慈善觀點的產物。另一種持醫療觀點的人聲稱:障礙者是一群需要被治療的人。他們相信醫學、科技的進步,能夠幫助障礙者「恢復正常」。[3]
個人模式好嗎?我並不認為。
如果,聽覺障礙的小孩覺得耳朵聽不到是「自己」的問題,就會覺得在普通學校跟不上別人也是「自己」的問題,轉到特教學校是連累家人。這種負罪心態,導致聽障學生在學校遭受霸凌或性侵後,寧願保持沈默。聽障小孩覺得,他已經因為「自己」的問題連累到別人,在特教學校已經夠好了。這在《無聲》簡直隨處可見:
比起(在啟聰)被同學們欺負,我更害怕到「正常」社會去。(《無聲》,手語對白)
自1970年代後,個人模式遭到「社會」模式的挑戰。社會模式以「人權」的立場,堅信障礙是社會的問題,認為是社會環境無法包容個人差異才造成障礙。持人權觀點的人強調,各式各樣的障礙者呈現的是人類的多樣性,而非需要「同情」或「修復」的人。以社會模式觀點詮釋《無聲》,聽障角色害怕離開啟聰學校的理由,不是還沒有學會回歸社會的能力,而是社會環境還沒有能力可以接納更多的人。
為什麼沒有阻止下一個「小光」的誕生?
特教老師王大軍(劉冠廷飾)一開始替張誠(劉子銓飾)解圍,並利用翻譯之便為委屈的張誠出一口氣。王老師儼然一位熱血教師:他不但細心感性,能突破貝貝(張妍霏飾)心房,鼓勵她勇於說出真相;他還耐著性子,個別訪談所有可能牽涉的學生;他更能理性分析,釐清聽障學生受害的時間順序、發生地點,最後在白板寫下127起疑似性侵的事件,並且勇敢舉發。這麼一個集全人類優點的王老師,彷彿整部電影的穎雄人物。為什麼他已經勞心勞力了,還是沒有來得及沒有阻止下一個「小光」(金玄彬飾,此處指下一個由被害者轉為加害者的案例)的誕生?
當我們面對危機或困境時,常常會期待有全能的英雄出面解圍。就像市民看到高譚市被人搞得烏煙瘴氣,就期待有蝙蝠俠能出來鏟奸除惡。而《無聲》像是提醒我們,沒有絕對無辜的被害者,沒有十惡不赦的加害者,也沒有人能置身事外。如同導演在專訪提到:「這部片想傳達的不是對與錯的問題...我盼望的是更多對話。」[4]假如我們把教育或是救人的責任全盤丟給特教老師,就只會壓垮一個充滿熱血的王老師,製造出下一個懦弱怕事的竇老師。
姚貝貝(陳妍霏)第一次被啟聰學校的同學欺負的時候,寫日記向竇老師求助。但是老師只是推託說「你們不是在玩嗎?」「他們(欺負貝貝的男同學)人都很好,不可能會做這種事」,然後轉頭離開。也是導致貝貝往後不敢向王老師坦承的理由之一,因為她認為「反正老師不會相信」。
校園性犯罪並非單一個案,而是整體社會結構的問題。不是抓出犯人就好,而是包含成人在內乃至於整個社會,都需要性/別、同志教育以及情感等再教育,才有可能從根本改善缺乏性別意識的結構。除此之外,我認為還需要人權教育。如果我們接受社會模式理解障礙的人權觀點,便會發現日常生活中不乏歧視的例子,對原住民、新住民、身心障礙者以及有前科的人等等。人權教育的核心很間單,就是把這些人當人看,可惜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這些人被當成非人的時候還是占大多數。
人,是單一人稱複數
若我們接受人權觀點的解釋,相信「障礙」只不過是人一種多樣性的展現,而真正造成障礙的是這個「不健全」的社會。那麼,《無聲》將幫助我們思考,每一個人都是單一人稱複數。他/她可能長期遭受霸凌,又因為個性內向不擅長表達情緒,只好透過性侵別人來緩解壓力。他/是聽障,同時可能有量表測不出來的輕度智能障礙,卻因為特教學校只能提供單一特教資源,而被長期忽視。他/她是聽障,同時可能是同志,卻因為沒受過同志教育,誤以為自己是變態,只好透過性侵異性來「矯正」性向。他/她是聽障也是同志,卻誤以為障礙跟性向是自己的問題,只好利用權勢性侵孩童,還誤以為這是愛與付出。關於生而為「人」的複雜性,我想《無聲》提供了一個顯著而難忘的案例。
我並不是要為加害者/犯罪者開脫。他們的確做錯事,而且罪證確鑿。但是我們也應該考慮到,在他們受到應有的懲罰之後,重新接納他們的可能。《無聲》是一則震耳欲聾的通知:提醒我們不該活在無聲的孤島,而應該重新建構社會安全網,以期接住更多快要犯錯或犯過錯的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考資料:
[1] 可參考奇摩新聞整理 。
完整報導應詳參,陳昭如,《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台北:我們出版,2014年)。
[2] Kristin,〈【電影】無聲 The Silent Forest,我們一路奮戰,是為了不讓世界改變我們。〉,刊載於《方格子》(2020年10月10日)。
[3] 黃怡碧主編,《CRPD話重點:認識《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關鍵15講》(台北: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台灣國際醫學聯盟,2020年),頁19。
[4] Ren,〈《無聲》台北電影節開幕片探討「愛與救贖」:「不是對與錯的問題,更不是批判,而是試圖去看到、聽到那些無能為力。」〉,刊於《美麗佳人》(2020年06月15日)。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