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集_《解放的悲劇》毒草
第十四章 毒草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共產主義世界迎來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捩點:在蘇共二十大的最後一天,當外國代表團紛紛準備離開時,赫魯雪夫召集蘇聯代表們在克里姆林宮召開了一次臨時祕密會議。他發表了連續四個小時的談話,對史達林嚴詞抨擊,聲稱他為國家製造了巨大的恐怖,應該為殘酷的大整肅、大放逐、未經審判的死刑以及無數黨員所遭受的痛苦折磨負責。赫魯雪夫還指責史達林「好大喜功」,鼓勵對自己的個人崇拜。與會者聽得目瞪口呆,演講結束時沒有人鼓掌,許多代表帶著震驚的心情離開了會場。
這份報告的副本被送達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由此造成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在北京,毛主席不得不採取了自衛的行動,因為毛就是中國的史達林,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領袖,而這份祕密報告會使人們對毛的領袖地位產生疑問,並會動搖大家對他的崇拜。蘇聯的去史達林化對毛的權威構成了巨大挑戰,赫魯雪夫宣布要將權力歸還給政治局,而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和其他中國領導人也紛紛表示支持集體領導制。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召開的中共第八次黨代會上,不僅從黨章中刪去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而且提倡實行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面對赫魯雪夫造成的困境,毛別無選擇,只有接受現實,甚至在大會召開前幾個月就表示贊成這些措施,但是當他和李志綏私下談話時,卻絲毫沒有隱藏自己的憤怒,他抱怨說劉少奇和鄧小平聯手操控了大會,把他推到了後臺。
赫魯雪夫還指控史達林在一九三○年代摧毀了農業,甚至說除了莫斯科他哪裡都沒去過,從沒見過工人和集體農莊的農民,只是透過「美化農村的虛構電影」來瞭解農村。毛主席的情況也差不多,他是坐在舒適的專列上,從列車的視窗來瞭解農村的,專列所經的車站,除了安保人員,其他人全被清理一空。赫魯雪夫抨擊的雖然是蘇聯的集體農莊,但聽起來似乎也是在批評中國的做法。周恩來和陳雲在得知蘇聯的態度後,試圖減緩集體化的速度。他們在一九五六年夏天提出「反冒進」,不僅壓減了集體農莊的規模,而且有限地恢復了自由市場,允許農民更大規模地從事個體生產——這一切都被毛視為對他個人的挑戰。《人民日報》還準備刊登一篇社論,提出社會主義高潮不能一蹴而就。毛收到這份社論的草稿時,在文件的抬頭處憤怒地批道:「不看了。」他後來反問道:「罵我的東西,我為什麼要看?」中共八大廢除了「社會主義高潮」的提法,這對毛來說,不啻為重大挫折。
赫魯雪夫的祕密報告在東歐也引發了改革的呼聲,波蘭的工人走上波茲南街頭,抗議生產指標過高,要求提高工資。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幾萬群眾聚集在祕密警察所在地——皇家城堡周圍,搶奪警察的武器,並釋放了所有犯人。波蘭各地的共產黨總部也遭到了洗劫,超過一萬名蘇聯軍人前往鎮壓,動用了包括坦克、裝甲車和野戰炮在內的裝備。軍隊向示威者開槍,造成近百人死亡,受傷者則更多。然而,波蘭共產黨及波蘭統一工人黨的領袖瓦迪斯瓦夫.哥莫爾卡(Wladyslaw Gomulka)很快做出妥協,同意提高工人工資,並承諾實施政治和經濟改革。此後的一段時期被稱為「哥莫爾卡解凍期」,波蘭共產黨開始尋找「通往社會主義的波蘭道路」。
幾個月後,匈牙利也發生了叛亂,數千名學生走上布達佩斯街頭,有人甚至試圖進入國會大廈,向全國播送他們的要求,結果被警察槍殺。隨後,全國各地都爆發了示威者與警察的暴力衝突。為了恢復秩序,莫斯科向匈牙利派出數千名軍人和坦克,這一舉動激怒了更多的群眾,大家紛紛湧上街頭,加入反政府的隊伍。在布達佩斯用鵝卵石鋪就的狹窄街道上,示威者用燃燒瓶同坦克作戰,各地還成立了革命議會,從當地政府手中奪取了政權。示威者號召全國舉行總罷工,各地還砸碎了各種象徵共產主義的標誌,焚毀了相關書籍,大樓上的紅星被摘了下來,紀念碑也被推倒,豎立在布達佩斯城市公園裡的史達林銅像也不例外。到了月底,大部分蘇聯軍隊都被迫撤離了布達佩斯,新任總理納吉組成聯合政府,釋放了政治犯,解禁了非共產黨的組織,並准許其加入聯合政府。
對於匈牙利的局勢,莫斯科的反應起初還比較克制。十月三十一日,新成立的匈牙利政府宣布將退出華沙公約組織,就在同一天,位於布達佩斯的共產黨總部附近爆發了暴力衝突,群眾將祕密警察揪出,把他們吊死在街邊的路燈上,幾個小時後,這一場景的照片便出現在蘇聯的報紙上。赫魯雪夫當時正在史達林的別墅裡度假,他考慮了整整一個晚上。由於擔心匈牙利的暴動會波及到鄰國並最終導致蘇聯集團的解體,蘇聯領導人改變了之前的態度。十一月四日,蘇軍大舉入侵匈牙利,殺害了數千名群眾,超過二十萬難民逃離了匈牙利,大規模的逮捕行動持續了好幾個月,所有的公開反對意見都被鎮壓了下去。
對於這些因去史達林化而引發的國際事件,中共的領袖也在密切關注著。一九五六年十月,哥莫爾卡發表了一番激勵人心的演講,承諾要實行自由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freedom),他還提到,波蘭集體農莊的產量不如私人農場來得高,北京全文轉載了這篇演講。對中國讀者衝擊最大的,是哥莫爾卡關於蘇聯的評論。他說波蘭欠蘇聯的錢,其原因是蘇聯逼迫波蘭向其廉價出售商品,同時向波蘭高價出口蘇聯商品,因此蘇聯似乎對波蘭進行了「帝國主義剝削」。正當波蘭的混亂達到高潮時,又傳來匈牙利動亂的消息,這讓許多中國讀者越發感到興奮。羅記述道:「大家對報紙的熱情前所未有地高漲,之前讀報紙都是被迫的,因為平時開會都得討論報紙上的內容,但是現在許多人寧願曠工,也要排長隊買一張報紙來看。」因為報紙上的新聞都經過了嚴格的審查,所以人們不得不從字裡行間發掘其背後的深文大義,有些工人甚至以匈牙利為榜樣,公開發表批評政府的言論。
因各種原因對當局心懷不滿的群眾開始走上街頭,透過示威和請願的方式發洩心中的憤恨。學生也開始罷課。一九五六年秋,南京航太航空學院有三千多名學生宣布罷課一個月。這所學院號稱是全國一流的大學,但實際上最多只能算是一所中等的技術學校。在與它相隔幾條街的南京師範大學,有一名年輕人無意間撞到六名學生,遭到這些學生毆打,公安局卻包庇打人的學生。很快地,全校學生組織遊行,要求伸張正義,警察則威脅要以暴亂的名義逮捕示威者,結果促使四百八十名學生聚集在南京市政府門口,高呼口號,要求民主和人權。南京並不是唯一出現這種情況的城市,除非檔案完全公開,沒有人知道當時學生的不滿有多麼嚴重。但僅在西安這個中等規模的城市裡,就爆發了不下四十起工人和學生的請願示威活動。到一九五七年初,全國各地有上萬名學生參與了示威遊行。
與此同時,工人罷工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一九五六年,工業部統計的罷工就超過了兩百二十起,大多數發生在十月分之後。上海有數千人參加了罷工,甚至有黨的幹部和共青團員參與領導。工人抗議的內容大都是實際收入減少、租房條件差和福利縮水,這些不滿在許多工人的心中已經累積多年,而社會主義高潮運動中對私人企業的集體化改造直接引發了這些不滿情緒的集中爆發。上海之外的許多地方也爆發罷工,甚至導致了相關經濟活動的癱瘓。例如:在東北,有兩千名從事糧食運輸的工人故意怠工,要求政府漲工資,當幹部威脅要把他們打成反革命分子時,示威者的態度反而變得更加堅定。在福州,工人不斷向市政府請願,前後多達六十起之多。
農村也是一樣。一九五六年,農民對集體化的不滿達到了高潮,政府也實行了一些改革,如縮小集體農莊的規模、允許農民出售部分自留地裡種的農產品等,但農民們最希望的是退出集體化。一九五六年秋,浙江仙居縣出現了糧食歉收,農民們開始公開表達不滿,許多人退出合作社,發表反黨言論,毆打當地幹部,一百多個合作社因此完全瓦解。在江蘇泰縣,數千名請願者聚集到黨委大院門口請願,當地的經濟倒退到了以物易物的方式,村民們成群地退出合作社,有些還拿回了自己的耕牛、種子和工具。
在廣東省,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的冬天有數萬名農民退出合作社,其中鬧得最凶的是中山和順德兩個縣。在順德,多達三分之一的農民堅持拿回自己的土地,恢復單幹,遇到幹部阻撓,就會對其進行毆打。在湛江下轄的幾個縣,每十五人中就有一人大膽提出退社,他們牽走自己的耕牛,並拒絕把小孩送到學校,出於報復,有些地方甚至不許這些村民上街。在信宜縣,憤怒的村民開始毀壞集體財產,燒毀糧庫,有人甚至帶著刀子參加集體會議,強迫幹部准許其退社。
甚至有些地方幹部也開始發表反對集體化的言論。有人說:「生活上不如勞改犯。」在廣東汕頭,有些幹部認為糧食壟斷政策的剝削程度超過了封建時代。在保安縣,百分之六十的幹部反對糧食統購統銷。在羅定縣,一名副書記說:「在到農村之前,我是相信集體化具有優越性的,但是到了下面卻連粥都喝不飽,餓得頭暈,所以我再也不覺得集體化有什麼好處了。」在英德縣的一次黨的會議上,好幾名與會人員公開說一九四九年前的經濟狀況比現在好。在崖縣(今三亞),有四十幾名領導幹部及其家屬跟農民一起拒絕參加合作社。陽江縣一名合作社社長控訴說,在施行糧食統購統銷的三年裡,除了稀飯,黨什麼都沒有給過農民。在懷陽地區的十一個縣,總共有一萬四千兩百六十四名幹部,其中有超過一萬人被上級認定為「糊塗思想」。
有些村民甚至前往北京上訪——其中部分人得到了地方幹部的默許。雖然戶籍制度限制了人們遷徙的自由,但在政務院的門口,每天都聚集了數十名上訪者,要求複查他們的情況。有一名婦女帶著四個嬰兒站在大門口,身上掛著一條標語,上面寫著「餓死」——對一個承諾沒有人會挨餓的政權來說,這無疑是赤裸裸的控訴。還有一個男人大白天點了一盞燈籠,在中南海的大門外要求面見毛主席——他的用意很明顯,是說黨製造的黑暗籠罩著大地。
上訪者中還有許多老兵。解放後,有五百七十萬士兵復員,他們的生活大都很悲慘。最好的情況是回到農村自力更生,但在集體化的過程中,許多人被當成了賤民,因為他們無法自食其力。有五十萬復員軍人不得不忍受各種慢性疾病的折磨,而且得不到什麼救治。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冬,他們終於忍無可忍,大批復員軍人聚集在城市裡向當地政府施壓,有些還組織了革命委員會,聲稱要發動游擊戰爭。陳宗霖來自飽受饑荒之苦的安徽,他高聲抗爭道:「要是政府不給我們工作,我們就跟他鬥爭到底!」在北京政務院的門口,發生過五起退伍軍人示威的事件。
羅在上海目睹了這些示威,他說:「從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身上,可以感受到一種生命力,這讓人感到無以言表的興奮,同樣讓人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是,共產黨幹部的態度也在發生轉變,他們既感到害怕,也感到困惑,不再像以前那樣傲慢了,他們試圖安撫每個人,特別是對工人,他們最怕的就是工人。」幹部們沒有理由鎮壓這些示威,因為毛主席自己就曾捍衛學生、工人和農民表達意見和示威的民主權利,他鼓勵大家「百花齊放」,因此成了人民擁戴的對象。
* * *
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魯雪夫發表祕密報告後,毛澤東花了兩個月時間認真考慮如何應對。他必須小心應對,因為史達林去世後,赫魯雪夫成了共產陣營強有力的新領袖,他試圖與北京建立新的雙邊關係,不僅增加了對中國的援助,甚至在一年前就承諾會為中國提供核技術。與此同時,在中共黨內,許多領導人都建議壓縮工業化的規模,減緩集體化改造的步伐,這些意見讓毛不得不有所顧忌,他希望赫魯雪夫能支持自己的立場。
四月二十五日,毛對去史達林化做出了正式回應。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為〈論十大關係〉的談話,宣布中國已經準備好用自己的方式開闢一條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他嚴厲批評了對蘇聯「一切照抄,機械搬用」的做法,表示中國不再盲目地仿效史達林單純強調重工業的舊模式,而要發展出自己的社會主義模式。毛指出蘇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即透過強制的手段從農民那裡掠奪了太多的資源,而中國將大大降低農業稅,以兼顧農民與國家的利益。毛認為「我們比蘇聯和許多東歐國家做得更好」,因為這些國家忽視了農業和輕工業。他甚至提出,在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時,中國應該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然而,毛同時指出,那些追隨赫魯雪夫完全否定史達林的人也是錯誤的,毛批評這些人「今天刮北風,他是北風派,明天刮西風,他是西風派,後來又刮北風,他又是北風派」。他說:「蘇聯過去把史達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如今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毛認為自己的立場比較中立,他宣稱史達林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七分功,三分過。
毛希望其他中共領導人都能與他達成共識,為此,他也試圖做出讓步,接納那些反對集體化改造的意見。他讓大家討論如何在發展重工業的同時又能保證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以此來「確保人民的生活」。他說必須研究如何提高工人的工資,以解決群眾「日常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毛的這些觀點令他得到許多人的稱讚。除了在經濟問題上做出讓步,毛還採取了更多的舉措提高個人的威望。例如:為了重新占據領導全黨的道德制高點,他表現出支持民主的一面。他將自己置於其他中共領導人之上,教訓他們說:「共產黨有兩怕,一怕老百姓哇哇叫,二怕民主人士發議論,他們講得有理,你怎能不聽?」不到一年前,毛曾譴責梁漱溟和彭一湖是「反革命分子」,如今他卻表揚他們捍衛了民主,提出要把梁漱溟和彭一湖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養起來,讓他們罵,罵得無理,我們反駁,罵得有理,我們接受。這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比較有利」。他對民主黨派表示支持,甚至說「要有兩個萬歲,一個是共產黨萬歲,另一個是民主黨派萬歲,資產階級不要萬歲,再有兩、三歲就行了」。
這些表態讓毛的形象勝過了赫魯雪夫。就在幾個月前,他還處於防守的地位,猶如過氣的人物,死抱著過時的觀念,跟不上現實發展的腳步。如今,與赫魯雪夫比起來,他才是真正的反叛者,他的態度聽起來比蘇聯人更開放、更自由。五月二日,毛提出要鼓勵知識分子自由地表達觀點,要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然而,毛對其他中共領導人的立場仍不放心。他已經被迫同意削減開支,實行經濟改革,還不得不支持恢復集體領導制。幾天後,他飛往南方,希望得到地方領導人的支持,五月底,毛不顧湍急的水流和漩渦,在渾濁的長江裡游了三個來回。除了警衛員外,李志綏醫生也不得不拚盡力氣跟在主席身邊,不過他很聰明,很快便學會了像毛一樣仰面浮在水面上。透過在長江裡游泳,毛向其他領導人證明了自己的意志,他還為此寫了一首詩:
不管風吹浪打,
勝似閒庭信步。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毛繼續鼓勵大家公開討論國家存在的問題。在九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上,黨中央放棄了社會主義高潮的提法,從黨章裡刪除了與毛澤東思想有關的所有內容,並明確提出反對個人崇拜。毛在大會上沒有發言。他看似非常寬容,實際上卻在暗中準備反擊。
匈牙利事件給了毛重新獲得主動權的機會。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初,蘇聯軍隊鎮壓了布達佩斯的動亂後,毛主席批評匈牙利共產黨已經變成了「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此時,國內的反對聲浪不斷高漲,毛卻聽之任之,欲藉機在中共領導層內發動一次整肅運動,以避免出現類似匈牙利的狀況。他的辦法就是來一次新的整風運動,就像當年在延安一樣,他要求對每個人進行嚴格的審查,挖出其中隱藏的間諜和特務。在一次內部的高層會議上,毛指出最危險的敵人不是那些在街上示威的工人和學生,而是黨內存在的「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他說:「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學生向我們示示威,很有必要。」一九四二年,毛曾號召抱著理想主義的年輕人主動向黨內的「教條主義」發起進攻,企圖利用他們來對付自己的反對派。如今,經過周密的計畫,他再次提出中國共產黨應當歡迎黨外人士提出批評意見。他說:「如果罵群眾,群眾應該把他消滅的。」當時,學生和工人的示威已蔓延至全國,毛想透過這種方式對全黨發出警告。
那些發表「反革命言論」的知識分子當然要冒極大的風險。一九四二年,延安的年輕人沒有遵從毛主席的指示,對延安的制度大肆抨擊,結果遭到了嚴厲懲罰,不得不在沒完沒了的鬥爭大會上互相揭發與批判。十四年後,毛自信攻擊黨的領導的類似情況再也不會發生了,因為經過反覆的思想改造,知識分子們都已馴服,而且僅僅一年之前,已有七十七萬「反革命分子」遭到逮捕。然而,仍有不少黨的領導人對發動群眾的做法心懷疑慮,毛安撫他們說:「關於鎮反問題,現在是十個指頭,去掉了九個半,只剩了半個反革命分子。」這個判斷在兩週後得到公安部長羅瑞卿的肯定。他報告說,幾週前當匈牙利發生示威時,有人寫匿名傳單,號召群眾起來推翻黨的領導,甚至有人計畫幹掉毛主席。但他保證,這些只是個別的聲音,因為產生反革命分子的溫床早在一年前就已經被剷除乾淨了。
儘管如此,其他領導人對發動一場新的整風運動還是感到顧慮重重,更不要說讓黨外人士公開發表不滿意見了。為了安撫大家,毛提出將以「和風細雨」的方式展開運動,對那些犯了錯誤的人,只進行意識型態的教育,而不施以紀律的懲罰。即便如此,劉少奇和彭真等高層領導人還是擔心情況會失控。當時,許多黨內人士都認為要嚴禁一切反對黨的聲音,毛不得不逐一找他們談話。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他甚至說少數反革命分子可能占據了顯要位置,但鎮壓只會讓情況變得更壞。過了幾天,他又說:「不要怕鬧,鬧得越大越長越好。」、「百家爭鳴有好處,讓那些龜子王八、牛頭蛇神統統出來。」毛認為,反對黨的人就像鮮花叢中的毒草,不管拔得多勤,每年總會冒出來。一月二十七日,他指出:「即使犯了路線錯誤,全國大亂,占了幾省、幾縣,傷亡很大,且打到北京,西長安街通統是反對的隊伍,是否會垮臺呢?如軍隊可靠,也不會亡國。」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這一天,對毛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日子。差不多就在赫魯雪夫發表祕密報告一周年之際,他在國務會議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演講。毛說,四個月前匈牙利人民走上街頭,但他們絕大多數都不是反革命,錯誤在黨,特別是具有官僚主義思想的幹部們,未能分清群眾的合法訴求與對國家的惡意攻擊,結果使用了暴力而不是說服的辦法來應對這場危機。毛承認中國在一九五一和一九五二年的政治運動中也犯了錯誤。他向與會人員保證,許多被判處勞動改造的人很快將得到特赦,他甚至對許多人的無辜死亡表示遺憾。同時,毛警告說,如果對群眾的合法需求處理不當,中國就會走上匈牙利的道路,人民內部的矛盾就會變成人民和黨的矛盾,最終只能用暴力來解決。毛的演講聽上去態度誠懇,他歷數了中國共產黨犯下的嚴重錯誤,對黨內的官僚主義予以嚴厲批評,並宣布將很快發動一場整風運動來幫助黨員改進自己的工作。他再次提出要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呼籲各界群眾一起幫助中國共產黨整頓風氣。他鼓勵大家說出心中的不滿,討論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並保證不會報復敢講真話的人。在結束演講時,毛把自己比作一名京劇演員,因為衰老而無法繼續扮演主角。透過這種方式,他暗示自己不久將退居二線。
這次演講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使許多人相信,毛確實想改變過去的激進做法,建設一個更加人性化的社會主義。為達成此一目標,他竭盡所能地將大多數人團結在自己周圍,許諾他們一個美好的未來。參加這次會議的不僅有黨和政府的高層領導人,還有民主黨派人士,毛的演講錄音還在全國對一定範圍內的人員進行了播放。羅當時在上海,他與其他兩百名代表一起收聽了演講錄音,大家對毛的真誠堅信不疑。他當時曾計畫逃往香港,並為此準備了一年多的時間,但現在產生了猶豫:「毛的演講讓人覺得,似乎一切改變都可能發生。許多年來頭一次,我看到了希望。」
* * *
然而,一開始並沒有多少批評的聲音。北京市長彭真運用其權力掌管著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官方報紙,試圖以此來控制運動的發展。
於是,毛決定再次離開北京,來到南方尋求支持。他施展個人魅力,鼓勵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大膽發言,從而贏得了眾人的好感。與此同時,他接見了軍隊和地方領導,對他們極力主張鎮壓示威學生的立場表示理解。他說:「知識分子有一條尾巴,要潑他一瓢冷水。狗,潑牠一瓢冷水,尾巴就夾起來了。你如果是另外一種情形,牠就翹得很高,牠就有些神氣。因為他讀了幾本書,確實有些神氣。勞動人民看見你那個神氣,他就不舒服。」
毛在布局一盤很大的棋:一方面,他從內心深處對知識分子充滿了不信任,但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利用他們對黨內的官僚主義展開攻擊。四月下旬,他動用自己的全部影響力,下令宣傳機器開足馬力來推動這場運動。一開始,批評的聲音還很微弱,但到了五月分,這種聲音開始變得越來越響,並很快發展成洶湧的浪潮。
工廠、宿舍和辦公室的牆上貼滿了大字報,人們在粉紅色、黃色和綠色的紙上,用毛筆發表自己的觀點。有些人寫的是要求民主和人權的口號,有些則是對社會主義國家民主的長篇討論,還有人對社會上存在的不公平現象以及黨內高層的腐敗問題提出批評。學生們抗議黨對文化和藝術的控制太緊,他們批評建國初期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不公正、太殘酷,並且對胡風表示同情。在南開大學任教的巫寧坤就是因為同情胡風,一年前遭到了搜家,如今他提出,批判胡風的運動是「不公道和荒謬的」。他說這場運動是「對公民權利的公然踐踏,是官方組織有預謀的私刑審判,其本身就是一個錯誤,就是為了消滅思想和言論的自由,是仿效史達林的整肅運動,而史達林的錯誤已經被赫魯雪夫揭發並受到了譴責。」巫寧坤滿心期待南開大學會向他道歉。
莫斯科也成了許多人批評的對象,因為大家不願意什麼事都得盲從蘇聯。幾乎每個人都在抱怨住宿條件差、工資太低,而黨員卻享有種種特權,生活的條件比普通人要好。少數人還寫了長篇大論,對整個政治體制提出批評,甚至攻擊共產黨和毛澤東本人,將毛主席比作教皇。有人寫道,在蔣介石統治期間,大家享有比新中國更多的言論自由。就連官方媒體也發表了對共產黨的尖銳批評。在一篇批評「黨天下」的文章裡,畢業於倫敦經濟學院、曾師從拉斯基(Harold Laski)的儲安平批評毛澤東自以為是,以為整個世界都是屬於他的。儲安平同章伯鈞和羅隆基一樣,都是民盟的成員。這些民主人士和無黨派人士召開了一系列會議,許多人在會上提出建議,要求中共將黨委撤出學校、政府機構和合營企業,少數人甚至嘲笑毛主席。殺傷力最大的是羅隆基的評論,他說毛主席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卻想領導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
還有些人提到了農民的問題。戴煌是一名虔誠的黨員、著名的戰地記者。他在農村採訪時,看到地方幹部享用著奢侈的宴席、住著豪華的房子,而大多數農民的生活條件卻比解放前好不了多少。深感震驚的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毛主席,提出了自己的建議。費孝通是一名社會學家,解放前就因研究農村問題而出名。他發表了一篇文章,記述了江蘇一個偏遠村莊的情況——他從一九三○年代就開始關注這個村子了。他說,剛進村子就遇到幾個老太婆,向他抱怨糧食不夠吃。費孝通因此寫了一份報告,對黨的農村政策提出溫和的批評,指出靠集體化來解決所有問題是「頭腦簡單」的想法。
在由黨的幹部們參加的不公開會議上,衝突更為激烈。上海市副市長與解放後歸國的兩百五十名留學生舉行了會談。這次會談是在上海市文化宮舉行的,這棟藝術裝飾風格的建築以前曾是法國俱樂部。這些留學生大都畢業於世界名校,發言時氣氛熱烈,許多人嚴詞批評政府說謊,未能兌現當初的承諾。他們抨擊黨的專斷和對知識分子的不公待遇,以及每次思想改造運動對知識分子的殘酷鎮壓。但最令大家不滿的,是在新中國沒有用武之地。大家的情緒普遍非常激動,十幾個人幾乎搶著高聲發言。副市長很快就坐不住了,頭上開始冒汗,頭髮亂了,中山裝也皺了。「他坐在那裡,緊握扶手,目光盯著一個個高聲發言的人。」
會議的高潮是一名工程師抱怨說他放棄了每月八百美元的工作回來為祖國服務,但至今卻沒有機會做任何事情,因為即使他提出一個很小的技術建議,也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觀點而遭到拒絕。自從一九五一年回國後,他已經換了四個崗位,每換一次他的工資都要下調,如今他的薪水很低。這名工程師越說越生氣,突然脫掉上衣衝向副市長,將衣服扔到他臉上,大聲叫道:「六年了,我連一件衣服都沒有買過,六年了,我從來沒有獲准運用我的能力和技術。因為這些遭遇,我整個人瘦了三十磅,為什麼?為什麼?你還想我們對你的愚蠢和冷漠忍耐多久?你以為我們還會老老實實地坐著,讓你們這些共產黨員越來越胖、越來越無恥嗎?」聽了他的發言,所有人都發出了憤怒的吼叫。
批評者取得了一些小小的勝利。上海市長向一名曾被錯劃為反黨分子的教授公開道歉,那些被錯抓了的知識分子也從監獄裡放了出來,其中就有淩憲揚——他曾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擔任上海大學的校長。淩憲揚在監獄裡關了六年,放出來時形容消瘦,但內心很高興,並迫切地表示想跟上形勢的發展。
從一九五六年夏開始,各地就不斷發生學生的示威活動,如今有數萬名學生走上街頭。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八千多名學生聚集在北京紀念五四運動,他們開闢了一堵「民主牆」,在牆上貼滿大字報和標語,批評共產黨「在全國所有的教育機構鎮壓自由和民主」。他們還與其他城市的示威者聯絡,企圖組織全國範圍的抗議活動。在成都和青島,學生示威變成了暴力衝突。示威者衝進地方黨委大樓,毆打了當地官員。武漢也爆發了動亂,一所中學的學生因為對招生政策不滿,憤怒地衝進市委大樓。結果門窗被砸毀,文件撒了一地,有幾名幹部還被綁了起來遊街示眾。
工人也走上了街頭。同學生的示威一樣,工人的罷工已經斷斷續續持續了將近一年,造成東北、天津、武漢和上海等城市的經濟陷於部分癱瘓。但如今,問題變得更加嚴重了。僅上海一地,就有五百八十多個企業的三萬多名工人參加了罷工,其規模超過了此前所有的罷工,甚至比一九三○年代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罷工還要大。另外還有七百多座工廠也出現了小規模的抗議事件,工人們採取罷工和有組織的怠工等方式進行抗議。
有些工人訴諸暴力,從牆上撕掉提高產量的標語和大字報,並公然批評共產黨。在群眾大會上,工人們長篇大論地傾訴心中的不滿,並嚴厲質問黨的幹部。有一次,憤怒的工人甚至把一名幹部推到黃浦江邊,每隔兩、三分鐘就把他的頭按進水裡。一個小時後,這名幹部的臉上全是汙泥和鮮血。他縱身跳入水中試圖逃跑,有一名圍觀的群眾試圖幫助他,結果被工人用石頭砸。不僅上海,全國其他地方的幹部也都變得恐慌不安。羅說:「有好幾次,我在馬路上看到有幹部遭到憤怒的群眾謾罵、攻擊和嘲弄。」吳介琴是一名藝術專業的學生,之前曾參加過「打虎隊」,他對當時的情形評論說:「這真的是一場公開的發洩。」
羅對這一切深感困惑,因此儘管幹部們不斷要他發言,他仍非常低調。幾個星期之後,他逃亡到了香港。還有很多人也持謹慎的態度,如樂黛雲(她是黨員,在土改時曾試圖保護一名被判處死刑的貧苦裁縫)就很警覺:「雖然我對那些發言的人很同情,但出於本能的警覺,我沒有參加批評者的大合唱,我覺得在發言之前應該耐心等待,看事態會怎麼發展。」她後來決定與其他的年輕教師一起提出建議,希望出版一份新的文學雜誌。
* * *
百花齊放運動造成的批評洪流讓全國各地的黨政官員們深感震驚,毛主席本人也不例外。事實證明,他之前嚴重錯估形勢。他的醫生李志綏記錄說:「(毛主席)待在床上,神情沮喪,明顯不能動彈。當進攻越來越激烈的時候,他患了感冒,因此把我喊去。他在重新思考戰略,計畫進行報復。」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事情正在起變化〉。這篇文章被發給黨的領導人,毛告訴他們:「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段時間,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不需要釣。」毛計畫發動反擊,同時,他卻命令宣傳機器鼓勵更多人站出來批評黨。他對民主黨派人士尤其感到憤怒,因為事實證明這些人都不可靠。他對李志綏說:「這些人就是一群土匪和婊子。」
很快地,《人民日報》得到祕密通知,要對那些被毛主席稱為「右派分子」的人發起攻擊。六月八日,毛發表了一篇社論,指責少數人試圖攻擊黨和推翻政府。六月十一日,他幾個月前所做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終於公開發表了,但是當初報告裡的和緩語調已經變得截然相反,整篇文章都被仔細地重新修改過,看上去似乎從一開始毛就給那些反對政府的人布下了陷阱,其目的是為了「引蛇出洞」。毛當初鼓勵大家辯論,現在看來似乎是個巧妙的策略,他的真實意圖是為了透過辯論讓革命的敵人自我暴露。
如今,爭鳴的階段結束了,毛又被迫同黨內反對他的勢力形成了暫時的合作,而受到各方面批評的黨內領導人也與毛團結在一起。鄧小平和彭真從一開始就對這場運動持不同意見,如今他們強烈要求對所有的右派分子採取果斷行動。毛主席讓鄧小平來主持這個行動,結果數十萬人受到了打擊。五月十五日,毛提出右派分子的人數是「右派大約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不同」。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被迫害的人數逐漸增長,最終超過了五十萬人。
那些被毛稱為「土匪和婊子」的民主人士受到的指控是:追隨了一條「反共產主義、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路線」。批評黨想獨霸世界的儲安平被民盟開除出黨,被迫在沒完沒了的大會上做自我檢討。其他人則受到學生積極分子的騷擾。人民大學的學生曾兩次衝進時任交通部長章伯鈞的辦公室,而被稱為「中國頭號右派」的羅隆基也在家中受到學生的攻擊。作為民盟的領導人,他們被指控為領導了一個祕密的「章羅反黨聯盟」,兩個人都因此被剝奪了一切職務。
那些參與示威的人受到了更為嚴厲的懲罰。武漢有幾名中學生被指控為接受了「章羅反黨聯盟」的指揮,結果在上萬名群眾面前被公開處決。
人們開始互相揭發,章伯鈞和羅隆基也彼此指責對方。有一次羅隆基來到章伯鈞家,用自己的拐杖憤怒地敲打他家的大門。其他民盟的成員(如吳晗等)都不甘落後,紛紛加入對章和羅的大批判中。有時候,家庭關係也會因政治原因而破裂。戴煌就受到了妻子的指責,她貼出一張大字報,控告自己的丈夫陰謀反黨。費孝通也被迫對自己寫過的農村調查報告進行批判,並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大會上做檢討,承認自己曾支持「章羅反黨聯盟」,反對「社會主義的目標」。
許多受迫害者一開始認為反右運動與自己無關,因為他們只是響應黨的號召才發表意見的。巫寧坤就是這麼認為的。然而,當南開大學的教師們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研讀了黨的指令和報紙的社論後,大家便開始強迫他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了。同事和朋友都躲著他,他坐在會場上,就像一名等待判決的犯人。直到被送往「北大荒」的勞改營,他才感覺放鬆下來。
甚至連平時自認言談舉止都很小心的黨員,如今也得面臨大會小會的嚴厲質問,受到各種委員會無休無止的審查和批判。樂黛雲就是這樣的例子。她奉命領導一個委員會,對五名右派分子進行批判。她花了整整一個夏天翻看了十幾名同事的人事檔案,沒想到,不久她自己也被劃成了右派。「這麼嚴重的指控當然不適用於我,我向上申訴,以為這個錯誤的決定很快就會得到糾正。」但事實是,她不得不面對全系師生的批判,八、九個人接連站起來發言,罵她是叛徒和反革命分子。最惡毒的指控來自一名年輕教師,他本人也被劃成了右派,因此非常渴望抓住這個機會來證明自己對黨的忠誠。
有時候,批判大會變成粗暴的咆哮,批判者甚至會對受迫害者施以肉體的攻擊,如揪他們的頭髮、把他們的頭壓在桌子上等。北京就有幾名大學教授遭受了這樣的虐待。在北京政法學院,有人憤怒地將茶杯砸到一名受害者的頭上。不過,跟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比起來,知識分子們在反右運動中所受的肉體痛苦算是輕的了。
讓人更痛苦的是,這場運動完全由領導說了算,個人根本沒有辯駁的餘地。毛給劃右派定下了指標,全國每個單位都必須完成任務。然而,劃定右派的標準非常模糊,只要曾經發表過意見,每個人都有可能被劃成右派。「反對社會主義文化」、「反對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制度」、「反對國家的基本政策」、「否定人民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以及「反對共產黨領導」都是致命的錯誤。即使有這些所謂的標準,用歷史學家王寧的話說,許多受害者其實只不過是「偶然的異見分子」。有時候,為了完成指標,幹部就在一張名單上隨便勾幾個名字。有一家電影院要求職工抽籤決定誰是右派,結果一名會計不幸抽中,成了右派分子。錢辛波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記者,有一天,一名幹部找到他,問他對劃右派有什麼想法——當時他有好幾個朋友都已受到了批判。錢恭順地說:「我沒什麼好說的,讓黨來決定吧。」他知道其實黨委早就決定了他的命運。有一名十七歲的女孩只是讚揚美國製造的鞋油好用,結果因為「對外國帝國主義事物的盲目崇拜」而被送入集中營。
同以往的政治運動一樣,有些人也會因為嫉妒和私人恩怨而被劃成右派。何英就因為提拔得太快遭人嫉妒而受到批判。他解釋說:
我十九歲時變成了右派。當時我是吉林省一份文學雜誌最年輕的編輯,在全省的文學圈子裡很有名氣,我的工資比許多同事要高,是公眾關注的焦點人物。所以有時候,我顯得過分自信和驕傲。許多同事都嫉妒我,想看我倒楣。我在百花運動中對政治一言不發,但是運動開始後,他們還是說服黨委書記把我劃成了右派。
殷潔的故事與此驚人地相似:「當時我還是一名大學生,比許多同學有更多的零用錢……而且,我學習不用功,但成績卻很好,因此就成了大家嫉妒的對象,有些人非常恨我。運動開始後,他們敦促系主任把我劃成了右派。」
有些蒙冤者選擇自殺。在一次批鬥大會上,從維熙目睹一名受害者自殺的情景:「當會議達到高潮時,會場上響起一片叫罵聲,坐在我前面幾排的一個男人突然站了起來。我還沒反應過來,就見他迅速衝向四樓的陽臺縱身躍下……血!當我向外看時,看到了血,我捂上眼睛,沒有勇氣再看下去了。」類似事件有數千起,所有的自殺行為都被認為是背叛人民的舉動。胡思杜在一九五○年曾批判自己的父親胡適,並積極要求入黨,如今因為建議改進他所在的學院的教學品質而被迫害致死。
而另一種極端的情況則是,受害人不僅全盤承認黨的指控,而且自願前往「北大荒」進行自我反省和改造。丁玲就是一個例子。她曾是一九三○年代的左翼著名作家,如今她跟丈夫一起認為自己應該接受改造,要用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觀開創一條新的道路。這類知識分子將自己的命運與黨牢牢綁在一起,他們無法想像離開了黨人生會變成怎樣。
在這場反右運動中,超過五十萬人被劃成右派,其中包括像丁玲這樣將全身心奉獻給黨的知識分子。而黨的領導層也得到一次深刻的教訓,知道毛可以號召人民攻擊他們。此後,許多黨的領導人再也不敢質疑毛主席的決策,完全與毛站在了一起,周恩來和陳雲在經濟上所持的謹慎態度也無人附和了。毛為此非常高興,此時距中國解放尚不足十年,但他已做好準備,即將展開一場大膽的新試驗,欲將中國推向共產主義陣營的最前沿。毛將這場運動稱為「大躍進」,全國都將加快集體化的步伐,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創造一個人人豐衣足食的烏托邦。在接下來的四年裡,數千萬人將被迫參加繁重的勞動,並且忍饑挨餓,甚至遭受毆打,直至死亡。這個國家將經歷一場人為製造的空前大劫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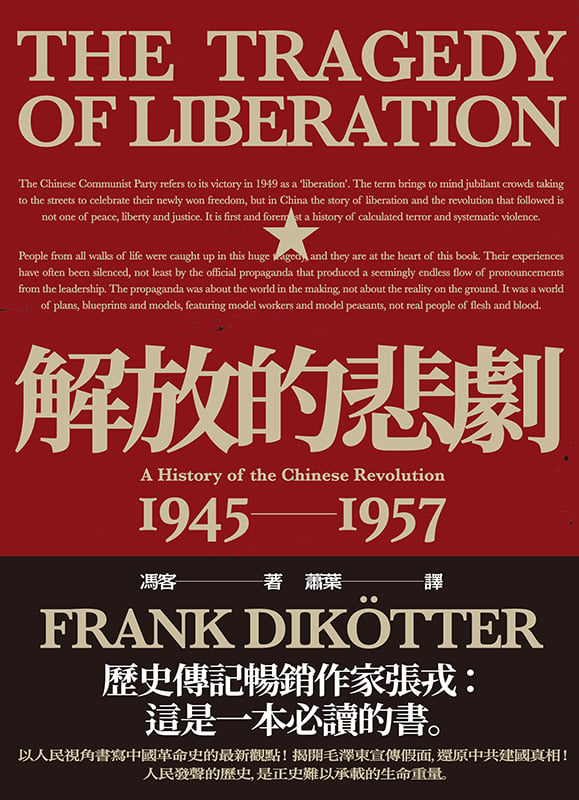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