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集_《解放的悲劇》幕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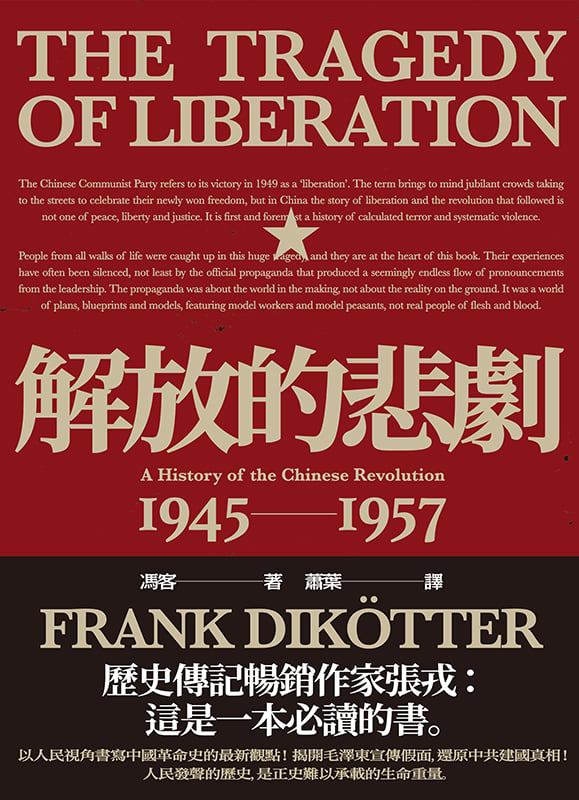
第十三章 幕後
到了一九五六年,展現在世人面前的中國是一副勝利者的姿態:戰爭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通貨膨脹也得到了抑制,失業的問題似乎也已解決,工業方面鋼和鐵的產量越來越高,中國的國際聲望也達到了頂峰,人民共和國在朝鮮戰場上和美國人打成平手,中國人再也不是東亞病夫了。史達林死後,毛澤東的聲望比其他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都更高。他集哲學家、政治家和詩人於一身,日益感覺自己肩負著領導全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重任。
從表面上看,中共政權代表了一些普世的價值:自由、平等、和平、公正和民主——當然一切的前提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它承諾為貧窮和吃不飽飯的人提供生活的保障,並為全體農民提供工作和住房。與自由主義的民主制度不一樣,它主張透過一項特別的社會實驗來實現這些理想的目標,那就是將所有人都帶入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物質富足,國家也隨之消亡。就像布爾什維克革命後的蘇聯一樣,中共也非常善於向人民描繪一幅烏托邦的景象,令不同階層的民眾都為之嚮往。對那些不喜歡資本主義的人,它承諾實現經濟平等,對那些痛恨專制政府的自由主義者,它承諾要給他們自由。「它在民族主義者面前大談愛國主義,在虔誠的人面前大談奉獻,在被壓迫者面前大談復仇。」總之,共產主義可以滿足所有人的夢想。
人民共和國對其取得的成績到處大肆宣傳,它用大量資料構建了一幅燦爛的圖景。「新中國」的一切都是可以用數字來衡量的,從煤炭和糧食的產量到解放後新建的住房面積。不管衡量的物件是什麼,一切都呈上升趨勢,即使有時資料本身含糊不清,但所有的統計都指向積極的一面。而且這些統計通常只有總體數字,並沒有分類的詳細資料,分類標準也沒有詳細說明,各類指標下面沒有具體的內容,資料的對比隨意性很大。成本和勞動力似乎並不重要,無須納入統計範圍。資料蒐集的方法和產生官方統計數字的方法從來不公開說明,雖然滿心狐疑的統計學家發現這裡面有巨大的漏洞,但全世界心懷夢想的人卻為之欣喜。人民共和國似乎在所有領域都正大步前進。
除了數字以外,革命本身對很多人來說也充滿了浪漫的吸引力。天安門廣場每年都要舉行大規模的群眾集會,以展示這個國家在鋼、鐵和人力方面的資源,坦克和火箭發射器轟隆隆地駛過天安門廣場,戰鬥機在空中劃過,一眼望不到邊的群眾敲鑼打鼓,載歌載舞,工人們揮舞著橄欖枝,或者放飛和平鴿和彩色的氣球。一名站在興奮的群眾當中被此情此景所深深打動的外國人評論說:「甚至連騎兵身下個頭矮小的蒙古馬都邁著整齊劃一的步伐,就像是一個個人工製造的發條玩具。」
不僅在北京,其他地方也是一片紅色的海洋——紅色是革命的象徵,代表著權力和平等,被用在標語、旗幟、圍巾、領帶和袖章等各個地方。社會主義的標誌簡潔明瞭,隨處可見,上面畫著麥穗和初升的金色太陽,還有紅色的五角星。許多建築物的牆上都貼著宣傳畫,畫上的工人和農民或雙手高舉,或緊握拳頭,栩栩如生。有一幅宣傳畫令人印象頗為深刻,上面是一個紮著辮子的姑娘,驕傲地開著拖拉機在田野上耕作。蔡淑莉和三十名同學從北京的一所高中畢業時,聽說了一個叫劉英的姑娘堅持在「北大荒」開拖拉機的故事,大家深受鼓舞,紛紛表示自願到東北去。她寫信給彭真市長說:「心情的激動無法形容……經過考慮,我們已決定把自己的青春奉獻給北大荒,決心和劉英同志一起開拓北大荒的富饒土地。」
這一時期,中央各部門的領導人發布了許多報告和聲明,毛主席本人也寫了不少東西。對局外者來說,這些文字可能很難理解,因為它們充斥著大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專門詞彙,並且字裡行間暗示著共產黨內部權力結構的變化。但總的來說,這些文字都表達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和承諾:要提高工人的工資,為沒有工作能力的人提供更多保障,為少數民族爭取尊嚴和權力。類似的美好願望多得說不盡,但隨之而來的卻是越來越多的規章制度,政府希望藉此推動中國在通往共產主義的道路上快速前進。
然而,官方描繪的都是將來要實現的理想社會,談的都是些計畫、藍圖和設想,而不是當前的現實。除了這些官方文件,對群眾影響更大的是一些通俗易懂的口號。毛澤東本人就非常善於創造富有感染力的口號,許多口號達到了家喻戶曉的程度,如「婦女能頂半邊天」、「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以及「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等。他提出的一個座右銘「為人民服務」出現在全國各地的宣傳海報和標語上,往往是大紅的底色配著白色的文字,看上去有些誇張和俗氣。
就像蔡淑莉一樣,大批黨員不顧眼前的種種困難,對未來充滿了美好的想像。丹棱在解放前讀書時就加入了共產黨,數年之後,雖然對鎮壓國家公敵的各種運動心存疑慮,但他依然保持了年輕時的理想主義和熱情。李志綏如今成了毛主席的醫生,他於一九四九年連同妻子回到中國,此後的經歷讓他對現實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但他依然堅定地信仰共產主義。甚至在那些享有特權的黨員幹部圈子之外,「建設社會主義」的宏偉理想同樣深入人心,特別是接受解放後教育長大的年輕一代更是如此。
年輕的學生們自願地奔赴邊疆,或者到偏遠地區修築水利工程,他們對此既感覺興奮又充滿激情。雖然現實很嚴峻,但共產主義仍具有很強的號召力,這主要是因為它讓許多人堅信自己親身參與了歷史轉變的重要過程,為實現一個更高更好的目標奉獻了力量,可以開創一個前所未有的美好未來。在這個新社會裡,工人們競相創造新的紀錄,士兵們用血肉之軀保衛著國家的安全,每一個人都能成為英雄。國家的宣傳機器開足馬力,不斷宣傳工人、農民和士兵中的英雄人物,並樹立了許多模範和榜樣。
除了模範工人和士兵,還有模範學校、醫院、工廠、辦公室、監獄、家庭和合作社,這些榜樣為大家提供了未來的願景。至一九五六年,經過政府的精挑細選,已經有數千名外國遊客在導遊的陪同下參觀了這些模範單位,而且所有費用都由中國政府承擔——當然,他們的一舉一動全在監視之下。有一個外國人寫道:「我們就像嬰兒一樣,從一個地方被帶到另一個地方,從一個人的手裡轉到另一個人的手裡。」但許多人對此仍然感到高興,他們渴望幫助人民共和國消除外部世界對其實行的共產主義制度的誤解和敵意。
外賓只能訪問那些最忠誠且經過考驗的黨員。榮毅仁在潘漢年倒臺後再也得不到高層領導人的保護,因此決定參與對外國人的「表演」。透過這種方式,他可以為政府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把自己打扮成一名專供外國人參觀的企業家,在政府的資助下,幫助構建了一個虛幻的世界。外賓到他家裡參觀,會發現他的妻子心滿意足地在織毛衣,兩隻狗在花園裡歡蹦亂跳,草地上還有一名穿著制服的護士推著嬰兒車。「牆上特地掛了一個十字架,用來證明信仰自由,書架上除了馬克思的書還擺著莎士比亞的著作。」他的女兒則在隔壁的房間裡彈鋼琴。榮毅仁和外賓的對話大都是關於他的花園,似乎只關心怎麼為他的牡丹施肥,除此之外別無所慮。有一名法國人目睹了這幅溫馨的畫面後深感震驚,她說:「我從來沒見過比這更幸福的家庭。」榮毅仁對每個問題都有準備好的答案,當客人問他怎麼會如此幸福時,他會抿著嘴脣沉思道:「一開始我也擔心過。當共產黨解放上海時,我們很擔心,即使不擔心我們的性命,至少也擔心我們的財產。」然後他會盯著客人的眼睛,鄭重其事地說:「但是共產黨遵守了自己的承諾,我們逐漸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從來不欺騙人民。」
全國都在上演這樣的表演,觀眾是外國的記者和政府官員、中共的高層領導人、學生團體,當然還有毛主席本人。當數百間寺廟被毀壞後,政府卻投入大量資金用來修建少數豪華的寺院,和尚可以在裡面表演,講述新中國宗教的繁榮盛況。在模範工廠裡配備著最先進的設備,廠裡的工人都經過仔細挑選和訓練,以展示計畫經濟的成功之處。在所有重要城市都建設了一些模範村莊用來證明農業集體化的好處。從表面看起來,全國人民都在勤勞地工作,而且熱情高漲,不遺餘力地歌頌黨。
中國成了一個大舞臺。即使在沒有人參觀時,大家也被迫要裝出微笑。當農民被逼迫交出更多的糧食時,他們不僅得積極回應,還要顯得很開心;當店主們被迫交出他們的財產時,他們不僅得自願這麼做,還要滿臉堆笑。同其他亞洲國家一樣,微笑在中國並不一定表示高興,它也可能表示尷尬或者被用來隱藏痛苦和憤怒。但不管怎樣,誰都不希望被別人指責為拖後腿。大多數人都得依靠政府來生活,所有人在解放後都花了無數時間參加政治學習,學習如何跟上黨的路線,如何正確回答問題,以及對黨的政策表示完全滿意。普通人也許並不能成為了不起的英雄,但許多人卻是一流的演員。
* * *
為了維持這個龐大的形象工程,國家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並因此在交通建設上獲致長足的進展,全國建成了前所未有的交通網絡,公路四通八達——許多道路是徵用勞力和戴著鐵鐐的犯人所修建,火車按著時刻表準時運行,外賓和領導們可以享用高級的臥鋪和餐廳。許多城市裝扮一新,下水道得到了清理,路面還定期灑水。
在首都北京,一座座雄偉漂亮的的公共建築拔地而起,俯瞰著四合院的灰色屋頂和紫禁城的紅牆。市中心和郊區蓋起了許多政府大樓、研究所和博物館,不管是平頂,還是鋪著琉璃瓦的飛簷翹角,所有建築都帶有蘇式的雄偉風格。有一個區似乎在短短幾個月就興建了十幾座新樓房,包括航空研究所、石油研究所和冶金研究所,所有的大樓都有寬敞的前廳和開闊的翼樓。在西直門外,很快建成了一座蘇聯展覽館,很多人傳說這座建築的塔樓使用了大量純金來裝飾。在首都的心臟地帶,為了給每年舉行的閱兵儀式提供場地,當局拆除了許多老建築,擴建了天安門廣場,阻礙交通的城牆也被拆除了。
其他城市也仿效北京,新建了許多規模宏大的標誌性建築。重慶在人民文化公園的中間建起了一座漂亮的音樂廳,隨後又建了一座大型體育館和大會堂。大會堂體積龐大,裝飾華美,有三層鋪著綠色琉璃瓦的屋簷,每年的維護費用即達十萬元,不過平時這裡很少開放。其他許多新建築也大都空著,因為重慶已經不再是四川的省會了。在河南鄭州,似乎從麥田裡一夜之間就誕生了一座嶄新的城市,不僅開闢了寬敞的馬路,還興建了一座座雄偉的政府大樓,每棟樓都帶有花園和宿舍。在甘肅的省會蘭州,沿著長江兩岸綿延數公里的範圍新建了許多政府大樓以及研究所、醫院、工廠和住宅區,城市的面積幾乎擴大了一倍。工人們用鋤頭和鏟子一點點挖出寬敞的馬路,分成快車道與慢車道,筆直地穿過一條條老街,似乎對這座城市的過去毫不留戀。
全國各地的基礎建設速度快得驚人,領導人只重速度,不重規劃,致使許多房子建得「雜亂無章」,而且各地互相競爭,都想把房子建得更高更大,結果許多新建的樓房連自來水和下水道都沒有。在像鄭州這樣的地方,因為把新城區建在主城區外,由此造成了巨大的財政赤字。為了迅速躍升為共產主義城市,許多基礎建設開工前根本沒有對地質結構、土壤成分和水資源進行考察,結果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有些馬路剛修好不久就被挖開,而且各部門之間常常陷入財務糾紛。就連北京也不例外,雖然許多工廠的建設是由政府補貼的,但建築的大梁卻經常變形和裂開,由此造成的浪費十分驚人——這個國家雖然實行的是計畫經濟,但實際上卻似乎毫無計畫可言。
即使那些被用來向外賓展示的形象工程也漏洞百出。在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表象的背後,卻隱藏著粗製濫造的豆腐渣工程。例如:北京新建了三座專門用來接待外賓的賓館,其中之一是前門飯店。一九五六年,那裡接待了許多對中國充滿善意的外國人。但是,賓館房間裡的水管經常漏水,洗臉盆和浴缸裡斑斑點點,馬桶的水永遠在流,有時甚至會溢出來,門關不嚴,燈光不停閃動,窗子也關不緊。
政府花了大量資金修建各類形象工程,但對普通居民的居住條件卻並不重視——被用來展示的模範宿舍(如北京大學的學生宿舍和西安的人民大廈)除外。工廠和宿舍混雜在一起,經常達不到最基本的衛生要求,當地的老百姓時常抱怨說:「死人活人連續搬家。」大部分宿舍的外觀都單調乏味,一排一排的平房,看上去像軍營一樣,通常沒有娛樂設施,建築品質也很差。在遠離公眾視線的首都郊外,工人的宿舍都是用廢棄的材料建造的,牆一碰就會晃動,一下大雨門框就會斷裂,屋頂還會漏雨。在紫禁城往南大約三公里的郊區南苑,新住宅的牆面出現滲水,有些房子連門都沒有。這樣做其實是有意為之的。一九五六年二月,劉少奇曾對紡織工業部指示說:「工人宿舍應該建平房,不應該建樓房,現在的樓房工人住起來不一定習慣。未來我們可以興建好的樓房。你們不需要把平房建得很好,比一般工棚好一些即可以,將來反正是要拆的。」劉少奇覺得種些樹是可以的,但沒必要有池塘、假山和花花草草,就連北京第二棉紡廠提供茶杯給工人的做法,也被批評為對工人「太好了」。政府的目的就是要縮減開支、節約成本。
在大搞基礎建設的同時,各地對老房子進行了大規模的拆遷。據李富春講,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北京、武漢、太原和蘭州需拆除兩百萬平方公尺以上的住宅區,花費至少需六千萬元。太原和蘭州的五分之一從地圖上被抹掉了。在四川,從省會直到縣城,多達百分之四十的城鎮面積被拆成了廢墟。當地的老百姓把土地比喻成豆腐,而黨則是鋒利的刀子,想怎麼切就怎麼切。那些因拆遷而被趕出家門的人無處可去,就算在北京也得不到幫助。東郊火車站附近的拆遷戶被安置在臨時搭起來的棚子裡長達十個月,有些人在下雪天冷得哭起來。全國各地都出現了住房短缺的現象。
許多工人的居住條件簡陋得令人無法想像。在東北的鋼鐵基地鞍山,工人的宿舍設施簡陋,一家六口只能睡一張床。屋頂偶爾還會變形,甚至牆體倒塌,迫使工人不得不和動物住在一起,或者住在東郊黑漆漆的山洞裡。有些人沒有食物,下工後在馬路上徘徊,向行人乞討。工人們普遍缺衣少穿,在零下二十度的冬天也無法取暖,單薄的房子、破舊的毛毯和被子根本無法保暖,甚至有嬰兒被凍死——這些情況在鞍山黨委的一份祕密報告中都有所提及。
在南方的南京,解放後工人的數量增加了一倍多,但住房卻跟不上,因此每個工人平均只有二平方公尺的居住面積。宿舍裡通常缺少通風設備,許多人早上起來時會因為缺氧而頭疼。但他們還算幸運的,因為政府只為單身工人提供宿舍,成家的人只能住在廠外,通常距離工廠有二十五公里遠,因此差不多有百分之十的工人每天得花許多時間通勤。坐十二公里的公車就要花費四毛錢,這樣算下來,一個星期的路費就差不多花掉了他們一個月的零用錢。
在位於南京南部的工業城市馬鞍山,有些工人病了幾個月也沒錢看病,根本得不到基本的治療。宿舍非常擁擠,有些家庭只好全家人擠在小棚子裡,冬天最冷的時候也無法在室內取暖。穿著破衣爛衫的小孩在大街上乞討,車間裡沒有飲用水,甚至連廁所也沒有。幹部們只忙著完成生產指標,根本顧不上照料工人的生活,有些工人說:「(幹部們)不送活錢,專送死錢。」
更多的研究表明,與解放前相比,解放後工人的平均住房面積反而縮小了,有時減幅達到了一半。武漢平均減少二十二點四平方公尺,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居住在棚子裡的四分之一工人。武漢有一百九十萬人口,根據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其中有八萬名工人沒有固定的住所。勞動局的統計則顯示,全國各地都有普通老百姓長期處於居無定所的狀態。
* * *
許多人的身體出現了問題,但在宣傳畫中,每個人看上去都很健康,都對未來充滿了信心。政府公布了許多與健康和衛生有關的統計數字,包括打死的蒼蠅數目、感染霍亂的病人數量等,勾勒了一幅不斷進步的景象。當局還經常發動群眾參與衛生運動,在工作之餘打掃馬路、清理垃圾、捕捉老鼠和填埋化糞池。在一九五二年的愛國衛生運動中,大家被組織起來對細菌開戰,許多城市都展開了消毒工作。正如本書第七章所示,衛生部後來承認,這場運動實際上造成了很大的浪費。
不過,這些衛生運動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像大多數亞洲國家一樣,中國的醫療衛生一直面臨著嚴峻的問題,特別是在農村地區,血吸蟲病、鉤蟲病和腳氣病很普遍,嬰兒的死亡率在解放前很高,除了大城市,西醫在大部分地區還不普及。一九五○年代,醫療領域取得了新的突破和進步。例如:二戰後許多國家開始大規模生產盤尼西林,細菌感染的發病率因此大幅下降。在中國,長達十多年的戰爭終於結束了,政府開始推動公共衛生的許多領域向前發展。內戰期間堆滿城市的垃圾如今得以清理,街道也被打掃乾淨,溝壑被填了起來,排水系統得到了修繕,疫苗也開始普及——雖然幹部們強迫大家接種疫苗的目的是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與此同時,政府動用一切資源來對抗嚴重的傳染病,許多疫情一出現就很快得到了控制。
然而,醫療並不是免費的。事實上,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國家才開始訓練大批赤腳醫生為農民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解放前,農民們可以從非官方管道得到醫療救助,全國各地的鄉村地區分布著數百家傳教士開設的醫院,如今這些醫院都被政府徵用了。道觀、寺廟及其他各類宗教和慈善機構也大都被關閉了,只剩下少數幾家由政府掌管。各地的藥劑師、醫生和護士都不得不服從政府的命令,在一次次的思想改造運動中證明自己對新政權的忠誠。到了一九五六年,包括藥店和私人診所在內的絕大多數公司也都被國家接管了。
儘管衛生領域取得了一些進步,但老百姓的健康卻很快就出現了下滑的狀況。從公開的報導和新聞來看,中國的醫療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檔案裡保存的調查資料卻顯示,人們普遍營養不良,健康狀況很差。不僅農村是這樣,城市裡也是如此。造成這個現象的一個原因是大多數工人的收入減少了。農民的口糧越來越少,而工人的工資也在降低,看病的費用卻很高,藥品都很貴。一九五六年,勞動局調查了數百家工廠後得出結論:「近幾年來工人的實際工資確有下降趨勢。」通貨膨脹超過了工資的增長,有一半重工業企業的工人每月工資不到五十元,從事輕工業的工人收入更低。北京有六分之一的工人生活困難,每個月的日常開銷不足十元。而大批處於社會最底層的窮人則不得不從事建築業,他們占了工人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人口的健康狀況持續下降,得病率年年上升。至一九五五年,幾乎每二十名工人中就有一人得請半年以上的病假,有些工廠百分之四十的工人都患有嚴重的慢性病。雖然政府宣傳說工人享有療養和休假的福利,但事實上只有少數人才能得到休息的機會。
北京之外的地方條件就更差了。在南京,一個工人每月掙不到二十元,除了最基本的日常開銷外,什麼也買不起。一九五六年,南京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赤貧狀態,每個月的收入不足七元。這還沒有算上那些解放後被迫離開城市的數十萬居民。這些窮人中有一半是集體化造成的,其中包括失業的人力車夫、倒閉的小商店老闆以及反革命分子的家屬,還有些是因違反勞動紀律而被國營工廠開除的工人——這些人一輩子都留下了汙點,生活在社會的邊緣,很難再找到就業的機會。
在南京的工人當中,有百分之七患有肺結核,百分之六患有腸胃疾病,另有百分之六患有高血壓。中毒和工傷很普遍。在南京化學廠,空氣中的有害顆粒比蘇聯人制定的標準高出三十六倍。在一個使用硝石的車間,「工人有百分之百程度不同的中毒情況」,有人甚至出現肝脾腫大的問題。在玻璃廠和水泥廠,許多工人的肺部都受到矽石的感染,而且砂眼和鼻炎也「很嚴重」。
因為缺少相關資料,很難把解放後的情況與解放前做對比。但是新政府卻非常熱衷於同國民黨比較,它對國民黨統治期間直到一九三七年的情況進行了詳細統計,並考慮了通貨膨脹率的因素。但大多數統計數字並沒有公布,因為它們顯示,在許多方面人民的生活還不如二十年前的水準。例如漢口的申新紡織廠,解放後對糧食、豬肉、食用油和布匹的消費水準全部急劇下降。與一九三七年相比,一九五七年平均每個工人比解放前多了六公斤的口糧,但豬肉的消費減少了幾乎一半,食用油也少了三分之一,布疋則少了五分之一。如表二所示,這種情況並非一家工廠特有,許多工人營養不良,吃、穿、住等條件普遍很差,甚至無法與內戰打得最激烈的一九四八年相比。
一九五二年,工人的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但在接下來的五年裡,情況卻持續惡化。而且,政府的統計只涉及消費情況,而不是關於生活成本的全面統計。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七年,生活成本急劇上升,在上文提到的申新紡織廠,一九五二年工人的房租是每年八十八元,五年後漲到四百元。在統計局調查的每一家工廠中,情況都是如此,工人的居住面積不斷縮小,房租卻日益上漲。在表二中的武昌造船廠,房租從一九四八年的兩百七十一元增加到一九五二年的三百六十一元,一九五五年則激增到七百二十一元,一九五七年更達到了九百九十元。
學生當中也普遍存在營養不良和健康不佳的情況。共青團對中學生進行了廣泛調查後,認為學生「身體很差」。在武漢,每個學生每個月只有三百克的蔬菜和一百五十克的豆製品,學生們吃得最多的是粗糧和紅薯。在河南,學生們有一整個月沒有蔬菜吃,只能吃麵條。在四川綿陽,學生編了個順口溜來描述他們的伙食:「飯不夠,湯來湊,越吃越瘦;菜不好,樣式少,沒鹽沒油。」在遼寧省,有三分之一的學生營養不良。營口是個繁忙的港口城市,該省的玉米、大豆、蘋果和梨,透過海運大批銷往國外,而當地卻有不少學生在上體育課時餓得暈倒。當局對糧食實行嚴格的供給制,理由很是冠冕堂皇,因為「糧食吃多了是浪費,沒有共產主義美德」。挨餓的人被告知可以喝水充饑,因為「開水也含有卡路里」。離瀋陽不遠的新民市透過調查發現,十分之四的學生因營養不良(特別是缺乏魚油和乳製品提供的維生素A)而患有夜盲症。有些班級不得不在寺廟或廢棄的教堂裡上課,室內的光線通常很不充足,甚至大白天也「像監獄一樣黑」。
其他一些方面也出現了倒退。政府決心消滅一切疾病和害蟲,但是這個遠大的理想卻無法透過群眾運動的方式來實現。每個人都分配到指標,要將一定數量的老鼠尾巴上交政府,於是有人開始飼養老鼠。政府無視醫學常識,試圖運用軍事戰術來對抗傳染病,他們將群眾按部隊的編制組織起來,拉著布條、吹著喇叭消滅害蟲。對血吸蟲病就是這樣進行消滅的。解放後,感染血吸蟲病的人數每年都在增長,華東地區特別明顯,但是領導階層對此並不在意,當時正值韓戰,他們更關心如何消滅敵人散布的帶有細菌的黃蜂和蝴蝶。直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毛主席視察浙江時親眼看到了血吸蟲的嚴重危害,這才引起全黨對這個問題的重視。毛還特意寫了一首詩,標題起得豪情萬丈,叫〈送瘟神〉。一九五六年二月,他下令展開一次群眾運動:「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
於是,數百萬農民被要求站在河水的淤泥中捕捉傳染病菌的釘螺。但是醫學權威們早就表示,透過捕捉釘螺的方式是不可能消滅血吸蟲病的。釘螺只是人的肉眼看不到的血吸蟲宿主,農民和耕牛接觸到牠們就有可能被感染,因為這種蟲子會進入宿主的血管和肝臟。被感染的人和動物若帶著蟲卵再次進入水中,蟲卵不僅無法被消滅,反而恰好得以進入釘螺的體內得到孵化。但是專家們被當作資產階級,他們的意見根本得不到重視,無數的村民赤手將釘螺挖出,剛建成的灌溉溝渠也被挖開用來掩埋抓到的釘螺。這場運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而且運動剛剛結束,這些人又被送去那些未被感染的水域從事割草和採集蘆葦的工作。
湖北的情況就是如此。湖北位於長江中游,境內有上千個湖泊,盛產鴨子、蓮藕和菱角。全省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暴露在血吸蟲病的風險之中。雖然當地的領導在報告中誇耀已經「送走了瘟神」,但仍有超過一百五十萬的人口被感染。漢川縣在消滅血吸蟲的運動中,治癒了大約七百名病人,但運動後一下子又冒出來上千病例。其他省分也是這樣。檔案顯示,這場運動幾乎無法遏制血吸蟲病的蔓延。政府根本沒有耐心對疾病進行全面的防治(如更妥善地處理人的糞便等),而是透過發布無數的口號和指標,以及發動一場接一場的運動來管理著國家。集體化也無助於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所有的耕畜和家禽都屬於集體所有,大家對牠們根本不關心,也不會注意用正確的方式來處理糞便,而且因為條件所限,一些傳統的衛生習慣(如喝開水和吃熟食等)如今也不能完全實現。
有時候,宣傳和現實之間的差距之大,猶如天壤之別。政府頒布了一系列照顧痲瘋病人的措施,包括為他們提供集中居住的地方以及各種便利條件。古往今來,對所有政府來說,消滅痲瘋病都是一項巨大的挑戰,而且難上加難的是,人們對這個病存在廣泛的誤解。在人民共和國,就連正常的勞動者都吃不飽,地方幹部有許多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根本不把患有嚴重傳染病的人放在心上。衛生部門印製了一些關於防治痲瘋病的小冊子,但並不能一下子改變人們的成見。檔案中有大量的證據表明,解放後的幾年裡,痲瘋病的情況變得更加糟糕,其原因之一,也許是因為地方幹部的權力比以前更大了。
傳教士們被趕出中國後,之前成立的痲瘋村再也得不到外國的援助了。在位於四川山區的磨西,傳教士們被迫放棄了一座建有漂亮鐘樓的教堂,同時還被迫離開了一個有一百六十名病人的痲瘋村。從此,病人們只能自力更生,得不到任何幫助。沒過多久,便有病人陸續離開痲瘋村,在崎嶇泥濘的山路上乞討。他們受到眾人的嫌棄,被心懷恐懼的村民追打,有幾個人甚至被活埋。四川的衛生部門報告說:「永定縣在一九五四年夏季活埋了一個痲瘋病人,其他縣也有同樣情況。」四川並非特例,在臨近的貴州,得病的人數在解放後急劇攀升,鄉村裡瀰漫著恐慌的情緒,有些地方幹部甚至將病人活活燒死。這種案例不止一起,最可怕的一次有八名病人被處死。有時候,地方政府會命令民兵參與行動:「民兵將患者及其父母一起綁起來,把患者燒死,其父母日夜啼哭。」
最可怕的情況可能出現在雲南省永仁縣。一九五一年六月,這個地方有一百名痲瘋病人被燒死。燒死的建議最早是在一個月前的縣委會議上,由負責農村工作的高級幹部馬學授提出:「四區痲瘋病院的痲瘋人經常出來洗澡亂跑,群眾反映這樣不好,並要求燒掉。」縣委書記說:「不能燒。」但是馬堅持這麼做,過了一個月,他主動提出會為此承擔全部責任:「是群眾要燒就燒吧,為群眾辦事,這是群眾的意見,搞,我負責。」其他幾個人均表示同意。於是,民兵們把所有痲瘋病人集中起來,關在醫院裡,然後放火燒掉了整棟房子。病人們哭著求救,但是無濟於事,一百一十名病人中只有六人倖存。
就算有些痲瘋病人得到了護理,相關的專項資金也常常去向不明,而且根本無人追究地方幹部的責任。在四川鹽邊,相關負責人員挪用痲瘋病人的資金為自己蓋了漂亮的房子,而病人們只能住在幾公里外的土房子裡。不過,痲瘋病人的人數實在太多。一九五三年,廣東省大約有十萬名痲瘋病人,但當地的醫療機構只能照管其中的兩千人。
痲瘋病人是社會上最弱勢的群體之一,他們的需求在這個一黨專政的國家裡無法得到滿足,因為政府希望控制每一個人,而不是為大家提供服務。此外,還有許多其他弱勢群體的命運也完全掌握在地方幹部的手裡。例如:解放前由非政府組織成立的孤兒院如今全被政府接管,但死亡率卻高達百分之三十。盲人和老年人也很難適應這個新社會,因為要想生存下來就得服從命令、掙取工分。隨著被逐步剝奪大部分基本自由(包括言論、信仰、集會、結社和遷徙的自由等),大多數老百姓已經越來越無力反抗國家的控制,只有少數人仍試圖掙扎。
* * *
解放曾激發了許多人對未來的美好想望,然而到了一九五六年,這些希望都破滅了。政府絲毫不尊重人民,只將他們當作財務報表上的數字和可以利用的資源。以集體化的名義,農民失去了土地、工具和牲口,並被迫向國家上繳越來越多的糧食,每天早晨在軍號聲中起床,處處都得服從地方幹部的命令。在城市裡,工廠和商店的職工根本享受不到宣傳中工人階級的英雄地位,而是被當作「包身工」一樣對待,為了完成一個個生產指標,每天都不得不工作很長時間,各項福利卻不斷縮水。除了那些享有特權的黨員,每個人都得勒緊褲腰帶來追求一個烏托邦社會。全國各地充斥著不滿的情緒,緊張的氣氛一觸即發。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