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丹 | “贫穷电影”的自由
魏丹导演——《方舟》cathayplay采访实录
(Q:主持人,W:导演)

Q:魏丹导演您好,首先非常欢迎你接受cathayplay的专访,这次我们聊天的内容有关于您的影片《方舟》和您其他的作品或动态。我们先从片子大致的拍摄过程说起吧!
W:最早是2020年的时候,疫情刚刚爆发,我姥姥病危。当时回去第一次见到姥姥,我就坐着拉着她的手,她一直看着我。
整个病房的气氛非常窒息,那个监护仪一直在报警,然后心率已经飙到180多,医生说随时可能就没有了。但是过了晚上11点之后,它又渐渐平稳。从那之后基本上每天就跟大人在医院轮班照顾。然后我当时预感她可能挺不过这一次了,所以就拿手机想存留一些影像。拍了差不多一周之后,就感觉这个东西这么散,为什么不把它串在一起呢。而且因为好不容易一家人能在这个时间点聚集在这个医院,外面又是疫情的爆发,我当时的确很迷茫、很焦虑。
陆续拍了一个多月直到我姥姥4月份去世,那时候我已经回到北京,他们给我打电话我又回去。所以片中结尾那段是家里的妹妹帮我拍摄的。

《方舟》剧照
Q:你提到的焦虑和迷茫,会影响到你作为纪录片创作者工作时的态度吗?
W:在拍摄的时候,我尽量控制自己的情感,试图更冷静的、客观的去呈现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尽量让自己置身事外,但事实上这很难。
Q:这样置身事外的状态对你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决定吗?
W:拍至亲很容易被浓烈的情感裹挟,而我只是希望冷处理。这不意味着没有情感,而是更理智。否则我会觉得影片反而失真。
Q: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表现这件事?
W:对,形式问题。
Q:那片子有关信仰的探讨,是不是也是形式的一部分?
W: 对,包括像画幅的变化、黑白色调、巴赫的音乐都是基于形式考虑。它虽然是纪录片,但实际上我也希望在美学上融入一些风格化的处理。叙事层面也尽可能按照剧情片的方式去结构,本质上是一样的。
Q:用剧情片的方式拍摄纪录片事实上并不多见?
W:实际上包括我现在的新片创作,它也有记录的成分,也有虚构的。就《方舟》而言,它是个真实的事件,但它同样需要有美学诉求,或者一种作者性。比如有人看到我的这个片子,觉得有很强的宗教情感在里面。
Q:这次纪录片的拍摄经历会对你以后剧情片的拍摄产生转折作用吗?
W:早在拍完《母腹之外》后,我就深刻的认识到如果你想拥有自由,就遵循自己的感受,并采用“贫穷电影”的制作模式,用最低的成本完成。现在新片我们拍了两个方案,第一次拍的时候也就5、6个人,第二次拍的时候就一个人,基本上身兼数职就把它拍完了。
Q:可以透露一些你平时看书的类型吗?
W:电影方面可能是理论类的比较多,我觉得做电影,技术已经是一件这么普及的事,更重要的是你首先对电影的理解和观念,你怎么看待创作这件事本身,然后才考虑技术的东西。
Q:那你自己有比较热衷于技术的那个时期吗?你是怎样把自己从那个里面解放出来的?
W:我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是出了5D2,我当时特别迷恋所谓的电影感。后来潜移默化,我也想不到是什么影响,可能是达内兄弟吧,这种低成本创作模式和风格其实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比较大的影响。后来就是布列松, 我看了他的电影之后突然发现,他的电影里有强烈的宗教精神,包括德莱叶,让我觉得特别震撼,我希望在我喜欢的这些前辈的体系里找到自己的突破和延展。
Q: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导演,你对他们风格的喜爱和你学美术的经历有关吗?
W:我高中就是在美术学校,每周五老师会放一些经典电影,当时也看不太懂,但是现在想想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潜移默化的把一些审美像种子一样种在你心里。并且我喜欢的这些导演在形式上的理念深深影响着我自己的创作,甚至会到了极端苛刻的地步,当然前提是你需要知道你这样做的意义。

《方舟》剧照
Q:你会给你的学生讲这些吗?
W:不一定,因为大家做什么职业的都有,然后都是第一次,我觉得更多偏向于电影这媒介本身和一些基础的东西。让他们在观念上至少有了一定的认知,而不是拍摄之前已经被电影吓到了,再让他们非常自由的尝试拍摄。在他们自己拍摄或者剪辑的过程中,再一起分析,把一些比较重要的、不会轻易变化的一些理念传递启发他们。
Q:你的公众号叫“纪录片初学者”,你觉得谁是纪录片初学者。
W:我觉得在影像创作这件事情上,我永远是初学者。有一个同学上次咨询我有没有一些高阶的东西,我说我教不了高阶,我只教小学级。
Q:你会像一些院校学者一样研究全面的影像理论,还是只研究自己感兴趣的?
W:我首先不是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者,我更多的是用理论去反思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也许是很寻常的东西但时常被创作者忽略。
Q:谈到自我驱动的东西,你的家人看过《方舟》成片后的反应对你来说是正向驱动还是反向驱动?
W:他们看完之后有两种反应。一种是不想看,就是不忍直视。还有一种是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能是电影呢,太糙了。
Q:你后来又把片子放在网上了,你现在看来觉得是值得的吗?
W:我没有想到的是它引起了一些反响,然后让我在非常迷茫的、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推动了我接下来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你或者可以理解为一个创作者的个人重要事件,这些事件会驱动他之后的一些发展走向。
Q:放在网络上之前有预料到这个结果吗?
W:当时问了一下蒋能杰和蝉鸣知了导演,然后他们分享了一些经验给我。当时《方舟》走完电影节后一直在那扔着,然后想要不然把它公开算了,之后就开始在社交平台逐渐发酵。
Q:那你这次拍的长片,如果走完节展之后,你还愿意把它放在网络上吗?还是说可能如果有更好的路,你未必会这样。
W:如果有更好的路,能在国外的一些流媒体或者国内能上线的话,肯定是不走这个路。
Q:你有办过几次训练营,你现在还在持续做这件事情吗?
W:因为没有别的收入,就是只能靠这个,今年计划就是主做线上。
Q:你还会做之前绘画的工作吗?
W:目前没有。
Q:你训练营的学生多数是怎样的一个背景?
W:基本上北京和上海和海外的居多。有宾大,多伦多的的学生;有广告行业的设计师;有香港的银行高管,也有新加坡的律师;有互联网大厂的工程师等等。
Q:是不是男性在影视行业里相对技术性工作多一些的原因?
W:我发现我接触的男生似乎普遍比较浮躁,眼高手低,相反女生比较上心,而且没那么多废话。
Q:会有人找你做留学作品集吗?
W:有辅导毕业作品集的。

《方舟》剧照
Q:所以现在的训练营像是一个乌托邦,但是又能有收入。
W:一方面我希望为那些真正热爱电影,想要创作的未来的艺术家提供一个学习探索的微型场域,另一方面赚钱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生活和创作的基础。
Q:所以这对你和学员来说,都是一件正向的事情。你有想长期做训练营的打算吗?
W: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我的重心始终在创作上!
Q:你应该会在各种平台收到不少私信吧?
W:私信普遍都是有关训练营的咨询和让我看片子或者看剧本的,还有问一些技术方面设备的建议。
Q:对这些,你是比较持排斥态度的,还是觉得其实也是想帮一下他们?
W:就是看剧本的,我一般不看,因为你这个东西几句话根本帮不到,他也说不清楚,然后我也不了解他;然后看片子可能有的会看,但是跟剧本一样,三言两语我觉得对Ta的实际帮助并不大。
Q:有人会在你的理论博文下方评论,你会回复。你喜欢这样的过程吗?还是说你觉得回复也是种负担。
W:正常交流吧。

《方舟》剧照
Q:你有过干脆就不发了这样的想法吗?
W:不发就没有人知道你,你也无法让需要你的人找到你。我的学生都是通过我的社交媒体找到我的。
Q:你最近发的一些小视频,是不是也在这个房间录制的?
W:对,就是这个房子。我现在创作的那部电影也有一个主场景在这。
Q:这些小视频的选题有计划性吗?
W:基本上一次会想4、5个选题,然后大概列一个大纲去说。
Q:你新的长片已经拍完了,现在的后期大概是怎样的情况?
W:剪了一个trailer,但是还没有完全定剪。得先赚点钱,电影也不能很快弄完,理想的状态是我希望工作和电影同步进行,现在基本上就是后期剪辑。
Q:你的新片也有过众筹。
W:当时《方舟》发布了之后,我希望借着这波热度去筹集新片的资金,独立的创作姿态并不意味着盲目的排斥商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大家信任我,我也不会想要辜负别人的信任。
Q:所以你不仅在做一个艺术家,好像还在做这个艺术家的联络人和经纪人。
W:自己推自己,不然没有人会帮你去策划这些事情。
Q:那你心里会矛盾或者纠结吗?
W:理性的去看待自己,你有短板也有长处。工作就是为了让我维持生活,然后又能做自己热爱的东西。商业这些东西它不是什么不好的,只要你能正确的看待它,没有什么东西本身是坏的,只是你的认知和看待它的眼光决定了它的价值。
Q:Cathayplay把你的《方舟》归到了人类学片单里,你怎么看?
W:拍摄之前,就本意希望它站在一个人类学的角度,或者宗教的角度去审视这个人的处境。我一直在研究神学,其实神学已经涵盖了一切。并意识到对于人类的宗教性和精神性的关注是当下中国电影最缺乏的东西。
Q:可能因为现在社会上没人关注宗教这种东西。
W:和社会环境也有关系。
Q:你的片子也把宗教和艺术结合,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W:嗯,既自由又不自由吧。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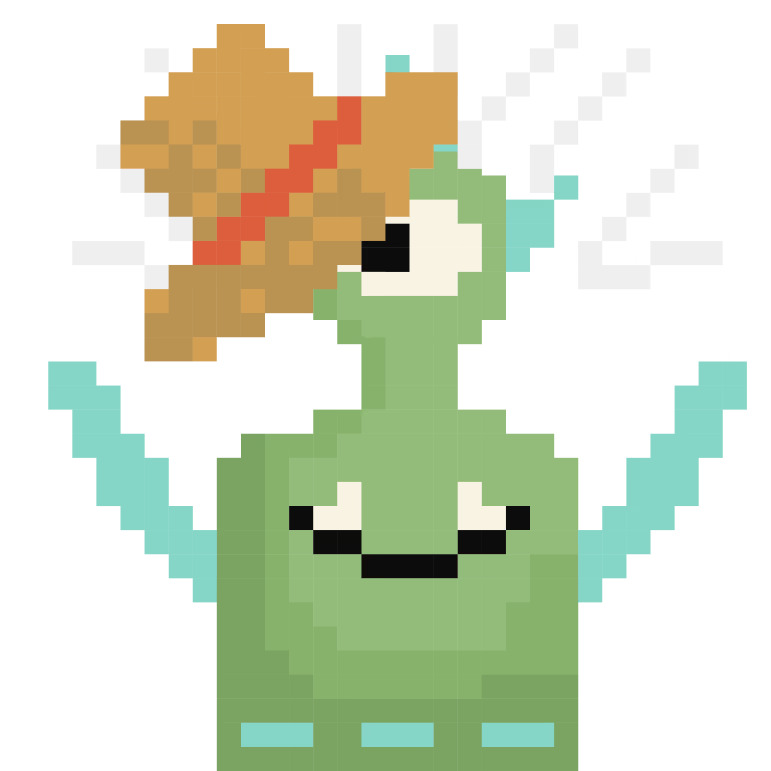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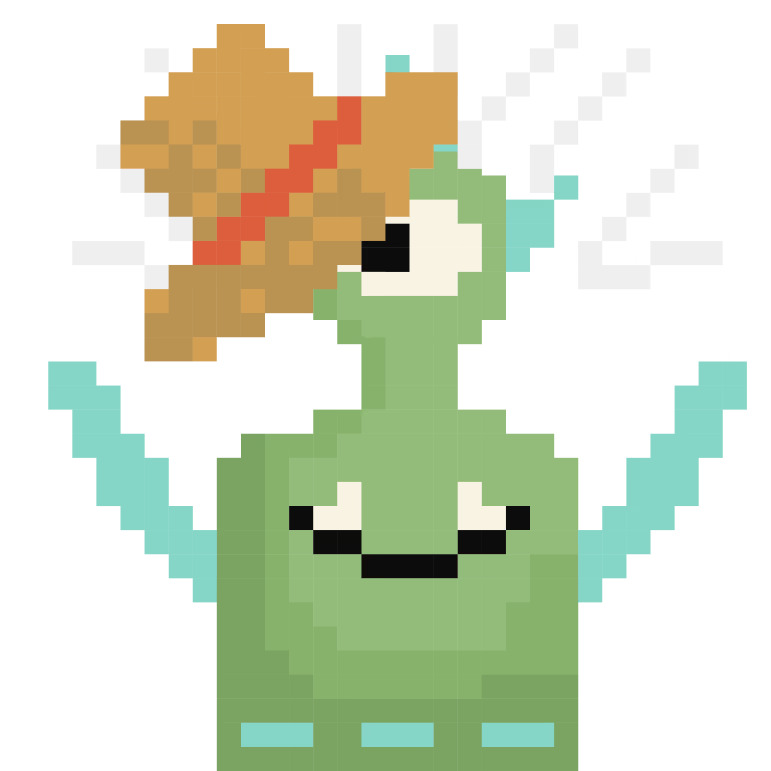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