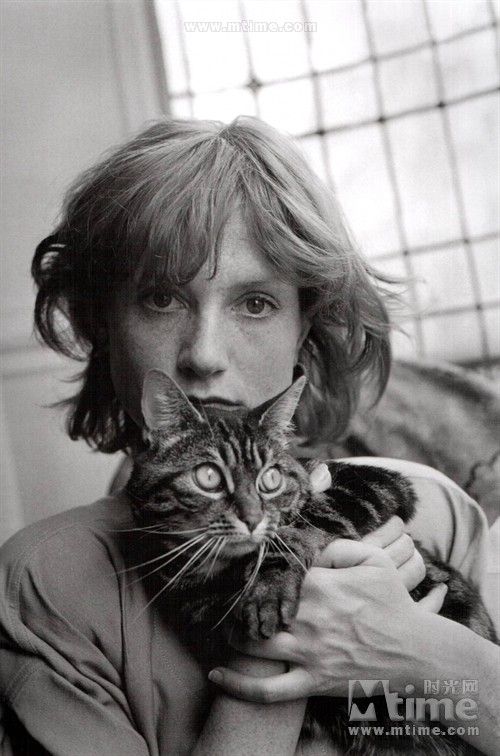我做了一個夢
當我從滿眼皆是廣告的春秋航空的機艙,一頭鑽出來時,迎接我的是上海的秋天——風吹到皮膚上,是冷的。上海的夜晚在此時此刻,顯得平和,而充滿安全感。
在公寓歇息了一天之後,我的生活回歸到日常——將衣服丟到洗衣機,用APP買菜,然後做飯、餵飽自己。
洗衣機發出了「嘀嘀」聲,我打開蓋子,取出洗好的衣服,去晾曬。接著,看書、睡覺。彷彿在海島的一週,是一個不同片段組成的夢境。
波麗士
夢中的人,個個都心神不寧、一臉緊張,像是隨時做好了戰鬥的準備,又像是隨時做好了逃跑的準備。
夢中的高樓連著高樓,天空只有一扇窗那麼大。街道與街道之間,沒有樹,連結它們的磚塊的隙縫裡,連一棵小草也沒有生長出來。小蝦小蟹在水泥路上,做著最後的垂死掙扎。
腥味,只有腥味。
雷聲大作。
「下雨了吧?」我問房間裡的人,她們沒有回答我,只是盯著電視機。
我們回到房間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視,看新聞。電視裏的打鬥、血腥畫面,彷彿動作片一般不真實。但我們知道,煙霧、槍聲、燃燒的火和紅色的血,就發生在離我們五百米遠的街上。
「波麗士怎麼可以做到像沒有感情的機器呢?」我不解,他們肯定不是機器生下來的,如果他們在街頭對峙時,對面的人是他們的親朋好友,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開槍嗎?
「你真是天真」,朋友笑我,「他們本來就是機器,不是天生的。」
牆
席地而坐的青年,像是一道道黑浪,拍打著,毫無方向。定睛一看,立在他們面前的是堅硬、冰冷的石牆。
他們陆陆续续地站了起來,張大著嘴巴,在訴說著什麼。
我聽不見任何聲音,我懷疑自己突然之間失聰,立刻用手拍打耳朵,還是沒有聲音傳進我的耳膜。
我冷靜了一會。
從他们的口型和氣勢判斷,他們應該在大合唱。
划水,怪獸,眼淚,蚊蟲,出口,面具,過火,做夢,重複,理智,打擾,樓梯,樹根,失败,紅綠燈,熟提子。
一個個的詞語,飘散在空中,慢慢地,一张张烧起来,像是烧着的纸钱一般掉落在地上,灰飞烟灭。
雞蛋
女孩掀開手帕的一角,又打開另一邊,包裹著的東西這才顯露出來——一枚雞蛋。
她把手裡的雞蛋,扔了出去——她這一劇烈的動作,嚇了我們一跳。
雞蛋在地上滾動了兩下,伴隨著碎裂聲。
她撿起雞蛋,剝掉蛋殼,說她沒來得及吃晚飯。
「一個雞蛋,含蛋白質6-7克,脂肪5-6克,營養豐富。它的外殼——硬且易碎,但是裏面,很有彈性。」她舉著脫去外殼的雞蛋說,「而且,受傷的時候,還能拿來熱敷。」
她丟出手裏的雞蛋,像是扔出一顆手榴彈一樣。砸在牆上的雞蛋——分離成蛋黃、蛋白,反彈回來,濺了圍觀人群一身。
女孩掏出手帕,繡著紅花綠葉的手帕,她打開手帕——裏面有三枚雞蛋。
她把雞蛋一一在地上排開,然後,俯下身來,她在雞蛋上做俯臥撐。
「我拒絕成為高級動物。」她說。
拖鞋
女孩喜歡穿拖鞋的程度,不分場合和季節。她說,腳趾頭也需要解放。
有一天——就這樣降臨在她人生的第27個年頭裡,不能說它是毫無預兆地出現。「有一天」,在來臨之前,總是會給她一些提示的。只不過,她沒有預料到「有一天」來得這樣突發。
有一天——女孩一如既往地套上了拖鞋,在打開家門之前,鞋架上的球鞋一霎那間有了意識,發出了請求——「今天穿我吧,為了安全著想」。
她停在門口,拿起球鞋,又看了看腳上的拖鞋。
「我今天穿球鞋還是拖鞋」這個問題,那一天,她思考了很久。在這一天之前,她的人生從不需要做這樣的抉擇。
她出門了,左腳穿著球鞋,右腳穿著拖鞋。
她要去黃大仙求簽。每一天,她都會去黃大仙求簽。
那一次,她求了一隻上上簽。簽上說,「堅定不移,走下去。」
她覺得不準。
因為,她還是不能做夢。
她能入眠,卻做不了夢——這太令人無望了。
父與子
我在雲吞面店吃3號套餐。坐在我對面的阿婆,跨著個花包,在等待她的雲吞面上桌的間隙,與我攀談起來。
「我準備回珠海住了。」她說,她在這個島上住得不舒服。她回憶起兩年前,她剛回來的時候,不管是地鐵上、還是巴士上的乘客,全都是一張張生氣的臉。
「現在的孩子,要這要那的,成天為了自己想要的東西鬧騰。做父母的沒有那個能力,沒有條件,怎麼可能滿足得了他們?」說完這些話,她搖了搖頭。
搖頭,通常表示的是否定的意思,但也有無奈之意。在搞清楚阿婆的意思之前,我覺得我有必要表達自己的看法。
「孩子們爭取自己應得的東西,或許方式不對——但是,那也是因為父母讓孩子太失望了。父親反對的事不斷增多,父親為孩子們制定了許多戒律,可自己卻說髒話罵人,做出的承諾也從不遵守。他一刻不停地統治著,發號施令,因命令不被遵循而動怒,因此咒罵、威嚇、打孩子。父親警告孩子們‘不要頂嘴’,早就禁止孩子們說話了。老大長期在這樣的教育之下,變得唯唯諾諾,話也不敢說了,也不會思考了。父親的威嚴令老二心生恐懼,為了苟活於世,對父親百依百順。老幺想要擺脫父親無處不在的控制,一直在逃遁,試圖結婚成家——」我滔滔不絕的演講,被阿婆硬生生地打斷了。
「你以為,從一個家逃離到另一個家,你就自由了、獨立了?」阿婆瞪著眼,問道。
安全過境
街道上的行人,一下子多了許多。有的人撐著雨傘,步行。有的人站在路邊,不時把腦袋從手機屏幕裡拔出來,轉動著脖子,望向巴士駛來的方向。
運載乘客回家的巴士,會來嗎?
晚上9點鐘不到,超市、便利店、餐館全都大門緊閉。有一些商鋪的燈牌還亮著,櫥窗前的塑料模特仍保持敬業精神,優雅地站立著。
一位拉著兩條狗的市民,迎面而來。其中的一條狗,對著一排的波麗士吠了起來。市民拉緊了遛狗繩,訓斥了幾句。
我在街上走,一個人。
我不能忘卻那條狗對著波麗士吠叫的畫面,因為懦弱的我,還不如一條狗有勇氣。
經過了花香四溢的殯儀館門口,接著,小心地從水馬下通過。不遠處的海浪聲,召喚著我。
大海,就在前方。
我站在鐵門前,等待。
等待一隻戴著一次性手套的手,打開我的腦顱。
傳輸帶上的一顆顆腦子,像是一件件行李箱,排著隊,接受X光機的檢查。
(2019.11 原文首發《字花·別字》第二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