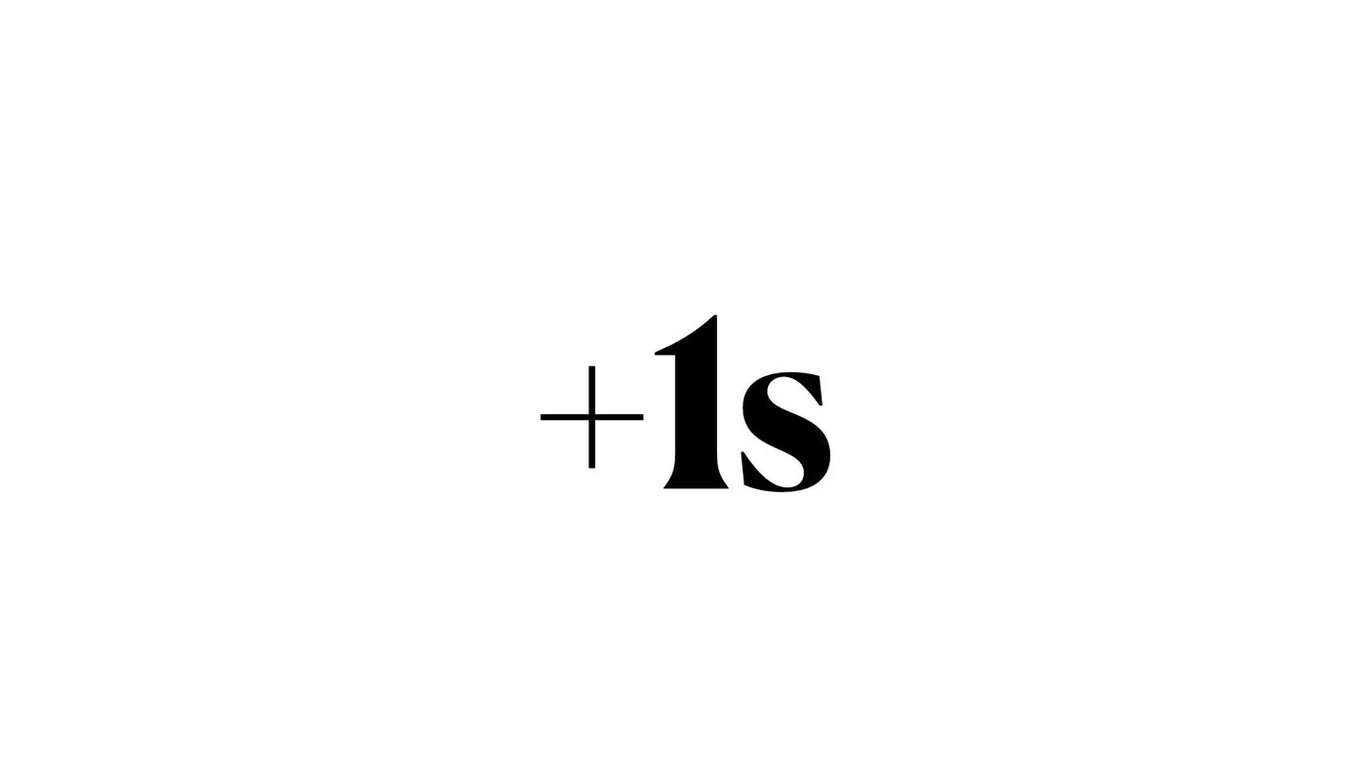成为阿廖沙
我的奶奶原来不识字,但在我出生前信了基督教,所以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家里泛黄的墙纸上贴着褪色的以马内利,她读经和祷告断断续续,含糊不清,以至于分不清她到底是不是睡着了,我好奇走近翻动那本厚厚的圣经,里面总夹着她用圆珠笔在折起来的草稿纸上写下的生字,一个字重复几遍,歪歪扭扭,有些残缺不全,像符文和咒语。有时,整整一个下午漫长而凝滞地过去,会听到我爸语气中带着被试炼过的耐性。我想,这也很简单,因为他是一个大学生,一个曾经有重量的身份,而我也不止一次骄傲地宣布,“我相信科学”,期待着他沉默的认可。所以我也不再去教堂,不再期待记忆中的那里分发的大白兔奶糖,像是被弄脏的小恩小惠,别有用心。
去年看到一篇学生的文章,恰好写到了同样的故事:午后的阳光洒在烫金的圣经上,ta搬一把椅子坐在不识字有阅读障碍的奶奶身边,一个字一个字地点读教她。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那么这样的画面简直像是编的。
ta又接着写道:
有时,我想活在人们之中帮扶、奉献,感受内心因苦楚和幸福而震颤(feeling my heart quiver with miseries and bliss)。但有时,我又想隐居起来,远离人群,如菩提佛祖凝视孤墙九年,寻求超然。到底是该和神近一些,还是和人近一些?
结尾是一个或许并不存在的和解,然而这不重要。如今,要通过否认这种二分困境来拒绝回答这个的问题已经太过容易,足够打动人心的是这个问题的真。
我去找辅导ta写这篇文章的朋友,问:“所以,有多少是你?”
Ta坚决否认,说全都是学生,自己只是适当修饰了一下。
“是么… 阿廖沙一样。”我为我自作聪明而失望。
癫狂而饱受折磨的伊万因为痛苦而潇洒,给人痛快(catharsis ),一切理所当然。可对于阿廖沙,也一样要承受想通的痛苦。The pain is one and the same.
其实,我并不期待生活中遇见阿廖沙,倘若真的出现,需先忍住嘲讽和说教,还需抗争彻彻底底的羞耻和困苦自己为何不能善良如一,甚至偏爱都显得自私和不公。
我常常只为写一两句话苦思一天,翻翻自己的心底,是否对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多少爱怜,所以失去了温柔的心肠。但力竭而倦怠并非恶意,只是可以习惯的苦涩。慰藉也突如其来,他,她,还有他,流淌着爱意的人们,原来也有快意恩仇,强烈的感情仍然被允许,而不是一种鲁莽的天真。
一直以来,我总觉得自己被一种恶灵所缠绕。起先是数字编织的谜语,后来是文字的深渊,现在早臻于无形。回过神来,心智也被松绑,再看曾经的苦困原来都不言自明。可我却不愿把这种认知的错位当作是一种以年龄和经历为代价的智慧。因为我想坚信那不是,而是找回被剥夺的,重新成为我本该属于我的自己(re-becoming what I am supposed to be),一切才得以重新开始。过往是序章(What's past is prologue),好,那一生是为了赶到起点上到此为止。What a life.
我们知道《卡拉马佐夫兄弟》没有写完。原本,阿廖沙终将要堕落成一个千夫所指的恶棍,是为《大罪人的一生》。我仍然想要好。我认真审视自己的内心,发现:一切皆可;一切罪行都能被理解;一切邪恶都离我一步之遥。而我仍然不知道人与人,灵与肉,在他们腐烂之前,各持自己那战无不胜的破绽,到底如何一次次来到、踏上那不可言说的不归之路。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