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太快還是太慢/蒼老或少不更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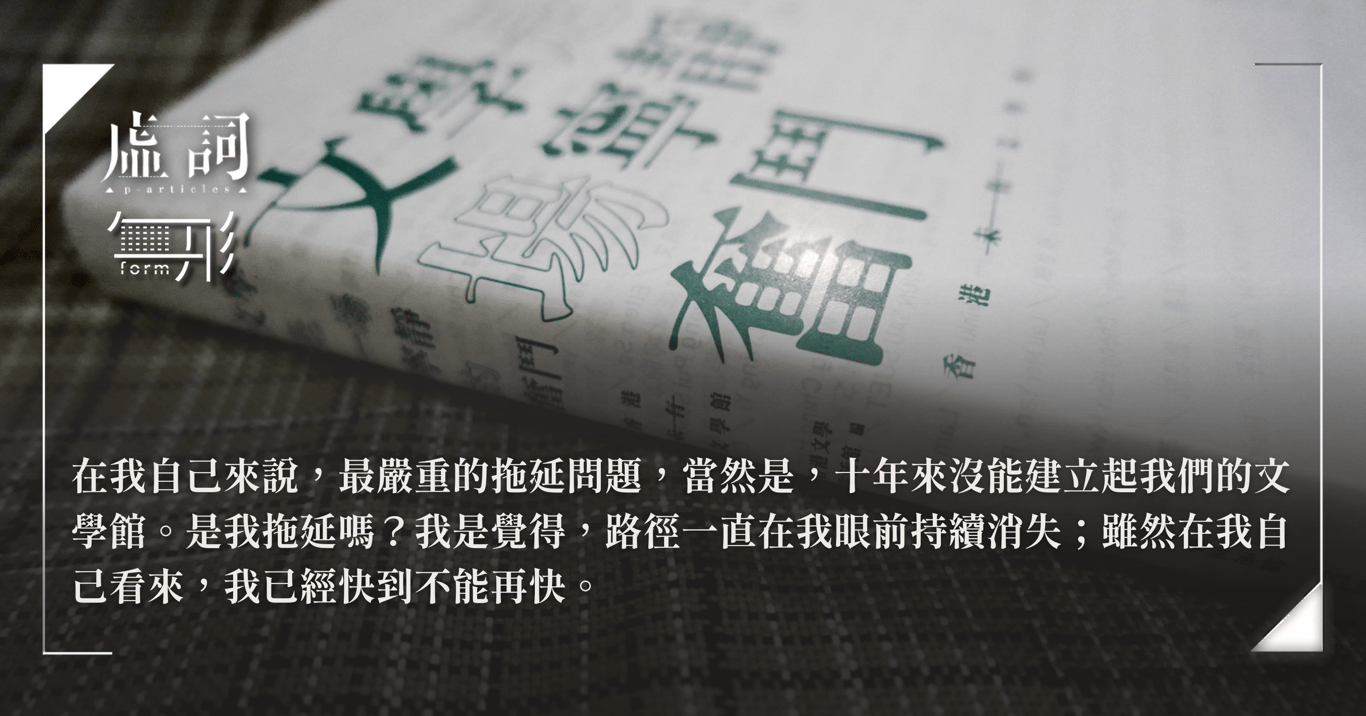
文|鄧小樺
「虛詞」、「無形」這兩個名字,定的時候當然是因為我喜歡「虛無」這個詞組。一如文學雜誌歷來以紙本為先,「無形」這名字是先有的,本來網站想叫「大象」,取《老子》「大象無形」之意;但發現當時中國已有個文化網媒叫「大象」,避諱之而有「虛詞」。也有人說過以「無」為名意頭不好,我沒有理會。如今《無形》紙本要結束,想起前事,微微一笑。
◯
回想起來文學雜誌也是個奇異的脈絡,它既包含一些媒體的編採經驗,但和大眾媒體的經驗相比起來是頗局限的,相反很著重文學話語圈的話語及人際脈絡。而偏逢這十幾年來媒體生態激烈變化,文學圈內的話語及人際脈絡亦嚴重斷裂。我作為保留著上一代文學雜誌記憶的人,有時覺得自己是在廢墟的地景上一邊掇拾一邊開拓,向外播種向內傳遞。
以往在文學雜誌上出道的人可能會進入大眾媒體工作,但我並沒有,完全是靠著以前的文學雜誌經驗和其他文化媒體的外在觀察,來揣摸該如何做,接近少不更事,有時叫媒體人做行家都有赧顏——但我亦不懷疑自己的信念。要之,原則有三:一是重視文字本身,我始終很嚮往那種開放性,完全不認識的名字,帶來好的文字,那就要給予發表的機會。二是扶老攜幼,必須讓不同年代不同性別不同背景的作者都能進入園地,讓不同的視野與風格交鋒。三是秉持一種文藝與文化政策的視角,不被時勢和政治完全蓋過——文藝的視角是容納曖昧和抒情性,文化政策的視角是建設性建言及多方角度的對話比照。編輯團隊的年紀距離我愈來愈遠,有時我也不知自己是否一再傳遞某些過時的東西——但始終覺得,這是我成長時見過的,重要而美好的東西,其他地方的好雜誌依然在做的,就算現在眼前已再沒有,也是應該要努力傳遞下去的。到2023年後半年,估計資助可能會斷,反而勉力用文化專題的方式做了兩期《無形》,分別是「文學館在他方」及「給敬而遠詩的人」,逼迫年輕同事,至少體會一下文化雜誌專題怎麼做的。
文藝團體的小而美好,本該是比較易走的一條路;但我是個離家的孩子,總是想去更遠的地方。記得2018年有一期「荷爾蒙」,結合神經科學與文藝抒情,題目算是前所未見,編出來的作者陣容也很新異,但那期,一篇投稿都沒有。那就算是設題曲高和寡了,我自覺不滿——《紅樓夢》寶釵夜擬菊花題,說要新巧又容易,讓人人都可寫的,才是大方。之後有許多題目,都由編輯部的年輕同事發想,果然收到數量和質量都不錯的投稿。我只保留提出一些抽象的題目,像今期。
◯
文藝雜誌往往以做過的人名存,如《現代文學》以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等人名存歷史;所以營運《虛詞.無形》時,我想來想去亦是要「培養人」。儘量讓同事看好書好文好電影好作品,非以巿場論;成品先論質素,再論hit rate;以九十年代較人性的媒體output rate來作標準,讓同事有足夠時間寫好訪問及資料性炒稿——如此種種在網媒時代算是開善堂的做法,別處多半不可能的了。
雖然把培養後生看得這麼重,但我一向後輩緣薄;紫微斗數子女宮代表後輩,我是空宮,借對宮太陽天梁。陽梁是個書卷味重的組合,亦多成名,惟亦是個代表疏隔與分離的組合。所以我早知道,我所看重過的後輩,多有成就,而會離開我;化解方法是我自己主動走遠一點罷?2019年八月編輯部四人同時離職,我整個八月沒有笑過,自己也去了另一世界。而後再入職的,就都留得比較長。2019年如水過無痕,但我困在某個世界裡無法回到公司的時候產生過一種奇異的團結與關懷,在之後還維持了好一段日子。雖然我不肯定這是否我自己想像出來的。
在編輯部裡我當然是蒼老的,依然像在其他工作環境裡那樣,有跟同事吃飯和一起玩的問題;只在所有狀態都最好的時候,我可以撒嬌高叫「這地方總編是完全沒有地位的!」駛出雙魚座的情緒勒索手段。
◯
我也有在編輯部抬不起頭來的時候:交稿時常寫著「贖回人格」——拖稿問題一直嚴重削弱總編的威信。最標誌性的拖稿,應該是「拖延症」一期,徹底拖延了,至今沒有交出來。那篇文章的草稿第一句寫著「其實我覺得自己根本沒有拖延症。我已經快到不能再快了。」歷代執編看到這句應該會燃起沉默的熊熊怒火吧。
在我自己來說,最嚴重的拖延問題,當然是,十年來沒能建立起我們的文學館。是我拖延嗎?我是覺得,路徑一直在我眼前持續消失;雖然在我自己看來,我已經快到不能再快。
作為持續遲到的人,我算是相當熟習遲到之後的補救方式——今次可以在《無形》結束之前,找到資金讓「虛詞」繼續運作下去,希望是一個補救。雖然這無法讓我保全現在的編輯部同事,但至少讓後來的人可以想像,並不是沒有藝發局資助就等於末日,要有自己的方法去保全文學空間,確實有這樣的可能。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