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學為認同發聲III》創造更理想的社會共同體 ft.楊佳嫻、李琴峰、Apyang Imiq(程廷)

主持人:楊佳嫻;與談人:李琴峰、Apyang Imiq(程廷)
文字整理:李怡坤、陳柏均
➤學習部落文化時,要找到舒服的狀態很重要
楊佳嫻:Apyang的書有提到Gaya,意義很複雜,簡單來說可以指「禁忌」。你覺得部落裡面的Gaya,是可以挪動的嗎?
會問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們說要復興部落文化、學習部落文化,其實也包含遵守這些Gaya。可是如果你喜歡的自己的樣子,或者你感興趣的事情觸犯了Gaya的話,到底該怎麼做?比如說,社會還是會不斷變化,新觀念也會傳到部落裡面,Gaya是不是因此有可能被鬆動呢?
我記得你在書裡有寫,作為生理男性,你非常熱心學習務農還有獵人的文化,可是你同時對織布也很感興趣。你描寫到,你想要碰織布機的時候,有些人會嚴厲地說絕對不可以,因為你是男性,你不可以碰。
你既學習獵人也學習織布,是有意為之嗎?你希望去挑戰Gaya嗎?

Apyang:我們講Gaya,其實不是專指禁忌啦,可以比較概括詮釋的講是「文化」。我其實不是有意為之,只是純粹覺得很好玩,這跟我的成長背景有關。雖然我是在部落長大,一直到大學才離開。前陣子接受專訪時被問到,我在台北市大概待了10年,會不會覺得我在台北的階段就是被漢化的過程。後來想一想,其實不用離開部落,原住民在家裡就會被漢化、現代化,或者是各種比較複雜的情境。
Gaya對我來講,本身不是一個固著、不變的點。「傳統」本身就會變,比方像結婚、離婚、上山、買車、當兵,都會殺豬,這個我們也叫Gaya。有些殺豬的原因其實跟以前不一樣,怎麼去殺豬、怎麼去分豬,也跟過去不一樣。
以前自己還不太懂部落文化的時候,總會覺得,很難得可以聽到一些Gaya。比方獵人上山的時候,在山林裡面不可以放屁,會影響到你的收穫。但是實際跟著長輩上山的時候,發現他怎麼在放屁?其實很多我們把它視為不能變動的東西,實際上現實情境就有很多鬆動的可能。我也聽過有的部落的女生是學習打獵的,因為她家真的就沒有男生,她們家就要有人去打獵,她還是得去做。
所以對我來講,Gaya是一種感覺,當我們對自己的認同,或對自己的文化有很強大認同的時候,應該是舒服的狀態,我們要讓自己找到那樣的狀態。不是說我在學習文化的路上應該怎麼樣,而是要讓自己找到一個舒適的狀態,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用文學探知自己的處境
楊佳嫻:提到返鄉、學習部落文化,想到的形象都是很任重道遠,好像承擔起某種時代責任的感覺。但我覺得Apyang說的很有趣,也很人性化,「舒適」這件事情是滿重要的。而且,傳統確實不是僵化的、等大家挖出來的古物,應該是有彈性,而且也是逐漸生成、不斷變化的東西。我們認識這個文化的方式可能也在變化中。
接著我想回到琴峰這邊。在台灣,因為同志書寫已發展滿長的時間,甚至可以說台灣同志文學已有自己的小傳統。讀琴峰的作品時,常常會指涉別的文學作品,從古典到現代,或者不同國家的文學等等。很多台灣性別書寫的作家,比如邱妙津、賴香吟、陳雪等等,在你的作品當中很明確地現身。你的其他作品中,也有寫舊體詩送給心儀對象的情節。似乎對你的小說人物來說,文學是非常重要的認識自我的方式,同時也是傳達感情的管道。
因此,想請你談一談,對你的性別書寫而言,文學作為資源或中介物,會起什麼作用?你是有意把這些東西放到作品裡,希望讓讀者體認到這樣的書寫傳統嗎?
李琴峰:首先,以《獨舞》來講,與其說有意,倒不如說是自然的。首先設定主角是台灣人,台灣的同志,同時又喜歡文學,在這個世代,喜歡文學又是女同志,有很大機率會碰到邱妙津,所以我覺得把邱妙津放進來是滿自然的。再加上主角是1989年生,她接受的國、高中國文教育,也都是以古典中文、古典文學為主,所以在這個作品中去引述邱妙津、賴香吟或一些古典詩詞,是滿自然的事情。
以我自己來講,文學的確在我對世界的認知過程,或對自我的認知過程起到滿大的作用,當然並不是絕對、不是全部,但它起到滿大的作用。它讓我們能夠用俯瞰的視角,或比較全知、宏觀的視野,去看到自己的處境,看到自己的生命,然後漸漸建立自我認同。當然不是全部的人都是這個樣子,但是對我,或者對趙紀惠來講,它就是滿重要的。
楊佳嫻:我自己就是從邱妙津的書才知道太宰治。我覺得,文學本身會形成某種傳遞,我可以在這個人的書裡面,發現其他閱讀的可能性,像一條長河一樣,不斷傳遞下去,也因此形成自己的閱讀版圖,然後又會反過來哺育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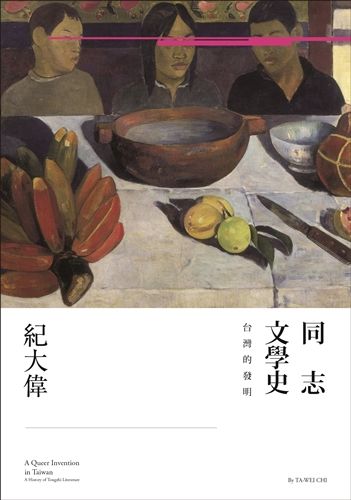
我當然也是一個文學青年,在讀《獨舞》以及琴峰其他作品的時候,都會感受到文學的力量。這也可以回應到紀大偉,他在《同志文學史》裡特別提到,過去報章媒體關於同性戀的知識或描寫,常常是負面或聳動的新聞,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同志,要怎麼認識自己、怎麼想像未來等等,可能要透過文學(也許有些人會透過影視作品)。顯然在某些時代,文學是一個滿重要的管道。
➤〈告白河壩〉朗讀
楊佳嫻:鏡好聽推出了《獨舞》、《我長在打開的樹洞》的有聲書,是透過專業聲音主播朗讀。但這次收到許多讀者回饋,大家非常期待能聽到兩位作者親「聲」上陣。接下來我們要邀請兩位作者來讀讀其中的片段,先邀請Apyang。
Apyang:我要讀的是〈告白河壩〉。寫完這篇的時候,我的室友,也就是我的配偶,其實正在睡覺。當我寫完的時候,我就在他的耳邊唸給他聽。這其實是我寫給他的一封情書,也是我寫給自己部落的一封情書。
你給我勇氣,讓我變強壯。你無懼出櫃,一派輕鬆地跟身邊人說你的性向,那種彈性像水,我也想像水,自在地分享生活。回鄉定居本是舒適而非禁錮,相愛是人的本性,這個部落有太多風花雪月:房間裡的床墊、山上的工寮、水溝旁的草叢、卡拉OK的廁所,學校教室的後面……每一則都讓我稱羨不已。
愛情充斥支亞干,河水懂得吞噬,河水不會排除,我對你的喜愛和性衝動也是如此,悉數包含在流動的支亞干溪裡。
河壩上,我說好多支亞干的故事給你聽,其中有打開的樹洞,這條溪從白石山往東流,水沖到河壩這邊,開口突然擴張,像一張大嘴,像一個洞穴,把我們一起含住,吞嚥在樹洞裡,我們的Bhring形成龍捲風,原地旋轉直到消逝在水波裡。
那一晚,我們接吻擁抱,交換彼此的風。白天的時候,你回傳訊息:「我們在一起吧!」
楊佳嫻:〈告白河壩〉這篇是整本書裡最甜美的一篇。用非常純真而大膽的方式,把性作為愛情的重要組成寫出來。在台灣過去的同志書寫裡,很少有這麼自然的表達。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大家不寫性,滿多寫性的東西,但是這篇是在散文這個文體裡非常直接的告白,毫不扭捏。
接下來請請琴峰朗讀所選的段落。
➤《獨舞》朗讀
李琴峰:接下來我會朗讀《獨舞》第十六章後半,主角到達雪梨走過同志遊行後,抵達林肯巖的內心獨白。
她回想起這一路上看過的風景,以及旅途中邂逅的人們。被氤氳水氣覆蓋而顯得朦朧的金門大橋,以及全身被雨淋濕、靜靜望著橋的Caroline。如白銀巨龍般蟠踞群山的長城,以及仰望長城的烏仁圖婭。六色彩虹四處騰躍的遊行隊伍,以及一邊觀賞遊行隊伍一邊嘻笑打鬧的柏彥與八四。夜不眠的紐約曼哈頓,石牆酒吧茜紅色的鮮豔霓虹,冬日暖陽舒適地糝在中央公園裡。秦始皇陵與華清宮南倚驪山北臨渭水,大雁塔南側玄奘三藏的塑像莊嚴佇立,一旁廣場上各個世代的男男女女歡欣跳著廣場舞。緋紅的紫禁城覆著純白的雪,狹窄微髒的胡同受霧雨濡濕。然後是雪梨,碧藍得使人不禁吞聲的天空與海洋,群山神聖幾乎要讓人忘卻世間所有苦痛的存在──
她閉上雙眼,霎那間蒼穹、白雲、群山、綠樹都為無邊的黑暗所覆蓋。二十八年的人生裡所見過的人事物,那些景色與人物表情歷歷在腦海裡打轉翻騰。而後漸漸地,那些景象也沉澱了下來,不久,知覺的表層回歸到不興一絲波紋的平靜水面。
一滴淚沿著臉頰滑落,感受到那滴淚滑下的同時,她才注意到,自己有多麼醉心於這塵世的美,多麼由衷地愛著這個塵世。這世界啊,人要求生則嫌太過狹窄拘束,要求死卻又有太多羈戀牽絆。直到經過與世界作別的旅途,真正站在生與死的邊界上,她才重新體認到自己對這世界的眷戀之情。
➤住在太魯閣族部落的男同志情侶幸福之道
楊佳嫻:《我長在打開的樹洞》這本書出版之後,在關注性別、原民書寫的朋友當中引起滿多討論的。Apyang說,大家一直關注返鄉青年這種嚴肅問題,他希望大家可以聊聊生活化的事情,所以我想問一些真的超生活化的事:請問在部落裡,同志們如何交男朋友?
搞不好大家還是透過交友軟體——這個問題好像有點預設了什麼。但是當我們對部落生活非常陌生,是個原民文化麻瓜,可能會想到這樣的事情。你跟你的伴侶是住在部落裡嗎?(Apyang:對。)你們一起住在部落裡,最快樂的事情是什麼?他會跟著你一起去打獵嗎?他可以跟你一起去打獵嗎?你覺得最大的困難跟考驗是什麼?
Apyang:一開始還不太敢跟別人公開關係的時候,家裡的人都知道,但我部落裡的家族總是來來去去,有很多親戚朋友、好朋友會進來我家,然後看到他,就會問他是誰?我爸媽不知道怎麼回答,就會說他是煮飯的。一開始他覺得很困擾,覺得奇怪,為什麼他只能被介紹成這種角色。
我覺得快樂的事情,是他跟我一起,在我喜歡的地方一起生活。我們不是一直都住在我的地方,我們其實是隔壁部落、隔壁村,所以我們會兩邊輪流住,有時候住我們部落,有時住他那邊。我覺得可以住在自己喜歡的地方,跟喜歡的人住在一起,就是最快樂的事情,然後可以跟自己的家人或是對方的家人處得很好,就很幸福。

➤不同於既有的社會、國家、家國的想像共同體
楊佳嫻:《我長在打開的樹洞》整本書,如果大家是從第一頁開始慢慢讀到最後,會覺得最後一篇文章太過分了吧,放閃放成這個樣子!全書最後一句話是:「我們在一起吧」。
接下來想要問琴峰。《獨舞》裡面出現了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志,因為各種偶然與必然而相遇,這樣的情節在琴峰其他作品裡也會出現。對你來說,同志是否會有一種隱隱然聯合起來、成爲彼此力量的可能性?換言之,在這個不見得美好的現實世界,隱然存在著像同志共和國一般的可能性。你的小說,最後會希望提出這樣的可能性嗎?
李琴峰:我覺得,並不是我願不願意提出這樣的可能性,而是這樣的可能性的確存在。不過,我覺得它比較像是想像的共同體,是一種不同於既有的社會、國家,或者是既有組織的想像共同體。這樣的連帶,可能建立在虛構的基礎之上,但是我們會去想像,我們共享一些歷史、一些經驗、一些痛苦。
比方說,我們講到同志權利的歷史,就會回溯到石牆運動,回溯到愛滋的歷史等等,會立刻想起這些東西。基於想像共同體的虛構連帶,我們也可能會去同理——當然不可能完全感同身受,但是我們也可能試圖同理——車臣在排斥同志的時候,同志族群是經歷非常大的痛苦。
又比方說,俄羅斯推出反同志宣傳法,我們會覺得非常氣憤。又或者說,阿富汗又遭到塔利班的支配,很多女性以及同志族群就會遭到打壓、遭到壓迫,甚至會有生命危險,我們就感到痛心疾首。

其實講殘酷一點,這些好像並不是跟我們那麼相關,但基於你是女性,或者同志族群,基於這樣的共同想像,我們能夠想像這些人的痛苦,想像這些痛苦是不是有可能、或者過去真的發生在自己身邊。
我有一次到中國旅行,因緣際會認識了幾個中國的女同志,她們就帶我去玩。我跟她們真的只有一面之緣,但她們跟我說,天下拉拉本一家。我感覺非常奇妙,我跟她們只見過一次,或者說根本不認識,只是我認識A,然後A介紹我認識B。A在北京,她的朋友B在西安,然後我到西安,B還會帶我去逛。
我覺得這是一種滿奇妙的連帶,你也可以說,它是一種反諷的連帶:假如沒有社會壓迫、不是弱勢的話,可能就不會存在這樣的連帶。但這樣的連帶,的確是一個可能性,讓我們試圖去抵抗男性霸權、異性戀霸權、順性別霸權等等社會的壓迫與歧視,而成為這樣的力量。
楊佳嫻:我還滿喜歡想像這種同志共和國的。在琴峰的作品裡,我們也可以看到文學共和國的存在,大家以文學作為橋樑或平臺,讓心靈找到可以對話或安住下來的可能性。
➤把痛苦變成一種力量
楊佳嫻:今天很高興可以跟兩位對談。
我在讀Apyang《我長在打開的樹洞》時,覺得整本書帶我們去感受一個返鄉部落青年怎樣重新成爲自己,做一個太魯閣族人,也做一個堅強而快樂的同志。當然,我所謂的堅強與快樂,並不是說只有正面而沒有其他面向,但我覺得Apyang是很有力量的一個人。
樹洞是這本書的重要意象,我們既可以說它是寶物的儲藏地點,也是吐出河流的洞穴,當然也像是身體裡面的激情通道。全書最後一篇文章,我最喜歡的幾句:河水懂得吞噬,河水不會排除,一種包容的、流動的意象,我覺得非常美麗,而且可以代表Apyang這本書的核心精神。
琴峰的《獨舞》,從台灣到日本,在痛苦的成長中摸索「女人愛女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是一場跨越幅度滿大的追尋。當趙紀惠和小雪在雪梨重逢,把一切事情說開,小雪說紀惠其實是堅強到了逞強的地步,然後紀惠腦中就浮現黑衣女子獨自旋轉跳舞的畫面。
我們可以說,這其實是死亡與童女之舞,死亡與誕生之舞。接著,紀惠想著她要活下來,她要繼續寫。作品的最後,她跨越死亡的閘門,但是我們不希望繼續停留在死亡的這一刻。雖然這篇小說的開頭是死,結尾似乎也朝向這邊走,但是最後跨越了、克服了。
因此,我覺得這兩部作品,其實都帶給我們新時代性別書寫往前看的氣象。往前看,並不是說沒有痛苦,而是我們怎麼樣把痛苦變成一種力量。
今天是鏡好聽夏日耳朵閱讀節的第一場,如果你已經讀過《我長在打開的樹洞》和《獨舞》,絕對值得再讀一次。如果你還沒有讀過,這會是你夏日閱讀時光的最好選擇。今天的活動就進行到這邊,非常謝謝兩位,也非常謝謝在線上一直陪伴我們的聽眾朋友,謝謝大家。●(原文於2022-07-10在OPENBOOK官網首度刊載)
➤以文學為認同發聲,完整側記
從語言、性別到族群|在多重弱勢中,摸索出賴以為生的奇蹟 |創造更理想的社會共同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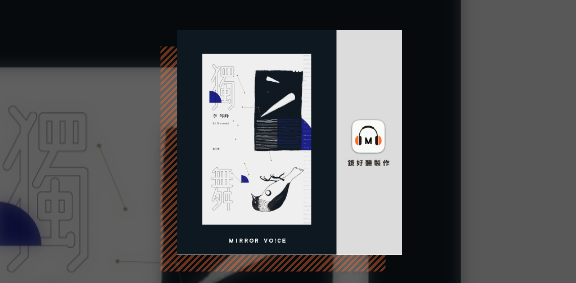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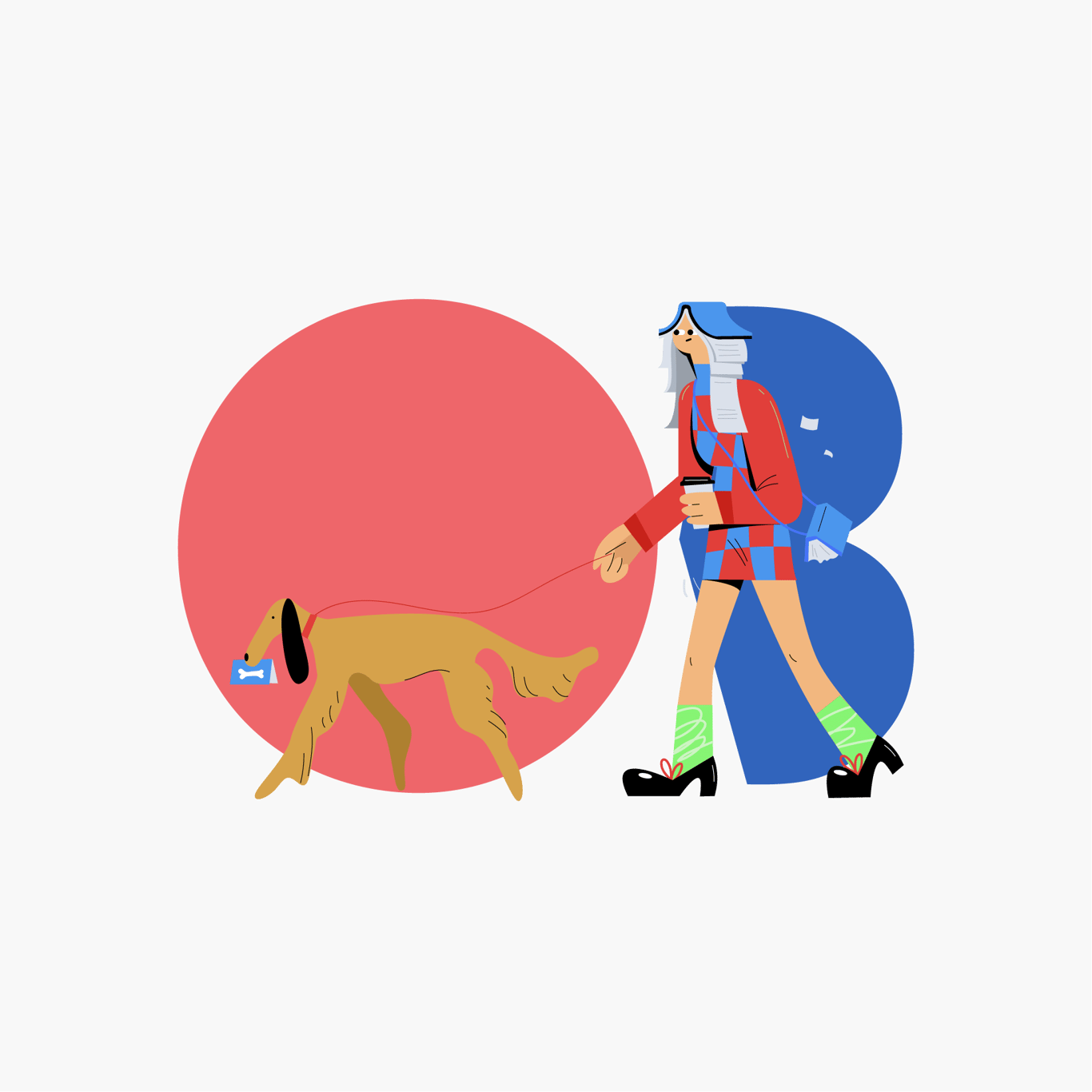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