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文化操控》其實你應該要怕你的手機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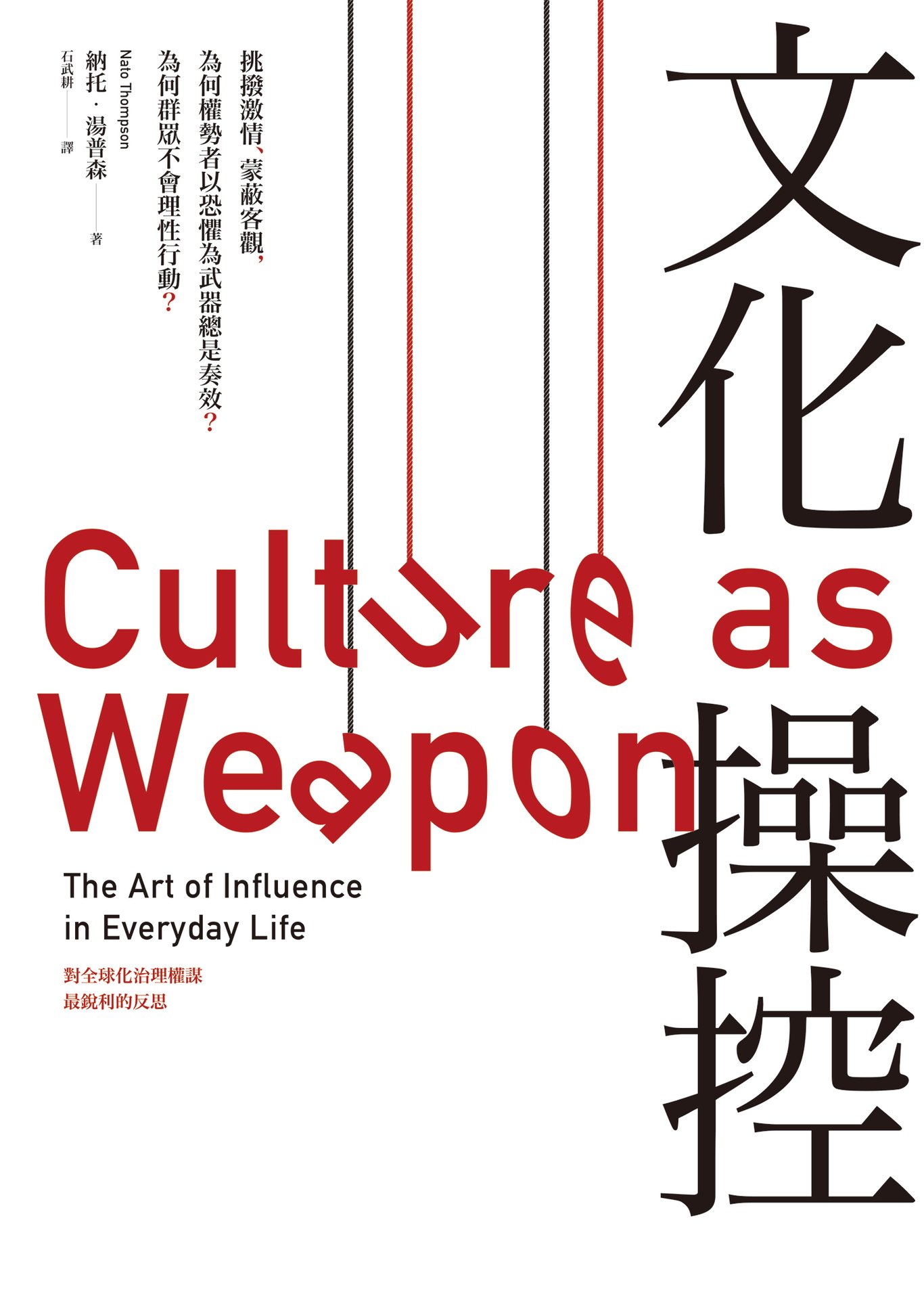
有史以來最個人的電腦:其實你應該要怕你的手機才對
若說文化操縱的演化方向,是越來越感性地訴諸我們的私密欲望、恐懼以及對社會聯繫的需求,那麼電腦當然會是這則故事的一部分。這種從開關切換發展而成的設備,可是花了很長時間,才將自己塑造成現在這種取悅感官的肢體延伸。然而,在過去四十年間,這種機器已經全盤重新定義了所謂的文化。因此,讓我們回顧一下電腦迄今的演變。
過去由單人操作的電腦,如今成為整合並動員我們對整個世界感受的平台。社群網絡既是朋友、熟人、同溫層、乃至敵手之間的一張互聯網,也示範了「私密」在輿論脈絡下的力量。我們的私生活在社群網絡上變得公開,公共世界被併進我們的私生活。
若說在一九八○年代中期,人們還只是隱約覺得電腦將會改變一切,到了二○一六年,已經明顯到說出來都嫌傻。電腦改變地緣政治與個人樣貌的程度如此劇烈,以至於每個世代都覺得對全新的生存方式感到暈頭轉向。個人電腦來臨以及隨之而來的社交平台,已經讓私密成為公共生活的主宰模式,而這場科技革命對世界造成的改變之巨,可以與印刷術並列人類史上之最,連廣播的力量或許都相形見絀。
寫作本書時,全世界使用中的智慧型手機約有二十億支(全球人口約七十億),使用網路的人口則有三十五億。美國有一億五千五百萬人固定會玩電子遊戲,五分之四的家庭擁有電玩設備。二○一三年的一份研究也顯示,世界上每四人就有一人使用社群網站,而這個數字在接下來十年內預計還會繼續增長。
電腦的故事不只是關乎銷量,更重要的是消耗的時間與用途。最近的一份研究顯示,「在美國,每天用在看螢幕的時間是四百四十四分鐘,也就是七小時又二十四分鐘。其中又可以再劃分為看電視一百四十七分鐘、看電腦一百零三分鐘、看智慧型手機一百五十一分鐘、看平板四十三分鐘。」電腦時代所帶來的,是全套生活方式突如其來的徹底轉變。
飛彈變成了「飛彈指揮官」
電腦是從什麼時候起,再也不是一連串引導核彈與NASA太空發射的閃燈與電路板,轉而變成一般人用來消磨整天的東西呢?此外,它又是何時從家裡書房的小器材,變成我們身體的延伸呢?重點就是電腦的改變。電腦急速蓬勃發展之際,恰逢這項科技不再受政府防衛支出保障,並走進大眾消費市場的時候。在一九五○至六○年代的大多數時間裡,電腦對平凡的消費者來說,仍然只是個遙遠陌生的概念,它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就是科幻片布景裡的閃爍燈光,以及偶爾出場的大型破爛機器人而已。
不過,讓電腦融入日常生活,是要花上一些時間。
後來被稱為矽谷的地方,就為此提供許多基礎。曾協助發明電晶體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威廉.蕭克利(William Shockley)在一九五六年從紐澤西搬到加州的山景城(Mountain View),引發長達數十年的後續效應。他在此成立蕭克利半導體實驗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oratory),並且積極招攬當時業界最敏銳的年輕人。蘇聯於一九五七年發射史普尼克一號,使得一波資金注入美國的太空產業,其中也包括這間做得出電晶體的公司。
蕭克利半導體雖然獲得成功,公司卻在不久後流失八位最優秀的雇員。這是締造矽谷(以及某種經濟模式)的決定,後來於一九六八年創立英特爾的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與高登.摩爾(Gordon Moore)在內的這八人會出走,則是因為蕭克利的管理風格疑神疑鬼又有侵略性,且不肯製作以矽為材料的電晶體。日後被蕭克利罵成「八叛徒」(traitorous eight)的這些人所創立的快捷相機設備公司(Fairchild Camera and Instrument,後來改名為快捷半導體),就是以矽作為製造電晶體的關鍵材料而獲利。該公司率先採用平面製程(planar process),大幅壓低電晶體的成本。這些科技上的創新,後來又催生革命性的半導體,才使得原本跟冰箱一樣大的電腦,縮成可以手持的尺寸。成本降低也使一個新族群得以出現:電腦業餘玩家。
矽谷此後成為資訊時代的帝國中樞,每家重要的公司,都搬進史丹佛大學校園的周邊地區,而那裡當初也以較低的地價吸引企業入駐。科技公司若想成功,就必須開在舊金山南邊的聖塔克拉拉山谷(Santa Clara Valley)。而這樣的群聚效應,不免也會讓人為了商業機密、違反著作權,以及員工要自行創業還是跳槽而疑神疑鬼。科技創新對公司來說攸關生死,而這些殘酷的價值觀也將塑造幾位關鍵人物的人格,直到二十一世紀。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快捷半導體推出第一套基於微處理器,可編寫程式的卡匣式家用電子遊戲系統,就此創造歷史。這台機器還搭配名為電玩卡帶的八軌規格塑膠殼電子遊戲匣。雖然這套主機上市第一年就售出了二十五萬台,卻很快因為雅達利(Atari)這家劃時代公司的出現,而相形失色。
雅達利的創造者,是個著迷於遊樂場機台的人。他喜歡那些穿插點綴在檯面上的小機關,以及它們所製造的博弈競賽感。這些機台也是互動式的,舉例來說,彈珠台(pinball)遊戲就能讓人專心到硬幣用完為止。雅達利的創辦人諾蘭.布希內爾(Nolan Bushnell)既熱愛遊戲又熟練於工程,他開發史上最重要的一套電子遊戲系統。
雅達利發表於一九七二年的乓(Pong)遊戲,就已在街機市場上脫穎而出。這款由兩側各一塊的長方形白色板子來回擊球,有如數位版的網球遊戲,在剛成形的街機世界引發轟動。布希內爾的這個點子,是從另一款較不複雜但具有開創性的家用電玩系統,也就是美格福斯奧德賽(Magnavox Odyssey)那裡抄來的。但雅達利的版本熱銷,而他們在一九七五年聖誕節檔期推出可接上電視的家用款乓遊戲機,增強了他們的聲勢。
這台家用遊戲機,或許也轉變了二十世紀後半最重要的一項科技,也就是電視的樣貌。原本進行單向影音傳遞,突然就變成互動式關係了,觀眾也因此變成參與者。對許多美國人來說,能對客廳那尊不動如山的注目焦點做點什麼,已經是件天翻地覆的事。
雅達利在一九七○年代末至一九八○年代初盛極一時。電玩與雅達利的家用遊戲機,就是大眾消費者與電腦的首次接觸,但電腦科技的未來,在當時仍是未定之數。
雅達利等主機雖然稱霸一九八○年代初,但在一九八○年代後半,就被任天堂遊戲機(Nintendo Entertainment System,亞洲機型又俗稱紅白機)取代。在日本賣出兩百五十萬台紅白機之後,一九八五年登陸美國的任天堂遊戲機,此後就成為電玩市場的霸主。任天堂剛推出時共有十五種遊戲,其中包括打鴨子(Duck Hunt)、敲冰塊(Ice Climber)、功夫(Kung Fu),以及歷久不衰的超級瑪莉(Super Mario Bros)。光是在一九八八年,就賣出七百萬台任天堂遊戲機,到了一九九○年,三十%的美國家庭都有一台任天堂。而我們也都知道,雅達利與任天堂遊戲機都只是家用電玩系統的起步階段而已。
育兒有了新的定義,包括要在小孩瞪著螢幕握緊遊戲手把時,放任他們玩掉當天的好幾個小時。在通勤時感到無聊的人,則會在手機上玩一些像是憤怒鳥(Angry Bird)或糖果傳奇(Candy Crush)之類無害又高度重複的遊戲。電子遊戲不只能拿來放鬆調劑,也利用了深層的意義。與朋友對打時,遊戲可能有社交性,但一個人玩也很棒。練等級時,可能感到時間飛逝;在無盡的虛擬追尋中,小小的成就也能讓腦部釋放多巴胺。
肢體的延伸
電子遊戲開啟在家使用電腦科技的大門,但是最有潛力的使用者們卻大多還不確定,除了或許能做複雜的文書處理之外,家用電腦還能用來做什麼。就跟電子遊戲一樣,家用電腦與相關軟體的成長,也是業餘玩家社群的努力經過某種市場鞏固(market consolidation)的結果。比爾.蓋茲與史蒂夫.賈伯斯這兩人就代表了家用電腦的興起,而且他們就像專橫的前輩亞歷山大.格拉漢姆.貝爾(Graham Bell)一樣,都執著於爭強好勝。
比賈伯斯更好勝的比爾.蓋茲,原本就是個寫程式的人。一九五五年生於華盛頓州西雅圖的他,成長的過程也跟上程式語言的演變。他十三歲時就用過有龐大米色外觀的自動收發型電傳打字機三十三式(Teletype Model 33 ASR),又透過學校的合作案,接受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的程式訓練。蓋茲隨後就開始寫起程式,並且在第一年就寫出了自己的第一個程式。一九七六年,他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奎基市(Albuquerque)創立微軟時,走在同領域的前頭,也在正確時間來到了正確的地點。但讓他成為億萬鉅富的,或許是他的另一個強項:他能夠壟斷市場。
業餘的電腦同好社群,或可說是讓如今徹底商業化的微軟/蘋果瓜分天下的無名英雄。這群玩家不僅喜愛探索寫程式的可能性,也崇尚開源(open-source)科技與共享,後來便演變成駭客社群。在微型電腦MITS Altair 8800於一九七五年推出之後,他們的熱情又大為增長。外觀像個沉重藍色箱子,附有八吋軟碟機的這種早期版本的家用電腦,就是為了吸引居家玩家而特意創造。《大眾電子》(Popular Electronics)雜誌一九七五年一月號的標題就是:「重大突破!世界首部媲美商用機型的迷你套裝電腦。」
MITS Altair 8800讓比爾.蓋茲與保羅.艾倫(Paul Allen)有了發表的平台,才創立了後來的微軟。他們與製造商MITS聯絡,說他們有一套叫作BASIC的直譯器(讓電腦更容易操作的程式碼)要賣。MITS表示有興趣。比爾.蓋茲與艾倫用他們自製的程式語言,讓Altair 8800在一捲收據紙上印出了「READY」的字樣。然後他們又輸入了「PRINT 2+2」,Altair 8800就吐出了答案「4」,與電腦的通訊已經成功在望。這套語言把一系列的開關切換轉譯成可解讀的東西,也就創造第一台家用電腦的通訊程式,這是個重大的歷史時刻。MITS以一年期的合約買下了這套程式,而比爾.蓋茲與艾倫則明智地保留著作權,有此前例的著作權與程式碼的觀念,後來更是從核心撼動電腦世界。
有一場典型的糾紛是,比爾.蓋茲曾在一九七六年向這些在開源基礎上作業的業餘玩家發表一封公開信,要求他們付錢購買BASIC軟體。他寫道,「大多數玩家一定都很清楚,你們使用的軟體多半是偷來的。硬體要花錢才買得到,但是軟體卻可以共享,誰在意為此工作的人有沒有拿到錢呢?」
雖然也有人會對這種怨言產生一定的共鳴,但這些不滿被針對的龐大玩家網絡也覺得,集體努力不但為程式編寫帶來顯著的進步,更挑戰了比爾.蓋茲的資本主義路徑。比爾.蓋茲這波攻擊的關鍵焦點,就是「自組電腦俱樂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這個由電子愛好者與工程師一時興起組成的社團,後來不但奠定矽谷的基礎,也促成蘋果電腦的成就。在這個自組電腦俱樂部的成員裡,就包括了史蒂夫.沃茲尼克(Steve Wozniak)這位工程暨程式大師,以及如今名滿天下的強迫症患者賈伯斯。賈伯斯在一九七四年進入雅達利工作,成為該公司的第四十位員工。傳說中的情節是,他的強迫症令其他同事痛苦不已,讓創辦人布希內爾只好特別安排賈伯斯改上夜班。
若說沃茲尼克對技術比較在行,那麼賈伯斯就是這兩人當中的伯內斯。他是行銷人,他讓科技變得個人。賈伯斯在一九七六年決定將他們的公司命名為蘋果,最能體現這一點。當時的主機還會取名為Altair 8800,不然就是稍微親切一點點的雅達利。取名叫做蘋果,與電腦代表的每件事都背道而馳。而這當然就是重點所在,蘋果讓我們被趕出伊甸園,蘋果是混合了欲望的知識,這也是一種日常的水果,平凡而樸實。蘋果電腦領先別人的地方不在微處理器與記憶體的速度,而在於個性。在比爾.蓋茲靠家用軟體賺進幾十億美元之時,賈伯斯所強調的則是,電腦就是欲望、夢想與身體的延伸。
在推出Apple I電腦(因在賈伯斯的車庫設計出來而聞名)之後,沃茲尼克跟賈伯斯又在一九七六年推出Apple II。雖然第一代的蘋果電腦更像是一套給業餘玩家的器材,但第二代機型卻確立了公司的地位,並且建立了電腦的某種經典造型。加裝基本試算程式的Apple II,便逐漸打入家用的消費市場。這個市場雖然尚未爆炸性發展成如今的規模,但從一九七七年九月到一九八○年九月,年度銷售額就從七十七萬五千美元成長到了一億一千八百萬美元,平均每年成長五三三%。
電腦產業的重大躍進發生在一九八四年,此時電子遊戲市場的崩潰已是一年前的事,而賈伯斯也會在一年後離開自己創辦的公司。就在這年由洛杉磯突擊者隊(Raiders)對上華盛頓紅人隊(Redskins)的超級盃決賽上,播出劃時代名作《銀翼殺手》(Blade Runner)導演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所執導的蘋果廣告。這支廣告的開場,是一群穿著連身工作制服的光頭男子,在踏步聲中,沿著走廊列隊行進。接著,有一名穿著紅短褲與慢跑鞋的金髮女子衝過來,穿越在大殿裡坐成一排排、無助望向大螢幕的光頭人。螢幕上播映的巨幅影像裡,有個男人似乎在進行演講。這就是歐威爾筆下的老大哥了──畢竟是一九八四年。遭到鎮暴警察追趕的這名女子拋出手上拿著的大榔頭,砸爆大螢幕。在炫目的亮光中,旁白讀出字卡,「蘋果電腦將於一月二十四日推出麥金塔(Macintosh)。屆時你會知道,為什麼一九八四不像一九八四。」
雖然麥金塔並沒有被搶購一空(對家用市場而言太昂貴),卻體現讓賈伯斯被譽為行銷與設計大師的每個元素。一方面,這支廣告很有野心,不只要跟IBM,或許也要跟傳統對於一般電腦的印象做出區隔。這支廣告就是蘋果,IBM則是那個男人,蘋果是人文精神與自由的延伸。這是把大企業定位成叛逆者的行銷譬喻(trope)早期案例。這支廣告預示Mac後來「不同凡想」的(Think Different)企劃,更是把電腦綁上了賈伯斯崇拜的巴布狄倫,以及甘地與愛因斯坦等創造不同的人。
將這些廣告斥為在消費者友善與叛逆之間求取平衡的伎倆,雖然是很誘人的想法,但從史考特執導的這支廣告,若能看出一些更具感性力量的東西,則會更有幫助。透過把電腦的精神定位成個人,這支廣告與個人電腦本身所關注的焦點,就變成消費者的私密欲望與需求了。也就是說,這支廣告所呈現的,不僅是個人革命的形象,還有個人電腦也將成為這場革命的媒介。
這顯然不是一場經濟上的革命,因為蘋果所遵行後來也加以擴張的,仍是資本的邏輯。但這是一場行為、態度與情緒上的革命。伯內斯憑直覺就感受到了私密與公眾之間的深刻連結,但要在將近一個世紀之後,才發展出能合成這種關係的科技。最後,電腦掀起革命,改變個人在文化環境當中的角色。
麥金塔是第一台讓圖像式操作介面與滑鼠普及化的電腦(全錄率先做過但沒人注意到)。這台電腦還配備打字與繪圖程式。換言之,這是第一台強調觸覺與藝術創作功能的電腦。
賈伯斯不顧自組電腦俱樂部原本的信條,反而像比爾.蓋茲一樣,致力於讓這些科技以及蘋果的一切都變成專屬規格。賈伯斯相信,消費者其實不想做選擇。他們需要自由沒錯,但只在侷限的環境內。
電腦終究開啟以文化做為武器的新時代。這是一種有著多方效應、有利有弊的武器。跟現在的情況很相似的是,我們在電視出現時也見過消費市場像這樣急速擴張,可是電腦不僅是接收器,也同樣是傳輸器,是一種名副其實的工具。賈伯斯也強調,身體是貪求接觸與感受的,而這些工具則可以成為延伸。觸控螢幕是手的延伸、iPod是耳朵的延伸,iPhone則是社交生活的延伸。蘋果不僅把身體帶進科技中,也讓這些元件一起把身體纏進連結性(connectivity)的網羅。
窺探
要理解數位革命所造就的複雜世界,就必須了解個人電腦(以及電子遊戲系統)的興起,以及網路的運用範圍在此時也日益擴大。網路的源起,可以追溯到約瑟夫.利克里德(J. C. R. Licklider)在一九六○年代初寫給「星系間電腦網絡」(Intergalatic Computer Network)成員與附屬單位的一些早期備忘錄,其中他表示,「我明白到未來大多數或全部的電腦可能只在少數場合才會在統整的網絡下運作。然而,在我看來有趣也重要的是,開發出在統整網絡下運作的能力。」這段話有如預言,影響後來好幾代的軍方科學家。當時仍是搖滾樂與電視的全盛時代,電腦主要還是軍方與學界研究的附帶課題,它只存在於科幻作品與研究經費的世界裡。
許多早期的電腦研究,都是在艾森豪於一九五八年設立的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旗下進行。DARPA是專門為美軍研究科技的智囊團。在一九六○年代,該單位已經逐漸開發出一套升級版的摩斯電碼,能以電子方式轉發訊號。網路是美軍創造出來的,這事乍聽雖然驚人,但要記得,美軍可是少數能進行開放式研究的單位。勞倫斯.羅伯茲(Lawrence G. Roberts)就在這裡創造網路的最早版本之一,也就是縮寫名稱拗口的阿帕網(ARPANET,高等研究計劃署網路)。阿帕網當時就已經獲得DARPA、蘭德公司以及英國國家物理實驗室(NPL)的注意。在一九七二年發出的第一份電子訊息,就像是電腦之間進行的電話會議。
一九七八年,在芝加哥建立的第一套撥接電子佈告欄系統(Bulletin Board System,BBS),相當程度上受惠於Apple II的實惠價格,以及配備擴充槽的S-100 bus machines電腦。此時,還只有一小群科技玩家在使用這些科技。這套早期的BBS在退役之前,一共登錄了二十五萬三千三百零一筆通訊。這些系統讓早期的電腦使用者可以像在佈告欄一樣發布資訊讓人查閱。電子佈告欄服務的成長,以及成長期必然產生的問題,都將促使數據機的性能增強。
一旦有可能從佈告欄板面下載GIF格式的低解析度圖片,網路色情以及其他每一種社交活動的初期發展也就隨即展開。正如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在她的著作《在一起孤獨》(Alone Together)中寫道,「所以,舉例來說,作為網路祖父的阿帕網,原本是開發讓科學家合作論文,但很快就變成了一個八卦、調情與聊小孩的地方。」隨著人們越來越容易負擔與取得電腦,網絡的運用範圍也隨之擴大。
新的力量
各種不同的大規模生產科技,已經為網路最終能提供的事物奠定基礎。由娛樂、性、同溫層、八卦以及無聊玩笑等內容交織而成的連繫,讓我們成為了我們,也結構我們的日常生活。就從一九九一年開始講起吧。當時還沒有Friendster,也還沒有MySpace,更遑論臉書了,當時連撥接數據機甚至是電子郵件都尚未普及。大家都還在用市內電話,而最接近手機的東西,則是會在戰爭片裡看到、或是有錢人對著講話,一整台組裝起來就像電晶體收音機一樣的東西。
為社會聯繫打下基礎的除了電子佈告欄系統與ARPANET的數位革命之外,還有一個逐漸成長由文化生產者所組成的社群,而他們也都有興趣將掌控媒體。當然,另類媒介的歷史很悠久。紐約市的紙老虎電視台(Paper Tiger Television)創立於一九八一年,其中一位創辦人說得簡明扼要:「批評大眾媒體譴責他們濫權是一回事,創建一個活得下去的替代選項,則是另一回事。」紙老虎電視台的訴求,就是為受到資本主義宰制的主流無線電頻道,提供一個替代選項。由於製作成本的緣故,小眾電視需要更多的器材也更仰賴電視訊號的頻譜。但他們所體現的自製媒體的精神,後來也隨著媒體傳播科技流入大眾手中,而變得更有可能實現。
如果說,在二十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裡,文化絕大多數都是在權力送往群眾的單一方向上移動,那麼到了二十一世紀,多向溝通的能力則得到了大幅擴充(現實情狀容後再辯)。影印機、八軌錄影機、錄音帶以及無線電廣播科技的傳播,都讓小規模的生產者具備自己辦媒體的能力。只要科技的成本變得更低廉,渥荷對未來的預言「每個人都會成名十五分鐘」就會成真。人們不只是想看搖滾巨星,還想自己成為搖滾巨星。人們想要的不是看雜誌,而是辦自己的雜誌。這是DIY的時代,而小眾雜誌(zine)、混音帶(mixtapes)、廣播節目等內容的製作能力,也已經交到大眾手上。
一九九三年夏初,在風氣一度激進的加州柏克萊,留著鬍子的史蒂芬.杜尼佛(Stephen Dunifer)爬上柏克萊後山(Berkeley hills),意圖打破大企業對廣播媒體的控制。當時正值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戰況激烈,在杜尼佛看來,包括全國公共廣播網(NPR)的當地成員KPFA電台在內的主要媒體,都在往中間派靠攏,而他受到這種挫折,決定親自採取行動。他為此設立的柏克萊自由電台(Free Radio Berkeley,FRB),是一家低功率的無照地下電台,收聽頻率為FM 104.1。杜尼佛把電台架設在山頂,使信號的覆蓋範圍極大化,就此展開後來遍及全美、向人民報導獨立新聞的運動。廣播,這種曾經為美國人帶來爵士樂與搖滾樂的裝置,就這樣落入尋常人的手中。
鼓舞杜尼佛從事這場革命行動的原因,就是低功率廣播科技的成本已經越來越低。只需一千至兩千美元,就能讓一家低功率電台投入運作。柏克萊自由電台啟發全美各地的幾百家地下電台,使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FCC)也以監管者的身分介入,阻止獨立電台開張。對電波控制權的爭奪戰就此真實上演,最後到一九九八年六月,已在灣區放送幾千個小時的柏克萊自由電台,也不得不停止播音(此時他們的注意力已經轉往如何散播無線電科技)。
於此同時,在一九九○年代,小眾雜誌文化也開始廣為流行。隨著影印機越來越普及,業餘的爆料者、新聞工作者、漫畫家與作者們能將自己的影像與故事放在紙上,按下按鈕經過碳粉熱壓,整疊傳單就印出來了。像是後來改名為聯邦快遞服務站(FedEx Office)的金考快印(Kinko's)等店家,也在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成長。
隨著大家越來越負擔得起四軌錄音設備(four-track recorders),樂團也逐漸得以自行將專輯錄製成錄音帶再加以散播。若是沒有MC們錄製在錄音帶上再親手散發混音帶,嘻哈(Hip-Hop)就永遠無法像現在這麼受歡迎。不同於黑膠唱片,錄音帶很便宜,單手就拿得起來而且大家都有卡帶播放器。
在一九九○年代,人們越來越負擔得起能夠延伸個人聲音的科技,也重新塑造傳播的樣貌。從地下電台到混音帶再到影印機,這些傳播模式都把原本單向傳輸的關係轉變成水平關係。溝通與表達自我的方法固然屬於所謂的次文化(subculture),卻也預示即將到來的社群網絡時代。
九○年代的社群網絡
大多數美國人最早認識的社群網路,就是網路聊天室與約會網站。雖然如CompuServe等公司,也在一九八○年代晚期提供過相對即時的通訊平台,但要等到美國線上出現,才把線上通訊引介給更廣大的閱聽人。一九九三年時,美國線上已經超越CompuServe與Prodigy,成為家用上網的第一平台。當時還是上網要以時計費的時代。到了一九九七年,已有十八%的家庭裝有網路,其中半數裝的都是美國線上。
在早期的社群網絡相關運動當中,有許多都搭載線上約會與性愛欲望。第一個約會網站Kiss.com成立於一九九四年,接著在一九九五年又出現Match.com(該站到二○○二年已有兩千六百六十萬名用戶)。這時也陸續出現族群導向的約會網站,如一九九七年的AsianAvenue,以及二○○○年的BlackPlanet。不用做精神分析也看得出來,講到一般民眾的網路使用量成長,性吸引力就會是其中的骨幹。
所以,在談到Friendster以及MySpace陸續興起與衰落之前,簡短回顧一下網路色情的發展,對我們會很有幫助。因為色情在網路的故事裡,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如布萊恩.麥卡洛(Brian McCullough)在他的《網路色情史》(A History of Internet Porn)當中就寫道:「到了一九九六年八月,前十大新聞群組當中就有五個是成人導向,還有一個是據稱每天服務五十萬名用戶的alt.sex。」在《時代》雜誌一九九五年的〈網路色情〉這篇封面故事裡,菲力普.埃爾默─德威特(Phlip Elmer-Dewitt)也報導說,「usenet上有八三.五%的影像都是色情影像。」
在我們接受這項資訊之前(如今網路色情顯然已是網路的主要項目),要先了解它驚人的歷史。或許是由於確實能帶動經濟,也因為本質高度私密的緣故,色情內容已是當代生活運作的關鍵。驚人的是,色情出現得甚至比網路服務上的內容產製還早。有一種名為ASCII的早期色情形式線上圖片,就是以排成行列的文字,像點畫一樣組成圖案的作品。
雖然色情在歷史上也曾伴隨特定科技興起,從印刷媒體到照相機與早期的電影皆然,但如今網路色情的經濟規模,卻龐大得令人震驚。根據近期估計,網路產業的產值,色情內容就占了將近三十%。一份二○一一年的研究也發現,年齡介於十八至二十四歲的男性,有七成每個月至少會上一次色情網站。而第一次接觸網路色情的平均年齡則是十一歲。
色情內容不僅驅動電子商務,也形塑線上影片的許多科技創新。作為一九九○年代中期主要的網路商務企業,色情網站也開發了一些最早期以進行追蹤支付、會員登入,以及抓出詐騙系統的方法。而且,色情內容顯然也近身衝擊到電腦利用私密題材的方式。正如統計數據所顯示,網路色情不僅會延伸欲望,也會助長欲望。
全世界都在看
到了一九九○年代晚期,個人電腦與網路不僅走進日常生活,網路的社會意涵也發展到公眾可見的程度。能進行分配與社會聯繫的個人電腦,已開始界定包括約會與政治抗議等各種事物的社會結構(social texture)。
再回來看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的西雅圖反世貿組織抗議,就能明顯看出網路的潛能。蘭德公司所預期由NGO、非營利組織以及社運人士所組成的網絡,也在此時實現所謂的另類全球化(alt-globalization)運動,尤其是成立獨立媒體(Indymedia)網站。
西雅圖抗議的不同之處,除了他們以多國貿易組織而非單一政府為目標之外,網路存在也讓人得以在現場隨時更新報導。獨立媒體網站使用的是開放出版(open publishing)的指令碼,讓來自世界各地的社運人士都能見證,這裡的新聞是報紙、廣播或電視肯定都不會報的版本。警方在街頭施放催淚瓦斯時,可以聽見抗議者在喊:「全世界都在看」,而他們指的可不一定是電視。不可小覷的是,這種驚人的基層報導,既轉變對於特定議題的感知,也轉變對於小眾媒體力量的看法。
繼這幾場反WTO的抗議之後,接下來幾年裡,全球各地又發生多起抗議,而這些抗議之間的鬆散連結以五花八門的方式,抵抗新自由主義式的資本主義。於是,獨立媒體的分支也在各城市遍地開花。到了二○○二年,已經有八十九家個人的獨立媒體,分布於三十一個國家。薩帕塔運動所期待的社群網絡,至此已經成長茁壯。
MySpace垮台
當然,獨立媒體與薩帕塔運動一般不會被認為是社群媒體的起源。通常來說,社群網絡的前身都是從約會與交友網站演變而來。而可以建立個人檔案、邀請朋友加入網絡的六度空間(SixDegrees)與Classmates等網站所提供的模板,之後在二○一七年成為臉書時代的成功公式。
二○○二年,Friendster網站一推出就大受歡迎,三個月內就累積三百萬名用戶。大家突然間都在網路上尋找彼此。在網路上,既能找回失聯的朋友、看看老同學的近況、當然也能遐想各種有可能的戀情,而社群網絡興起,也開啟各式各樣原本受地理與通訊限制的社會關係。對於創辦人喬納森.阿布拉姆斯(Jonathan Abrams)來說,Friendster(這個名字是由當時風行的音樂共享網站Napster、再加上朋友friend組合而成)背後的構想,就是透過朋友網絡來尋找約會對象。阿布拉姆認為,這個案子的競爭者是當時最傑出的約會網站──年收入七千三百萬美元的Match.com。而用戶與投資人也都注意到了Friendster。《財星》雜誌在二○○三年的一篇報導就寫道,「一種新型態的網路或許正在浮現,主要是把人連向人,而非把人連向網站的網路。」二○○三年,Friendster拒絕谷歌的併購提議,因為他們相信,這個網站在自己手裡會運作得最好。在一九九○年代末的網際網路泡沫後,社群網絡看似可讓網路經濟復活。Friendster的成功使得伺服器不堪負荷,才過了短短一年,光是載入網站就要花掉將近一分鐘。創辦人阿布拉姆忽然發現,他的網站已經跑不動了。
二○○四年,Friendster獲得巨額資金挹注,阿布拉姆成為談話性節目的固定來賓,董事會也納入了亞馬遜、eBay、甚至是CBS派來的成員。這時卻已浮現不祥之兆。阿布拉姆到處上節目,他們的網站依然很慢,另一家社群網絡的霸主,似乎正在吸引越來越多網站用戶。這個網站就是MySpace。
從MySpace有如荷馬史詩般的興起與衰亡當中,能看出的不只是網路如何運作,還有資本與廣告的需求是如何替web 2.0這塊新興文化領域設定了發展的航向。相當巧妙的是,MySpace的創辦人克里斯.德沃夫(Chris DeWolfe)與湯姆.安德森(Tom Anderson)原本任職網路行銷公司eUniverse,大多數的業務就是製作彈出式廣告,從護膚產品到墨水匣什麼都賣,以及生產給行銷人員的電子郵件清單,也就是網路廣告的後台單位。網際網路泡沫化之後,許多防制垃圾信的法規通過,這兩人便從Friendster那裡找到靈感。據MySpace的前線行銷副總監西恩.佩西瓦(Sean Percival)說,「他們看著Friendster:『哇,大家瘋狂地花時間在這個網站上到。我們應該抄過來。』他們一心想要建立一個社群網絡,好在上面發布他們的廣告,賣給大家這些可怕的產品。一切就是這樣開始的。」他們向前老闆提案另創一個社交網站的點子,MySpace就這樣在二○○三年誕生。
不同於社群網絡的用法,MySpace讓用戶可以隨意瀏覽使用者檔案,檢視他人已不用受制於Friendster推廣的朋友圈模式。瀏覽功能為約會與社會聯繫開啟新的可能性,而他們的基本軟體也運作得比先前的其他網絡更好。在這裡還可以客製化自己的個人檔案頁面,使其成為真正的個人空間。又因為MySpace起初瞄準的對象是洛杉磯的樂團與演員,因此網站帶有某種內建的酷炫感。若說Friendster仍以朋友網絡作為關注焦點,那麼MySpace很快就把社群的焦點變成自我吹捧與線上的性邂逅。他們提供一個自我表達的平台。
MySpace迎來歷史性的成長。在二○○五至二○○六年之間,會員人數從兩百萬增加到八千萬。全盛期的MySpace在一個月內就吸引一億人造訪。在二○○五年,福斯的梅鐸(Rupert Murdoch)與維亞康姆公司(Viacom)競相出價,想要收購MySpace。結果由福斯得標,並以誇張的五億八千萬美元買下MySpace及其母公司Intermix Media。這筆交易在當時被認為很值得,但後來則被認為是網路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被收購之後,鞭策廣告營收的壓力也隨之而來。谷歌與他們簽了為期三年的合約,每年支付三億美元成為MySpace唯一的搜尋引擎。這份合約的部分條款還規定網站流量需達成的一系列指標,廣告數量也因此加倍。
奠基在網路上塞滿廣告所創立的公司,後來自己的網站也塞滿了廣告。除此之外,能自由更改個人檔案,也讓使用者可以假冒別人,如同常見於約會網站的情形一樣,MySpace也迅速成為越來越多垃圾信與色狼行徑的來源。性妄想(sexual paranoia)氾濫,而且正如我們所知,媒體也會大肆炒作對於性的恐懼(尤其他們還不只是個平台,而是一家打對台的媒體公司)。二○○九年,MySpace宣布移除九萬個性犯罪者的帳號,這會讓人比較安心嗎?
MySpace很快就成了一間執迷於營收的巨型公司,企圖成為某種社群媒體版的亞馬遜。他們添加各種功能,如影片、部落格、卡拉OK與讀書會等等,什麼都試,最後網站就成了西恩.佩西瓦所形容的,「一大坨糊掉的義大利麵。」經過多次人事改組,連創辦人也被踢走之後,這個網站終於在二○一一年以三千五百萬美元的價格售出。雖然一間公司的出售價格不見得能反映社群價值(舉例來說,獨立媒體從來就沒有售價可言),但在這個案例上,作為一個完全為了資本主義而生的網站,這個價錢倒是精準反映社群力量。佩西瓦提到,「有些公司沒有走向社群,也永遠不會如此。蘋果是其中一家,谷歌則是另一家,他們就把Google+做垮了。專注於工程,就不了解社群。社群是很情緒性的體驗。在很多情況下,工程沒有那麼情緒性。」
這些早期的社交平台是怎麼改變社交關係的呢?又如何影響我們對戀愛的理解?還有對性愛的理解?以及對時間的理解?孩子一天花幾小時在瀏覽個人檔案?花幾小時在拍照上傳?這種規模上的大幅轉變,就是社群網絡的真正革命。社群網絡徹底改變文化產製的方式。
蘋果暴力
假以時日,在電路板上直譯開關切換的程式碼字串(string of code),就能深刻影響全世界的集體情緒,只是需要時間而已。在蘋果於二○○三年推出的iPod廣告以及後來的iTunes廣告(又簡稱為剪影廣告)當中,有個人形剪影戴著由蘋果的設計師強納生.艾夫(Jonathan Ives)所設計的經典白色iPod與耳機,隨著音樂舞動,而周遭的世界則在繽紛的色彩中閃爍。這支廣告用來誘惑觀眾的圖像,呈現的正是電腦與世界之間的當代關係。電腦可以把私密帶進與公眾的深刻聯繫,也就是說,私密世界可以為外在世界塗滿顏色。一如蘋果先前的一九八四麥金塔廣告,至少在某種意義上,這波廣告確實是切合現實。iPod就像iMac一樣,也能把外在世界拉進得更貼合自我。很快地,iPhone也將掀起全世界革命。
作為一台掌中的電腦,iPhone讓世上幾種最強大機器的功能,都有了實際上的行動能力。兼具相機、簡訊、日曆、電子郵件、電子遊戲、天氣預報、慢跑功能,這種口袋型的數位式延伸肢體簡直無所不能。此刻問世的iPhone不僅是一項新科技,也成為重新塑造社會的強力工具。
iPhone的源起,可以追溯到賈伯斯對觸控螢幕的興趣。滑鼠只能做到他所追求的一部分手指觸感而已,但是二○○七年上市的iPhone做到了,而且更甚於此。
這支手機在財務上顯然大獲成功,由艾夫設計的iPhone讓手機具有感官性質,很快成為集體身體性(corporality)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電腦的世界就此裝進你的口袋,撫觸著你的肌膚,成了一個略帶急迫感的神經末梢附件。
走向社群
這時,進一步深思這些科技創新的社會面向,就很有意義了。當佩西瓦隨口說出,有些公司「走向社群」時是什麼意思呢?這句簡單扼要的見解,不過是現象的冰山一角。因為「走向社群」(getting social)言下之意,就是頗為推崇那種伯內斯式,在二十年間襲捲個人電腦與線上世界的感受力(sensibility)。若說伯內斯相信第三方專家有助於做出選擇品牌的決定,那麼好朋友的意見就更有幫助了。按「讚」界定累積社會認可的意義,社群網絡已經大量占據當代都市生活,也深深改變公眾輿論。如果文化是一種武器,那麼社群網絡就更是火力更大的大型武器了。
MySpace垮掉之後臉書一飛沖天。臉書的成功曾被歸功於各式各樣的原因,其中包括初期的邀請加入制,它回歸更直接的朋友圈;初期更明確的反廣告立場,網站後台的介面更流暢,以及讓外部公司用較簡單的原始碼去開發臉書的相容程式等。無論如何,臉書達到史無前例的規模。在二○一六年的第一季,臉書的每月活躍用戶就有十六億五千萬人(全世界人口為七十一億兩千五百萬),臉書已經確立了社會領域的樣貌。
當然,其他網站也在此時興起。如推特(三億一千五百萬活躍用戶)、領英(一億活躍用戶)、Instagram(兩億活躍用戶)、YouTube、Pinterest、Tumblr、Flickr、以及Reddit等(待本書付梓時,這些名字無可避免又會顯得過時,屆時新平台與新科技也將浮現)。如同廣播及電視的初始時期,社群媒體文化編排的主導模式仍處在初始階段,而科技之於社會生活的意涵,也才剛開始讓人有感。
在《相連: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如何全面影響你的感覺、思考與做事》(Connected: How Your Friend's Friend's Friends Affect Everything You Feel, Think and Do)當中,尼可拉.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 Christakis)博士與詹姆斯.佛勒(James H. Fowler)這兩位教授問了一個基本問題:社群網絡是什麼東西,又如何動搖我們的身分?一部分的答案就在於,社群網絡是我們長期以來視為理所當然,卻直到現在才真正變得可見。有人或許一直都曉得,自己生活在特定的社會環境(milieu)當中。我們有一些知道彼此是誰的朋友,我們也曉得有些人跟我們就是沒有聯繫。無論是因為他們屬於不同階級、不同文化、不同地理範圍、還是不同宗教。我們出於直覺了解到,社群網絡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克里斯塔基斯與佛勒在所寫的書中證明,形塑我們的不只是朋友的意見,甚至還有朋友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意見。再深入思考這番見解就會發現,在了解我們花時間與誰相處以及影響我們的思考方式上,社群網絡都占有極大的分量。
如今,這些線上的社群網絡也運用很個人的東西,才成為友誼與關係的黏著劑。雖然有些成人會覺得這種資訊稍嫌誇張,但對許多青少年而言,這種聯繫的真實性是再確切不過。常識媒體(Common Sense Media)的一篇報告就發現,七十五%的美國青少年都在使用社群網站,並且覺得自己深深陷入一個社會關係與情感都經過中介的全新領域。從網路霸凌到性愛簡訊,社群網絡的現象都為現今的青少年訂定涉入世界的方式。
當然,受到影響的並不只是青少年而已。整個公共領域都發生轉變。當你看到別人在檢查手機時,他們既在這裡,也不在這裡。在我們把自己的社會與私密世界發生的轉變視為理所當然之前,必須先試著了解,這個世界在多少程度上,是從專屬所有權與行銷的歷史中浮現出來的。如前所述,文化這種武器,及向來對我們自身最私密部分的吸引力,很少用於純粹善意目的。
用感染情緒來傳遞資訊
社群網絡已經成為散播資訊的強力根據,個人狀態更新被順暢地整合到轉發的新聞報導、呆萌的貓貓影片以及名人八卦當中。所有資訊都以類似的格式流過螢幕,也以類似的方式被人接收。傳統的新聞通路從廣告收入下滑感受到身後的天搖地動,而流通新聞的方法也有了劇烈的改變。
正如克雷.薛基(Clay Shirky)在他的著作《鄉民都來了》(Here Comes Everybody)當中所寫的,「出版的大規模業餘化,解除了須具備少量傳統印刷通路的先天限制。」突然之間,網誌就像大多數社群網絡平台上的簡單分享功能一樣,成為分享新聞的有力載具。隨著資訊一起民主化的,還有這些資訊本身的調性與情緒空間。無論這些資訊談的是分手還是校園危機,都成為了傳播私密情感空間的一部分。
克里斯塔基斯與佛勒所闡述的,正是社群網絡如何影響我們所想的事。他們詳細介紹臨床上所謂的群體心因性疾病(massive psychogenic illness,MPI),也就是一種情緒爆發。也可以把這想成一種情緒上的感染,與抽大麻的人所謂的人來瘋(contact high)相似。實驗證明,人們可以「捕捉」到從別人身上觀察到的情緒狀態,所需時間從幾秒至幾星期不等。隨著社群網絡成為體驗新聞(在此連新聞這個詞都需要重新定義)的主要方式,新聞的質地也跟著改變,變得充滿情感。正如我們在全書中所詳述,人類的各種情緒並不是價值中立,有些情緒可以把資訊傳遞得比其他情緒更快。
凡是用過幾年網路的人都已經習慣,在某種社群媒體的修辭方式裡,會有強化情緒性焦慮的調性。這有點像是每天都在全天候觀看福斯新聞台的恐慌本質,即使在意識形態內容上或有不同。
二○一二年十一月,諷刺雜誌《洋蔥》(Onion)的一則標題是:「歐巴馬勝選後,『怒嚎白熱火球』競跑共和黨一六年候選人之爭,」。很諷刺,但也很寫實。在一九八○年代的文化戰爭期間,義憤填膺的氛圍也曾為共和黨的策略推波助瀾,但這樣的情緒訴求如今已經主導一切形式的政治內容。
在史蒂芬.史蒂格利茲(Stefan Stieglitz)與凌登春(Linh Dang-Xuan)的論文〈社群媒體上的情緒與資訊傳播:對微網誌與分享行為之感受〉當中,他們報告了極為明顯的研究發現:「基於總數超過十六萬五千條推文所構成的兩組資料,我們發現相較於情緒持平的推文,帶有情緒的推文往往更常更快被轉推。實務意涵在於,企業應當更注意對品牌與產品的相關感受分析,無論在社群媒體溝通上,還是在設計引發情緒的廣告內容上,皆是如此。」學者用他們的學術發現來告訴企業怎麼利用人們的情緒,還真有一套。
有一個談線上行銷的網誌就特別建議行銷人員,要避免採用喜悅(因為這塊媒體空間已經擠滿了行銷人)與悲傷等情緒,反而要專注於用憤怒與驚訝作為他們產品的情緒包裝。在社群媒體的時代裡,也難怪傳遞資訊的情緒空間會讓人覺得負擔過重了。
如果說歐巴馬在二○○八年當選,以及更早參選的霍華.迪安(Howard Dean)尚未指出資訊空間出現的轉變,那麼川普的崛起肯定可以提供引人入勝的事件背景。川普的氣質,幾乎是滔滔不絕的妄想、陰謀論與怒氣,而他高度適合發推特的措辭風格,也跟美國某群憤憤不平的邊緣人一拍即合。
但重點並非聚焦探討川普的言行,而是要去感受這些話在情緒上的質地,無論是恐懼、種族妄想、義憤、或是驚訝,是如何促成帶有情緒的資訊急速蔓延。川普的魅力並非來自他明目張膽地罔顧政治正確,而是因為他總是在驚訝、憤怒以及分享你的恐懼,而這些情緒都有著高度的感染力。正如研究指出,個人對團體的感受很敏感,而社群網絡又只會強化這種邏輯,而且散播得比以往都更快更遠。一九三○年代的希特勒演講就是如此,一九八○年代的文化戰爭期間更是如此,一九九○年代反毒戰爭的電視畫面還是如此。
稍微回顧過去,才能體會當前時刻為何如此獨特。最廣大的商業市場之一,就是進行社會溝通與互動的網路空間。網路這個私有化的空間,是用社會生活的各種基本功能來獲利。我們所認為的文化(社會生活)其中一項根本要素,已經在令人瞠目結舌的規模上,成為全球經濟的核心。文化就是一項武器,因為文化正在讓這個世界運轉。
然而,話雖如此,就連馬克.祖克伯與史蒂夫.賈伯斯這些人也沒有料到,電腦與社群網絡到來,會造成這樣的社會轉型。你用某樣東西賺了錢,不表示你明白它為什麼會如此、以及它在做什麼。到最後,媒體往自製內容轉型,已經改變我們對自我的理解,以及我們建構種種政治論述還有詮釋周遭權力世界的方式。
革命急速蔓延
科技媒體將二○一一年的阿拉伯之春稱為推特革命,將橫掃中東各國的抗議歸功於推特徹底落敗,但在擾亂執政當局的權力敘事上,卻仍不能小覷社群媒體所提供的力量。一如所有的革命,尤其是透過社群媒體急速蔓延的革命,這場事件實際上更像是群體而非單方行動。這群人潮也改變了埃及往後的面貌。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以及一些年紀稍長的人,占領市中心的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對上穆巴拉克總統的政府部隊。
在西雅圖舉行反WTO抗議並創辦獨立媒體的十二年之後,網路的革命潛力已經從個別運作的電腦,轉移到多數抗議者都持有的手機上。與獨立媒體集中式的發布相反,手機上的資訊是透過各人在全城、全國、全世界到處散播。那些貓咪影片與肯伊.威斯特(Kanye West)的推文都示範何謂病毒式急速蔓延(virality),控制公眾輿論的蔓延途徑正在不斷變化。
埃及這場革命並非全無暴力,其中有八百四十六人喪生、六千多人受傷,與軍方的衝突也導致殘忍的鎮壓。但是民眾有如蟻群般一直回到廣場,人數還越來越多。到最後,一如我們所知,穆巴拉克下台了,而埃及歷史也展開嶄新但複雜的篇章。
事後,《時代》雜誌必須找出一張能代表這場運動的臉孔。他們看上埃及社群網路創業家兼谷歌時任中東區行銷主管威爾.戈寧(Wael Ghonim),將他列入《時代》雜誌「二○一一年最有影響力一百人」。戈寧固然舉足輕重,但就像接下來的占領運動與後來的黑人的命也是命一樣,社群媒體對於文化的利用,借助群眾之邏輯者多,借助專心致志創業家之邏輯者少。戈寧曾是創設於二○一○年的粉絲專頁「我們都是哈立德.薩伊德(Khaled Saeed)」的兩名管理員之一。薩伊德是一名在亞歷山卓(Alexandria)被警察從網咖拖出毆打致死的青年。戈寧的粉絲專頁贏得了廣大的關注,他隨後就被偵訊與拘留了十一天。在接受電視專訪之後,戈寧成了名人,並在接受CNN訪問時聲稱,「我蠻希望有天能跟祖克伯見面向他致謝,」他說,「叫他打給我。」
但革命只會持續擴散,起始於突尼西亞、轉移到埃及、而後再擴散到利比亞、葉門與敘利亞的這些抗議,後來被稱為阿拉伯之春。接下來又發生西班牙與希臘的歐洲之夏,以及二○一一年秋發起於祖克提公園(Zuccotti Park),再擴散到全美國的占領運動。到了二○一一年十月,全球各地已經有九百個城市舉行各自版本的占領運動。
這些運動急速蔓延見證的不只是社群,更重要的是,或許還有社群是以什麼方式,促成與延續廣大公眾已深刻感受到的欲望。若說義憤是網路最能撼動人的情緒之一,那麼會讓廣大公眾感到憤慨的事可多了。如埃及與敘利亞的獨裁傀儡政權、在希臘與西班牙擊垮勞動階級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美國崛起中的一%階級、以及對非裔美國人堂而皇之的兇殘種族主義政策。義憤本身就會造成衝擊也有助讓大量的真相曝光。換句話說,警察殺死孩童的影片,不僅是在網路上流通且充滿感性力量的影像,更重要的是,這些影片也將權力的實情攤開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
社群媒體的組織能力當然也招致了許多批評。在美國,占領華爾街這場歧異的自我標籤運動,就拒絕提出任何特定要求,而黑人的命也是命在二○一六年的大選初選中,也拒絕為任何特定候選人背書。不少專家都指稱,這些運動在做出真正的政治改變時,都欠缺真正的實力。這種主張認為,不同於茶黨,要以政治立場影響政府單位運作時,占領運動與黑人的命也是命都是不成功的。但是這樣的批判並未領略到文化的根本轉變,也沒有把這些運動理解成反應政治意識的晴雨表。
社群媒體或許只是同溫層物以類聚,但隨著時間過去,他們似乎也讓政治討論產生演變。在推特與臉書快速興起的時候,社會主義在年輕人當中也已經不再是個壞字眼。於此同時,放肆的種族主義語言以及小報式的行為舉止,不僅成為川普的常態作風,也成為一種有效策略。於是,無論結果是好是壞,社群媒體似乎已經成為美國在選舉中,形塑政治類論辯最強而有力的工具。
預見的事都在發生
總而言之,我想說的是事實都顯而易見,電腦是一種非常強大的設備。賈伯斯預見了,這種工具將會迎合大眾消費市場非常情緒化且私密的需求。他在設計師艾夫的協助下,做到了這件事。但是電腦也成為了一種助長個人私密需求的器具,不僅能表現出私密性的形象,也強力擴大每個電腦使用者能觸及的範圍。
隨著網路與社群媒體的到來,這種延伸已經把公事與私事都融合成一個有力的槓桿支點,對全球人類的自我認識以及公共輿論的影響,堪與印刷媒體相比。
從一些小事上能看得出上述效應。有些朋友不檢查手機就渾身不對勁,一有問題就要查詢Google。擔心大家都知道你之前跟現在偷偷做了什麼,但也沒辦法無所事事。
人類的行為正在改變,電腦雖然大幅促成這種轉變,但要是你以為這些大企業的董事會跟向來惡質的廣告商,全都知道這種轉變會走向何方,那可就錯了。他們就算有厲害的消費者演算法能夠推知,舉例來說,喜歡薩帕塔運動的書,那或許也會喜歡關於伊朗革命的書。就算如此,在巨型公司運籌帷幄的這些人,也只能理解這些工具的短期效果而已。對於業餘玩家、夢想家,以及想像將這些科技用於獲利以外目的任何人而言,電腦仍然有著廣闊的前景,以及不可思議的可能性。
可以肯定的是,就像宜家家居、蘋果直營店以及星巴克這樣的企業式社會空間一樣,對於線上社會空間私有化,我們也應該投以合理的關切。臉書既不中立也不民主。他們會把自己在集體文化上的力量當成是營收的武器。谷歌雖然持續宣揚自己是個「不為惡」(Do No Evil)的品牌,卻也一直像任何企業一樣,以持久的財務成長作為營運目標。最後,蘋果雖然會叮嚀我們要「不同凡想」,但還是一直致力於推出蘋果專用的軟硬體,加上跟別人無異的海外代工模式,都使這則故事顯得沒那麼浪漫。沒錯,在這個屬於矽谷且理應充滿革命性的時代裡,資本主義還活得好好的。
但這也就表示(而且這個告誡至關重要)電腦對資本主義來說遠遠不只是一台機器而已。就像先前的收音機一樣,激勵效果可能會為我們帶來任何可能,或許是恐怖的種族滅絕也有可能是對資本主義的挑戰。這可能有助於發明一種新型的搖滾樂,或是增強對彼此最不堪的恐懼。簡言之,自古以來許多科技,都在力求連結與動員我們每個人內心的私密角落,而電腦正是其中最新,也最強大的工具。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