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瘂弦】 瘂弦:技術細節與解答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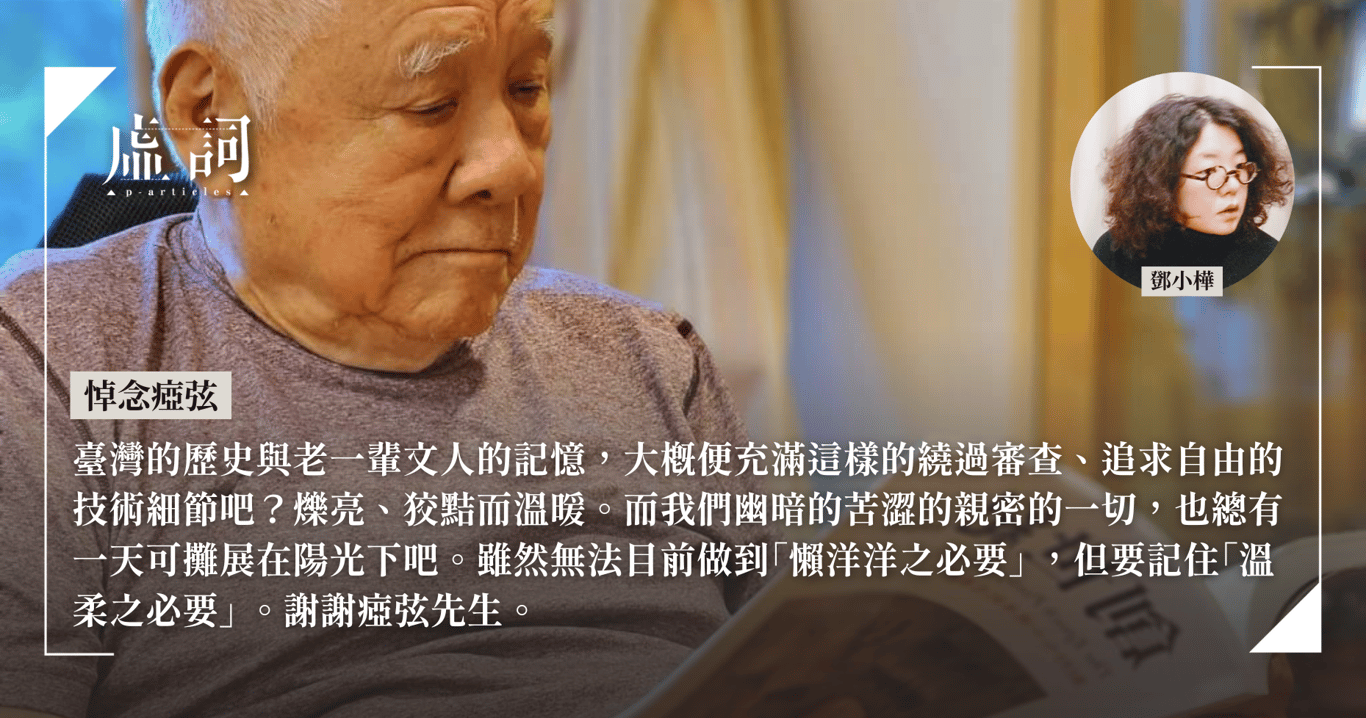
文|鄧小樺
瘂弦先生過世,在臉書看到好大迴響——當年楊牧先生過世,所有人引錄的楊牧詩都是不同的,好久都沒有一首重複;瘂弦先生過世時,除詩作之外,則見到好多照片、信件、相處小故事,也是人人不同。作家生命與人間的軌跡交錯若此:溫度盎然且幅及廣闊。
我自己的《瘂弦詩集》不幸還在香港,坐著哀愁,真是「觀音在遠遠的山上/罌粟在罌粟的田裡」(這兩句總會背的)。幸好手上有《瘂弦回憶錄》、《瘂弦書簡I:致楊牧》、《楊牧書簡I:致瘂弦》,憮然讀一個下午(排除萬般工作)。
早年接觸瘂弦自然是因為在大學裡讀現代詩,後來看瘂弦紀錄片《如歌的行板》,裡面除了見到熱情慷慨的詩人,也勾勒出臺灣報章文藝副刊戰國年代的歷史風貌,印象十分深刻。《瘂弦回憶錄》裡則談了很多軍中生活、軍中文藝社團的創作生命,後面有《創世紀》詩刊的部分,瘂弦、洛夫、張默三人的故事。瘂弦主張文人之間不要鬧掰,要互相欣賞、相交一輩子,如同敬亭山「相看兩不厭」。他就是張默和洛夫因文學意見吵起來時的緩衝地帶,做和事佬,「有我在他們就不會鬧僵」。這幾句家常話,現在看來真是十分難得。
另外好看的當然是三人如何胼手胝足捱窮辦詩刊,不停典當、吃飯掛賬,喝最便宜的烏梅酒,女朋友要和他們一起捱陽春麵……當時三人月薪是二百多新臺幣,扣掉基本生活費所餘無幾,而詩刊印費一期要四百多元,所以是靠借錢和典當來印詩刊,「我們那時的存款就是當票」,所有東西都當,發薪水之後再贖回來,下個月再當,「反復多次後,竟也不覺臉紅」。至於「發行」的「業務」,是三人自己用扁擔送詩刊到書店。還有「廣告業務」呢:就是去電影院打「尋人」的片前字幕:「《創世紀》詩刊出版了,張默速回」,是當時的植入式廣告——如此跑遍十幾家電影院,直至被電影院發現而不肯再讓他們打。瘂弦笑言當年出於狂熱,曾為《創世紀》用了很多誇張的宣傳語,如封面寫「第一流的心靈,第一流的作品」,「這份張揚,也是少不更事。」
我是生於寫計劃申請資助出刊物的年代,其後很少自資的案例。以前看這些只當是傳說故事,不過今日唏噓地想,香港經濟變差之餘,報章及文藝刊物等發表園地已經大大減少,文藝資助政策可能也會出現大轉變,前人自掏腰包養文學的故事,看來倒像是啟示甚或預叙了。香港文友不妨結結實實地讀一下當熱身。(最好我估錯啦)
瘂弦說臺灣的詩刊文化是以地下文學的方式崛起的,因為當時報章媒體都不登現代詩。當年發表還是要爭取的,原來說改個女性化的筆名據說比較易被刊登,於是很多男作者都改了女性化的筆名去投稿(一位「英麗鶯琳」,原來是四個女朋友的名字合起來,簡直天誅)——可比於今日打online game改女性玩家名會比較多著數,「有棍小妹」的招數文人也懂。筆名、投稿郵寄地址等等小節都指示了審查制度的存在,《創世紀》主張文藝不要跟隨官方宣傳塗脂抹粉,要匡正社會的黑暗與不平,才有價值。當時他們還身在軍中哩,瘂弦的說法是:
//我們覺得,做軍人要做個合格的軍人,但寫作時絕對不因軍人身份寫宣傳的東西,要寫生命內在的東西。這點我們比誰都看得清楚,這是藝術家應該走的道路。而且我們當時所寫的歌讚的東西少,抗議的東西比較多。這個抗議包括對戰爭的抗議、反戰的思想、對現實的不平的吶喊。在言論方面採用象徵的形式,把抗議、不平隱藏在朦朧的藝術形式之中,使得文化的審檢人員看不懂,使批判的精神得以傳播,是最有效的參與。比如洛夫的《石室之死亡》整首詩都是反戰的, 商禽的〈逢單日的夜歌〉暗示金門當時的情況,我的〈深淵〉等等,都是利用審檢機關看不懂而 「蒙混過關」,不如此不行。//
在意識型態強力監控的當時,「左派」可是極嚴重的罪名,但瘂弦說:
//《創世紀》不太像詩社,大家自由投稿,也沒有共同的美學路線,唯一的選詩標準就是選美好的詩、純詩,不和政治產生關係的詩。當時我就提出來,一個詩人、甚至所有有價值的知識份子,都應該是廣義的左派,不是政治社團上的左派。這種廣義的左派是站在大眾立場民眾土地立場上去做不平之鳴,講求人道主義的精神之發揚,不要做喜鵲,每天報喜,而要做烏鴉,可能大家都不喜歡它,可它對這個社會的不平、不義、不公發出聲音,就有價值,像胡適寫 的《烏鴉》。//
這樣自然是對軍方思想的反動,所以《創世紀》三人都上過黑名單://「保防資料」上說,「該員參加《創世紀》!」後面還跟著驚嘆號。//張默因為和香港文人李英豪通了幾封信,信件都被保防抄下來,張默的升級都受影響。瘂弦談及他們存活下來的技巧:因為審查已經是針對作者而非內容,所以身在大陸的作者要改名換姓,如卞之琳作品署「卞季陵」(卞用過此筆名),或隱去翻譯者的名字稱「本刊編輯委員會譯」,或取個外國名字。提到魯迅時,要加個括號「(此人曾受共黨的利用)」。瘂弦笑言《創世紀》改名換姓的絕招是絕對的高段,出了名的。如果仔細看,還有很多小技巧,關鍵是要讓審查人員看不懂;而也有很多長輩在幫助他們,比如他們的上司,軍中電台台長詩人彭邦楨用各種方法「縱容」他們,雖然他們編選年度詩選沒有選彭台長的詩,彭台長也不生氣,還在他們三人被有關單位懷疑思想有問題時,替他們作了重要的紓緩解釋:「沒問題的,小朋友喜歡寫新風格的東西。」好高尚的長者風度。
臺灣的歷史與老一輩文人的記憶,大概便充滿這樣的繞過審查、追求自由的技術細節吧?爍亮、狡黠而溫暖。而我們幽暗的苦澀的親密的一切,也總有一天可攤展在陽光下吧。
(我讀書信集比較少,《瘂弦書簡》如何與《楊牧書簡》對讀是我的一大問題,難道前提是我要有更大更整齊的書桌可以同時翻動二書?總之後來當成「解答之書」那樣信手翻——就遇到了1976年8月,張系國的作品被有關單位禁止流傳,為了讓書能夠成功出版,大家建議由瘂弦來處理,將張作品中「幾個容易引起麻煩的地方略作文字上的調整。」瘂弦補充:「對他作品藝術性的影響不大。這是不得已的事,一定要請張系國體諒,這也是為他好。」還在十日後的信件中再重複一次,甚見懇切。當時張的作品已被明令禁止,所以這其實是在讓步中堅持讓被禁的作品出版,一個非常高段編輯面對壓力必須懂得委屈求全。再翻一下,就遇到瘂弦請楊牧要建議一些「能銷的作者」——如果沒有銷得好的,下一批書就沒錢出了。啊。感受到解答之書般的魔力了。這些就是我現在面對的問題。)
我回去校對了。這就是「而既被目為一條河總得繼續流下去的」。雖然無法目前做到「懶洋洋之必要」,但要記住「溫柔之必要」。謝謝瘂弦先生。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