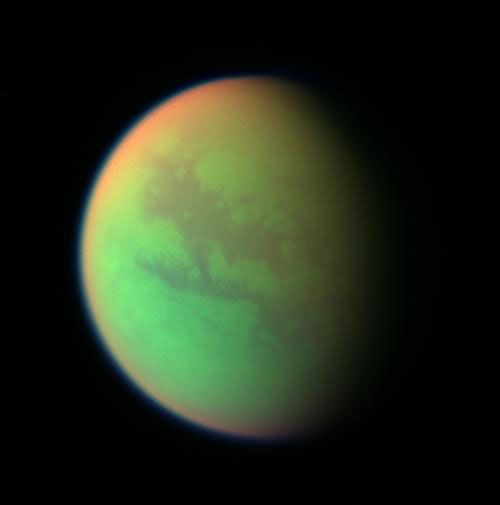沉默
今年我開始越野跑。從徒步到跑的這一轉變使得我完成同一條山徑的用時減少了將近40分鐘。掙脫重力是一個有意思的過程,我從中學會了把意識短暫消失。而此前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睡覺都在想東西的人。當然,消失的不僅是我的意識——在山上奔跑讓我覺得自己一無所有,不再有身份和平坦地形的庇護。只剩下我出門前帶上的水和少量食物、一副我確信其能運轉無虞的軀殼(即便有超出正常值的心跳以及強烈和微弱交替的呼吸),還有遍在於自然界中遠近窸窣作響的沉默。
我沉默地站在那個裝有防彈玻璃的窗口前,幾秒前我把護照遞給窗口內的穿軍裝的官員。那一刻的「沉默」不是被禁止說任何話,而是僅允許我說被允許的話。這些話的內容都被這個官員——或說他所代表的那套官僚——所徹底預設。我必須如護照所示來讀出我的全名,儘管我原本的生活中幾乎沒有會叫我全名的人。我不能說我回程的日期超過法律賦予我的逗留期限,也不能表示我此行的目的是販毒。我是某個等待被測試的程式,而建造防彈玻璃窗口的官僚所預設的所有程式都必然存在著可理解性:玻璃窗外的這個人,必然有國籍,必然有姓名,必然有出生日期,必然有(或被豁免)進入該地的許可⋯⋯這套官僚難以處理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說的「裸命」(naked life),意即不享有任何政治權利和法律保護的人。可即便某個被測試的程式是一條「裸命」,它依然有屬於其本身的特徵,比如語言、膚色或性別。這種某人身上「始終有特徵可被指涉」的屬性,在現象學上被稱為「同一性」。這個字的英文和「身份」一樣,皆為「identity」。
「裸命」只不過是在某一段時間內喪失了可辨識的「政治身份」,而不是被剝奪了所有能夠被指涉的特徵。
這便牽涉到「政治身份」在多大程度上被理解為「身份」的全部。至少防彈玻璃窗口內的官員是(被迫)這麼理解的,因為我無法在邊境檢查的現場拿我的那些不成文且不具價值的特徵説事。姑且不論,「政治身份」中的「政治」在多大程度上被詮釋為「統治/宰制」,後者如何被現代民族國家及其法律制度所演繹,又與「政治」的古希臘文詞源所指的現象(城邦、公民協商等)相距多遠。我無意在此探討這種譜系學,而只是想將「身份」一字引回對「同一性」的理解上,或說引回對純粹生命現象的關注上。這或許意味著我的哲學興趣轉向了生命政治學,也或許只是某些片刻的思考,畢竟世界被現代性包覆的其中一個後果便是將人命視如草芥。當權者如此,草芥亦樂意為當權者背書。防彈玻璃前的這個被測試的程式便是眾多草芥之一,而那本護照正是這個草芥用以祈求另一個草芥給自己開門的工具罷了,與草芥本身的生命型態關係甚微。
我始終無法忘記唸碩士的時候一門課的論文,題目是歷史學家是否能視檔案館為工廠和實驗室。換句話說,歷史學家能否利用檔案如自然科學家一般提取出固定真理,以及他們的任務是否僅為找到真理——歷史學家更偏向用「事實」這個字——是否僅為重建事實?這又牽涉到歷史學本身的定義:歷史學僅僅是關於事實的學問嗎?
我日常的工作便是與各類檔案打交道。在電子化之後它們不會遭到時間的威脅,像是在一個建造完好的劇場內。此時是幕間的沉默,毫無噪音,觀眾等待著接下來的「呈現」。再過幾十分鐘,這場戲劇將會結束,舞台燈會熄滅,殘影會在觀眾的瞳孔中停留片刻,隨後隱入他們的記憶中。而那銜接在時間之上的「呈現」便是我利用檔案做的事情,即重建線性的事實。台下的觀眾接過事實後,又如何將這個事實講述予它人,或是將這一事實補充——無論如何都是圍繞這一事實,這個「呈現」,所以他們的經驗都遵守事實的同一性。誠然,這些講述、描繪對事實不會有即時的影響,正如諸多物理定律在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都生效。然而,戲劇是表演者和觀眾共同構成的場域。我稱這個場域為「真實」。
歷史學家也許不是那種鍥而不捨追求「沉默的真相」的人。這樣的人更適合做自然科學家。因為「真實」的場域中不是沉默的、單向的演出,也有掌聲、噓聲、哭笑乃至場外的流言蜚語。而這些都構成了歷史的同一性,都是它可指涉的部分。因此,研究歷史給我帶來的,除了那些可以掛在嘴邊的鮮為人知的知識外,還有直面「不同真相」和「不同闡釋真相的方式」的勇氣。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