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評書|Jenny Erpenbeck為你講德國難民悲劇
最近才讀完Jenny Erpenbeck的《不是一本小說》的回憶錄,裡面也收錄了近十年內她領取各種獎項的獲獎感言,所以,這本回憶錄並不是小說,而是不少Jenny面對大眾發自肺腑的言語。
當然,很多發自肺腑的言語總是會或多或少跟一個人的家庭有關,所以,很多演講裡,Jenny都用自己的家庭背景和歷史進行引申和回答。作為擁有猶太血統卻生長在東德的作家,她的關注點自然跟社會背景、政治變革、歷史因素分不開——祖輩在二戰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中顛沛流離;Jenny生長在社會主義德國,在柏林牆倒塌的那一刻,其實Jenny在睡大覺,完美錯過了二十世紀的重大時刻之一;德國難民潮危機之後,Jenny在很多講演中談到了德國的難民問題,非常犀利且引人深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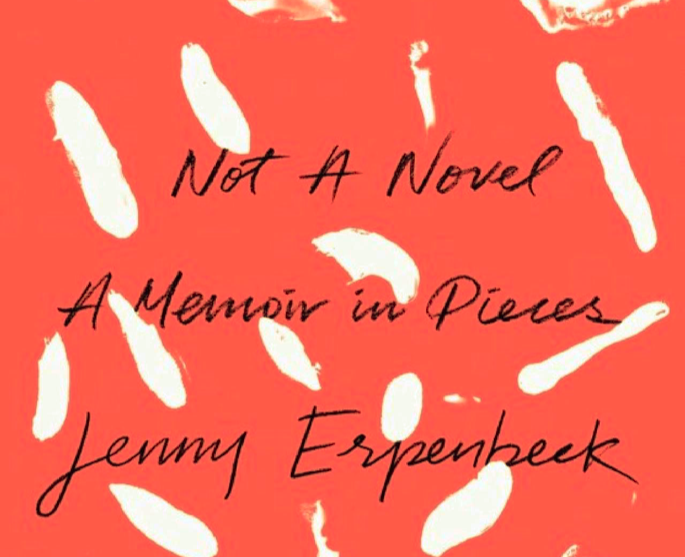
Jenny Erpenbeck2018年的Puterbaugh 主題演講題為「盲點」。在這個演講中,Jenny以一位東德成長的作家的視角發出了令人深省的問題:為什麼對於當年想要從東德逃到西德的人,我們充滿了憐憫,不時地替因此而失去生命的東德人們惋惜,然而,面對同樣追求自由卻淹死在地中海的難民,我們卻是另外一種態度呢?「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of people who aspire to a new life, to this thing we call “freedom”? The answer is nothing.」
演講中,Jenny談到了去年秋天她去美國藤校普林斯頓大學做一個閱讀reading,碰到一位該大學的教授,教授非常驕傲地告訴Jenny她給德國總理默克爾的顧問團隊建議大批量接受敘利亞難民。不過,她做出這個建議的初衷並不是敘利亞難民多麼需要幫助或者面對的困難多麼龐大,而是她告訴默克爾顧問團隊,你們知道嗎,所有的中東難民裡,來自敘利亞的難民才是最有知識層次,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如果你們德國只接收敘利亞難民,那麼其實對你們比較好,因為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難民能夠在短時間中融入德國的社會。這位女教授說,跟敘利亞難民相比,其他國家的難民不僅受教育水平低,也不是很sophisticated⋯⋯她告訴默克爾團隊,敘利亞難民就相當於是難民中的精英階層(原話),接收他們將是最快融入並且最快能夠開始回饋德國社會的。
我可以想像Jenny或許當時假裝認真地聽著女教授的滔滔不絕,教授自己甚至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當時的所作所為在很多層面上都大錯特錯了⋯⋯
之後,Jenny寫到了自己的驚訝——一個常春藤的教授,怎麼能夠堂而皇之就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以種族、受教育程度來決定他們的未來,並且沾沾自喜,覺得自己給出的「建議」是怎樣的聰明無敵⋯⋯
所以,面對同樣奔赴自由的人,來自東德的白人生命就是比其他膚色、來自其他國家、地區的人生命要珍貴許多嗎?
難道,這個女教授給默克爾團隊的所謂「建議」真的是德國政府大量接收敘利亞難民的原因嗎?我不知道,也很難想像,總覺得政府和人道主義法律並不是這樣運作的?可是,如果是呢?
Jenny說她認識的一位難民終於在輾轉了歐洲許多國家且無法工作、受盡暴力虐待的幾年後精神崩潰,被收容到義大利的精神病院。另一位難民在終於收到臨時身分文件且基於他嚴重的心臟病問題才被配發了一套在柏林的小公寓後心臟病發死去,離住進這個公寓過去了不到一年;而他的父親在15年前死在尼日利亞的宗教戰爭,兩個孩子在2011年死於逃往歐洲的船上⋯⋯
作者在為未成年難民做法定監護人義工的同時,其所在機構一名16歲的阿富汗男孩從四樓縱身跳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這一個個死去的難民都抵達了他們心心念念的歐洲,都朝著自由更近了一步,然而,所謂的近在咫尺的「自由」也成了最終將他們生命吞噬的概念。是啊,「自由」不過是一個概念,真正將這一個個背負著全家人的性命與希望的生命吞噬的究竟是沒有準備好接收他們的歐洲還是卡夫卡式的官僚系統;還是對於很多人生來就不應該存在的兩個字——「自由」?
這逝去的每一個生命背後應該有多少故事,多少感情,多少韌性、人性與人道?最終卻只能成為三言兩語即可帶過的「難民悲劇」。如果Jenny不說,不把這些「三言兩語」寫出來,那些故事又會去哪兒呢?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讀者送我情♥️♥️♥️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